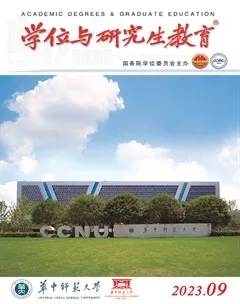研究生辯證思維的缺失與彰顯——以教育學學位論文寫作為觀察介質
李潤洲
研究生培養
研究生辯證思維的缺失與彰顯——以教育學學位論文寫作為觀察介質
李潤洲
闡釋了辯證思維蘊涵的三重意涵:從內容上看,辯證思維是對某事象內在矛盾的反映與揭示;從形式上看,辯證思維是正反概念、命題的對立與貫通;從結果上看,辯證思維是對某事象發生機制的探究與呈現。認為學位論文作為研究成果,是對某事象蘊含的研究問題創新解答的對話展示,理應針對某事象具有的內在矛盾展開辯證思考,并運用辯證思維闡發某種相對新穎的觀點。指出了在學位論文寫作中存在的辯證思維缺失現象,如用一元論的專斷置換二元論的辯證,用庸俗的辯證表達置換矛盾的深入分析,用二元的矛盾統一置換多元的矛盾轉化等。認為在學位論文寫作中,應彰顯辯證思維,要基于對某事象的矛盾揭示,變絕對為辯證;基于對某事象的矛盾分析,變籠統為具體;基于對某事象的矛盾史述,變平面為立體。
研究生;辯證思維;學位論文;研究生教育
辯證思維是辯證法的運用,用于揭示某事象(事物和現象的合稱)具有的矛盾,并基于對某事象的矛盾分析以解決問題的思維。學位論文作為研究成果,是對某事象蘊含的研究問題新解的對話展示。然而,在學位論文寫作中,有些研究生卻存在著辯證思維缺失現象。那么,何謂辯證思維?在學位論文寫作中,研究生辯證思維的缺失有哪些表現?研究生如何彰顯辯證思維?筆者在下文嘗試回答這些問題。
一、辯證思維的釋義
辯證思維是指人在遇到問題時,揭示、分析問題產生的矛盾,自覺地運用矛盾分析法把握某事象運行機制的思維。從不同維度看,辯證思維具有不同內涵。
1.從內容上看,辯證思維是對某事象內在矛盾的反映與揭示
矛盾是某事象發展、變化的內在動力,因此,研究某問題,應深入到某事象具有的矛盾中。正如黑格爾所言:“一切現實事物都在自身包含著對立的規定,因此認識一個對象,確切地說,把握一個對象,恰恰意味著意識到這個對象是對立規定的具體統一。”[1]在此意義上,學位論文作為研究成果,應直面某事象發展、變化的內在矛盾,自覺地運用辯證思維展開分析與論證。只有如此,才能深入、全面地把握某研究對象,才能為學位論文寫作確立一個阿基米德支點。比如,在《我國現階段教育公平問題的理論探討》中,筆者專門闡述了“教育公平所隱藏的內在矛盾性”,諸如“現實性和理想性”“具體性和相對性”“個體性和群體性”“過程平等和結果平等的兩難”等[2],從而為教育公平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學理基礎。后來,根據教育公平具有的內在矛盾,分析了教育公平的基本特征,并基于其基本特征闡述了實現教育公平的建議,諸如“確立公共學校教育公平的價值取向”“梯度增進教育公平”“確定合理的教育公平原則”與“增加教育投入,構建‘終身教育’體系”等[3]。當然,當時之所以要揭示教育公平的內在矛盾,只是憑著直覺意識到要想解決教育公平問題,則需直面教育公平自身具有的矛盾,并沒有運用辯證思維的自覺意識。現在,每當閱讀缺乏深度的學位論文時,才意識到時下有些學位論文之所以僅僅滯留于平行的抽象概念的漩渦中而不能自拔,就在于研究生忽視了對研究對象內在矛盾的揭示與分析,缺乏運用辯證思維的自覺意識。而一旦確立了辯證思維的自覺意識,那么學位論文寫作則會直面研究對象具有的內在矛盾,在揭示其內在矛盾中剖析、解決問題,從而使學位論文寫作成為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過程。因為辯證思維即矛盾思維,必然要揭示某事象的內在矛盾,從而為學位論文寫作勾畫、鋪設一條問題解決的路徑。
2.從形式上看,辯證思維是正反概念、命題的對立與貫通
如果說辯證思維是對某事象內在矛盾的反映與揭示,那么辯證思維表現在語言上則是正反概念、命題的對立與貫通。因為某事象的內在矛盾反映在人腦中,就得運用正反概念、命題來呈現。而正反概念、命題的對立有著多種表達樣式,諸如極性對立,即兩個概念、命題處于對立的兩極,且兩個概念、命題之間存在著中間狀態,如“大與小”“人是理性的動物與人是非理性的動物”等。互補對立,即兩個概念、命題非此即彼,二者相互排斥,如“動與靜”“教師資格的非制度化與其制度化”等。反向對立,即兩個概念、命題對舉、相對地處于一個統一體中,互為參照,存在著互為對立的關系,如“上與下”“教育學是科學與教育學是人學”等。一旦學位論文寫作直面某事象具有的矛盾,那么在分析、解決某事象的矛盾時,則需運用一些正反概念與命題進行言說。比如,在《論教育學的價值生成》中,為了闡述“洞察研究路徑,保障教育學研究的價值”,筆者將教育研究劃分為三種類型:教育科學研究、教育人文研究與教育實踐研究,分別陳述了教育科學研究、教育人文研究具有的內在矛盾,諸如教育科學研究的“客觀性的追求與其研究內容的主觀性選擇”“其結論可檢驗性的期盼與教育實踐的不可復制性”“其能解決一切教育問題的承諾與其研究方法的局限”之間所存在的價值悖論,教育人文研究所具有的“人文概念的不確定性與研究所需的概念明確性”“人文研究價值訴求的單一性與教育實踐的價值承擔的多樣性”“教育人文研究者的價值言說與其實際行動的表里不一”之間的矛盾[4],從而為倡導、論證一種教育研究的新路徑——教育實踐研究提供了邏輯前提。
3.從結果上看,辯證思維是對某事象發生機制的探究與呈現
針對某事象具有的矛盾,辯證思維最終要揭示出某事象發生的機制,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對某事象矛盾的二元對立的闡述上。的確,認識某事象,起初人們更多地關注某事象與其他事象的等同或差異,此種知性思維也是認識某事象的一種重要方式,而辯證思維則不僅看到了某事象與其他事象的等同或差異,而且關注某事象具有的二元對立的矛盾,并積極尋求二元對立的矛盾如何達成和解。這種二元對立的矛盾和解具體表現為某事象受到來自其對立面的否定而揚棄其片面性,接著對立面的片面性也被否定,并達成二者的暫時統一,對立面就在其發展過程中克服了其最初的片面性而在更高的層次上達成矛盾和解。作為分析、解決某事象蘊含問題的學位論文,在揭示、分析某事象具有的矛盾時,其著眼點和歸宿是通過揭示某事象發生、形成的機制來達成某事象具有的二元對立的矛盾的暫時和解。在《我國現階段教育公平問題的理論探討》中,筆者揭示教育公平隱藏的內在矛盾性,諸如“現實性和理想性”“具體性和相對性”“個體性和群體性”“過程平等和結果平等的兩難”等,則是為了探討教育公平的內在機制,認為“一方面,教育公平的狀況,歸根到底決定于社會生產力的高低和相應的生產關系的性質,也取決于社會公平的實現程度,直接決定于一定條件下教育政策的選擇和教育資源的配置;另一方面,教育公平的實現又反作用于社會公平,有助于增進社會公平。而后一點也正是研究教育公平問題的價值所在”[2]。探討教育科學研究與教育人文研究的內在矛盾,則是為倡導一種新的研究范式——“教育實踐研究”做鋪墊[4],以便在“教育實踐研究”中化解教育科學研究與教育人文研究具有的內在矛盾,充分實現教育研究的價值。
二、研究生辯證思維缺失的表征
學位論文總要就某事象有所主張,因此在學位論文寫作中需運用辯證思維。然而,在學位論文寫作中,有些研究生卻表現出下述辯證思維缺失的現象。
1.用一元論的專斷置換二元論的辯證
學位論文寫作總要就某事象闡述、論證某種觀點;而在論證、闡述某種觀點時,難免要批駁與其闡述、論證的觀點相對立的主張。但在闡述、論證的觀點與其質疑、反對的主張之間常常并不是非此即彼、非對即錯的對立關系,而是相互依存、彼此貫通的辯證關系。倘若缺乏這種辯證的認識,不能自覺地運用辯證思維正確地對待闡述、論證的觀點與其質疑、反對的主張的辯證關系,那么就極易導致一元論的專斷。比如,有研究生在闡述“課程即生成”時,運用懷特海的過程哲學觀進行論證,也不乏理論依據。因為在懷特海看來,“現實世界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就是實際存在物的生成;實際存在物是如何生成的構成了這個實際存在物是什么,因而‘存在’是由它的‘生成’構成的,這就是‘過程原理’。”[5]由此推論出課程也是一種“過程性”存在,表現為師生共在的“一段旅程”和“不斷生成的文本”①凡未標注的內容皆源于筆者盲審的學位論文,且為了避免對號入座,做了技術性處理。。自然,從過程哲學來看,既然萬事萬物皆表現為一種過程,那么課程也就呈現為一種“過程性”存在,就證成了“課程即生成”的觀點。但問題是,“課程即生成”的確證也是有條件的,它與“課程即預定”并不是非此即彼、非對即錯的關系。
從一定意義上說,現代哲學的發展趨勢之一是拒斥實體思維及其表現的預定論,而倡導過程思維及其表現的生成論。不過,一方面,生成論也存在著內在的矛盾,即“要生成某物,就必須預先存在生成某物的能力,而且被生成的某物的性質也必須是預定的,否則生成的過程就是無序而混亂的,從而無法生成任何事物”[6]。換言之,某事象的生成要以一定的預定為前提條件,某事象的生成與預定并非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另一方面,“無”不能生成“有”,凡生成皆有預定,預定論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聯系到“課程即生成”,就會發現此觀點雖相對于課程即學科、課程即教學計劃等預定論,具有一定的創新意義;但此觀點不僅是哲學生成論的邏輯推演,而且存在著用一種片面的認識取代另一種片面認識的偏頗,從而表現出一種自以為是的獨斷。究其根源在于,論者未能運用直面矛盾的辯證思維,通過揭示“課程即生成”蘊涵的內在矛盾,諸如人類之知與學生之知、教師之知與學生之知、學生的學科之知與學生的生活之知的矛盾等,來闡釋自己的“課程即生成”觀。因為課程無論是什么,皆是為了最終消除、解決人類之知與學生之知、教師之知與學生之知、學生的學科之知與學生的生活之知的矛盾,而為了解決這些矛盾,作為生成的課程至少需經歷三重轉化:一是課程編制者將人類累積起來的符號知識按照一定的目的、邏輯進行加工與整理,進而形成預定的課程文本。二是教師將客觀、系統的課程文本轉化為預定的教學知識。三是學生借助教師的教學知識對課程文本進行自我建構,生成個體化的主體性知識。由此可見,在“課程即生成”中,既預定了人類知識、教師知識、學生知識等的存在,也圍繞著這些預定的要素呈現了“課程即生成”的過程。
2.用庸俗的辯證表達置換對矛盾的深入分析
庸俗的辯證表達是指凡是遇到二元對立的概念、命題,就采用“一分為二”的“二分法”進行辯證統一的表述,常常用“既要……也要……”的話語將矛盾雙方統一起來,這種看似公允的“兩點論”卻掩蓋了某事象發生、變化的真實面貌,將直面矛盾的辯證思維蛻化為無矛盾的和稀泥。這也是人們常將“辯證法”戲稱為“變戲法”的緣由。實際上,辯證思維是一種通過對話、辯論探求真理的思維方式,也是客觀存在的事象具有的矛盾性、發展性和主體存在的超越性在思維上的表現。而一旦用庸俗的辯證表達置換矛盾的深入分析,那么辯證思維就會變成思想懶漢的工具。比如,研究深度學習,勢必聯系淺層學習,在二者的關系上,倘若用一元論的專斷置換二元論的辯證,那么就會主張深度學習,而反對淺層學習,這自然是一種辯證思維缺失的表現。但即使想到學習本要經歷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并據此主張深度學習與淺層學習的和諧共生,這種看似合理的主張也會因缺乏深入分析深度學習遭遇的矛盾,變成另一種辯證思維缺失的表征。因為深度學習與淺層學習作為學習方式,只有相對于具體的學習內容來說,才能評鑒其優劣,且深度學習受制于學習要求、問題解決的難度等因素的影響。而一旦缺乏對深度學習與淺層學習的矛盾分析,不能正確地闡述深度學習與淺層學習的關系,以及深度學習、淺層學習各自適用的對象與范圍;那么簡單地主張二者的有機統一,則有用庸俗的辯證表達置換對矛盾的深入分析之嫌疑,從而使自己的觀點表達表現為四平八穩的平庸。
倘若基于深度學習、淺層學習的矛盾分析,就會發現深度學習主要表現為對知識的深度理解與遷移運用,是對知識的結構化與體系化的掌握與應用,并伴有積極的情感體驗;而淺層學習則主要表現為對孤立的事實性知識的機械記憶與簡單呈現。作為學習方式,二者各有其適用的對象和范圍。比如,對于事實性知識,記住了就知道,記不住就不知道,只需淺層學習就能應對,無須進行深度學習。相反,若是對事實性知識也進行深度學習,反復追問為什么三國是“吳國、魏國與蜀國”或負數為什么用“減號”來表示等,則是浪費時間。但對于“為什么”和“如何做”的知識,則需進行深度學習。
3.用二元的矛盾統一置換多元的矛盾轉化
某事象常常包含著多種要素及其各要素之間的矛盾關系,這些矛盾可分為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并非只是呈現為二元的矛盾統一,而是表現為不平衡的多元矛盾轉化。然而,在學位論文寫作中,有些研究生卻慣于用二元的矛盾統一置換多元的矛盾轉化,具體表現為只是觀照某事象的二元矛盾,而未能分析出某事象蘊涵的多重矛盾以及多重矛盾各自的地位和作用。這種做法雖然明顯地優于庸俗的辯證表達,體現了一定的辯證思維,但因其未能全面地分析某事象蘊涵的多元矛盾及其轉化,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在探討教與學的關系中,有研究生雖正確地指出教與學是交互共生、相反相成的,但因其未能把握教與學皆是以知識學習為中介,且教與學皆和特定的知識之間存在著矛盾,就使教與學二元的矛盾統一顯得單薄、膚淺,有待進一步拓展為將特定知識與學生的學視為教學的主要矛盾,把特定知識與教師之教、教師之教與學生之學作為教學的次要矛盾,并在這種多元的教學矛盾轉化中,闡述、論證教與學的矛盾轉化,即特定知識與學生之學的主要矛盾決定了教學要“以學定教”與“以教引學”的教學觀。前者意味著教是為了學生的學,且要基于學生的學來展開;后者則體現了以教師之知表征的人類知識對學生之學的引導、規范作用。
當然,在學位論文寫作中,辯證思維并不能違背形式邏輯,而是在遵循形式邏輯的基礎上對某事象矛盾的辯證把握。確切地說,辯證思維在闡述對某事象所持的觀點時,始終關注其相反、對立的觀點,既要分清一個概念或命題“是什么”,也要澄清其“不是什么”,而不能僅僅用“相反相成”“對立統一”予以搪塞。或者說,對某事象多元矛盾轉化的陳述是將形式邏輯的矛盾律作為一個必要環節,在闡述某事象既是什么又不是什么時,無論是肯定判斷還是否定判斷,皆不能違背矛盾律,因為兩個判斷都是正確判斷。在此基礎上,將符合矛盾律的兩個對立的正確判斷在新的概念、命題的平臺上統一起來,使兩個對立的靜止認識轉化為動態的把握。比如,有學者探討科學哲學,在分析了聚焦“知識論”的科學哲學的價值及其困境和立足“文化論”的科學哲學的意義及其缺陷后,認為“前者切斷了科學知識的文化之根來理解科學,變成一種沒有文化內涵的科學哲學;而后者則切斷了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之間的深刻關聯,變成一種沒有科學內涵的科學哲學”,鑒于此,論者主張“要使科學哲學從根本上擺脫現有的困境……要在二者之間建構一種既不同于知識論又區別于文化論的研究范式,即‘科學文化論’的研究范式……科學文化哲學將不僅能夠最大限度地挖掘和發現二者的意義和價值,從而達到新的綜合,而且能夠最大限度地克服和糾正二者的缺陷和偏頗,從而實現新的超越”[7]。由此可見,辯證思維并不拒斥形式邏輯,而是在克服形式邏輯對某事象判斷的片面性與局限性的同時,把形式邏輯作為一個必要的發展環節,即在分析某事象的矛盾時,把握其各自的優劣特征,并通過創造一個新的概念或命題將相互矛盾的兩個方面統一起來。
三、研究生辯證思維的彰顯
在學位論文的寫作中,要彰顯研究生的辯證思維,則需基于對某事象的矛盾揭示,變絕對為辯證;基于對某事象的矛盾分析,變籠統為具體;基于對某事象的矛盾史述,變平面為立體。
1.基于對某事象的矛盾揭示,變絕對為辯證
學位論文寫作是對研究問題的創新解答,此研究問題既可能是與社會發展相關的“新”問題,也可能是與時代發展相關的“大”問題,還可能是迫切需要重新思考的“老”問題。但不管是哪種問題,問題通常表現為某事象的矛盾,而矛盾則既可能表現為某事象的“一分為二”,也可能呈現為某事象的“一分為三”,還可能體現為某事象的“多元矛盾統一”。不過,無論是某事象的“一分為二”,還是某事象的“一分為三”乃至“一分為多”,只有揭示了某事象的上述矛盾,研究問題才能逐漸清晰、明朗,才能為學位論文寫作尋找到邏輯起點。因此,作為對研究問題創新解答的學位論文寫作應基于對某事象的矛盾揭示,并在對某事象的矛盾揭示中根據其矛盾的發展、變化而變絕對的專斷言說為辯證的話語表達。試想,當論證“課程即生成”時,如果能深入分析課程蘊涵的多重矛盾,諸如人類之知與學生之知、教師之知與學生之知、課程學科之知與學生生活之知等的矛盾,那么闡述“課程即生成”就不僅能呈現出辯證的思考,而且能辨析出“課程即生成”與“課程即預定”之間的辯證關系,從而避免“課程即生成”的獨斷。
當然,由于研究問題的提出受制于研究者已有知識、能力、價值偏好等影響,究竟對某事象揭示出怎樣的矛盾,其呈現樣態是多種多樣的。但無論對某事象揭示的矛盾樣態呈現的是“一分為二”,還是“一分為三”,抑或“一分為多”,皆需予以翔實的描述與展示。比如,研究勞動教育,就要揭示當下勞動教育存在的種種矛盾,諸如有“教”無“勞”、有“勞”無“教”與教勞割裂等“異化”現象。倘若將勞動教育放置于人工智能的時代背景中,那么就要陳述人工智能對勞動教育提出的新挑戰,諸如“勞動工具的改進:從力量驅動到智能控制”,導致勞動教育“從操作技能訓練轉向數字能力培養”;“勞動認知的模擬:從符號編程到神經同構”,導致勞動教育“從靜態旁觀認識轉向實踐探究智慧”;“勞動存在的挑戰:從智能反超到存在奴役”,導致勞動教育“從工具實用謀生轉向存在美學提升”,從而為闡述勞動教育的變革——“從數字化轉向到美學化轉向”提供了論證依據[8]。概而言之,在辯證思維的視域里,學位論文寫作總是源于對某事象的矛盾揭示,并在闡述、論證某觀點時,運用辯證思維在揭示、分析矛盾中思考與言說,從而規避那種自以為是的一元論的獨斷。
2.基于對某事象的矛盾分析,變籠統為具體
辯證思維并不是簡單地尋求矛盾對立面的統一,而是基于對某事象的矛盾分析,把握某事象發展、變化的具體過程,進而尋求對某事象矛盾的深刻認識與自主掌控。比如,探討深度學習,倘若能結合具體事例,諸如學習負數,那么就能將深度學習與淺層學習的關系闡述得更清楚,指出對于負數的含義、符號、讀法等事實性知識,學生通過淺層的看書學習、明了其意義就能掌握;而對于負數由實數變虛數、由數的絕對性到數的相對性,則需采用深度學習,諸如呈現體溫、水溫與天氣的變化數據,讓學生理解負數是如何由實數變虛數、由數的絕對性到數的相對性及其數學價值。那種凡是遇到矛盾皆用對立統一化解的言說,只能是大而化之的敷衍與籠統的說教,難以在看似正確的論證中彰顯話語的力量。即使是對于宏大、復雜的事象,一旦通過對宏大、復雜事象的矛盾分析,變籠統為具體,那么就能釋放出話語的言說魅力。舉例來說,有學者借助布迪厄的實踐感理論透視了中國教育改革的“深度復雜”,在“場域”上,通過具體描述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的關系,即“短時逼迫長時—空間贏取時間—場域位置變化—時間緊迫無法等待”,闡釋了當下“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已經疲憊地不會去重復進行是否‘兩張皮’的相互拉扯,也似乎不怎么想去思考用考試解決素質教育問題的辦法會不會在考試中發生變質,而是相互攜手,在各不相同的場域中發揮各自的效用,生成各自期待的結局,形成各自場域中需要持有的相互競爭和較量的正當形式的權威”。在“慣習”上,通過描述40多年來中國教育改革實踐的邏輯,即“問題逼迫改革—國家全民動員—層層傳達響應—逐步推進實施—問題反復出現—效果不盡人意—繼續跟進推廣”,闡述了中國教育改革“深度復雜”的特有“性情傾向”。在“資本”上,通過對“作為象征資本的傳播資本、口碑資本、指標資本”相互勾連的描述,論證了“‘資本’集結成捆綁式‘資本束’,作用實踐甚至左右實踐,形成中國教育改革‘深度復雜’的特有‘象征力量’”[9],從而使對中國教育改革這一宏大主題的闡述變得深刻而具體。
任何事象的發展、變化皆是由矛盾驅動、創生的。直面矛盾的辯證思維自然不能回避、拒斥矛盾;但倘若在分析某事象的矛盾時,僅僅大而化之地進行抽象的概念辯證,而不是結合具體事例或事實的描述展開分析,那么學位論文寫作除了給人一種佶屈聱牙、晦澀難懂之外,并不能讓讀者讀后有所啟迪、擁有一種閱讀的理智愉悅。然而,在閱讀學位論文時,筆者不時看到有些學位論文慣于運用一些新概念、新術語進行包裝,或即使其采用的字詞我們都認得,但就是讀不懂其表達的用意,不知這些詞語是用來描述何種事象、解決何種問題的;論文內容總給人一種是非難辨、似懂非懂的朦朧與玄奧感,需反復意會、仔細揣摩論者到底要表達何種觀點,其論據是什么,讀者能否從證據中推出其觀點;而一旦追問上述問題,則會發現有些學位論文的寫作在有意或無意地回避對某事象的矛盾分析,只是用煩瑣、生僻或時髦的詞語掩蓋自己思想的貧困,從而使學位論文的觀點闡述蛻化為概念游戲乃至僅僅是碼文字。如果說某抽象道理皆蘊含在對某事象的矛盾分析中,那么運用辯證思維,借助對某事象的矛盾分析,在將籠統的說辭轉化為對矛盾的具體分析中,就能清楚、明白地闡明某抽象道理。只有如此,辯證思維才能給人以通透、鮮活的語言表達的美感,才能凸顯學位論文的思想力量。
3.基于對某事象的矛盾史述,變平面為立體
研究某事象的問題,既要分析某事象的矛盾,也要史述某事象的矛盾演進,且只有在對某事象的矛盾演進的史述中,才能動態、邏輯地呈現某事象的發展過程。這種對某事象矛盾演進的史述常常遵循著“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三個基本階段。比如,在教與學的關系研究上,倘若能基于對教與學的矛盾演進的史述,就會發現中國古代教學思想的核心是學習論,如《學記》,即從學習的角度論述教學;而西方早期教學思想的核心則是教學論,如昆體良的《雄辯術原理》,即從教師之教的角度論述教學;但二者皆是單中心論,即要么以學為中心,要么以教為中心。隨著人們對教學的認識日益豐富,發現教與學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不過,在教與學孰輕孰重,抑或雙方誰決定誰、誰主導誰上發生了論爭,出現了二元對立論,即要么教決定學,要么學決定教。時下,人們逐漸認識到教師之教與學生之學是教學活動的一體兩面,教師之教離不開學生之學;而學生之學也離不開教師之教。在教與學的交互共生中,倘若抓住人類之知與學生之知這一主要矛盾,那么就能辯證地處理好教與學的關系。上文所述的“以學定教”與“以教引學”的有機統一,則是解決人類之知與學生之知這一主要矛盾的教學原則;其操作路徑可以用“新基礎教育”研究創設的“有向開放—交互反饋—集聚生成”的教學流程展開。“有向開放”即激活學生資源,激發學生參與;“交互反饋”進一步豐富、篩選和提升學習資源;二者皆旨在貫徹“以學定教”的原則,指向對學生已知的激發與優化。而“集聚生成”則在前兩步的基礎上將相對分散、局部的認識進行聚類、清晰化和結構化處理,旨在貫徹“以教引學”的原則,指向學生對特定知識的理解、掌握與運用,最終化解人類之知與學生之知的矛盾[10]。如此闡述教與學的關系,則在陳述教與學的矛盾演進中,動態、立體地展示了教與學的豐富聯系與相互生成。
從一定意義上說,基于對某事象的矛盾史述,變平面為立體,就意味著回顧某事象的歷史發展過程、洞察其演變的特征及其蘊涵的矛盾,并在此基礎上動態、發展地闡述某事象的未來形態。因為一旦靜觀某事象,那么某事象就會呈現出“A就是A,B就是B”的知性狀態;而一旦動觀某事象,將某事象放置于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那么某事象就會顯現出發生、變化的辯證特性。因此,成熟的研究者大多具有歷史視野,即在認識某事象時,能自覺地把某事象發生、發展的過程納入其認識中,以便把握某事象發生、發展的內在邏輯,具體表現為研究某事象時的歷史思維與歷史方法。前者是歷史視野的根基,后者則是歷史視野的呈現,具體展示為在面對某事象時會自動地啟動歷史思維,主動地運用歷史方法探究某事象發生、發展的過程,在洞察其演化的歷史邏輯的同時,觀照某事象的當下形態,從而對某事象獲得一種更加全面、深入的認識。比如,有學者探究中國教師資格問題,就基于對中國教師資格的矛盾演進,梳理出“中國教師資格的發展經歷了從‘非制度化’到‘制度化’再到‘后制度化’的過程”,揭示了中國教師資格在不同發展階段具有的特征及其蘊涵的矛盾,諸如,在“非制度化”階段,教師資格是“以有識者為師”與“以吏為師”,但教師并沒有獨立的職業身份。在“制度化”階段,教師資格經歷了由“以師范教育者為師”到“以持教育資格證者為師”的轉變,教師逐漸獲得了獨立的職業身份。在“后制度化”階段,教師遭遇著前所未有的身份危機,表現為“傳統社會中教師‘因官而貴’的崇高性被層層消解”、在市場邏輯的沖擊下“教師在世俗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與在信息激增、知識唾手可得背景下的“教師‘因識而貴’的時代一去不復返”。由此衍生、推論出中國教師資格的現代建構,即“在全球化、信息化與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時代背景下,教師應承擔起更多面向未來世界的使命,應從超越并引領制度的角度出發,在成為目的人、公共人及文化人上實現對職業身份的現代建構”[11]。從而使讀者對中國教師資格獲得一個全面、立體的認識。
[1] 黑格爾. 邏輯學(哲學全書·第一部分)[M]. 梁志學, 譯.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116.
[2] 李潤洲. 我國現階段教育公平問題的理論探討[D]. 曲阜: 曲阜師范大學, 2002: 10-18.
[3] 李潤洲. 試論教育公平的基本特征[J]. 教育評論, 2002(5): 14-16.
[4] 李潤洲. 論教育學研究的價值生成[D]. 北京: 北京師范大學, 2008: 111-128.
[5] 懷特海. 過程與實在[M]. 楊富斌, 譯. 北京: 中國城市出版社, 2003: 38-40.
[6] 嚴春友. 生成論批判[J]. 河北學刊, 2012(4): 8-14.
[7] 孟建偉. 走向第三種科學哲學[J].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2019(5): 133-142.
[8] 王惠穎. 人工智能時代勞動教育的三重轉向與實施路徑[J]. 南京社會科學, 2021(10): 156-162.
[9] 馬維娜. 實踐感: 中國教育改革的“深度復雜”[J]. 探索與爭鳴, 2021(7): 144-153.
[10] 葉瀾. 新基礎教育論——關于當代中國學校變革的探究與認識[M]. 北京: 教育科學出版社, 2006: 268-275.
[11]宗錦蓮. 中國教師資格的制度化歷程與現代建構[J]. 南京社會科學, 2020(12): 133-140.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一般課題“高質量教育視域下師德養成的機制與路徑研究”(編號:BEA190115)
10.16750/j.adge.2023.09.002
李潤洲,浙江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金華 321004。
(責任編輯 周玉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