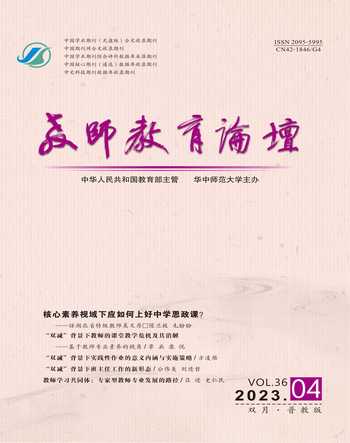青年鄉(xiāng)村教師的鄉(xiāng)村融入:現(xiàn)實困境、影響機理與突圍路徑
徐書銘 鄒太龍 譚貴平 張前銳
基金項目:2022年國家級大學(xué)生創(chuàng)新訓(xùn)練計劃重點支持領(lǐng)域項目“螢火計劃——青年人才參與鄉(xiāng)村振興的實踐路徑研究”(編號:202210517001),2022年度湖北省高等學(xué)校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研究青年項目“青年人才參與民族地區(qū)鄉(xiāng)村振興的行動邏輯與長效機制研究”和2020年湖北省高等學(xué)校省級教學(xué)研究項目“守一而望多:小學(xué)教師職前培養(yǎng)模式改革探索”(編號:2020551)。
摘 要 鄉(xiāng)村融入對于提振鄉(xiāng)村教師幸福感、穩(wěn)定鄉(xiāng)村教師隊伍和推動鄉(xiāng)村全面振興都有重要的價值意義。然而,當前青年鄉(xiāng)村教師的鄉(xiāng)村融入現(xiàn)狀令人擔(dān)憂,主要表現(xiàn)在“城市人”的身份認同、“候鳥型”的生活方式、“孤島式”的活動空間和“飛鴿化”的職業(yè)期待。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依然客觀存在、新生代青年城市化特征明顯、鄉(xiāng)土知識在教師培養(yǎng)中的失落、城優(yōu)鄉(xiāng)劣的社會心理根深蒂固是影響青年鄉(xiāng)村教師鄉(xiāng)村融入的重要因素。破解青年鄉(xiāng)村教師的鄉(xiāng)村融入難題,需要多方協(xié)同,共同發(fā)力:高等院校要在人才培養(yǎng)各環(huán)節(jié)滲透鄉(xiāng)土元素,鄉(xiāng)村社會要搭建參與公共事務(wù)的廣闊平臺,鄉(xiāng)村學(xué)校要增強與當?shù)厣鐣穆?lián)系,教師個人應(yīng)內(nèi)化“為鄉(xiāng)村而教”的職業(yè)信念。
關(guān)鍵詞 青年鄉(xiāng)村教師;鄉(xiāng)村融入;身份認同;城市化特征
中圖分類號 G45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5995(2023)04-0019-04
青年鄉(xiāng)村教師是指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且在鄉(xiāng)村學(xué)校工作的教師。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接受過城市教育熏陶、擁有先進教學(xué)方法、掌握最新教學(xué)藝術(shù)的青年鄉(xiāng)村教師逐漸成為鄉(xiāng)村教師隊伍的主力軍,是推動鄉(xiāng)村教育振興的重要力量。然而,由于城鄉(xiāng)差距大、青年教師“向城性”心理傾向強、鄉(xiāng)土知識儲備不足等原因,產(chǎn)生了青年鄉(xiāng)村教師“留不住,教不好”的問題。2018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wù)院印發(fā)《關(guān)于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shè)改革的意見》,提出要“拿出務(wù)實舉措,幫助鄉(xiāng)村青年教師解決困難,關(guān)心鄉(xiāng)村青年教師工作生活,鞏固鄉(xiāng)村青年教師隊伍”。2020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門在《關(guān)于加強新時代鄉(xiāng)村教師隊伍建設(shè)的意見》中明確強調(diào)要“強化教育實踐和鄉(xiāng)土文化熏陶,促進師范生職業(yè)素養(yǎng)提升和鄉(xiāng)村教育情懷養(yǎng)成”。解決青年鄉(xiāng)村教師“留不住”難題,既要分析青年教師鄉(xiāng)村融入的現(xiàn)實困境,為其紓難解困;又要透析青年教師社會融入的影響機理,為其破解心理障礙;還需多方協(xié)同、共同發(fā)力,為其尋找破解路徑。
一、青年鄉(xiāng)村教師鄉(xiāng)村融入的現(xiàn)實困境
(一)“城市人”的身份認同
身份認同是教師個體對自身教師身份、意義與價值的主觀感知,不僅影響教師職業(yè)認同感與幸福感,還影響著教師職業(yè)場域選擇與目標追求。“城市人”身份認同的形成主要表現(xiàn)為三個方面。首先,“在基礎(chǔ)教育階段,農(nóng)村教育的定位是培養(yǎng)城市人,為城市發(fā)展輸送人才”[1],因此,青年鄉(xiāng)村教師不可避免地烙上城市印記。其次,受長輩“走出農(nóng)村”價值觀的影響,部分青年鄉(xiāng)村教師從小便萌生定居城市的動機。最后,在職前培養(yǎng)過程中,部分青年教師深受城市文化的影響,更加認同城市文化與城市化生活方式。當其以“漂泊者”的身份邁入鄉(xiāng)村“大門”時,既要面臨語言、文化、心理等差異,又要面臨重構(gòu)教學(xué)思維、改變生活方式等挑戰(zhàn),同時還會面臨子女教育、薪資待遇、職業(yè)發(fā)展等問題。基于對以上多種因素的綜合考量,部分鄉(xiāng)村教師不愿扎根基層,而是選擇“轉(zhuǎn)戰(zhàn)”城市。
(二)“候鳥型”的生活方式
隨著城鎮(zhèn)化的快速發(fā)展和交通條件的改善,“縣域內(nèi)鄉(xiāng)村教師工作生活兩地化成為一種新趨勢”[2],青年鄉(xiāng)村教師愈發(fā)呈現(xiàn)出明顯的“候鳥”特征。在上班時間,“候鳥型”教師待在鄉(xiāng)村學(xué)校,非工作時間則會選擇留在城市,出現(xiàn)了工作、生活異地化的現(xiàn)象。青年鄉(xiāng)村教師要么從小就生活在城市,要么在城市接受過高等教育,他們已經(jīng)適應(yīng)了城市化的生活方式。這使得他們不愿意融入鄉(xiāng)村,更不會在鄉(xiāng)村成家立業(yè),而是選擇在城市買房定居。隨著鄉(xiāng)村社會不斷發(fā)展,城鄉(xiāng)交通也更加便利,這為“候鳥型”教師提供了有利條件,他們可以在非工作時間選擇乘坐村村通班車或開私家車返回居住城市,在上班之際又返回鄉(xiāng)村。“候鳥型”鄉(xiāng)村教師長期保持著這種生活方式,在鄉(xiāng)村社會生活的時間與精力通常較少,與鄉(xiāng)村民眾的溝通與交流也較少,容易出現(xiàn)難以融入鄉(xiāng)村社會的問題。
(三)“孤島式”的活動空間
相較于老一輩鄉(xiāng)村教師而言,青年鄉(xiāng)村教師所處的不是“熟人社會”,而是近乎陌生的“不流動”的社會。以往鄉(xiāng)村學(xué)校是村鎮(zhèn)重要文化活動的舉辦場所,但隨著時代變遷,鄉(xiāng)村學(xué)校的社會功能逐漸喪失,“傳授城市中心的現(xiàn)代知識”[3]成了鄉(xiāng)村學(xué)校的主要任務(wù)。由于鄉(xiāng)村學(xué)校逐漸失去鄉(xiāng)土文化傳承主陣地的作用,久而久之,“學(xué)校圍墻”就切斷了學(xué)校與鄉(xiāng)村社會的文化聯(lián)系,最終使鄉(xiāng)村學(xué)校成了鄉(xiāng)村社會的“文化孤島”。此外,部分青年鄉(xiāng)村教師與老一輩教師之間的代際阻隔、與學(xué)生之間的關(guān)系疏離、與鄉(xiāng)村基層社會治理之間的被動參與進一步造成了“關(guān)系孤島”現(xiàn)象。[4]而語言與文化之間的差異使得青年鄉(xiāng)村教師與鄉(xiāng)村社會之間不易溝通、難以理解,使得二者間的關(guān)系更顯微妙。最終,在“文化孤島”與“關(guān)系孤島”的影響下,青年鄉(xiāng)村教師融入鄉(xiāng)村社會變得日益艱難。
(四)“飛鴿化”的職業(yè)期待
由于城市就業(yè)壓力較大,部分青年教師選擇了鄉(xiāng)村教師崗位。但考慮到職業(yè)發(fā)展空間有限以及“城市人”的身份認同影響,部分青年教師并未將鄉(xiāng)村教師作為長期的職業(yè)規(guī)劃,而是一旦時機成熟便化作“飛鴿”飛往城市。其實,“飛鴿”教師逃離鄉(xiāng)村的原因主要有四:一是青年教師對鄉(xiāng)村“落后、愚昧與閉塞”的刻板印象影響其職業(yè)期待;二是薪酬待遇較低、社會地位不高、課業(yè)負擔(dān)繁重以及榜樣示范缺失導(dǎo)致青年鄉(xiāng)村教師產(chǎn)生較大壓力,進而使其感到無奈、無助與自卑;三是未來職業(yè)發(fā)展空間受限進一步加劇青年鄉(xiāng)村教師的迷茫、焦慮,從而導(dǎo)致其在心理層面想方設(shè)法逃離鄉(xiāng)村;四是工作與生活異地、工作與家庭關(guān)系失衡成了鄉(xiāng)村教師不可回避的現(xiàn)實問題,如何破解工作與家庭之間的矛盾沖突成了困擾青年鄉(xiāng)村教師的難題。總之,“飛鴿化”已成為青年鄉(xiāng)村教師的真實寫照,以至于有學(xué)者感嘆,他們“不是在逃離就是在逃離的路上”[5]。
二、青年鄉(xiāng)村教師鄉(xiāng)村融入困境的影響機理
(一)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依然客觀存在
在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依然客觀存在的情況下,鄉(xiāng)村教育振興面臨的形勢較為嚴峻。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的阻礙作用,一是表現(xiàn)為城鄉(xiāng)基礎(chǔ)教育設(shè)施的差距。受區(qū)域位置與發(fā)展條件的限制,鄉(xiāng)村經(jīng)濟相對滯后,其基礎(chǔ)教育設(shè)施不足以完全支撐教師職業(yè)發(fā)展。以E市T小學(xué)為例,極其不利的交通造成當?shù)亟處熉殬I(yè)發(fā)展“上不去”而市區(qū)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下不來”的問題突出,導(dǎo)致該校教師職后培訓(xùn)流于形式。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的阻礙作用,二是表現(xiàn)為教育資源的供給不足。一直以來,受城市中心價值觀念的影響,我國一直沿用“中央—省—市—縣—鎮(zhèn)—村”的教育資源分配制度。由于鄉(xiāng)村學(xué)校始終處于分配體系的末端,所獲教育資源不足嚴重影響鄉(xiāng)村教育的公平與質(zhì)量[6],也對教師的就業(yè)選擇產(chǎn)生負面影響。最后,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的阻礙作用還體現(xiàn)在文化差異上。城市以高聚集、快發(fā)展和服務(wù)優(yōu)的獨特優(yōu)勢造就了其商業(yè)性、通俗性、流行性和娛樂性的文化氛圍,鄉(xiāng)土文化則呈現(xiàn)出守舊性、封閉性、權(quán)威性和傳承性特質(zhì)。[7]隨著時間的推移,青年鄉(xiāng)村教師逃離鄉(xiāng)村、憧憬城市的心理更為凸出。
(二)新生代青年城市化特征明顯
青年鄉(xiāng)村教師是鄉(xiāng)村教育振興的主力軍,是提高鄉(xiāng)村教育質(zhì)量的關(guān)鍵。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青年鄉(xiāng)村教師更傾向于接受城市文化價值,展現(xiàn)出明顯的城市化特征。一方面,這種城市化特征集中表現(xiàn)為居住地向城市遷移。據(jù)有關(guān)調(diào)查研究顯示:鄉(xiāng)村教師居住地位于城市的占比高達53.0%[8],這也就意味著超過一半的青年鄉(xiāng)村教師工作生活異地化。教師在城鄉(xiāng)之間往返奔波,一會導(dǎo)致教師身心疲憊,不利于教師提高教學(xué)質(zhì)量;二會產(chǎn)生城鄉(xiāng)兩套教育思維,導(dǎo)致教師教育價值感知產(chǎn)生偏差,即視鄉(xiāng)村教學(xué)為“生存工作”而非“太陽下最神圣、最光輝的職業(yè)”。另一方面,青年鄉(xiāng)村教師城市化也表現(xiàn)為育兒模式的城市化。育兒模式城市化是指青年鄉(xiāng)村教師以城市父母的標準進行育兒,強調(diào)科學(xué)育兒和精致化育兒。[9]在幼兒閱讀的選擇上,青年鄉(xiāng)村教師更側(cè)重于選擇體現(xiàn)城市生活的讀物,而有意忽略與鄉(xiāng)土相關(guān)的內(nèi)容。居住地的城市化與育兒模式的城市化不僅會阻斷鄉(xiāng)土文化的代際傳遞,同時也會影響青年鄉(xiāng)村教師的鄉(xiāng)村融入。
(三)鄉(xiāng)土知識在教師培養(yǎng)中的失落
從師資來源看,與老一輩鄉(xiāng)村教師多來自本土的情況不同,新生代鄉(xiāng)村教師多通過全國性招聘入崗,跨域流動更為明顯,這就使得外域鄉(xiāng)村教師不懂本地鄉(xiāng)土知識。就培養(yǎng)過程而言,鄉(xiāng)土知識屬于民族學(xué)與社會學(xué)范疇,而師范生多由教育學(xué)或?qū)W科教育專業(yè)進行培養(yǎng)。由于學(xué)科門類之間的交叉不易整合,因此鄉(xiāng)土知識也就無法深層融入師范生的培養(yǎng)體系。而在課程設(shè)置上,不論是通識性課程還是專業(yè)性課程都未將農(nóng)村教育學(xué)、鄉(xiāng)土文化、鄉(xiāng)土課程的開發(fā)與利用等知識內(nèi)容納入其中,這就導(dǎo)致青年鄉(xiāng)村教師在入職前對鄉(xiāng)土知識知之不多。而職后培養(yǎng)又多關(guān)注教師教學(xué)技能的提升,注重如何教的更有效問題,導(dǎo)致鄉(xiāng)土知識難以進入教師職后培訓(xùn)內(nèi)容體系。鄉(xiāng)土知識缺失導(dǎo)致青年鄉(xiāng)村教師的鄉(xiāng)土情懷難以生成。而事實是,鄉(xiāng)土情懷的生成與鄉(xiāng)村教師掌握的鄉(xiāng)土知識密切相關(guān)。[10]知識的缺失與工作要求之間的矛盾,會使青年鄉(xiāng)村教師難以適從。久而久之,青年鄉(xiāng)村教師只能選擇伺機逃離。
(四)城優(yōu)鄉(xiāng)劣的社會心理根深蒂固
長期以來,受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的影響,城優(yōu)鄉(xiāng)劣一直是人們對城鄉(xiāng)之間的整體印象,并逐漸產(chǎn)生了鮮明對照。[11]在城鎮(zhèn)化浪潮的沖擊下,鄉(xiāng)土文化的地方性、離散化、保守性、禮俗性等促使青年鄉(xiāng)村教師選擇逃離,而城市文化以其多元性、高集聚、快發(fā)展、服務(wù)優(yōu)等獨特優(yōu)勢形塑著青年鄉(xiāng)村教師的教育觀念、生活方式和行為習(xí)慣,逐漸形成了城優(yōu)鄉(xiāng)劣的社會印象。在職前培養(yǎng)過程中,青年鄉(xiāng)村教師深受城市化生活方式的影響,其不僅更易接受城市文化,還會在精神生活和物質(zhì)生活價值取向上向“城市人”靠攏。此外,青年鄉(xiāng)村教師“非城非鄉(xiāng)”的社會屬性致使其職業(yè)認同面臨諸多困境:一是社會地位較低遭遇其他教育主體“忽視”;二是城鄉(xiāng)專業(yè)發(fā)展模式趨同造成自我定位迷茫[12];三是鄉(xiāng)村發(fā)展不景氣導(dǎo)致其職業(yè)發(fā)展空間受限,進一步強化了青年鄉(xiāng)村教師城優(yōu)鄉(xiāng)劣的社會認知,致使其無法安心從教,在“去留”之間來回擺動,無法全身心融入鄉(xiāng)村。基于以上種種因素,部分青年鄉(xiāng)村教師產(chǎn)生逃離鄉(xiāng)村的想法,將自身所從事的工作當作“跳板”或“緩沖墊”,伺機尋找機會“飛往”城市。
三、青年鄉(xiāng)村教師鄉(xiāng)村融入困境的突圍路徑
(一)高等院校:在人才培養(yǎng)各環(huán)節(jié)滲透鄉(xiāng)土元素
在職前培養(yǎng)階段,鄉(xiāng)土元素和地域文化的滲透對于青年鄉(xiāng)村教師的鄉(xiāng)村融入具有內(nèi)源性價值,“鄉(xiāng)土知識可以豐盈鄉(xiāng)村教師的精神世界,增加鄉(xiāng)村教師的知識資本,增強鄉(xiāng)村教師的鄉(xiāng)土情懷”[13]。高等院校作為師范生培養(yǎng)的核心主體,應(yīng)采取措施讓青年教師在入職前加深對鄉(xiāng)土知識的了解和掌握,從而培養(yǎng)出具有鄉(xiāng)土情懷和能夠勝任鄉(xiāng)村教育工作的鄉(xiāng)村教師。首先,高等院校應(yīng)開展校本課程,結(jié)合當?shù)氐奶厣幕浞珠_發(fā)和利用鄉(xiāng)土資源,將鄉(xiāng)土知識有機融入課堂教學(xué)中。例如,湖北民族大學(xué)開設(shè)的“恩施土家族民歌”“民族文化傳播”等課程,讓學(xué)生在學(xué)習(xí)中加深了對鄉(xiāng)土文化的認知,促進了鄉(xiāng)土元素在人才培養(yǎng)過程中的滲透。其次,高等院校應(yīng)完善師范生鄉(xiāng)土課程內(nèi)容,深度挖掘優(yōu)秀鄉(xiāng)土文化,推進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文化的有機融合,推動校園文化與鄉(xiāng)土文化的有機統(tǒng)一,從而構(gòu)建“通識教育+教師教育+鄉(xiāng)土文化+實踐教育”的課程體系。最后,高等院校應(yīng)引導(dǎo)學(xué)生開展社會調(diào)查,通過實地考察及查閱資料的方式對鄉(xiāng)土文化進行深入剖析,這不僅可以增進學(xué)生對鄉(xiāng)土文化的認同,還可以激發(fā)他們對鄉(xiāng)土文化的保護意識,促進鄉(xiāng)土文化的傳播。
(二)鄉(xiāng)村社會:搭建參與公共事務(wù)的廣闊平臺
2020年,教育部等六部門在《關(guān)于加強新時代鄉(xiāng)村教師隊伍建設(shè)的意見》中指出:注重發(fā)揮鄉(xiāng)村教師新鄉(xiāng)賢示范引領(lǐng)作用,塑造新時代文明鄉(xiāng)風(fēng),促進鄉(xiāng)村文化振興。發(fā)揮新鄉(xiāng)賢的示范引領(lǐng)作用,鄉(xiāng)村社會需為青年鄉(xiāng)村教師搭建參與鄉(xiāng)村公共事務(wù)的廣闊平臺,通過強化青年鄉(xiāng)村教師的社會實踐,引導(dǎo)青年鄉(xiāng)村教師深入鄉(xiāng)村,促使青年鄉(xiāng)村教師知鄉(xiāng)俗、曉民意、愛鄉(xiāng)村。第一,要把握關(guān)鍵點,即優(yōu)化鄉(xiāng)村管理平臺。青年鄉(xiāng)村教師博學(xué)多才、見識廣博,將他們“請”進鄉(xiāng)村管理平臺,有助于推動鄉(xiāng)村治理、實現(xiàn)鄉(xiāng)村振興。第二,要抓住著力點,即完善鄉(xiāng)村教育平臺。青年鄉(xiāng)村教師不僅是“一校之師”,還可以成為“一村之師”。聘請青年鄉(xiāng)村教師擔(dān)任村民教師,向村民傳授現(xiàn)代文化知識,有利于提升村民文化素養(yǎng),同時還有助于促使青年鄉(xiāng)村教師了解鄉(xiāng)風(fēng)鄉(xiāng)情,拉近青年鄉(xiāng)村教師與鄉(xiāng)土之間的距離。第三,要找準落腳點,即健全職后培養(yǎng)機制。將青年鄉(xiāng)村教師吸納至鄉(xiāng)土文化保護與研究活動中,以職后培訓(xùn)的形式補齊鄉(xiāng)土文化知識,既有利于青年鄉(xiāng)村教師更好地開展教育教學(xué),又有利于青年鄉(xiāng)村教師知鄉(xiāng)風(fēng)、懂鄉(xiāng)俗、傳承鄉(xiāng)土文化,從而厚植鄉(xiāng)土情懷,實現(xiàn)鄉(xiāng)村融入。
(三)鄉(xiāng)村學(xué)校:增強學(xué)校與當?shù)厣鐣穆?lián)系
在傳統(tǒng)社會中,鄉(xiāng)村教師多為生于斯、長于斯的知識分子,能夠很好地與當?shù)剜l(xiāng)村社會相融。但在當下,青年鄉(xiāng)村教師與鄉(xiāng)村社會之間的聯(lián)系變得越來越弱, 青年鄉(xiāng)村教師正逐漸淪為鄉(xiāng)村社會的“邊緣人”,而鄉(xiāng)村學(xué)校則成為青年鄉(xiāng)村教師聚居的“孤島”。破解這種局面,需要學(xué)校增強與當?shù)厣鐣穆?lián)系,幫助青年鄉(xiāng)村教師融入當?shù)厣鐣W(xué)校增強與當?shù)厣鐣穆?lián)系,一是構(gòu)建良好的家校合作機制。開展家長會、家訪和辦“家長學(xué)校”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強鄉(xiāng)村教師與家長之間的交流,在教育觀和學(xué)生觀上達成一致,實現(xiàn)家校合力育人。二是開展鄉(xiāng)村文化進校園活動,充分發(fā)揮隱性教育的作用。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和優(yōu)質(zhì)鄉(xiāng)土文化補充了書本中沒有的內(nèi)容,有利于拓展學(xué)生的視野、拉近學(xué)校與當?shù)剜l(xiāng)村的聯(lián)系、打破學(xué)校“文化孤島”與“關(guān)系孤島”現(xiàn)狀。三是學(xué)校需要走出“圍墻”。比如,學(xué)校可以聯(lián)合鄉(xiāng)村民眾組織文藝活動——以鄉(xiāng)土文化為背景,以農(nóng)民豐收為主題,以學(xué)生發(fā)展為焦點,創(chuàng)建師生村民更為喜聞樂見的文化活動,彌合學(xué)校與鄉(xiāng)村社會之間的信息代溝、消解觀點沖突,促進學(xué)校與鄉(xiāng)村社會的關(guān)系融合。
(四)教師個人:內(nèi)化“為鄉(xiāng)村而教”的職業(yè)信念
鄉(xiāng)村教師的職業(yè)信念是鄉(xiāng)村教師對自身所進行的教育活動的勞動價值感知,影響著鄉(xiāng)村教師的幸福感、歸屬感和自我認同感。內(nèi)化“為鄉(xiāng)村而教”的職業(yè)信念,一要明確鄉(xiāng)村教育的價值立場——“為生活而教”。2021年發(fā)布的《鄉(xiāng)村教育新觀察——中國鄉(xiāng)村教育發(fā)展報告》對鄉(xiāng)村教育提出了新期待:從城市化的“應(yīng)試教育”和“升學(xué)教育”走向能為農(nóng)村學(xué)生帶來實質(zhì)性變革的“為生活而教”。[14]青年鄉(xiāng)村教師只有弄清鄉(xiāng)村教育之于鄉(xiāng)村學(xué)生的價值意義,才能有針對性地開展教育教學(xué),提升教育實際質(zhì)量,提高鄉(xiāng)村教育水平。二要扭轉(zhuǎn)鄉(xiāng)村教師的價值觀念——從“要我教”走向“我要教”。如何認知鄉(xiāng)村教師這一職業(yè),決定了鄉(xiāng)村教師如何對待鄉(xiāng)村教學(xué)。從“要我教”走向“我要教”,扭轉(zhuǎn)了鄉(xiāng)村教師價值觀念,增強了鄉(xiāng)村教師的工作熱情,有助于鄉(xiāng)村教師實現(xiàn)從“在鄉(xiāng)村從教”向“為鄉(xiāng)村而教”的思維轉(zhuǎn)向。[15]三要激發(fā)鄉(xiāng)村教師的內(nèi)生動力——厚植鄉(xiāng)土情懷,涵育鄉(xiāng)村教育初心。鄉(xiāng)村教師的內(nèi)生動力在最抽象意義上是指鄉(xiāng)村教師的根本性力量,只有厚植鄉(xiāng)村教師鄉(xiāng)土情懷,才能涵育鄉(xiāng)村教師教育初心、鑄就鄉(xiāng)村教師職業(yè)之魂,才能真正破解鄉(xiāng)村教師鄉(xiāng)村融入困境。
(徐書銘? 鄒太龍? 譚貴平? 張前銳,湖北民族大學(xué)教師教育學(xué)院,湖北 恩施 445000)
參考文獻:
[1] 姚巖,鄭新蓉.走向文化自覺:新生代鄉(xiāng)村教師的離農(nóng)化困境及其應(yīng)對[J].中小學(xué)管理,2019(2):12-15.
[2] 姜超.工作生活兩地化:城鎮(zhèn)化背景下鄉(xiāng)村教師職業(yè)新樣態(tài)[J].中國教育學(xué)刊,2018(7):94-99.
[3] 黃小麗,任仕君.論鄉(xiāng)村學(xué)校應(yīng)成為鄉(xiāng)土文化的傳承中心[J].當代教育科學(xué),2019(5):86-89.
[4] 蹇世瓊,彭壽清,冉隆鋒.由“他者”走向“我者”——新生代鄉(xiāng)村教師的鄉(xiāng)村社會融入困境與破解路徑[J].四川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21(3):107-113
[5] 謝麗麗.教師“逃離”:農(nóng)村教育的困境——從G縣鄉(xiāng)村教師考警察說起[J].教師教育研究,2016(4):71-76.
[6] 于莎,劉奉越.城鄉(xiāng)關(guān)系視域下鄉(xiāng)村教育的演進圖景與發(fā)展展望[J].教育發(fā)展研究,2021(24):24-31.
[7] 羅生全,李越.城鄉(xiāng)一體化下的鄉(xiāng)村教師政策轉(zhuǎn)型[J].教育理論與實踐,2020(25):38-42.
[8] 肖正德.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中鄉(xiāng)村教師新鄉(xiāng)賢角色擔(dān)當意愿的相關(guān)影響因素分析[J].華東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教育科學(xué)版),2021(7):92-106.
[9] 姚巖,鄭新蓉.走向文化自覺:新生代鄉(xiāng)村教師的離農(nóng)化困境及其應(yīng)對[J].中小學(xué)管理,2019(2):12-15.
[10] 王中華,賈穎.論新生代鄉(xiāng)村教師鄉(xiāng)土知識的建構(gòu)[J].教育科學(xué)研究,2020(6):85-90.
[11] 鄒太龍.鄉(xiāng)村教師助力民族地區(qū)鄉(xiāng)村文化振興:現(xiàn)實困囿、角色期待與行動路徑[J].湖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22(5):106-114.
[12] 王肖星.我國鄉(xiāng)村教師職業(yè)認同的現(xiàn)實困境及其突破[J].教學(xué)與管理,2020(24):50-53
[13] 王中華,賈穎.論新生代鄉(xiāng)村教師鄉(xiāng)土知識的建構(gòu)[J].教育科學(xué)研究,2020(6):85-90.
[14] 于忠寧.《鄉(xiāng)村教育新觀察——中國鄉(xiāng)村教育發(fā)展報告(2021)》倡導(dǎo)——農(nóng)村教育應(yīng)該“為生活而教”[N].工人日報,2021-12-03(5).
[15] 趙鑫,謝小蓉.從“在鄉(xiāng)村從教”到“為鄉(xiāng)村而教”:我國鄉(xiāng)村教師身份認同研究的進展及走向[J].當代教育與文化,2020(1):83-89,109.
責(zé)任編輯:謝先成
讀者熱線:027-67863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