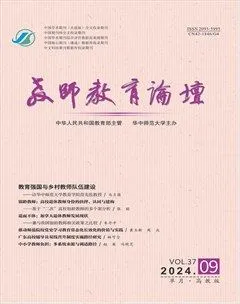中小學教師負擔:多系統來源與調適路徑
摘" 要:近年來,我國學者圍繞中小學教師負擔的現狀表征、負擔來源以及治理路徑等方面展開了廣泛研究。經文獻梳理發現,中小學教師負擔現狀主要表現為時間困境、角色異化和機制盲區三個方面。教師負擔緣起于教師個體層面的“微觀系統”,受學校“中間系統”的主導,并在家長和社會層面的“外觀系統”及政府“宏觀系統”的深層作用下產生。破解中小學教師負擔問題,需系統聯動,相關利益主體形成合力,編制多主體協同的共治網絡。此外,現有針對中小學教師負擔的研究仍存在局限性,未來研究需要關注不同義務教育階段以及不同地域類型中的教師負擔問題。
關鍵詞:中小學教師;教師負擔;減負
中圖分類號:G4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5995(2024)09-0084-08
基金項目: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省域追蹤數據驅動的高質量教師隊伍建設研究”(項目號:22JJD880012)
作者簡介:
趙英,博士,山西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黨委書記、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比較教師教育;馮艷芝,山西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教師教育.
構建優質教育教學環境,有效減輕教師負擔,是助力中小學教師回歸“教書育人”價值本位的必要舉措。為此,眾多學者從多個維度對教師負擔問題展開了廣泛深入的研究。經查詢,相關研究可追溯至20世紀90年代,但研究的轉折點為2018年。2018年之前,教師負擔問題尚未引起廣泛關注,研究成果相對較少,每年以“教師負擔”為篇名的文獻數量在5篇以內。2018年之后教師負擔問題逐漸成為了研究的熱點,每年以“教師負擔”為篇名的文獻數量都在10篇以上并逐年攀升,2021年發文量達到30篇,2022年增至37篇,2023年發文量激增至57篇。表明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并深入研究教師負擔問題,試圖從多個角度剖析其成因、影響及解決策略。
一、教師負擔的概念界定研究
關于教師負擔的界定,存在多種觀點和解釋,不同的研究者從不同的視角對教師負擔進行了界定,總的來說存在以下幾種論點。
其一,廣義和狹義區分說。[1]廣義上,教師負擔涉及家庭、學校、社會等多個層面,包括教師在生活和工作中承擔的責任、義務與壓力。這種觀點將教師負擔定義為教師應擔當的責任、履行的任務和承受的壓力,認為適度的負擔對教師來說是必要的,并將教師負擔細分為生活、工作與心理三個方面的負擔。[2]狹義上的教師負擔主要聚焦于學校和職業層面,認為教師負擔是指教師在學校教育工作中承受與擔當的教育責任、教育工作與職業壓力以及由此而付出的代價等。[1][3]多位學者認同并在研究中沿用了這一界定。[4][5]
其二,主觀與客觀區分說。劉善槐等研究者認為,教師工作負擔的本質即教師的時間分配,以教師的工作時間與工作任務結構等客觀指標來量化教師負擔。[6]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教師在各項事務上分配的時間數量特征,二是時間配置中內容與結構的本質屬性及其表現特性。[7]一些學者則將教師負擔視為教師個體生理機制上的主觀感知,此類研究認為,教師負擔更多地體現為教師在面對工作任務和責任時,所體驗到的身心壓力、疲勞和緊張等主觀感受。[8]
其三,消極與中性區分說。即對教師負擔詞性的界定與理解存在分歧,存在消極和中性的區別。部分學者主張從消極層面定義教師負擔,將“教師工作負擔”界定為教師在教育教學過程中承受的與工作無關的、超出合理范圍和程度的,以及給教師身心帶來負面影響的教育責任、工作壓力和職業代價等。[3]也有學者更傾向于持中立態度看待“教師負擔”,將其視作中性的直觀描述,他們認為,“教師負擔”這一詞匯僅用于描述教師的工作量和壓力,其本身并不具備評價性質。[9]
其四,適度與失度區分說。這種區分以程度為界限,將中小學教師負擔具體分為適度負擔與失度負擔。[1]比如,龍寶新借助“是否應該”和“是否適量”兩個實然標準來對教師負擔進行判定,“是否應該”主要關注教師負擔的合理性問題,即教師是否應該承擔某項工作任務或壓力。而“是否適量”則主要關注教師負擔的適度性問題,即教師承擔的工作任務和壓力是否與其承受能力相匹配。[10]
綜合分析,諸多學者傾向于采用客觀和主觀兩個維度來定義教師負擔,并呈現主客觀相結合的趨勢,在考量教師負擔時,不僅關注教師工作時間、工作內容等客觀可量化的指標,還重視教師對負擔的主觀感受和認知。同時,在不同的語境中存在“工作負載”“工作過載”“教師壓力”“教師倦怠”等其他近似于“教師負擔”一詞的表述。[11]
二、中小學教師負擔的類型及其表征
(一)時間困境:工作生活失衡
研究者從社會時間結構的視角出發,對教師日常工作中的時間分配和負擔情況進行深入的分析和反思,提出文化時間的加速、制度時間的緊湊、互動時間的擴張以及自我時間的缺失,致使了教師陷入時間困境。[12]相關調查數據顯示,我國大多數教師的工作時間遠超8個小時,甚至有些教師的在校時間達到10小時以上。[7]而且,“雙減”政策正式落地后,學生在校時間有了明顯的延長,中小學教師的工作時間也被進一步拉長,特別是班主任、主科教師、骨干教師與學校管理干部。
[13]有研究者通過大規模隨機抽樣調查收集和分析數據發現,在“雙減”政策全面實施后,中小學教師每日的工作時長普遍超過法定標準,其中小學教師的工作時間超過10小時的比例約為1/4,初中教師則達到了1/2。[14]過長的工作時間及其形成的壓力,使教師面臨嚴峻的身心挑戰。
由于教師職業的特殊性,眾多職責往往超出正常工作時間范疇,教師需在下班后及周末繼續履行職責,將工作延續至個人生活中,教師的職業特性進一步延伸到了家庭場域中。[12]除了有形的工作內容之外,許多教師仍然需要在下班之后進行教育教學反思,與家長密切溝通并及時反饋學生的學習動態,解決各種問題等一系列隱形工作。[15]各類教學工作中所使用的群組、家長微信群以及班級群,要求教師保持“全天候在線”,[16]教師們工作時間長,壓力大,導致家庭溝通存在障礙,尤其在雙方均為教師的家庭,他們在家庭中的時間相對減少,無法充分陪伴家人、教育子女,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家庭成員之間的有效交流,甚至引發家庭矛盾。[9]
(二)角色異化:工作重心偏移
從現代教育制度的脈絡考察發現,教師職業的角色化、專業化和現代學校制度的建立是并行演進的過程,在“國家”“市場”和“專業”三種制度邏輯共同作用下,教師角色異化在所難免,[17]教師陷入“忙碌”“茫然”和“盲目”的狀態。[16]相關數據顯示,中小學教師實際用于教學的時間在總體工作時間中所占比例較低,教師超過50%的工作時間被用于完成各種非教育教學任務。[18]已有研究依托全國各省份的“減負清單”等形式的文本分析進行剖析,發現各省所要“減”的“負”更多的是非教育教學工作性質的負擔。[19]有研究者對國內的35份教師減負政策進行了深入剖析,發現行政工作的垂直下沉以及社會性事務的橫向擠入是導致教師角色發生異化的重要原因,在這一過程中,“社會事務分擔者”和“行政末梢承壓者”成為了教師身份的新標簽。[17]各類督查檢查、信息收集、填寫復雜的表格、提交各類報告、參與與教育無關的“投票點贊”等非教學任務繁多,致使教學反而成為了教師的“副業”。[20]
鑒于當前教師職責范疇尚未有明確的界定,社會各界對教師職業予以高度的期望。對教師的各種要求持續加碼,教師被期望成為各方面的專家。[21]教師在傳統觀念中的“園丁”“蠟燭”等角色基礎上,[16]進一步衍生出多種角色,如“行政工作者”“社會工作者”等角色,教師被迫成為“多角色教師”。[17]部分學生由于家庭原因遠離父母進入寄宿制學校就讀,在家庭教育缺位的情境下,教師則需要變身為學生的“學校父母”。[18]
在身兼數職的情況下,教師主要職責的時間和精力受到各類次要責任事務的侵蝕,致使職責邊界無限擴展。[13]教師教書育人的主體地位被剝奪,職責邊界逐漸模糊不清,工作內容逐漸被異化,且額外的付出與回報不相匹配,這導致教師群體心力交瘁,頻頻產生職業倦怠。[22]
(三)機制盲區:專業發展受限
新時代背景下,國家對教育質量的提升給予了高度重視,并相應地對教師的專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標準,而現實中,囿于源于學校內外部環境以及教師個人因素的制約,教師專業發展還存在一定障礙。比如,工作任務的增多、可支配時間的減少、工作與家庭失衡感的增強等問題均對教師的專業發展和工作動力產生了消極影響。[23]一方面,教師在承擔繁重的教育教學任務的同時,還需消耗大量的時間投入到非教育教學任務中,在教學與非教學任務雙重疊加的情況下,教師自主權被削弱,教師用于自我發展、教師之間交流學習的時間被嚴重擠壓,使得他們在應對教育教學任務時感到力不從心。[18]鄉村地區教師所面臨的專業發展困境更為突出,受地理位置偏遠、資源配置不均等因素的制約,教育教學條件相對滯后,進一步加劇了鄉村教師專業發展的困境。[24]另一方面,教育領域中教師激勵機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教師自我提升的內驅力,進而限制了教師追求專業發展的持續動力。在面臨高強度工作時,由于缺乏相應的福利待遇支持,教師的教學熱情逐漸被消磨殆盡。[15]部分教育工作者在履行職責過程中,出現自我效能感減退、情感耗竭及職業倦怠等現象,[22]對教育質量的提升及教師隊伍的穩定性構成了潛在威脅。
三、中小學教師負擔的多系統來源
教師職業的特殊性與復雜性決定了其負擔來源的多重性,綜合已有研究來看,以張雅靜為代表,將教師工作負擔的來源歸納為:“社”源性負擔、“校”源性負擔、“生”源性負擔和“師”源性負擔。[4]張家軍將教師負擔來源的主體總結為“政府”“社會”“學校”“家長”和“教師”。[18]布朗芬布倫納的生態系統理論認為,每個人都生活在由微觀到宏觀的多個系統之中,并強調各個系統的多元互動關系。[25]教師處于開放的系統之中,其負擔狀況受家長、社會、學校、政府等因素的共同影響。站在生態系統角度來看,中小學教師負擔緣起于教師個體層面微觀系統,包括如教師心理素質、教育教學能力和學科知識等主體性要素。學校作為中間系統,其管理方式與組織支持程度等構成了教師負擔生成的主導因素。家長和社會層面的外觀系統以及宏觀系統中的政策制度等構成了教師負擔的深層因素。
(一)宏觀系統:政府行政權力越界,任務缺乏整合
政府作為中小學教育的辦學者和直接管理者,掌握著實質性的教育行政權力。[26]部分政府部門將文明城市創建、城市創優評先、宣傳組織工作等任務攤派給學校和教師,直接增加了教師的負擔。[27]研究者依據各省份發布的教師減負清單提煉出文本中的高頻次關鍵詞并進行了量化統計,結果顯示,在所有減負清單中涉及的教師負擔來源主體中,政府部門占比高達73%,即教師非教育教學工作中來自政府部門的行政事務比例最高,政府部門將部分任務下沉到學校,最后攤派到教師身上,占用了教師原本應投入于教學和教育活動的正常工作時間。[19]
在各級政府行政管理過程中,形成的“條塊關系”常因部門間職責與權力界限的模糊性,引發功能重疊與交叉現象。[26]在此逐級下達、條塊分割的管理體系之下,行政條線壓力層層傳導,行政塊面任務多層加碼。[15]處于條線傳導末端的教師通常還需處理未經有效整合的任務,重復性的工作造成了中小學教師時間與精力的額外消耗。[6]各類檢查、考核評比的要求也是形形色色,標準不一。教師需要重復填寫各種報表,多次準備各種材料,這無疑給他們增加了沉重的負擔。
我國法律關于教師職責范圍的界定存在一定模糊性,未能為教師權益保障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致使教師職責邊界不夠清晰,眾多非義務性責任滲透至教師義務性工作領域,[13]增加了教師的工作負擔的同時,使得教師難以專注于教學工作,影響了教學質量和教師的職業發展。
(二)中間系統:學校價值導向偏離,組織支持薄弱
政府與公立學校是一種領導與被領導、管理與被管理的隸屬關系,同時表現出外部行政關系和內部行政關系的雙重性。[28]在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門的指導與監管下,學校自治權受到了合理限制,運作管理中存在上層依賴性和被動執行傾向,且缺乏主動性和積極性。[29]在與政府部分的博弈中往往處于被動地位,學校被迫遵循上級命令和任務指令,進而將之分配至教師團隊,這種唯上級命令的行動邏輯可能會導致教師負擔的進一步加劇。[19]
效益為導向的管理模式忽視了對教師團隊的人文關懷。學校之間的競爭轉化為對效益的追求,將學生學業成績與升學率作為衡量教師績效的核心指標,[15]教師考核體系過于注重量化、細化,無法全面考慮中小學教師所承擔的多樣化學科和繁重的工作任務。[14]有研究調查發現,我國中小學教師的工作強度存在總體水平偏高,工作內容隱性投入高的特點,而現有的績效考核存在主觀盲區,教師的隱性投入難以被準確衡量和認可,導致教師在職稱評定和績效考核中處于不利地位。[21]此種情況下,學校不僅未能有效營造一種寬松和諧、有利于教師專業發展的工作環境,反而使教師成為被管理者而非合作者。[30]
依據資源節約理論,個體在面對工作要求時,獲得相應的資源支持是確保其成功應對的關鍵必要條件。而當前學校對教師在專業發展過程中所依賴的資源投入和支持機制尚顯不足,限制了教師的專業成長進而阻礙了教師應對挑戰的能力的發展。[31]由于缺少有助于提升職業技能的學習資源及機會,教師在適應時代變革、更新教育理念和教學方法方面面臨著一定的挑戰和困難,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們在教學中應對各種問題的能力,從而增加了工作難度和負擔。[23]
(三)外觀系統:社會理性期待缺失,家長主體責任轉嫁
社會對教師職業的期望過高,教師被視為“多面能手”,[13]常常被迫處理各種超出職責范圍和能力范疇的社會事務。作為傳統觀念中的“圣人”,教師也理所應當肩負更多重任,面臨不斷提升的社會期待,教育工作者主動或無奈地陷入了一種“忙”的循環狀態。[32]另外,社會對人才培養的期待存在一定的扭曲和異化。在“唯學歷”的社會背景下,學校和教師不得不追求學生的學業成績,而當學生出現問題或者培養的人才不滿足社會要求時,公眾又會將責任歸咎于學校和教師。[18]
學校作為社區不可或缺的關鍵機構,肩負著特殊的社會管理職責。利用學校資源條件配合社區推進公益性和服務性工作的合作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各種社會事務涌入教師的日常工作中。[19]社區活動組織、公共服務等社會事務占據了教師原本用于教育教學與研究的時間,使其工作重心發生了偏移。[6]同時,部分社會輿論將個別極端現象泛化至整個教師隊伍,此類以偏概全的現象忽略了教師隊伍的整體素質和專業性,進而深化了社會對教師的誤解和不公平評價,[8]使教師在心理上承受巨大的壓力。
部分家長將本該自我承擔的責任被轉嫁到教師身上,把教育看作是購買行為,傾向于將孩子在教育過程中的大部分責任委托給學校和教師。[13]教育欠發達的鄉村和偏遠地區生源狀況復雜,單親家庭子女、留守兒童、隔代撫養兒童比例高,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席,教師在承擔學生的學習責任的同時,需要對他們的生活給予更多的關注,同時要對鄉村兒童進行即時的心理疏導和情感上的關懷。[33]
“雙減”政策的推行使校外培訓市場得到了強有力的監管,學生們從繁重的課外培訓中解脫出來,學業負擔得到了有效減輕,而家長的焦慮情緒卻在持續為中小學教師負擔加碼。[22]一方面,家長們普遍缺乏科學的教育觀念與專業的教育知識體系,過度以分數和升學率為評判教師的標準,從而削弱了教師的自信心。[12]另一方面,家長將教師減負等同于對學生關注的減少,權衡利益之下,更傾向于教師工作量的增加,而非關注如何為教師減負,[18]不僅打擊了教師的工作熱情,還對家校之間的順暢溝通與合作造成了障礙,無形中給教師增加了不必要的負擔。
(四)微觀系統:教師自我調控無力,專業能力有限
教師產生的負擔一定程度上是由外部客觀環境引起的主觀感受,自我調節能力的不足以及較低的承壓能力使得教師對負擔的主觀感知更為敏銳。[34]研究發現,自我調節能力是一種幫助鄉村教師在高強度工作要求下,保持積極心態、有效應對工作挑戰的重要心理資源,使他們能夠從認知上減輕工作負擔對自己的影響,以更加輕松、平和的心態去面對工作中的困難和挑戰。[33]
教師普遍缺乏應對繁重工作負擔的有效策略,在應對繁重的工作負擔時,往往缺乏系統而全面的指導與培訓。[16]部分教師由于經驗不足、專業素質較低以及教學能力有限,在面對現代教育中多種復雜的角色時,顯得力不從心,難以在多個角色中保持平衡。
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投入不足,專業發展受到制約。教師專業發展是教師從容應對各種教學壓力的基本路徑,而過多的教育教學任務和行政事務使教師在專業發展方面的投入時間嚴重不足,在專業發展方面難以取得新的突破。[6]同時,現有的教育體制和評價體系往往過于關注教師的在提高學生學業成績方面的成果,眾多教師將主要精力聚焦于提升教學成績之上,從而忽略了自身專業素養的提升,教師在處理各項事務方面能力不足,導致難以獲得成就感,自我效能感低,教師的心理壓力在不斷加大。[15]
四、系統聯動:中小學教師負擔調適路徑
針對上述問題,已有研究對教師負擔源頭的追問關涉宏觀、中觀、外觀和微觀多個系統與多重主體,為教師負擔的有效調適提供了依據。基于此,研究者提出中小學教師減負工作應沿著源頭精準減負、優化各層級系統的功能和互動關系,系統內外協作、多主體合力共治的路徑展開的建議。
(一)政策驅動:厘清職責界限
教師負擔過重的問題根源復雜多元,其中,政府部門權力的過度擴張以及行政事務的不合理分攤,是導致教師非教學性工作負擔的增加的直接原因,對此,應從政府宏觀層面出發,采取有效措施加強對教師權益的保障力度。
1.完善相關法律制度,明確教師職責范疇。
研究者建議應修訂相關法律制度,明確教師的職責界限與權力,賦予教師對與本職工作無關的事務說“不”的權力。[35]各地應結合實際出臺教師減負清單,將教師減負清單納入各級教育督導與監察體系之中,對于未能有效執行與落實相關政策的黨政機關及學校,進行嚴格的責任追究與問責。完善相關配套政策,合理設定教師工作時間和工作量的核定標準,構建科學明確、權責清晰的教師負擔管理體制。[36]同時,對各個部門的職能進行明確的劃分和界定,縱向上明確各個部門的職責范圍和權限,確保每個部門都能夠各司其職、各負其責;橫向上促進部門間的溝通和協作,實現信息的共享和資源的整合,建立高效運作的跨方式治理模式。[15]
2.優化資源配置,提升教師福利待遇。
保障教師資源的供給,尤其是鄉村地區,要確保人事編制、教師聘任及職稱晉升等方面合規達標。[37]同時,要提高教師薪酬待遇,加大對教師工資待遇的保障力度,確保教師待遇水平得到有效提升,使教師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與其工作付出相匹配,[38]這不僅是對教師辛勤付出的肯定和激勵,更是對教師職業尊嚴的尊重和保障,以提升教師職業吸引力,進而吸收更多優秀人才致力于教育事業的發展,讓教師成為幸福的職業。[21]
(二)優化管理:增強組織支撐力
教師負擔的有效調節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充分的組織支持,針對當前學校管理模式中存在的導致教師負擔不合理的因素,研究者建議從多個維度出發,探討如何構建更為人性化的管理體系。
1.實施人本化管理,營造良好環境。
在學校治理層面,要增強學校的辦學自主權,明確政府和行政部門與學校的權責關系,建立保障機制以確保權責一致,有效抵制行政和社會事務對教師時間的擠壓。[39]學校可根據實際情況推行“彈性上下班”制度,提高工作時間安排的靈活性,確保教師基本休息權益得以保障,給予教師充分的時間自主權。[40]
2.優化考核評價機制,釋放教師活力。
研究者建議制定全面兼顧教師職責之復雜性與特殊性的評價體系,確保評價體系能夠全面反映教師的實際表現。在制定評價指標時,既要關注教師的基本職責和核心使命,也要充分考慮教師個體的差異,制定具有針對性的評價標準。[41]并將評價結果作為教師選拔、任用、晉升、職稱評定等方面的重要依據,使優秀青年教師能夠脫穎而出,激發教師隊伍的整體活力。此外,還落實教師民主參與地位,充分吸收教師合理意見,賦予教師參與決策、管理等權力。[42]
3.完善資源匹配,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針對不同發展水平的教師,研究者建議制定個性化的發展方案,確保每位教師都能得到與其專業發展相匹配的資源和機會,以更高效地應對教育教學實踐中的挑戰。[15]針對教師面臨的“時間饑荒”問題,應優化教職工時間管理策略,以提升工作效率。[43]保障每位教師都享有公平的發展機會,讓他們能夠在專業成長的道路上暢通無阻,營造積極向上的學術氛圍。[23]
(三)凝聚共識:助推教師角色歸位
社會和家長對教師角色的期待往往過高,這導致教師需要承擔更多的壓力和責任。研究者建議,應該讓教師從過多的壓力和責任中解脫出來,社會和家長應共同努力,確立對教師角色的合理認知,協助教師回歸本質角色。
1.引領社會理性認知,彰顯社會輿論正面效應。
引導社會對教師角色建立合理預期,營造尊重、理解教師工作的良好社會風氣,使中小學教師獲得普遍的社會認同。深化對優秀教育工作者事跡的宣傳推廣,塑造教師隊伍的正面形象,增進社會對教師職業的認知與尊崇。[18]大眾傳媒應充分發揮宣傳引導作用,通過多樣化的途徑客觀真實地展示教師職業現實狀況,破除社會對教師隊伍的傳統固有認知,引領公眾正確理解教師工作及教師肩負的責任,并構建輿論監測與管控機制,從根本上阻止負面輿論的蔓延。[21]
2.轉變家長教育觀念,促進家校協同育人。
研究者建議,家長應當摒棄“分數至上”和“升學為王”的思維定式,應以更長遠的視角,全面關注學生在個人品德、學習能力、興趣愛好等多方面的進步和成長。[31]此外,家長應協助教師減輕壓力,為他們創造一個寬松的教育環境,從而助力學生全面和諧發展。另一方面,提高家長對教育責任的認知也至關重要。家長應認識到教育并非學校與教師單方面承擔的責任,而是需要家庭、學校和社會共同參與、協同努力的過程。[27]
(四)自我更新:深化自我專業成長
除諸多外源因素,如政府的宏觀政策、學校的管理模式、社會期望等對教師負擔的影響外,研究者建議教師個體亦需強化自我管理與規劃,以更好地應對各種工作挑戰和壓力,提升個人的職業幸福感。
1.變革自我觀念,增強自我效能。
教師需以正確的視角審視負擔,以客觀的態度評估自我負擔的程度。保持積極的心態予以接納,并主動探索有效的途徑以減輕過度和額外的負擔。[18]同時,教師要積極關注自身的心理健康,進行必要的心理層面的自我調適,學會應對工作壓力、調整情緒狀態、增強自我效能感,以及培養積極的生活和工作態度。[16]
2.加強專業學習,深化交流合作。
教師負擔過重的原因之一是專業能力的不足,教師應樹立終身學習的理念,不斷提高自身的專業能力和綜合素質,包括學習新的教育理念、掌握現代教育技術,以及不斷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學水平。[8]與此同時,需強化教師間的協作與交流,通過組織學科組或教研組,聚焦教育教學中的熱點與難點問題展開深入研究,以期形成集體智慧與共識,促進專業能力的提升。[22]
五、研究述評與啟示
我國學者對中小學教師負擔的研究已較為豐富且逐步深化。然而,現有研究在某些方面仍存在局限性。總體來說,教師負擔的研究呈現出以下特點。
在研究對象層面,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全體中小學教師負擔的影響、來源及治理,普遍采取整體性的研究視角,將中小學教師視為同質的群體,而對于小學和中學教師負擔情況的差異性、針對性研究尚顯不足。此外,鑒于農村和經濟欠發達地區處于教育資源配置的洼地,已引起不少研究者對農村或者經濟欠發達地區教師負擔情況的重視,相比之下,城市或經濟相對發達地區教師負擔的研究則有待進一步深入。后續的研究工作應當全面考量不同教育階段、不同教師群體以及不同地域背景下的教師負擔的異質性,以期尋求更具針對性的調和策略。
在研究范圍層面,既有研究已較為客觀、全面地勾勒了我國中小學教師負擔情況的整體樣態。而在“雙減”政策實施背景下,教師負擔情況呈現出一系列新的特質,關于“雙減”政策下教師負擔具體變化情況的的研究有待深入,還需通過實證研究的調查與分析來加以明確。同時,還需結合政策實施的具體情境,分析教師負擔現狀及變化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從而為中小學教師減負對策的調整和優化提供科學依據。
在研究方法層面,思辨、定量、定性等單一研究方法在現有研究中應用最為廣泛,如有學者以江蘇省某市23所中小學為樣本,通過電子問卷收集全員教師數據,以反映“雙減”背景下教師工作負擔與教學熱情的變化。亦有學者采用多案例抽樣方法,以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16名鄉村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半結構化訪談,以深入了解其工作負擔情況。總體而言,當前關于教師工作負擔的研究范式尚顯單一,缺乏深度與廣度的雙重拓展。未來研究需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整合并發揮多種研究方法的互補優勢,以深化對中小學教師負擔的混合研究。
在理論運用層面,近年來我國教師負擔的研究已經開始關注理論在其中的運用,如部分研究者運用“工作要求—資源”模型來探索教師工作負擔的本質、產生機理和重塑機制。同時,有學者運用風險管理理論探討了“雙減”政策下教師工作負擔的風險管理,提出了風險識別與化解策略。但整體而言,教師負擔研究的理論意識需進一步強化,未來的研究應更加注重理論的運用與深化,建立教師負擔研究的理論體系,為教師負擔問題的剖析提供更加全面的視角,以期對個體內生與外部環境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教師負擔的形成作出更適切的闡釋。
參考文獻:
[1]王毓珣,王穎.關于中小學教師減負的理性思索[J].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13,12(04):56-62.
[2]柳士彬,胡振京.論“減負”背景下教師負擔的減輕及其素質的提高[J].繼續教育研究,2002(01):64-66.
[3]黃志軍,劉冰欣,黃春花.英國新一輪中小學教師減負政策探析[J].外國教育研究,2020,47(08):70-87.
[4]張雅靜.中小學教師工作負擔的來源與排解[J].教育科學論壇,2019(04):59-64.
[5]付睿.論中小學教師減負[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9,21(02):13-16.
[6]朱秀紅,劉善槐.我國鄉村教師工作負擔的問題表征、不利影響與調適策略——基于全國18省35縣的調查研究[J].中國教育學刊,2020(01):88-94.
[7]王潔,寧波.國際視域下上海教師工作時間與工作負擔:基于TALIS數據的實證研究[J].教師教育研究,2018,30(06):81-88.
[8]宋洪鵬,郝保偉,魚霞.中小學教師不合理負擔表現、不利影響及應對策略——基于北京市的調查[J].教育科學研究,2021,(10):70-76.
[9]蔣帆.“雙減”背景下教師工作負擔與教學熱情的關系研究——基于身心健康的中介作用[J].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24,23(01):112-123.
[10]龍寶新,周莎.中小學教師工作負擔治理路徑研究[J].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05):64-74.
[11]鐘景迅,王迪.何以為負,如何測量——西方視野中的教師負擔概念辨析[J].比較教育研究,2023,45(05):30-41.
[12]張家軍,何心玥.教師負擔的社會時間結構分析及治理路徑[J].教育學術月刊,2023(07):11-18.
[13]王牧華,游婷婷.論中小學教師責任的泛化與修正路徑[J].中國教育科學(中英文),2023,6(03):123-134.
[14]趙平,胡詠梅.“雙減”背景下中小學教師減負:問題、成因與對策[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05):151-161.
[15]張家軍,閆君子.中小學教師負擔:減與增的辯證法[J].教育研究,2022,43(05):149-159.
[16]李躍雪,趙慧君.中小學教師工作負擔異化的生成邏輯與治理思路[J].教師教育研究,2020,32(03):67-72.
[17]董輝,劉許,張海蓉.教師的工作負擔、角色異化與減負治理[J].教師教育研究,2022,34(05):64-70.
[18]張家軍,曾照瑤.中小學教師負擔的表征、來源及治理[J].現代教育管理,2023(12):61-71.
[19]龍寶新,楊靜,蔡婉怡.中小學教師負擔的生成邏輯及其紓解之道——基于對全國27個省份中小學教師減負清單的分析[J].當代教育科學,2021(05):62-71.
[20]滿忠坤.莫讓上課成為教師的奢望[J].教育科學研究,2015(07):32-33.
[21]李廣,蓋闊.中小學教師工作強度調查[J].教育研究,2023,44(10):54-65.
[22]秦一銘,李廣.中小學教師工作強度的影響因素與調適策略——基于“雙減”背景[J].現代教育管理,2022(12):61-70.
[23]姚計海,張蒙.“雙減”政策下教師專業發展的機遇、問題與對策[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06):41-49.
[24]柏大鵬,程天君.鄉村教師緣何向城而教——基于空間社會學的視角[J].教育發展研究,2023,43(18):9-16.
[25]師海玲,范燕寧.社會生態系統理論闡釋下的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2004年查爾斯·扎斯特羅關于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的新探討[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04):94-97.
[26]宋萑,吳健健.我國中小學教師負擔生成機制的質性研究[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3,41(09):16-37.
[27]馮凱瑞.“雙減”政策下教師負擔的表現形式與治理路徑[J].教學與管理,2022(16):1-5.
[28]羅朝猛,胡勁松.變革社會中我國公立學校與政府關系的調諧[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9,29(07):22-26.
[29]楊小微,張秋霞.新時代我國基礎教育改革的難點與對策[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41(03):79-90+2.
[30]陳振華.中小學教師管理制度建設:問題與改進策略[J].教育研究,2015,36(09):99-103.
[31]張家軍,閆君子,韓碩.中小學教師負擔治理的效果測度與改進路徑[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49(05):163-175.
[32]王富偉,張森,謝珊等.穩態循環或惡性循環?——教師之忙的扎根理論研究[J].全球教育展望,2022,51(08):71-91.
[33]李瓊,林怡文,王清,等.“迎難而上”還是“消極逃避”:鄉村教師的工作負擔及其重塑機制研究[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3,41(09):38-55.
[34]殷竣曉,趙垣可.中小學教師工作負擔:概念、歸因與對策[J].江蘇教育,2019(78):30-33+37.
[35]李祥,周芳,蔡孝露.中小學教師減負政策的價值分析:權利保障的視角[J].現代教育管理,2021(07):62-69.
[36]張倩.從資源配置到制度安排——國際比較視域下的教師減負[J].教育研究,2022,43(02):29-43.
[37]趙英.當前我國農村學校教師編制、聘任和職稱研究述評[J].當代教師教育,2014,7(02):32-37.
[38]李新翠.中小學教師工作量的超負荷與有效調適[J].中國教育學刊,2016(02):56-60.
[39]張家軍,陳苗.中小學教師減負的系統分析與行動路徑[J].南京社會科學,2022(04):143-152.
[40]于川,楊麗樂.“雙減”政策背景下教師工作負擔的風險分析及其化解[J].當代教育論壇,2022(01):87-96.
[41]張迪.中小學教師負擔的多源分析及其緩解之道[J].教育導刊,2021(06):91-96.
[42]胥興春,左越,李星宇.“雙減”背景下教師工作負擔的現實表征、深層根源及減負路向——基于新浪微博43500條直接評論的剖析[J].教師教育研究,2023,35(06):68-75.
[43]樊秀麗,王志燕.教師減負:日本教師工作強度與工作時間制度的改革之路[J].比較教育研究,2023,45(03):3-14.
The Burde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MULTI-SYSTEM
SOURCES AND ADJUSTMENT PATHS
Zhao Ying , Feng Yan-zhi
( School of Education ,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 Taiyuan , Shanxi 030031)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in China have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 on various aspect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burden, including its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sources of burden, and governance path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 burden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 the dilemma of time, role alienation and mechanism blindness. TEACHERS' BURDEN ORIGINATES FROM THE \"MICRO SYSTEM\"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DOMINATED BY THE SCHOOL \"INTERMEDIATE SYSTEM\", AND UNDER THE DEEP INFLUENCE OF THE \"APPEARANCE SYSTEM\" AT THE PARENT AND SOCIAL LEVEL AND THE \"MACRO SYSTEM\" AT THE GOVERNMENT LEVEL. To manage teachers ' burden, it requires the joint efforts of ALL LEVELS OF SYSTEMS and relevant stakeholders to form a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tructure. In addition, there are still limitations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and subsequent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the burden of teacher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in different regions.
Keyword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eachers ' burden; burden-reduction(責任編校:周文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