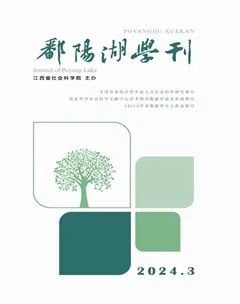新中國工業廢水治理的早期探索
[摘 要]1950年代末以東北工業基地、漢陽造紙廠和長壽化工廠為代表的典型廢水污染災害事件,嚴重影響周邊群眾生產生活,威脅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早期的工業廢水污染治理主要是從衛生與疾病防治的角度,探究河流水體對工業廢水的最大稀釋能力,找到工業廢水直排河道與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之間的平衡點。由于1950年代末開始的工業廢水污染治理探索,并非從水污染源頭解決問題,因而未能取得真正有效的成果,但為我國鍛煉和培養了一大批環境科學研究人員,為后來的環境污染研究與治理奠定了堅實的人才基礎。
[關鍵詞]新中國;工業廢水治理;典型水污染災害
隨著現代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速,水污染問題日益凸顯,它本質上是經濟發展帶來的問題。西方發達國家都曾經歷過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有過水污染的慘痛教訓,如1858年英國泰晤士河倫敦段發生的“大惡臭”事件,①1950年代日本相繼發生由水污染導致的“水俁病”、“痛痛病”等公害病。②近代以來,隨著國門被打開,西方工業逐漸引入,中國城市得以發展。民國初年,一些地方已經出現比較嚴重的水污染。如上海閘北自來水廠原本從恒豐路橋蘇州河取水,因蘇州河市區段嚴重污染,1928年被迫搬遷至楊浦軍工路,改從黃浦江下游取水。③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將工業發展作為立國之本,開始了大規模的工業化、城市化建設。特別是通過“一五”計劃,我國實際完成了150個重點工業項目,初步建成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打下了較好的工業基礎,特別是重工業基礎。然而,機器大工業不可避免會產生大量污染物,工業廢水往往包含大量有毒有害物質。早期由于對工業廢水的危害缺乏足夠的認知,將廢水直排河道,造成了水污染災害事件。
環境問題是史學界近些年研究的熱點之一。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時段不斷延伸,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新中國成立后的環境問題。目前史學界關于新中國環境史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區域污染史研究。河北師范大學張同樂教授關注新中國成立后河北相關環境污染問題,①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金大陸研究員對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上海的大氣、廢水、廢渣、城市綠化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②二是全國范圍內的工農業污染史研究。如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張連輝教授從經濟史角度切入新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系統研究了農藥、廢水灌田等工農業污染問題及城鄉之間的環境互動關系。③三是國家戰略與環境污染問題研究。如上海大學徐有威教授在研究小三線建設的過程中,發現其對當地環境影響極大,指出雖然在20世紀70年代國家意識到了相關環境污染問題,也開展了防治工作,但由于種種原因,防治效果并不理想。④這些成果為本文進一步探討新中國成立以來環境治理問題提供了借鑒與參考。
學界一般將1970年代初官廳水庫水污染事件作為新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的“起步”“先導”。⑤這是因為,受此次水污染災害的影響,我國開始了大規模的水污染調查與治理行動,并于1972年參加了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的第一次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接著在1973年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不過,在此之前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已經在多個領域顯現。本文以1950年代末三處重點工業項目,即東北工業基地、漢陽造紙廠和重慶長壽化工廠的廢水污染災害為典型案例,探討新中國初期黨和政府對工業廢水問題的認知與治理,以期為我國當前的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建設提供歷史經驗。
一、東北工業基地系列水污染災害及應對
(一)吉林工業基地工業廢水對松花江流域的污染
新中國成立后,根據“一五”計劃,東北大力發展重工業,其中吉林省很快形成以吉林、長春為中心的重工業基地,黑龍江省形成以齊齊哈爾為中心的重工業基地。“一五”期間實際建設的150項重點工程化學工業項目大部分集中在吉林、蘭州、太原三地,形成了新中國的三大化工基地。1957年,吉林化工區“三大化”即吉林氮肥廠、吉林染料廠、吉林電石廠相繼建成投產。①這是新中國化學工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人民日報》為此專門刊發題為《我們要建設強大的化學工業》的社論。②1958年,在吉林氮肥廠、吉林染料廠、吉林電石廠的基礎上組建了吉林化學工業公司,該公司是新中國第一個大型化學工業基地。③
黑龍江齊齊哈爾也集中了“一五”計劃重點工程中的三項成果,即富拉爾基熱電廠、北滿鋼廠和富拉爾基重型機器廠。富拉爾基熱電廠是新中國第一座高溫高壓熱電廠,1953年動工,1955年投產。北滿鋼廠是第一座特殊鋼廠,1954年動工,1957年投產。富拉爾基重型機器廠是新中國第一座重型機器廠,1956年動工,1958年基本建成,1960年6月全面投產,當年10月更名為第一重型機器廠。④
吉林化學工業公司下屬的吉林氮肥廠、吉林染料廠、吉林電石廠均在第二松花江畔(松花江主源),齊齊哈爾富拉爾基熱電廠、北滿鋼廠和富拉爾基重型機器廠均在嫩江邊(松花江最大支流)。當時有毒有害工業廢水直排河道,松花江流域的水環境日趨惡化,水污染災害自相關工廠投產之后就不斷發生。⑤這些災害最初表現為死魚事件和水污染中毒事件。
據調查資料,由于工業廢水直排河道,水體受到污染,造成魚類死亡,這樣的事件首先發生在嫩江干流。1957年冬至1958年春,齊齊哈爾江段捕到的江魚有15%是死魚,50%是處于昏迷狀況的半死魚。⑥嫩江的漁業損失慘重,富拉爾基區以下100公里江段漂浮著大量死魚。⑦自1958年開始,人們在食用嫩江捕撈的各種魚類時聞到較濃的汽油味或其他異味。如:1958年2月21日,杜蒙縣的喇嘛寺漁場從嫩江左岸捕撈大量銀繃和璽條等魚類,在齊齊哈爾市出售后,因有異味,有顧客將煮熟的魚退回水產商店;同年春,泰來縣水產公司在泰來當地銷售嫩江產的鯉魚、鱖魚、鰱魚等1850余公斤,在沈陽、本溪、北安、齊齊哈爾等地銷售20余萬公斤,都因發現有汽油味先后被拒絕接受或退貨,致使漁業生產和魚的銷售曾幾度發生停頓。①
受吉林工業廢水直排的影響,1958年后第二松花江每年都會發生水污染災害事件,特別是連年發生大規模的死魚災害。吉林市下游烏拉街一帶,1950年產魚200萬斤,1958年減至10萬斤。②1959年開江期,第二松花江吉林市至松花江村江段發生嚴重死魚事件。吉林至法特江段,兩岸死魚形成0.33米厚、2米寬的死魚帶,估計死魚約2000噸。1960年4月至6月,吉林省扶余至三岔河口50公里江段死魚量約1000噸,主要原因是酚污染。③據統計,自1958年至1985年,共出現近90起污染災害事件,其中較大規模的污染事件近50起,死魚事件33起,漁業損失額按每噸1217元不變價格計算,25年間漁業損失額高達9.69億元。④
除了死魚事件不斷發生之外,水污染災害還給沿岸居民飲用水造成困難。1958年4月,嫩江齊齊哈爾段水污染災害系松花江流域第一次大規模的水污染災害事故,造成下游居民飲水中毒。當時,齊齊哈爾鋼廠和富拉爾基第一重型機器廠大量集中向嫩江排放含酚和煤焦油廢水,廢水中酚含量高達2000毫克/升。排污口下游15公里江段江水呈黃色,致使齊齊哈爾市飲用水源中含酚量為0.5毫克/升,超過飲用水衛生標準250倍。齊齊哈爾市江火屯居民飲用江水后出現嘔吐、周身不適等輕度中毒癥狀。富拉爾基紅阿大隊64人飲用江水后出現惡心、嘔吐和貧血等癥狀,經檢查為煤焦油中毒。⑤
1950年代末,松花江流域的水污染災害除了造成漁業受損、供水受阻之外,還有一個嚴重污染災害正在萌發,即慢性汞中毒,只是當時還沒有表現出來。1957年,“一五”計劃重點項目吉林電石廠正式建成。1958年1月1日,吉林電石廠醋酸車間乙醛工段用硫酸汞作催化劑生產乙醛的裝置投產,未經處理的含汞和甲基汞廢水經東10號線凈下水道直排第二松花江,到1976年,經調查證實松花江畔漁民中已出現慢性水俁病患者。⑥
(二)黨和政府的應對
1950年代末,松花江流域嚴重污染事件造成驚人的漁業損失,并危及城市供水,引起黨和政府的重視,為此多次組織有關部門聯合調查。①1958年5月,衛生部和國家建設委員會在沈陽召開河流衛生保護及污水處理綜合利用的全國性會議,討論水源保護和污水處理等有關衛生問題。②
松花江流域的水資源保護工作起步于1959年。當年2月12日,黑龍江省人民委員會決定在省建設廳設立污水處理利用辦公室,啟動黑龍江省的水資源保護工作。但直到1973年的14年間,由于機構人員少、治理資金不足,加上治理技術尚在探索中等因素,水資源保護工作進展緩慢。③
1959年,水利部門的水化學監測化驗工作正式開始,由省水文總站負責,省水文總站下屬各地區水文分站負責水化學的采樣及化驗工作,主要是開展水的基本化學、物理性質的采樣化驗。1959年,松花江流域已建成水化學測站28處,不過大多屬于試驗、探索性質的測站,觀測成果不正規,最終刊入水化學資料年鑒的數據僅占實際檢測結果的一半。1960年至1973年,松花江流域的水質監測工作主要是在齊齊哈爾、哈爾濱、牡丹江和佳木斯4個城市開展了一些簡單的水質監測化驗項目,多是為了解水污染事故或進行水環境科學研究而進行的臨時性監測化驗。④
1960年,吉林和黑龍江開展了工業污染源調查工作。⑤1964年,黑龍江省在省建設廳設立了“三廢”處理利用辦公室,只是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工作處于混亂狀況。⑥不過,在政府相關部門的組織下,一些科研機構也參與其中。在松花江水污染災害造成魚類大量死亡事件上,首先參與污染調研的是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成立于1951年1月3日,它是在北平研究院動物學研究所、國立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國立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等藻類部門基礎上組建而成的,其主要任務包括水生生物資源調查,研究水生生物與環境的關系以及養殖與育種實驗等,目標是解決實際應用問題。⑦在1959年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匯報中,“工業污水對漁業的影響”是其研究領域之一。⑧
鑒于松花江流域是我國東北地區漁業重要產區,1959年、1960年,以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為主導,聯合吉林師范大學生物系、吉林醫科大學環境衛生系潘云舟和中央水產部長江水產研究所劉世英等,開展了松花江污染調查,開始了新中國第一個河流污染調查項目,即“第二松花江污染調查”,以及第一例嚴重水污染事件研究,即“嫩江干流毀滅性死魚原因調查與嫩江有機廢水污染控制研究”。①這是新中國最早開展的河流環境污染科學調查。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參加人員有:徐伯亥、姚繼忠、翟子玉、劉衢霞、謝翠嫻、徐家鑄、丘昌強、孫興湘、盧奮英、黃建超、賀錫勤、沈國華、劉世英、張甬元、席承容、惠嘉玉。②通過調查,調查組查明了松花江吉林市至扶余江段的污染狀況及其對水生生物的基本影響,提出了關于工業污水排放和保護水產資源的五點意見:
(1)排放廢水時,必須進行魚類48小時的試驗,肯定了排放的廢水稀釋到對魚類沒有急性中毒后,才可排入附近天然水域;
(2)目前吉林市的含酚廢水(從南大溝排出)、造紙(黑液)廢水、苯胺酸性廢水和苯胺堿性廢水等,需經過處理而達到相當1%(即1份廢水與99份清水)稀釋度后,才可直接排入第二松花江;
(3)在主要魚類產卵場所及其附近,禁止工業廢水尤其是毒性強烈的工業廢水排入,以保護魚類產卵場所的安全;
(4)開江后,禁止在魚類產卵場及其周圍捕撈,在其他江段也適當地禁捕親魚,使魚類能正常滋生繁殖;
(5)有關排放廢水企業單位和主管部門,加強與水產和衛生部門聯系,使排污工作能經常得到嚴格監督和管理,以防止不合標準的工業廢水直接排入江中。③
作為新中國最早開展的河流環境污染科學調查,此次調查活動無疑對我國工業廢水污染的治理與水產保護研究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使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成為中國環境科學的研究重鎮之一,鍛煉和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如參與調研的丘昌強,后來持續對工業廢水污染災害的防治進行研究,成為我國水環境污染及控制研究領域的重要專家。④
因松花江流域水污染災害威脅人民群眾的衛生健康安全,吉林醫科大學也參與了調研。自1960年2月至9月,吉林醫科大學衛生系馮玉珊、潘云舟等對第二松花江吉林市區段水污染情況進行了初步調查,他們通過對吉林市區沿江兩岸30個放流口的位置、型式和排水量、排水水質進行初步衛生學評價,指出江水主要的污染源是:吉林省造紙廠的黑液和洗漿廢水、吉林染料廠的化學污水、吉林熱電廠的水力排灰水、吉林電石廠的含酚污水、市內主要生活污水等。在豐滿至扶余江段,研究人員發現大部分污水中的有害物質經過一段流程的稀釋和自凈之后,濃度越來越低,直到完全消失;但也有某些芳香族硝基化合物、芳香族胺基化合物和酚類化合物在水中相當穩定,甚至經過270公里的流程之后尚能在江水中檢出,且含量不低。最后,調查組根據上述情況,向吉林市污水管理機構提出了水體衛生防護綜合措施方面的初步建議。①但受制于時代背景,調查組對工廠廢水的毒性仍缺乏足夠的認知,認為吉林省造紙廠、吉林染料廠、吉林熱電廠、吉林電石廠每晝夜排出120余萬立方米的廢水,“大部分是符合放流衛生條件的,并非像一般想像的那樣,多是有害污水”。②是故,調查組提出做好水體衛生防護的建議顯然沒能起到多大作用,因為隨后幾十年松花江流域的水污染問題越來越嚴重,但從科學研究的發展過程來講,它仍然具有推動意義,且促使潘云舟等人持續關注松花江污染問題。后來潘云舟成為松花江甲基汞污染(水俁病)研究的權威專家。③
二、漢陽造紙廠廢水污染災害及應對
(一)漢陽造紙廠廢水污染災害概況
湖北省漢陽造紙廠始建于1951年,1953年正式投產,是新中國成立后湖北省興建的第一個現代化地方國營工廠,主要以草類纖維原料進行制漿造紙,1956年產量為4.4萬噸,④是湖北省最大的造紙廠。漢陽造紙廠選址于長江北岸的漢陽沌口鎮,除了考慮到交通便利、節省征地搬遷費用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用水、排水方便。眾所周知,造紙工業是一個重污染行業,制漿造紙過程中會產生大量廢水,而且是高污染、高耗氧、難生化降解的有機廢水(黑液),特別是漢陽造紙廠這種以草料為原料的造紙廠。⑤當時漢陽造紙廠廢水直排長江,1956年擴建時設計流量為5.5萬噸/日。⑥據調查,1958年初實際每天排入長江的廢水約為8000~12000噸,⑦這只是初期的廢水排量。隨著漢陽造紙廠不斷擴建,用水量不斷增加,排放設施卻沒有增加,以致后來“下水管道充滿度達到飽和狀態”。制漿洗滌后產生的廢水因含有皂化物而產生泡沫,又因下水管充滿度高而無法流走,常從窨井蓋沖出,污染生產區,為此只好采取措施,將下水蓋子用螺栓固定,變自流排水為壓力排水,但只要蓋子四周填料稍有破綻,泡沫就會趁機而出,泛濫成災。為了維持生產,工廠只好將蒸煮、篩選等處下水改為排入一碼頭東荊河,生活污水排入萬家湖。⑧
受工藝技術限制,在1965年前,漢陽造紙廠的廢水未經任何處理直排長江,如此巨量的工業污水不可避免會對下游水環境產生影響,尤其是漢陽造紙廠距武漢市漢陽區中心只有13公里,⑨距武漢市中心也只有20余公里。①早在1957年,漢陽造紙廠附近水域已經發生了污染災害,廢水被周邊居民稱為“藥水”。據1958年的調查,該廠每日萬噸左右的廢水,顏色黑濁,外貌頗似醬油,自工廠排出后,由江岸斜坡直瀉入江,在斜坡面上會形成厚達數尺的淡黃色的泡沫;同時,由于造紙廢水溫度較高,出廠遇冷后蒸汽四溢,散發惡臭。衛生檢驗發現,總固體3264毫克/升,總固體燒灼減重2088毫克/升,總固體固定殘渣1176毫克/升,耗氧量1318毫克/升;溶解氧0.0毫克/升;生化需氧量745.0毫克/升。從以上指標來看,造紙廠的廢水非常臟。居民飲用水受廢水影響,味苦而澀,甚至動物也難以承受,有農民家養的豬因用污水喂養而死亡,是故居民稱此廢水為“藥水”。
造紙廠廢水排入長江以后,自排水口以下的江水色度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變得黃濁。同時,大量泡沫飄浮在江面上,一直到鸚鵡洲頭還可以觀察到泡沫的痕跡。根據漁民反映,在順風時這些泡沫還會飄至武昌岸邊。由于造紙廠廢水中含有較多有機固體物質,排入長江后,隨著距離的增加,這些固體物質逐漸下沉到時江底。這些有機物質不穩定,會發生化學反應,不斷消耗水中的溶解氧,影響江水的水質。在漢陽造紙廠廢水排出口下約100米,距岸約10米處,江底沉積固體有機物的厚度為0.5米。在排出口下游300米處,約為0.2 米。這些沉積物的生化需氧量約為0.24毫克/克·日。雖然一般離江左岸(即污水排出岸)約300米以外沒有造紙廠廢水痕跡,但從下游來看,一直到漢水入江處還可以檢查到廢水污染的跡象。
綜合以上事實來看,沌口造紙廠廢水對長江水質的污染相當嚴重,雖然長江水流量很大,但是由于污水是靠近岸邊流動,不易向江心擴散,因而污染的距離很長。②
(二)黨和政府的應對
造紙工業廢水黑臭、有泡沫,其污染性人人都可以感知到。針對漢陽造紙廠的廢水污染,工廠付諸了一定努力進行改良,黨和政府后來也展開了調研工作。
一是進行黑液回收。早在1956年,漢陽造紙廠在擴建日產100噸凸版紙工程時,便設計了我國第一個草漿黑液堿回收車間,希望減輕造紙廢水對長江的污染,但該車間直到1959年11月才破土動工,1965年正式投入生產。堿回收車間的主要目的是“變廢為寶”,“使貴重的化學藥品得到再生利用”,同時“化害為利”“減輕對江水的污染”,但由于提取黑液的設備不完善等原因,1965年投產后不久就停止運行。1981年重新運行,但由于龍須草黑液提取工藝不達標,到1991年底也只是對荻葦黑液進行了堿回收。故黑液回收效果有限。漢陽造紙廠仍然一直向長江排放大量廢水及廢渣,是“武漢市污染大戶”,1980年代多次被湖北省、武漢市列為限期治理單位。③
二是開展長江武漢段水污染與自凈的調查。1957年,中央衛生部科學研究委員會指定武漢醫學院衛生系、江蘇省南京市衛生防疫站等單位,分別在武漢、南京段進行長江水污染與自凈方面的研究。長江武漢段水污染與自凈的調查由武漢醫學院衛生系蔡宏道教授負責。①蔡宏道是我國著名臨床檢驗學家、環境衛生學家、醫學教育學家,被譽為新中國預防醫學第一人,為我國的預防醫學特別是環境醫學的興建與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②
根據中央指示,自1957年10月至1958年9月,蔡宏道帶領相關人員,在長江武漢段進行衛生狀況的調查研究,工作內容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摸清長江武漢段水質變化的規律;二是研究工業廢水、城市污水、支流染污對長江水質的影響;三是進行長江水體稀釋能力的實驗探討。
蔡宏道的工作方法是進行系統的水質衛生分析,結合必要的環境衛生調查:在水質衛生分析方面,根據研究任務,選定采樣地點,定期進行衛生檢驗;在環境衛生調查方面,主要目標放在兩岸污水排出口的調查和污水分析上。通過近一年的調查,他們指出漢陽造紙廠在一定范圍內造成了長江武漢段較嚴重的污染,得出以下四點結論:
(1)長江武漢段的水質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在市區較明顯。但由于長江水量很大,稀釋能力高,故水質污染情況,從數字上看還不大顯著。岸邊的水質較江心差一些,漲水季節較枯水季節為差,這可能是由于雨水將岸邊污物沖入江內之故。
(2)沌口造紙廠(即漢陽造紙廠)廢水對江水的污染比較嚴重,一直到漢水入江處附近的江水中還可以發現污染的痕跡。黃浦路污水在枯水季節,對沿岸江水有一些污染作用,但在漲水季節沒有顯著的污染痕跡。
(3)長江水稀釋能力的特點是:江心的水不容易分流到岸邊來,而靠岸邊的水又不易向江心擴散,故一般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對江水的污染主要是在離岸200—300米的范圍以內。
(4)用泡沫法探測漢陽造紙廠廢水對江水的污染,是一種快速而經濟的方法。如何利用造紙廠廢水,較精確的測定江水的稀釋能力,將進一步進行深入的研究。③
1959年,衛生部頒布實施《生活飲用水衛生規程》。1960年12月,衛生部和國家建設委員會分別在沈陽及武漢召開有關河流衛生保護及污水處理綜合利用等全國性會議,討論關于水源保護及污水處理等有關衛生問題。1963年又頒布了“工業企業設計衛生標準”,規定了污水排入地面水的衛生規則。④這些規章制度的頒布實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工業廢水的早期治理。1963年1月,為了弄清長江稀釋污水的能力,湖北省衛生防疫站對武昌積玉橋抽井站污水由岸邊排入長江后的擴散情況進行了10次調查。⑤
三、重慶長壽化工廠氯丁廢水污染災害及應對
(一)重慶長壽化工廠氯丁廢水污染災害概況
橡膠作為重工業和生活產品的重要原料,廣泛應用于各個領域。早期只有天然橡膠,來源于橡膠樹。橡膠樹生長在熱帶地區,中國自1904年從巴西引種后,直到1949年種植面積和產量仍十分有限,年產量僅為199噸。朝鮮戰爭爆發后,部分西方國家對我國實行天然橡膠禁運。①面對嚴峻的形勢,除了建立自己的天然橡膠基地之外,開發合成橡膠成為解決橡膠來源問題的重要途徑。
1951年,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在實驗室中成功合成氯丁橡膠。1958年底,化工部工業設計院根據積累的經驗和蘇聯專家的指導意見,在重慶長壽化工廠建成了2000噸/年氯丁橡膠生產裝置,生產出國內第一批合成氯丁橡膠。②
隨著國民經濟與國防建設的需要,我國的氯丁橡膠工業生產日益擴大,排出的廢水也相應增多。氯丁廢水一般為棕褐色,有時為乳白色,含有大量的有機化合物、無機鹽、氯化物,具有較強的毒性和強烈的刺激臭味,污水表面常漂浮高巨物,有易燃性、粘結性及不溶于水等特點。③這種廢水不僅污染水體,而且有毒氣體還會沿途揮發,污染大氣。④
重慶長壽化工廠作為國內第一家生產合成氯丁橡膠的重要化工廠,鄰近長江,長期以來是重慶的工業廢水排放大戶。在1985年重慶的重點污染源企業名單中就有長壽化工廠,年廢水排放總量為725.3萬噸。⑤
(二)黨和政府的應對
長壽化工廠廢水給沿江人民健康和工農業用水帶來了嚴重危害。1960年初,國家下達了一項科研任務,即“氯丁橡膠廠工業廢水中七種有害物質在地面水中最高容許濃度的研究”,⑥要求確定長壽化工廠“廢水中氯丁二烯、乙醛、二乙烯基乙炔、乙烯基乙炔、乙炔、過硫酸鉀、二硫化四乙基秋蘭姆等七種有害物質在地面水中的最高容許濃度”。⑦承擔該任務的主要負責人是原四川醫學院的過基同⑧、詹承烈①兩位教授。1963年,過基同與詹承烈接到國家任務后,帶領四川醫學院藥學系和病理解剖教研組,與長壽化工廠及有關單位開展上述課題研究,②目的是確定氯丁廢水中各種有害物質在地面水中的最高容許濃度,從而為該類工業廢水的利用和處理及地面水的衛生防護措施提供科學依據。
過基同、詹承烈等人的研究是開創性的。當時,關于氯丁廢水中的7種有害物質,除氯丁二烯的最高容許濃度曾有國外研究報道之外,其余六種尚無衛生標準。自1963年底開始,過基同、詹承烈等人邊干邊學,不斷摸索與總結經驗,在將近3年的時間里,對上述各物質進行了以下四個方面的研究:一是研究各種有害物質在水中的穩定性;二是研究氯丁廢水對地面水感觀性狀的影響,以確定其嗅和味的感覺閾濃度(一級強度)和實際限度(二級強度);三是研究氯丁廢水對地面水一般衛生狀況(自凈過程)的影響,在實驗室條件下觀察不同濃度的物質對水生化需氧量、溶解氧及細菌生長情況等的影響,以確定能抑制生化耗氧過程的濃度,作為對地面水一般衛生狀況影響的閾濃度;四是研究氯丁廢水對機體的直接毒害作用,使用動物做急、慢性中毒實驗(包括以不同濃度的毒物溶液對實驗動物進行灌胃后,觀察它們在防御條件反射、血液常規、酶活性、病理形態等方面的變化),以確定其對機體慢性毒作用的閾下濃度。
根據多年試驗研究,過基同、詹承烈調查組按濃度最低的有害作用指標(即有害作用限制指標——根據毒作用、感觀性狀或一般衛生的最低限制濃度確定),并參照該廠廢水排放的實際情況,提出了前述7種有害物質在地面水中最高容許濃度的初步數據及建議標準,供實際處理該類工業廢水時參考。③該項研究成果后來獲得了全國科學大會獎。④
結 語
綜上所述,新中國的水污染問題與工業化相伴相生。隨著“一五”計劃的完成,我國基本建立了社會主義工業體系,特別是重工業體系。大規模工業化不可避免會產生大量有毒有害的工業廢水,特別是集中布局的重工業廢水排放問題,亟待解決。早期工業廢水都是直排河道,而河道往往又是當地人民的飲用水源、漁業產地。大量有毒有害的工業廢水直排河道,很快造成一些地區發生嚴重的水污染災害,影響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威脅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
針對各地不斷出現的水污染災害,黨和政府積極行動,安排發動科研人員和機構,特別是給水排水學界、醫學界、生物學界,開展工業廢水污染的調查與治理研究。但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從疾病防治的角度,分析河流水體對工業廢水的最大稀釋能力,從而找到工業廢水直排河道與保障人民身體健康的平衡點,還不能稱之為水污染源頭治理。污水處理專家湯鴻霄院士指出,這一時段我國環境科學與技術領域尚處于形成的開端,實際上以給水工程為主要內容,污水處理及污泥利用還處于起始狀態。①
具體說來,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在水污染調查治理過程中主要考慮的是工業廢水的利用和水體的自凈能力,從而為最大限度排污提供科學依據,水體稀釋能力、污水灌田的研究由此產生。這種污水處理方式與思路實際上是把水體、土壤完全當成納污場所,這一思路的長期延續,在1980年代之后造成我國大面積的水污染和土壤污染。
不過,這是受時代發展理念限制。前文已述,當時水污染問題遠非中國獨有,1950年代日本發生了一系列由水污染引起的公害病。工業發展與環境污染是一對矛盾體,我國對環境污染的認知是一個逐漸加深的過程,西方發達國家也是到1980年代才基本解決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1950年代末,我國不斷出現的工業廢水污染災害事件,使黨和政府意識到社會主義中國實際上也存在水污染問題。相關科研機構和人員被調動起來,開展水污染調查和治理的相關研究,這為新中國鍛煉和培養了第一批環境污染科學科研人員,其中有很多人日后成為中國環境科學研究的骨干力量,如前述丘昌強、馮玉珊、潘云舟、蔡宏道、過基同、詹承烈等人。新中國早期的工業廢水治理探索實踐,為我國后來的環境污染研究與治理奠定了堅實的人才基礎。
責任編輯:徐 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