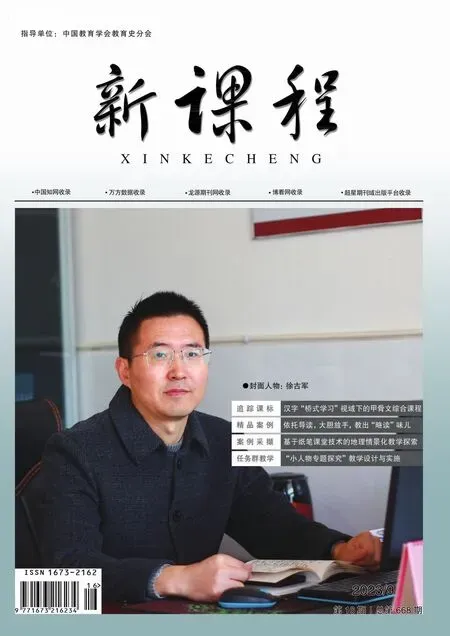漢字“橋式學習”視域下的甲骨文綜合課程
——以“人、大”教學為例
文|張 明
語言和文字是人類社會最偉大的系統工程之一,它是人類一切文明的基石。在當前的語文教學中,小學生學習漢字大多是機械拆解漢字為單獨的筆畫或者偏旁,采用死記硬背、重復抄寫的方式識記,學生學習非常枯燥且十分吃力。有部分電腦實驗班直接把漢字教學拼音化,學生只是學習拼音識讀,能通過電腦打出字形詞組,具體字源意思不清楚,漢字有拼音化的傾向。還有部分教師在實際教學中存在隨意拆解,是非無正、巧說邪辭的現象。
新時代背景下,學校教育要符合全方位融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要求,學習和了解中華文化的基因,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理應從基礎教育教學開始普及。應用甲骨文一脈相承的文字初始特征、文化融合特征和藝術創造特征,在小學教育中找到一個適合小學生學習漢字的契合點,創設一種他們樂于接受的教學形式,整合多學科內容,探索和學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一直探索的方向。
王鵬偉教授提出的“基于漢字的橋式學習”主張為我指明了方向。所謂“橋式學習”,是指從一個已知知識點或一個具體問題出發,向未知目標領域探索,建立通向未知領域的橋梁。
橋式學習有如下特點:首先,從一個知識點或一個具體問題展開,形成一個開放系統。其次,在已知領域和未知領域之間搭建一座橋梁,引導學生探究。最后,在探究過程中產生新問題,從而導向更加廣泛的未知領域。其基本思路是以漢字構形為橋,解讀漢字;以漢字為橋,解讀古代文化。
甲骨文具有字體的形象性、文字的延展性、圖形的識別性和人文的精神性等特征。其本身就具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綜合體的屬性,以此為橋式學習的內容,通過水墨的表現形式在學生心目中構建通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橋梁,讓學生認識漢字——“我是誰?”“我從哪里來?”“將到哪里去?”領會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歷史傳承具有重要的意義。
以我設計的甲骨文綜合課程“人、大”一課為例,談甲骨文綜合課程“橋式學習”的實踐運用。
一、依據甲骨文字體的形象性架設理解字義之橋
甲骨文作為最早成系統的文字,源于原始的近乎圖畫的符號,象形成分相當重,保留了30%以上的象形字。孫詒讓在《名原》中提出文字“本于圖像”。象形作為一種造字方法,東漢許慎說“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如“日”“月”“水”“火”“山”“川”“馬”,等等。課堂中我們以甲骨文字為橋,從象形字的造字方法入手,讓學生表現出這個字的形象,既形象又生動,學生浸潤其中,過程體驗中深刻領會到其中的要義。
二、依據甲骨文造字的延展性架設字理探索和字族拓展之橋
甲骨文字體的延展性有兩個方面。一是從一個字最基本的字形延展出其他字義的甲骨文,學生從一個最基本的漢字拓展出與之關聯的很多漢字。
字形與“從”相似但是位置不一樣,“從”字是前后關系,“比”字是左右關系,像兩個人并肩而行。“化”

由人字引申出有關人或人體以及人造之物的象形字有很多。與人有關的直接是人體的器官,如口、齒、舌、眉、目、自、首等,還有表示各種人的名稱如人、兒等,不一一列舉。現代簡化漢字講授中,人們很少把“大”與“人”聯系起來理解,而在甲骨文體系當中,它們都屬于“人”組系統內的。下面就具體介紹一下甲骨文“大”,以及由“大”引申出來的漢字:“大”()表示正面站立的人,由“大”引申出“夫”:甲骨文“夫”()在“大”()的頭部加一橫指事符號(),代表發簪,造字本義指成年男子束發,并用發簪固定。

漢字另一個方面的延展性是指漢字從甲骨文經歷金文、篆書、隸書、草書、楷書,后來逐漸發展到現在使用的簡體楷書,其中的變化是以甲骨文為基因。后來,基于甲骨文的演變,尤其作為形旁表義演變出許多形聲字,如人字轉變為單人旁的付、代、儀、仟、仗、他、仔、仡、仙、們等,人字頭的令、傘、佘、介、命、倉、企等,由大字轉變為偏旁后出現的夸、奔、奮、奇、奈、奄、獎、奎、契、奕等。我們可以由此編輯出漢字樹,讓學生探索出與之相關聯的更多漢字。這樣的學習,教師只是提供了一把打開漢字大門的鑰匙,搭建了一座古今鏈接的橋梁,讓漢字學習具有探究性和發散性,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欲望,變被動學習為主動學習。
三、依據甲骨文圖像的具象性架設漢字綜合藝術之橋
文字的起源“進取諸身,遠取諸物”,先人對自身的認識也很深刻,被加入文字的創造中命題,借用人的身體的文字,或者象形,或者指事,或者會意。同樣是一個人的身體的形態,不同的姿態或不同的位置表示不同的含義。側影是“人”,正面是“大”;從人的具象到甲骨文的抽象可以找到清晰的脈絡和線索。
從心理學理論上說,小學生思維發展的基本特點是從具體形象思維逐步過渡到抽象邏輯思維,但是這種抽象邏輯思維仍然是與感性經驗相聯系的,具有具體性和形象性。基于漢字的橋式學習模式中甲骨文綜合課程教學正契合小學生思維發展的特點。研究發現,4~12 歲的孩子喜歡畫畫,畫畫屬于圖像思維,結合甲骨文“因形賦義”的特點,甲骨文恰好具備圖像思維的特點,我們結合中國水墨畫表現形式和特點,在甲骨文形象的基礎上發揮想象并借助水墨畫的意象特點,能充分激發學生學習中華文化的興趣,提高思維水平,從而提高審美素養。
具體來說,在實際教學過程中一般分為以下幾個環節:圖片展示—甲骨文啟迪智慧—古今文字傳承比較—漢字樹形拓展—畫前討論編故事—畫中穿插水墨技法—畫后故事分享點評作品。如在筆者自編的甲骨文綜合課程第一模塊“人”字系列第一課學習“人”和“大”,首先學習甲骨文“人”和“大”字形及來源以及由它們衍生出來的甲骨文字,然后輔導學生運用學習過的這些甲骨文字編出一個故事,再用水墨畫形式把這個故事創作出來后跟大家分享。在創作中融入水—墨—畫的教學技法技巧,增強教學的趣味性和創意性,同時又體現出書畫同源的精神內涵。這種綜合課程學習形式深受學生喜愛、家長認可和專家的鼓勵。
四、依據甲骨文的文化內涵架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橋
從教育學理論上說,在小學,任何學科教學都提倡直觀性原則,甲骨文綜合課程教學借鑒了直觀性教學原則的理論精髓,充分利用小學生的觀察力和想象力,為學生直觀呈現漢字的組構規律,深入淺出,一節課一個(組)漢字就是一次文化活動,一次美的熏陶。
陳寅恪有一句反復被人征引的名言:“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我們不能把漢字割裂開來分析,需要綜合和整體的認識。基于漢字的橋式學習,教師在講解漢字時需要厘清漢字的源頭和文化含義,把一個個漢字講活,漢字才不至于僅僅成為語言交際的“工具”,而是具有人文性、審美性的符號。這種學習在學生的頭腦里會留下深刻的烙印,為以后了解和學習中國人文歷史以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打下堅實的基礎。
如在學習甲骨文綜合課程“人、大”一課中,教師結合魯迅設計的北京大學的校徽,讓學生理解“北大”兩個甲骨文的上下排列,其中“北”字構成背對背的兩個側立的人像,而“大”字構成了一個正面站立的人像。校徽要突出“以人為本”的理念,象征北大肩負開啟民智的重大使命。講述章葉青設計的中國人民大學校徽以三個并列的甲骨文“人”字圖形為基礎,其中“人民、人本、人文”的寓意深刻。
漢字作為古老而富有生命力的文字,早已成了五千年中華文明的重要元素。英國語言學家帕默爾說:“漢字是中國通用的唯一的交際工具,唯其如此,它是中國文化的脊梁。”根植于漢字書寫,以漢字獨特形體而成就的書法藝術,受豐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滋養,積淀成了中華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人文標識之一,成為彰顯民族精神、展示民族品格的典型代表,在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過程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甲骨文綜合課程“人、大”這一課僅僅是一個引子,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基于漢字的橋式學習將改變漢字教育的課程形態,作為一名基礎教育工作者,我們的使命是在啟蒙教育伊始,就將這把鑰匙交給未來的中國公民,讓他們去開啟中華文化的寶庫,窺探漢字文化的奧秘,傳承中華文化的火炬。通過甲骨文學習,讓漢字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延續發展,讓中華文明在國際舞臺上永放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