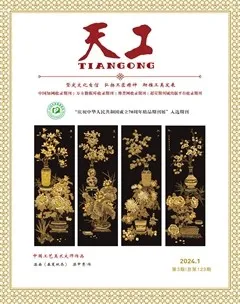淺析《馬踏匈奴》的藝術特質與風格源流
[摘 要]《馬踏匈奴》是漢代雕塑乃至中國古代藝術的瑰寶之一。從歷史文化背景、藝術風格與藝術精神、風格成因等方面對《馬踏匈奴》這件石雕作品進行簡要分析,對比其他朝代與地區的雕塑作品,乃至于繪畫的風格,觸類旁通,旁征博引。由此對整個漢代石刻藝術的特征及藝術精神進行梳理和總結,從而使今人更好地理解與借鑒漢代的藝術本質,汲取中國傳統藝術的精髓。
[關鍵詞]《馬踏匈奴》;風格;藝術
[中圖分類號]J32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7556(2024)3-0006-03
本文文獻著錄格式:趙金.淺析《馬踏匈奴》的藝術特質與風格源流[J].天工,2024(3):6-8.
《馬踏匈奴》是霍去病墓中最有代表性、最經典的石雕,也是我國幾千年來雕塑作品的精華之一。同時,它也是漢代寫意浪漫、雄渾魄大的整體藝術風格的代表作品之一。《馬踏匈奴》不僅在造型、技法上體現了漢代石雕的藝術追求,更在思想內涵、精神追求上揭示了漢代人開拓進取的精神品質,這也是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所流傳下來的寶貴精神財富。因而,研究《馬踏匈奴》的藝術特征與藝術精神,對于研究中國古代藝術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更深層面,思考與研究《馬踏匈奴》及霍去病墓石雕的風格成因,對研究中國漢代文明與域外文明的關系也有著參考作用,對未來提出更深入的學術觀點也具有重大理論意義。
一、《馬踏匈奴》誕生的歷史文化背景
漢王朝是中國封建歷史上歷時最長的王朝。漢代的造型藝術品也燦若星辰。尤其是漢武帝時期,國家經歷了幾十年的休養生息之后,國富民強。漢武帝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仁”是儒家學說的根本范疇,孝悌則是“仁”的根本,喪葬就成了孝悌觀念的表現形式之一①。于是,在漢武帝的推動之下,厚葬之風大興。伴隨墓葬而產生的藝術品也開始大量出現。而漢武帝又是一位擁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他平定了匈奴,打通了絲綢之路,在他的治理下,國家空前的繁榮昌盛。因而,這一時期包括之后的漢代墓葬藝術也是中國藝術史上最為包容、浪漫和雄渾的篇章之一。它一改秦代的寫實手法和漢初的肅穆氣息,體現了生動奔放、肆意浪漫、整體氣象闊大深沉的精神特質。霍去病墓的16尊石雕正是誕生于這個偉大的時代。而《馬踏匈奴》是其中的典范。
提到霍去病墓石雕,就不得不提這座墓的主人——霍去病。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歷史上,作為臣子,能在死后陪葬在帝王陵墓旁邊的人屈指可數,霍去病就是其中之一。他之所以能得到漢武帝如此喜愛,是由于他在短暫的一生中,率軍四次擊敗匈奴,將匈奴人趕出漠北,掃除了漢代近一個世紀來自北方的邊患。從此,漢朝控制了河西地區,打通了西域道路。可以說,霍去病不僅為漢朝的穩固與繁榮立下了不世之功,更對中國建立多民族國家、促進中國與中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這樣一位曠世奇才卻英年早逝,長眠于大漠邊陲。漢武帝為了紀念霍去病的偉大功績,調發屬國鐵甲軍,列隊從長安直到茂陵,破格厚葬霍去病,特賜霍去病陪葬茂陵,并下令“為冢象祁連山”。在墓的周圍,漢武帝沒有選擇為他打造雄壯的軍隊,或者為他塑造偉岸的雕像,而是選擇雕刻了14尊牛、馬、象等北方的野獸環繞在墓的周圍,以此象征將軍浴血奮戰,并為國捐軀的那片大漠戰場、曠野深山。這種以一當十、借物喻人的表現手法,既有別于秦始皇兵馬俑的宏偉軍陣,也不同于古希臘、古羅馬的英雄雕像,別開生面,讓人回味無窮。
這組雕像的核心就是《馬踏匈奴》。中國歷史上的雕塑很多是從動物的形象出發的,以動物的形象來表現人的精神。這一點有別于西方的以表現人體為中心的雕塑風格。“馬是所有獸類中最接近人性的動物,實在有資格代表漢朝蓬勃蔥蘢的帝國自信和思游萬仞的人的理想。”①并且,在冷兵器時代,馬更是攻城略地、沖鋒陷陣不可或缺的“戰爭武器”。在中國的雕塑史上,馬往往充當了建功立業者的紀念形象,如唐代的《昭陵六駿》,東漢的《馬踏飛燕》等。因而,在霍去病墓室石雕中,最核心的就是《馬踏匈奴》《躍馬》和《臥馬》了。這三匹“馬”不僅代表了戰爭的三個階段,更象征了奮勇殺敵的三軍將士。而其中《馬踏匈奴》中那匹嘶鳴的戰馬更是霍去病的化身,是他取得的赫赫戰功的寫照。
二、《馬踏匈奴》的藝術風格與藝術精神
《馬踏匈奴》之所以是漢代雕塑的經典,是中國藝術的瑰寶,并不在于它具備多么高超的雕刻技巧、多么精湛的寫實功夫。相反,在有些人看來,這尊雕像既不出彩,也不美觀,甚至極為平常,不足為奇。可正是這種平實、自然、不雕琢構成了這尊雕像以至于所有霍去病墓石雕的最寶貴的藝術精神。這不禁讓筆者想到了雕塑大師米開朗基羅的一句名言,他說,“雕塑應該是從高山上滾落下來也摔不碎的實體”。②細細品味這句話,筆者覺得可以成為一切藝術的評判標準。藝術是什么,藝術不是無限地模仿現實,不是無限地添加細節。藝術是整體,是感受,是自然的提純。不論是雕塑,還是繪畫,真正好的作品是天然的、不做作的、寫意的。《馬踏匈奴》就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它是自然天成的,仿佛是大自然鬼斧神工地隨意雕刻,卻恰到好處。整座雕塑渾然一體,有虛有實,有松有緊。在馬的處理上,馬的軀體采用圓雕的方法,使其具備大的形態;馬頭則用浮雕與線雕的技法,將細節刻畫得具體、生動,將戰馬那種經過一場激戰后精神百倍、氣宇軒昂的神情和體態雕鑿了出來;而馬腿以及馬蹄之下的匈奴人,則更多地使用淺雕與線刻的方法,處理得大膽、寫意,卻也將戰敗者哀號求饒、狼狽不堪的慘狀刻畫了出來,從而形成了上下、主次的對比,將戰馬勝利后的昂然與匈奴人失敗后的凄慘表現得淋漓盡致。
《馬踏匈奴》以及霍去病墓其他的石雕最讓人震撼之處就在于它整體的氣勢,就像米開朗基羅指出的“摔也摔不碎”。雕塑就是要施予被雕刻物體以生命力,將生命從材料中解放出來。《馬踏匈奴》正是這樣一件作品。雕刻者不是與石料做斗爭,而是因材施雕,保持了對材料的充分尊重,通過粗放古拙的線條與簡練的刀法,賦予頑石以生命。雕刻家去掉了一切可能擾亂體積的細節,只抓馬的大特征,抓大結構。至于馬蹄下的匈奴人,干脆與馬的軀體連為一體,就著整塊石頭的勢,只做線條上的處理。而正是這種連為一體、不做透雕的手法,使雕像看上去穩如泰山,更加渾然一體,空間利用也更加合理。
《馬踏匈奴》這種高度概括、大氣磅礴的氣勢既是霍去病墓雕刻的特征,也是整個漢代雕塑藝術的精神品質。雕塑,本身就是物質化的強大的生命的寓言,本質上應該是排斥陰柔文弱的。漢代雕塑的這種精神氣質既不同于先秦時期青銅器上過于繁縟復雜的雕琢,也不同于秦始皇兵馬俑彰顯集權統治思想的肅殺、莊重,更有別于宋元明清過分追求寫實的精雕細琢,而是洗盡鉛華,是直截了當,是大刀闊斧,是浪漫寫意,是粗放潑辣,這樣的藝術精神更貼近生命的本質、雕塑的本質、藝術的本質,就像漢代的畫像石、畫像磚、竹簡以及碑刻一樣。這種精神得益于漢王朝特別是漢武帝時期開疆拓土、積極進取、氣吞山河的民族氣質,這樣的藝術精神也更能代表中國傳統藝術理念,即寫意精神,正所謂“遺其行骸尚其神”。就像中國畫追求“筆才一二,象已應焉”的疏體作風③,《馬踏匈奴》這樣的漢代雕刻藝術可以說是這種作風在真實空間中的呈現,正是中國傳統藝術觀念中追求的所謂“逸品”的境界。黃休復說:“筆簡形具,得之自然。”“自然”與“簡”——簡練、概括、大氣——仿佛通體兩性,與生俱來。④“簡”不是簡單,而是“簡約”“簡練”。“簡”意味著滌蕩掉與體現藝術本質不相干的一切表面的東西,是超越了對自然的機械模仿。《馬踏匈奴》是“簡”的代表,“簡”到洗滌掉了一切與雕塑無關的細節,“簡”到馬與匈奴人融為一體,“簡”到馬的生命與石料融為一體,它讓人看到的不是一匹刻意雕琢的馬的模型,而是蘊藏在石頭當中的馬的生命、馬的力量,這種力量讓人感動、讓人敬畏。這正是雕塑的本質,也是漢代雕塑及其他藝術的精神特質。
《馬踏匈奴》所傳遞的漢代藝術精神,不僅是對漢朝與匈奴戰爭的紀念,還體現了中國古代藝術的道德教化功能。作品所表現的主題是對正義和勇敢的頌揚,也是對侵略和暴行的警示。這種通過藝術作品進行道德教化的做法,是中國古代藝術的一個重要功能,它能夠通過藝術形象的表現,引導人們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念。《馬踏匈奴》也體現了中國古代藝術的創新精神。作品雖然表現的是傳統的戰爭主題,但通過獨特的藝術手法和創意,將傳統的主題賦予了新的表現形式和意義。這種創新精神是中國古代藝術不斷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
三、關于《馬踏匈奴》及霍去病墓石雕風格成因的討論
自霍去病墓的石雕出土之后,就引起了海內外大量學者的探討與爭論。因為《馬踏匈奴》《野人抱熊》這類作品的雕造方式在中國幾千年的藝術史上實在是獨樹一幟。筆者之前也提到,先秦的青銅器以復雜的紋樣而著稱,秦代的兵馬俑以高度的寫實聞名,而宋元明清的藝術品則更是精致至極。突然出現了這樣高度概括、夸張浪漫的霍去病墓石雕藝術,不禁讓人費解。究竟其風格是如何產生的?
對于這個問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20世紀早期,外國許多學者,包括色伽蘭、畢士博、拉狄格、亨采、喜龍仁、阿登、福開森等,都將《馬踏匈奴》的形象描述為“其頭甚巨而后仰,眼大而圓,額低耳巨,其亂須蓬接馬胸”,并明確“非中國人而為夷狄”的判斷。他們還根據“《馬踏匈奴》其人顴骨較高的特點,亦傾向雕刻人物帶有斯基泰人的造型特點”。色伽蘭說:“霍去病墓的引人注目的馬的雕像,使人想起了巴比倫的獅子,這證明歷經數世紀之久,一種高度發達的文明對其他文化的影響。”①在他們看來,霍去病墓石雕是受亞洲多種文明影響的結果。
而日本學者水野清則持不同看法。他認為,《馬踏匈奴》這樣的霍去病墓石雕所產生的古拙、雄渾的風格是與西漢時期人們的思想觀念相一致的,是在繼承前人工藝美術成就、受到玉石雕刻及陶塑制品直接影響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與之前玉石雕刻和陶塑制作有著一脈相通的藝術軌跡。②
而國內的學者對此觀點也存在分歧。像滕固就認為,霍去病墓石雕的風格是經過若干次發展而形成的,并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而王子云則堅持,霍去病墓石雕的風格特征是西漢強盛國力的體現,這種豪放的特征正是封建社會初期精神風貌的寫照。顧鐵符則從雕刻風格上反駁西方學者的觀點,他說,“將整塊石料與題材作為一體來設計,混合運用圓雕、線刻、浮雕的方法,中國傳統雕刻古已有之,并且在歐洲沒有出現過”。而閻文儒的看法則與西方學者相似,他認為“霍墓石雕的風格與題材與關中漢墓中出土的陶塑、石雕不同,而與北方草原青銅文化的藝術品相似,這說明漢武帝時期的藝術吸收了諸如匈奴文化的特征”。③
諸如此類的爭論還有很多,至今也沒有一個讓人信服的結論。筆者作為一個外行人認為,霍去病墓石雕正如漢代的其他藝術一樣,是大氣、雄渾、開放的,這與其所處時代,即漢武帝時期的歷史文化背景有密切關聯。漢武帝打通了絲綢之路,與中國以外的民族第一次有了經濟、政治、文化上的交流。漢武帝時期的藝術應該是開放的、博采眾長的。回顧中國的歷史,其就是一部多民族文化交流史,各種文化互相滲透、借鑒,才有了今天的面貌。霍去病墓石雕也不例外。但僅從目前掌握的文物資料與考古發現就斷定霍去病墓石雕的風格受到哪種文化影響,還為時尚早。筆者認為,任何文化都不可能獨立地存在,尤其是在漢代這樣開放的時代。究竟霍去病墓石雕的風格如何形成還有待進一步深入挖掘。
四、結束語
《馬踏匈奴》作為中國歷史上不可多得的豐碑式的藝術精品,其藝術價值與學術價值還有待今后更深入、更系統地挖掘,對其藝術源流的討論還將不斷深入下去,還需要更多的、更大范圍的考古發掘來做支撐。總之,《馬踏匈奴》及霍去病墓的石雕藝術成就是值得所有從事藝術的人所借鑒與學習的,其所代表的漢代藝術精神也是應大力提倡的。
參考文獻:
[1]沈寧.滕固藝術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
[2]王子云.中國雕塑藝術史[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
注釋:① 劉宗超:《漢代造型藝術及其精神》,人民出版社,2006,第22頁。
注釋:① 黃宗賢、吳永強:《中西雕塑比較》,河北美術出版社,2003,第76頁。
② 黃宗賢、吳永強:《中西雕塑比較》,河北美術出版社,2003,第79頁。
③ 黃宗賢、吳永強:《中西雕塑比較》,河北美術出版社,2003,第86頁。
④ 黃宗賢、吳永強:《中西雕塑比較》,河北美術出版社,2003,第249頁。
注釋:① ② ③ 沈琍 :《霍去病墓及其石雕研究的回顧及思考》,《考古與文物》2010年第6期,第60-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