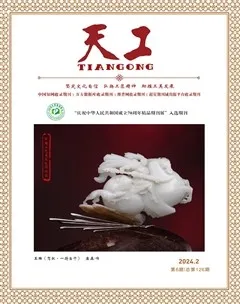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協同治理的現實困境及推進策略
倪菁 趙罡
[摘 要]在理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及特點的基礎上,探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協同治理的現實困境,提出明確多元治理主體權責關系,搭建合作、互動、協商的行動網絡,增加資源、制度保障,完善監督評價機制,構建良好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治理生態,助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工作走深走實。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遺產保護;協同治理
[中圖分類號]J5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7556(2024)6-0012-03
本文文獻著錄格式:倪菁,趙罡.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協同治理的現實困境及推進策略[J].天工,2024(6):12-14.
基金項目:2021年度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一般課題“協同治理視角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高質量發展路徑研究——以江蘇為例”(項目編號:2021SJA1468);2021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規劃基金項目“精準扶貧后非遺助力黔東南地區鄉村振興研究”階段性成果(課題編號:21YJA760096);第三批國家級職業教育教師創新團隊建設項目“工藝美術傳承創新教師創新團隊”;2022年江蘇省職業教育“雙師型”教師團隊建設項目“蘇作非遺技藝技能傳承創新平臺”。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及特點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日本頒布的《文化財產保護法》,其中提到了“無形文化財”的概念。198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保護民間創作建議案》中提到“民間創作”的概念用于表述非物質文化遺產。199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件中首次提出了“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的概念。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正式被確認,文件中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指被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我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注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1]。2005年,《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了中國化的定義,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種以非物質形態存在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世代相承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包括口頭傳統、傳統表演藝術、民俗活動和禮儀與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間傳統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藝技能等以及與上述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2015年,《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和文化空間。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頒布,其中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傳并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以及與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實物和場所[2]。
非物質文化遺產涵蓋眾多門類,每個門類下又細分了眾多項目,每個門類和項目都有特點,但總體上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活態性
活態性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本質特征,與文化遺產的靜態性不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其必須依賴于人,以人的語言、動作等形式口傳身授,得以延續和發展。傳統工藝類非遺項目的傳承和保護是一個動態保護的過程,依靠于非遺傳承人精湛技藝的展現和傳授,單純依靠博物館的靜態記錄是難以實現良好發展的。
(二)傳承性
傳承性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基礎特征。長期以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主要依賴于家族式、師徒式口傳身授、代代相傳,是指后代對前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繼承、創新和發揚。通過百年來代代相傳,人類的智慧、精湛的技藝、豐富的經驗和動態的行為被傳承和延續,這就形成了非物質文化遺產[3]。相比于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需要傳承人掌握一定的知識和技藝,在繼承的過程中,對先進文化不斷學習、借鑒、創新。
(三)地域性和民族性
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極其濃厚的地域特色,地域性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特點。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伴隨著地域文化發展而來的,與當地的自然環境、文化傳統、宗教信仰和經濟發展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地域性強調的是地域環境和地域文化對具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生成和發展的作用。同樣,不同民族因地域、生活環境和習俗不同,產生了各具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是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體現,具有深深的民族文化烙印。
(四)社會性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人類的特有遺產,它的產生、傳承和發展都離不開人類的社會實踐,是人類社會創造力、認知能力等的集中體現,是人類社會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體現在人類的具體實踐活動過程中。如,表演型非物質文化遺產通過表演實踐得以傳承和發展、節日型非物質文化遺產通過節日慶祝等得以傳承和發展。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社會性具有過程性特點,是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體現。
(五)綜合性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綜合性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涵蓋門類眾多,涉及人類的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二是構成要素和形式的綜合。戲曲等表演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文化、音樂、舞蹈等多種要素的組合;核雕、刺繡等傳統工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物質和非物質形態的綜合。三是功能和效應的綜合。非物質文化遺產既有文化效應,又有經濟效應。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也能促進文化和旅游產業的發展。
二、協同治理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治理
“治理”一詞源于國外,西方政治學家和管理學家主張用治理代替統治。治理理論的主要創始人羅森瑙認為治理是一系列活動領域里的或隱或顯的規則。1995年,全球治理委員會對治理做出了權威性和代表性的界定,認為治理是個人或者機構等其他組織從公或私的某一方面經營管理同一事務的許多方式的總和,是以調和為基礎的持續的相互作用的過程,而不是一種正式制度。現在“治理”一詞多強調按照客觀規律從主觀上對事物進行管理、控制、梳理、整治、處理的過程,是一系列活動領域里的管理機制,它們雖未得到正式授權,卻能有效發揮作用。
“協同”一詞源于希臘語,意為 “協調合作”。協同治理理論的研究起源于西方對善治的探討,其目的在于實現治理過程中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強調合作治理的協同性,指多部門、多層級政府、公共團體等多元主體在協同合作下,共同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管理活動的過程。在我國,協同治理被認為是一個公共管理的活動和過程,是政府部門、非政府機構(企業、非營利組織)、公民個人等多主體共同行動、彼此合作、共擔風險,參與公共事務管理的過程[4]。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協同治理是指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科研機構(高校、研究院所)、非遺傳承人、公民個人等多主體共同參與、協同合作,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動和過程,從而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發展。
三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協同治理的現實困境
(一)主體困境:多元主體權責模糊不清
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是協同治理的基本特征。協同治理的主體除了政府機構,還包括企業、科研機構、非營利組織、非遺傳承人及普通公眾。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是一項煩瑣的公共事務,在多元參與的治理模式中各治理主體的結構較為復雜。因此,明確各治理主體之間的權責關系和權責邊界尤為重要,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共治共管的基本條件。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存在各治理主體間權責認定不清晰、所依據的相關政策標準或規章制度不全面等問題,這導致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協同治理在實踐過程中出現部分具體問題的歸責困難、無法實現利益最大化、管理無序、缺位越位和濫用職權等現象。
(二)協作困境:多元主體協同合作力度低
協同合作機制是多元主體共同決策、共擔責任、共享利益、共同參與的治理機制,是實現公共治理多元主體之間良性互動的核心。協同合作機制具有多元主體利益的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認同性整合的多維功能,是當前社會利益多元化的現實需求[5],但目前多元主體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協同合作的機制并不完善。一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多依賴于文化和旅游部及其下屬部門等行政機構,管理層級多,且同級文化和旅游廳、文化和旅游局等行政部門協同合作較少,文化企業、非營利組織、非遺傳承人等雖然已經參與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但常因目標不同而缺乏協同合作。二是各主體間缺乏協同聯動和信息共享。
(三)制度困境:多元主體協同制度化保障供給不足
近年來,國家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也出臺了一系列相關的政策和制度,但在制度化保障方面仍存在供給不足的問題。我國的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政府的資金投入差距較大,特別是中西部貧困地區無力擔負大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費用。我國非物資文化遺產保護的監督評價機制也存在缺失,這不僅導致了相關部門無法及時地發現、解決非物資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也導致了各參與主體的權利無法得到保障,公眾無法有效參與監督。所以,建立多元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監督、評價機制任重而道遠。
四、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協同治理的推進策略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協同治理要樹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新理念,全局性、系統性、協調性地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進行謀劃和推進,優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體制機制,有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
(一)理清主體責任清單,提升協同共治水平
多主體共同參與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協同治理的重要基礎。唯有政府、企業、非營利社會組織、非遺傳承人等各主體明確權責、相互協同,共同參與其中,才能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高質量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協同治理的過程中,應當建立多元主體協同的責任清單制度,明確各主體的責任和義務,對各主體的實踐工作進行規范和約束,從而保證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相關事務得到及時有效的處理,形成多元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多方聯動效應。政府作為國家的權力機關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主體,具有優勢地位。在協同治理過程中,職能主要體現在宏觀指導、統籌協調、履行管理職能等方面。政府應制定并運用相關政策,引入市場機制,統籌協調基礎設施、人才、經費等各項資源。企業應當在政府的引導下,積極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建立與政府良好的合作關系,簽訂合同,履行責任和義務;同時遵循市場規律,借助產業力量,深挖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打造非遺品牌形象。非營利組織與非遺傳承人應當利用自身優勢和資源去開展各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活動和宣傳活動,同時積極參與監督評價。
(二)構建協同合作行動網絡,推進信息共享和協同聯動
多方力量的協同合作行動網絡的構建是統籌各方力量、優化多元主體責權、推進多元主體高質量協商互動的重要路徑,不僅可以促進各主體間信息互通和交流,提高保護效能,還可以提高各主體間合作的緊密度,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協同合作網絡的構建要求公共事務的信息公開化、透明化,公開建設內容、財務收支等內容,向社會展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優秀成果,提高各協同主體間的信任度。另外,在治理過程中,要完善秩序化、程序化協同聯動機制,充分利用互聯網、大數據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型技術手段,鼓勵多方平等表達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理性訴求、建議,形成協同合作的參與機制和問責機制,形成政府、企業、非營利組織、非遺傳承人等多元主體聯動共治、互助共建的新格局。
(三)加強協同治理的制度保障,完善協同治理的監督評價體系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是一項需要長久持續的龐大工程,政策、資金、人才等方面的引導和保障,以及有效的監督評價機制缺一不可。首先,建議中央與地方政府增加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資金投入并納入所在地區經常性財政預算,經濟困難的地區應由國家和省級財政通過轉移支付給予支持。社會捐贈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經費的重要補充,可設立項資金,接受社會捐贈,對符合條件的捐贈主體依法給予稅收優惠,確保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經費來源多元化[6]。其次,完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監督評價體系,以網絡為平臺,以信息公開、信息共享為前提,互相溝通交流,為多元化監督主體提供一個暢通的監督渠道,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和發展。以公正、客觀的態度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協同治理各環節的工作進行評價,并向各環節的負責單位、部門或個人及時反饋評價結果,從而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各環節不斷改進與完善,最終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協同治理工作的健康、有序發展。
參考文獻:
[1]黃新洋.合作治理理論視角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推廣研究:以漳州傳統刺繡為例[D].廈門:廈門大學,2019.
[2]李鶯.張掖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協同治理研究[D].蘭州:蘭州大學,2020.
[3]常潔琨.甘肅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分類保護研究[D].蘭州:蘭州大學,2017.
[4]張仲濤,周蓉.我國協同治理理論研究現狀與展望[J].社會治理,2016(3):48-49.
[5]王洪樹,張玉芳.協同合作的價值內涵和政治目標探析[J].領導科學,2010(17):17-20.
[6]魏紅梅,楊雪姣,李芹.“雙減”背景下課后服務協同治理的現實困境與紓解策略[J].教育理論與實踐,2024,44(7):1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