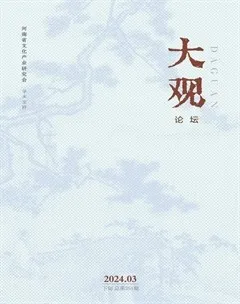桂林剖絲團(tuán)扇的文化價(jià)值與藝術(shù)特征研究
宋佳佳
摘 要:人們對(duì)現(xiàn)代藝術(shù)審美的追求反映著人們的文化訴求。團(tuán)扇是中國(guó)傳統(tǒng)器具,也是傳統(tǒng)文化中的禮儀之扇,其發(fā)展幾經(jīng)起伏,日趨成熟,但是后經(jīng)折扇文化沖擊逐漸沒落。桂林剖絲團(tuán)扇于近代煥發(fā)新的活力與生機(jī),其作為漢文化產(chǎn)物,在嶺南這個(gè)多民族聚居地與當(dāng)?shù)氐亩嘣褡逦幕蝗诮豢棧蚨辛藙?chuàng)造性轉(zhuǎn)變,其鮮明的藝術(shù)特征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guó)多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借鑒、融合的具象化表現(xiàn)。
關(guān)鍵詞:民間美術(shù);民族文化;桂林剖絲團(tuán)扇
一、扇文化與桂林團(tuán)扇
能搖曳生風(fēng)的“扇”極大可能源自祖先為排解酷暑燥熱、遮陰納涼,隨手扯下或撿拾的不知名葉子、片狀植物,或者禽類羽毛。扇的最初形態(tài)可能俯拾即是,是經(jīng)過簡(jiǎn)單加工后便能招風(fēng)、障日的物件。晉人崔豹在《古今注》中對(duì)于“五明扇”的描述:“扇,又名箑,黃帝內(nèi)傳有五明扇,天子用雉尾扇,即掌扇也。舜廣開視聽以求賢人作五明扇。”首先,根據(jù)“扇”字從“羽”,“箑”字從“竹”的意象分析,并結(jié)合考古發(fā)現(xiàn)的新石器時(shí)期大量復(fù)雜多樣的竹制編器物,可推測(cè)黃帝禹、舜時(shí)期的羽扇、竹扇已經(jīng)非常完善了,制作工藝也較為成熟,并且其在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是作為政治權(quán)力地位的體現(xiàn)而被使用的[1]。此后,扇文化以其強(qiáng)大的生命力成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一部分而流傳下來。清代王廷鼎的《杖扇新錄》對(duì)當(dāng)時(shí)御扇風(fēng)俗的描述:“今俗御扇,大抵初夏折扇,中夏用團(tuán)扇,盛暑用羽扇,稍涼復(fù)用團(tuán)扇,至折扇而捐矣。道專用折扇,盛暑僧用蒲扇,道用羽扇。商人止用折扇,近亦有羽扇、團(tuán)扇者。”可見當(dāng)時(shí)扇的類型、材料豐富多樣,對(duì)于扇的使用場(chǎng)景也更加細(xì)化,人們會(huì)在特定時(shí)節(jié)使用不同的扇,并且不同職業(yè)用的扇也有所不同,表明其發(fā)展已進(jìn)入成熟期。扇的體形逐漸由大變小,成為具有搖曳生風(fēng)功用的手中物,種類繁多,造型多樣,其因輕薄而面積較大的特點(diǎn)在扇面作書畫廣為流行,并一度成為身份地位和審美趣味的體現(xiàn),承載了主人的審美和價(jià)值取向,受到文人墨客們的喜愛。扇與書畫的結(jié)合標(biāo)志著扇開始從單一的實(shí)用性走向功用與審美的雙重功能,是“一種能夠游走的藝術(shù)”。其中作為藝術(shù)品為眾多藏家所喜愛的當(dāng)屬折扇和團(tuán)扇,而團(tuán)扇的產(chǎn)生遠(yuǎn)早于折扇,如今常見于民族服裝配飾和影視作品,深受女性群體的喜愛。
廣西地區(qū)文化又稱為桂系文化,從屬于嶺南文化。漢族自秦漢以后由中原各地陸續(xù)遷入廣西,遷入時(shí)間不一,遷入地點(diǎn)不斷變化,與當(dāng)?shù)厣贁?shù)民族長(zhǎng)期共處、互相同化。而桂林團(tuán)扇是中原文化與嶺南文化交融的產(chǎn)物,已有800多年的歷史,《杖扇新錄》就有:“篾絲扇:來自嶺表。”宋朝時(shí),北民南遷,團(tuán)扇制作技藝流入桂林,并與本地制扇技藝不斷融合。明清以后,題扇、畫扇之風(fēng)盛行,桂林團(tuán)扇的扇面繪制藝術(shù)高度繁榮,扇面用材不斷豐富。之后,桂林團(tuán)扇走向海外市場(chǎng),其制作工藝有所提升,團(tuán)扇種類變得更為豐富,桂林團(tuán)扇品牌也得到了廣泛傳播[2-3]。
在實(shí)地訪問邱廣初在桂林的團(tuán)扇工作室之后,了解到團(tuán)扇的外貿(mào)銷售國(guó)家主要為日本、韓國(guó)以及部分東盟國(guó)家,團(tuán)扇所呈現(xiàn)的中國(guó)文化和地方民族特色深受這些國(guó)家人民的喜愛。但團(tuán)扇的制作工藝復(fù)雜,面對(duì)出口銷量的日益增加,不得不對(duì)工藝進(jìn)行加工和升級(jí)。相較于其他團(tuán)扇延承原始團(tuán)扇造型精美的特點(diǎn),桂林團(tuán)扇制作技藝的代表性傳承人邱廣初及其弟子在傳承傳統(tǒng)剖絲團(tuán)扇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了創(chuàng)新,可以扇骨將團(tuán)扇劃分為三大品類:圓竹剖絲團(tuán)扇(丸竹團(tuán)扇)、平竹剖絲團(tuán)扇(平竹團(tuán)扇)、插絲團(tuán)扇(京都團(tuán)扇),其核心制作工藝是以剖絲為扇骨,并且扇柄與扇面一體成型。插絲團(tuán)扇是在剖絲團(tuán)扇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升級(jí)與改造,在保持基本工藝不變的情況下,解決了傳統(tǒng)剖絲團(tuán)扇手工制作耗時(shí)長(zhǎng)、工期久的難題,同時(shí)豐富了其外在表現(xiàn)形式。
二、桂林剖絲團(tuán)扇的藝術(shù)特征
(一)工藝表現(xiàn)的精巧化
竹材料具有極強(qiáng)的抗拉性和抗壓性,其輕便、堅(jiān)固、便于運(yùn)輸、取材容易且易于更換的材料特性使其成為人們?nèi)粘I钣闷返睦硐胫圃觳牧稀@逯窈兔袷莾蓮V地區(qū)較常見的竹子類型,也是團(tuán)扇扇骨的主要材料,竹齡要在3年以上,結(jié)實(shí)又不失韌性,竹身無花斑、無傷痕、無蟲蛀、不傷皮、不變質(zhì)、顏色清白。材料一般要用開水進(jìn)行2—4小時(shí)的蒸或煮,從而達(dá)到去蟲、去糖的目的,利于竹材進(jìn)一步的加工和保存。桂林剖絲團(tuán)扇與其他扇子的本質(zhì)區(qū)別在于剖絲這一步驟,這也是制作過程中最難的部分。尤其是圓竹剖絲工藝極為精巧細(xì)膩,扇骨與扇柄以竹節(jié)為界,一體成型。扇骨的制作需要在直徑約1 cm的厘竹上勻量剖絲,根據(jù)扇的大小剖出30—50根竹絲,并且需要保持竹絲光滑、平順、不扎手。每根竹絲拉開后不折斷,自然地從竹節(jié)處散開,根據(jù)扇面大小勻量分絲后編織定型,竹絲厚度僅0.5 mm左右,成品結(jié)實(shí)又輕薄,體現(xiàn)出桂林團(tuán)扇工藝的精巧之美。
(二)內(nèi)容和形式表現(xiàn)的豐富多樣化
扇面形制除講究對(duì)稱美學(xué)的圓形、方形和多邊多角的宮燈形、海棠形、梧桐、芭蕉等眾多自然擬形的傳統(tǒng)形制之外,還衍生出不規(guī)則橢圓樣式[4]。多樣形制的出現(xiàn)為扇畫創(chuàng)作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扇骨的勻量分絲工藝特點(diǎn)使扇面受力均勻,承載性能較好。同時(shí),扇面選擇多樣,扇骨被兩張扇面覆蓋,兩面皆可進(jìn)行繪畫、書法等藝術(shù)創(chuàng)作,桂林剖絲團(tuán)扇裝飾造型創(chuàng)新性地借鑒了剪紙、刺繡、壯錦、苗繡、侗繡、麥稈畫、雕刻等民族藝術(shù),其美術(shù)表現(xiàn)形式涉及多種民族特色文化,是漢文化和少數(shù)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集大成者。
桂林剖絲團(tuán)扇由三個(gè)部分構(gòu)成:扇面、扇骨、扇墜。團(tuán)扇的主體是扇面,其是主要的裝飾部位,勤勞的壯族人民利用當(dāng)?shù)刎S富的自然資源,憑借爛熟于心的竹編手藝以竹編扇面,手的起落間,細(xì)長(zhǎng)的竹篾被挑起又落下,交織成美麗的圖畫。竹編扇面平整有序,棕褐色的竹面透著微涼與刺繡的色滿而形多變。此外,文人墨客的世界少不了紙張扇面,根據(jù)書畫創(chuàng)作需求,文人所用團(tuán)扇往往選用生宣和熟宣質(zhì)地的扇面,除宣紙外,還有絹、棉、錦、綾等質(zhì)地的扇面[5-6],這些均是極具張力和支撐性的材料。
隨著現(xiàn)代科技的進(jìn)步,團(tuán)扇制作材料變得豐富多樣,而桂林剖絲團(tuán)扇與壯錦的結(jié)合,使壯錦傳統(tǒng)經(jīng)典紋樣以別致的造型樣式重新出現(xiàn)在人們的視野中,成為游走的手中風(fēng)物或收藏?cái)[件。就觀賞角度而言,面料的直觀平面性與團(tuán)扇的立體環(huán)繞性相得益彰。
團(tuán)扇扇柄除使用湘妃竹之外,還有紅木、桂林雞血玉等,這些均為天然材料。在材料處理過程中,往往會(huì)對(duì)竹子進(jìn)行形狀和顏色的處理,而為保留原材料的自然之美,多以水煮和煙熏等原始加工方式進(jìn)行處理,避免化工產(chǎn)品對(duì)原材料的影響。竹子、絲綢、玉石通過觸感和視覺能激起人們內(nèi)心獨(dú)特細(xì)微的情感變化,其手工制作是無法被機(jī)器所替代的。除此之外,壯族人民往往會(huì)將具有美好寓意的繡球縮小化為扇墜,在扇子的搖擺間,翩然而起的是壯族人民淳樸的祝愿。
(三)文化表現(xiàn)的多元融合化
文化的敘述構(gòu)成了恒常主題敘述的真正連續(xù)性,而同一主題的不同文化有著不同的表現(xiàn)形式。團(tuán)扇上的時(shí)間符號(hào)歷久彌新,那些借以抒情的山水花鳥是文人情懷的具象符號(hào),而抽象符號(hào)使蘊(yùn)含著壯民豐富精神內(nèi)涵和審美意識(shí)的稻作崇拜、植物崇拜、圖騰崇拜等文字記載成為具體的言說,它們靜默地述說著如何從漢族璀璨文化中的一支脈絡(luò),在廣西桂林扎根并抽出嫩綠新條,有了新的視覺實(shí)踐,產(chǎn)生新的視覺內(nèi)容。團(tuán)扇作為漢文化的產(chǎn)物,隨著漢民族的遷徙來到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在與當(dāng)?shù)孛褡宓慕蝗谥惺艿疆?dāng)?shù)厝宋牡乩淼纫蛩氐挠绊懚纬尚碌臉邮健3嘶B石魚等充滿了文人氣息的扇面內(nèi)容,在入鄉(xiāng)隨俗的過程中,團(tuán)扇逐漸親近地方民族,扇面從絲綢發(fā)展為由棉絲合織的壯錦,而壯錦中的吉祥紋樣也成為其囊中之物。同時(shí),吉祥主題的民間壯錦成為新的扇面素材,在織布機(jī)的一推一拉間織出壯族人民對(duì)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對(duì)現(xiàn)實(shí)生活的滿腔熱愛。
桂林剖絲團(tuán)扇不僅是案桌上的藏品,還是婚禮儀式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物品,更是游走人世間的手中風(fēng)物。團(tuán)扇除了在材料和工藝方面有所繼承和創(chuàng)新之外,在團(tuán)扇本身的呈現(xiàn)上,或是保留傳統(tǒng)制作工藝,將扇的整個(gè)體積縮小,增加其趣味性,使其既可以是身上的裝飾掛件,又可取下偶爾招陰涼;或是在扇面的內(nèi)容上一改往日的高山流水、鳥語(yǔ)花香、精致繁復(fù)和壯錦的豐富多彩,以時(shí)下的熱門話題和卡通形象而深受低齡受眾的喜愛;或是保留團(tuán)扇的外在形制,以不同的物質(zhì)材料進(jìn)行再創(chuàng)造,滿足社會(huì)需求的多樣性,制作出團(tuán)扇形制的賀卡、磁石貼和明信片等。
(四)桂林剖絲團(tuán)扇創(chuàng)作原則
其一,固本浚源,不舍其本。立足于現(xiàn)實(shí)的人間,不因創(chuàng)新而脫離現(xiàn)實(shí)需求,不追求一時(shí)的熱度。其二,標(biāo)新以求精而非立異。通過創(chuàng)新促進(jìn)自身更好的發(fā)展,而不是通過刻意表現(xiàn)、標(biāo)榜自身的與眾不同。其三,返璞歸真,向內(nèi)求索。不因追求創(chuàng)新發(fā)展和審美潮流而遠(yuǎn)離本民族的內(nèi)在審美觀念。
無論是載體和技法的跨界,還是設(shè)計(jì)的再開發(fā),都是探索傳統(tǒng)工藝美術(shù)是否可以在當(dāng)代實(shí)現(xiàn)品牌化發(fā)展,以實(shí)現(xiàn)其自身的持續(xù)發(fā)展。團(tuán)扇作為工藝美術(shù)品,其主要在于“用”,而工藝與美術(shù)的結(jié)合使“日常生活審美化”成為一種美的現(xiàn)象。
三、反思與總結(jié)
扇文化歷史悠久,扇的造型多樣,扇面精美,種類豐富,工藝成熟。宋代文人云集,文學(xué)、藝術(shù)蓬勃發(fā)展,折扇的出現(xiàn)恰逢其時(shí),因其扇小而面大,文人墨客興之所至題詩(shī)作畫于其上,一開一合間盡顯文人風(fēng)采,廣受歡迎,其審美與藝術(shù)價(jià)值開始獨(dú)立并分化出來,在此基礎(chǔ)上發(fā)展出獨(dú)立的畫種:扇面畫。之后折扇逐漸興起,中上階層對(duì)折扇的青睞,致使民間團(tuán)扇由此受到?jīng)_擊而衰落,不復(fù)往日的興盛,可見當(dāng)時(shí)上層主流審美意識(shí)和觀念對(duì)于社會(huì)的影響之大,以至于桂林團(tuán)扇在20世紀(jì)70年代的機(jī)遇下才開始煥發(fā)新生。
中國(guó)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多文化共同體,文化底蘊(yùn)深厚,文化類型多樣,文化歷史久遠(yuǎn)。受社會(huì)發(fā)展進(jìn)程、文化交流、地域局限等因素影響,民間美術(shù)在各民族和地區(qū)的生命力有所不同。目前,對(duì)民族文化的保護(hù),不應(yīng)只是將其列入非遺名錄,以及培養(yǎng)傳承人,尤其是民間美術(shù),其曾經(jīng)流淌于民間活脈文化中,如今卻陳列在高樓林立的博物館中。在漫長(zhǎng)的歷史進(jìn)程中,必然會(huì)有一些事物被淘汰,而團(tuán)扇等民間美術(shù)工藝品中特有的觀念能夠跨越物質(zhì)空間和時(shí)間,在現(xiàn)代社會(huì)引起風(fēng)潮并遠(yuǎn)銷海外,與不同個(gè)體的特定文化圈達(dá)成審美共識(shí),說明其文化內(nèi)涵是符合現(xiàn)代社會(huì)發(fā)展趨勢(shì)的。如何更好地促進(jìn)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與發(fā)展,值得人們不斷探索與實(shí)踐。
中國(guó)傳統(tǒng)的傳承機(jī)制一直以師徒傳承或是家族傳承制為主,桂林剖絲團(tuán)扇的傳承方式也不例外,邱廣初的桂林團(tuán)扇工作室就是家庭傳承和師徒傳承相結(jié)合的傳承模式,學(xué)習(xí)方式也有線上、線下學(xué)習(xí)班兩種方式,在工作室內(nèi)部也設(shè)有團(tuán)扇學(xué)習(xí)體驗(yàn)活動(dòng),對(duì)于團(tuán)扇的傳播發(fā)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要想在現(xiàn)代化社會(huì)進(jìn)程中維持其長(zhǎng)遠(yuǎn)且有活力的發(fā)展,需要一個(gè)更為完善的系統(tǒng),應(yīng)包含但不限于師徒傳承和家庭傳承,還要與社區(qū)傳承、學(xué)校教育、社會(huì)傳習(xí)等多種形態(tài)的國(guó)民教育進(jìn)行有機(jī)結(jié)合,以活態(tài)文化育人。
四、結(jié)語(yǔ)
對(duì)于團(tuán)扇這一民族文化的傳承,不能局限于對(duì)技藝的學(xué)習(xí),還要深入了解團(tuán)扇中關(guān)于社會(huì)變遷、內(nèi)涵傳承的故事。這有助于人們對(duì)其有更深入的理解,從而形成對(duì)團(tuán)扇的立體化認(rèn)識(shí);有利于完善民間傳統(tǒng)工藝美術(shù)傳承體系,充分發(fā)揮傳統(tǒng)文化在人的成長(zhǎng)過程中的重要引導(dǎo)作用,促進(jìn)民間傳統(tǒng)手工制作技藝的傳承與發(fā)展。
參考文獻(xiàn):
[1]趙音.中國(guó)古代扇面文化之探究[J].大家,2011(4):10-11.
[2]王勇.日本折扇的起源及在中國(guó)的流播[J].日本學(xué)刊,1995(1):115-130.
[3]雷一萍,邱燕珍.基于當(dāng)代多元審美視角的傳統(tǒng)工藝美術(shù)設(shè)計(jì)創(chuàng)新實(shí)踐:以廣西傳統(tǒng)工藝美術(shù)技藝“桂林團(tuán)扇”為例[J].藝術(shù)大觀,2022(14):52-54.
[4]加曉軍,王凱娜.桂林團(tuán)扇工藝研究[J].西部皮革,2016(14):13.
[5]黃武.秀竹清風(fēng)顯初心:荔浦邱氏傳統(tǒng)竹藝團(tuán)扇制作工藝及藝術(shù)特點(diǎn)[J].美與時(shí)代(上),2019(9):54-56.
[6]賴起鳳,羅明.扇面的特殊形制與當(dāng)代扇面書法創(chuàng)作[J].美術(shù)教育研究,2021(4):25-26,29.
作者單位:
廣西藝術(shù)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