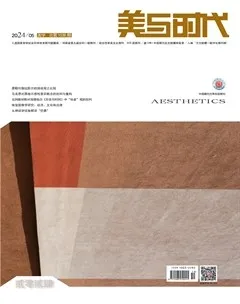中國神話中父權邏輯建構與人的主體精神覺醒

摘? 要:《封神第一部》是中國本土的英雄神話史詩,保留了神話內核的同時,以當代化的敘事視角與結構張力進行改編,站在父權制系統內部,以嶄新的視角述說著父權邏輯的建構、超越“度”的界限的權力欲望的放縱以及權力操控下主體的反抗與精神覺醒。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封神第一部》對古典神話進行現代化解讀,傳播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以“家國同構”的敘事方式將個體成長與國家興衰命運聯系起來,強化了主流價值觀,加深了當代社會的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
關鍵詞:中國神話;父權邏輯;主體精神;家國同構;文化認同;封神第一部
影片《封神第一部》以宋元時期話本《武王伐紂平話》和明代神魔小說《封神演義》為創作藍本,將這部古老的三千年前的中華國民英雄神話史詩,再一次帶到大眾面前。影片一播出,便掀起了一波熱烈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古典神話的現代化改編,以及古典神話中所蘊含的價值觀與現代社會思想的耦合等。誠如卡西爾學者所言:“神話的所有基本主旨都是人的社會生活的投影。”[1]作為中國古典英雄神話史詩,《封神》系列源于幾千年前的華夏民族,神話文本及形象的塑造符合當時歷史社會時期的藝術加工。《封神第一部》以傳統的封神故事為核心,守正創新,與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精神相結合,以當代化的敘事視角與結構張力進行改編,結合歷史現實與神話傳說,以一個嶄新的視角述說著一個新版封神故事,與當代觀眾產生情感共鳴,強化主流價值觀,實現民族文化認同。
一、權力秩序及“父”的英雄神話構建
《封神第一部》整部片子的核心都在講秩序。盤古把天地劈開,從此混沌的世界有了天地秩序,仙界、人界與妖界構成三界秩序,人界中的抗命謀反、弒父殺子等本質上也是在講秩序。總之影片中所有的沖突點都是圍繞著秩序被打破來進行的。殷壽與質子們,是父權制系統下的“父子”與“君臣”兩個復雜關系的情感融合。家國同構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忠孝一體的特有現象,家庭與國家是命運共同體。影片中帝乙、殷啟、殷壽的父子關系與姬昌、伯邑考、姬發之間的父子關系,便是家國秩序的具體表現。
關于紂王,《荀子》這樣描述:“長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史記》寫道:“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善識人心的特性及縝密的父權邏輯建構了紂王外貌杰出、智力超常、英勇善戰的英雄形象,為其成為質子所尊崇的精神之父提供了可能性。電影序幕中,冀州侯蘇護謀反,質子蘇全孝在紂王的鼓勵下以自殺來完成自己對父權最后的忠誠的使命,這一宏大敘事場面將紂王善于情緒操控的形象展現得淋漓盡致。他先是否定質子們的血緣之父,讓質子蘇全孝意識到自己只是父親的棄子,又在他最脆弱的時刻充當父親的角色,撫摸蘇全孝的頭頂,告訴他:“我才是你真正的父親。”精神上的壓迫打破了蘇全孝最后的心理防線,最終他用長劍刺破喉嚨,自我處決。“極端殘暴的處決在展示統治者權力運作的同時,也常常在參觀展示的民眾中煽動了仇恨和不安的情緒。”[2]紂王在馴化眾人接受他權力構建的真理與規則過程中,巧妙地利用蘇全孝的死,煽動其他質子與士兵仇恨與不安的情緒,給他們加上為蘇全孝復仇的義務與枷鎖。蘇全孝犧牲之后,紂王大喊:“是誰殺了蘇全孝?”眾軍齊喊:“叛賊蘇護!”紂王用他邏輯縝密的精神操控,成功將仇恨轉移到蘇護身上,同時振奮了士氣。在攻城的過程中,蘇護的軍隊用火防守,商軍的馬匹受驚不敢上前,于是,殷壽用布蒙上了馬匹的眼睛,并且告訴質子們,馬能看到什么,是由人來決定的。看似在說馬,實際上也在隱喻人,馬能夠被人訓練上戰場殺敵,人體則是權力實現的對象和目標,“人體是被操縱、被塑造、被規訓的。它服從,配合,變得靈巧、強壯”[3]。殷壽用他權利的邏輯和王者的手段,讓蘇全孝和其他質子們對他崇拜服從,成功地完成了英雄形象的構建。
朝歌在影片中處于權力中心地位的構建顯然是非常成功的,一是基于歷史事實,朝歌對應的商王朝在商朝時期是權力中心;二是從影片的社會空間呈現來看,我們也能明顯地感受到權力分布差異。誠如法國科學家布迪厄所言,“通過描繪個體和團體在社會空間中所占據的關系位置來圖繪社會空間本身的”[4]。從社會空間來看,商王朝處于權力的集中之所,紂王則是商王朝的君主,代表著最高權力,是父權主義至高的象征,他象征著權力、榮耀與自我價值的實現。社會學上有個概念叫“霸權式男士氣概”,它被認為是最具男子氣魄的類型,只有少數人才能擁有。這種氣質被當作男性理想的典范,被所有男性追隨與崇拜,影響著整個社會對男性的定義。因而大多數男人,需要通過與這種氣質發生關聯來找到自己的位置從而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姬發入商的目的便是在向霸權男性靠攏,從而獲得力量,成為英雄,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在他眼里,紂王,是父親,是力量的代名詞。力量、財富、霸權氣質、迷惑性、神秘感,造就了“父”的神話,完成了“父”的英雄神話構建。
二、被英雄主義
與權力欲望扭曲的父權(制度)
“父權”是常見的社會權利的一種表達方式,“中國封建父權更甚,兒子往往依附于父親的法內或法外權力之下,成為父權支配的對象”[5]。《封神》系列神話故事文本設定深刻地體現了商周時期的父權表達。無論是作為精神之父,還是權力君主,紂王對質子團及其他社會公民有著至高的主宰權。誠如盧梭所言:“人們一旦結成了社會,聲望和權威的不平等就不可避免地在個體之間發生……個人的身份是其他所有不平等的根源。”[6]影片中朝歌于諸侯國而言,是“父與子”關系的映射,是國與家、父與子的雙重建構,諸侯國需依附于朝歌,聽從朝歌的派遣;質子團于紂王,于其血緣之父而言,也是依附的關系,地位的差異造就了身體與精神的不平等,表現為“父”對“子”的規訓,強者對弱者的規訓,因此,人們會向往權力。正如影片中所展示,紂王對至高權力表現出了強烈的欲望,“欲望是人的本能體現,是作為自然的狀態呈現”[7]。而自然法所探討的就是最純粹的人性,紂王對權力的欲望是純粹的人性本能,他的所有的行為動機都是出于對權力欲望的追求。在影片中,大家以為紂王被妖孽迷惑,忠言相勸的時候,紂王說:“你們都說白狐是妖孽,她明明是祥瑞。”對紂王而言,妲己是他欲望實現的祥瑞,她能幫他得到他想得到的權力。然而,從人性純粹的欲望達到社會道德人倫的要求,需要經歷一個認知的階段,康德將這個認知階段分為感性、知性和理性,當認知符合“度”界限,才會出現正確的導向。“什么是‘度?‘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處。”[8]當超越“度”界限,就會產生錯誤的導向,違背秩序。人的感情是復雜多變的,“人在道德動機上的不純粹性,因為革命并非總是走向進步與文明,相反可能走向野蠻與暴力,這就是人性中的‘否定方面”[7]。當人被欲望控制,就可能破壞人倫秩序,違背社會道德,走向野蠻和暴力。影片將紂王塑造成一個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一個殺伐果斷的統帥、一個城府極深的權力追隨者,在利用完妲己達到最高權力之后,紂王開始希望得到永生。紂王在追求權力欲望滿足的過程中,道德動機的不純粹性將他帶向了人倫秩序的反面,造成他人格上的扭曲。
“刻畫‘性格,應如情節安排那樣,求其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9]影片中對紂王人物性格的刻畫,可以從社會背景和成長環境中找到合理性。紂王對權力的追求,與商朝的王權思想發展有關,“商朝至上神的出現,說明在商朝王權對權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真正掌握國家的大權而不受其他權力的影響”[10]。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紂王為何對至高權力如此著迷。紂王扭曲人格的形成,與原生家庭有很大關系。他是帝乙次子,是個不受寵愛的孩子,而哥哥殷啟則備受父親寵愛。在慶功宴上,殷啟跳劍舞,帝乙開心贊賞,而冒死出兵討伐蘇護,差點飲恨軒轅墳的殷壽,卻一句夸獎也沒有。由此可見,殷壽對于父王是一種因愛生恨的復雜感情,愛得越深,恨得也就越深。所以他樂于見證并制造人倫悲劇,毀掉屬于他人的親子之間的溫情,這是一種對父愛渴望卻不可得的宣泄。此時的紂王,已經人格扭曲,而他人格的根源,也能從影片想要探討的父權上找到原因。在無限集中的權力關系中,對于父的愛和恨會在子輩中代代相傳,永無止境。
三、人的主體精神的覺醒與回歸
反父權敘事是一種非常常見的敘事方式,如果說龍德殿“弒父”動搖了姬發對紂王的信任與尊崇,那么,當囚禁在地牢中的姬昌對兒子說“你是誰的兒子不重要,你是誰才重要”,則引起了姬發的精神覺醒。他開始深刻反思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意識到不論是君臣“父子”關系還是血脈親情,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個人的品德與行徑。中國的德性思想源遠流長,德性觀念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姬昌之所以被觀眾認為是為正面形象的父親,正是因為他是世人推崇的德性人格理想的藝術化身。“在家國同構的道德秩序中,……個體在這種道德秩序聯結中將自身命運與家族命運、自身道德與國家道德自覺地聯系起來,從而構筑了一個道德共同體。”[11]正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個人道德與國家的發展密切相關,君權與父權相輔相成,互為表里,由父權制度衍生發展的宗法制度的影響延續至今,“神話史詩”核心思想與當代價值觀相互呼應,與當代觀眾產生共鳴。影片中“家國同構”的敘述策略讓影片故事情節更具戲劇張力,完成了國家、家庭倫理敘事。
“王孝廉學者應用艾利雅得的‘原型回歸觀念研究中國神話所呈現的圓形時間結構表現出的‘原始‘歷劫‘回歸的三段循環。”[12]《封神第一部》遵循的神話圓形時間結構,對主人公姬發的個人成長線進行總結。在影片最后,姬發主體精神覺醒,結束了對精神父親的盲目崇拜,回到了血緣之父姬昌的懷抱,回歸了秩序與宗法,最終“德”戰勝了“權”,“仁”戰勝了“暴”。這就是這部電影的成長主題,姬發的成長,是對父的祛魅,對于情感的喚醒,這部電影的“弒父”,并不是西方概念的強行移植,跟西方俄狄浦斯截然不同,其內核是在探討植根在中國文化里的家國同構、父權秩序,探討父權為何會生效,由此衍生的宗法制為什么在今天依然會奏效,精神偶像為什么會層出不窮,且永無止境……
四、結語
《封神三部曲》是中國本土的英雄神話史詩,結合浩瀚的真實歷史與神話傳說,找到與當代觀眾產生共鳴的人類情感和普世價值,其中所體現的以民族精神為內核的神話體系與敬天法祖的民族信仰,是人的精神世界的隱喻及民族永恒的價值觀的表達。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不乏為民請命的先圣。他們將經驗與教訓留給了后人,是他們成就了我們。我們對封建與歷史的批判,不影響我們在精神上的民族認同。世界民族之林,各族競秀,方有文化之盛。《封神》系列能夠延續至今,對當代社會仍然產生影響,神話敘事的包容性是主要原因。因此,我們要結合不同歷史時期特點,理性繼承傳統優秀文化,并將其與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精神相結合,共同鑄就博大的中國神話。《封神》系列將千年歷史神話帶到當代年輕群體面前,為神話的當代改編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參考文獻:
[1]卡西爾.人論[M].甘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74.
[2]張之滄.論福柯的“規訓與懲罰”[J].江蘇社會科學,2004(4):25-30.
[3]福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M].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154.
[4]格倫菲爾.布迪厄:關鍵概念[M].林云柯,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8:29.
[5]李守庸,彭敦文.特權論[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331.
[6]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M].呂卓,譯.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171.
[7]翁少龍.黑格爾論道德與倫理——以《倫理體系》的欲望概念為中心[J].現代哲學,2023(1):69-76.
[8]李澤厚.歷史本體論[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1.
[9]亞里士多德.詩學[M].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61.
[10]王樂意.儒教早期王權思想述論[D].北京:首都師范大學,2014:20.
[11]李曉璇.在古今視野下理解習近平總書記的家國觀[J].世界宗教研究,2021(6):23-32.
[12]葉舒憲.中國神話學百年回眸[J].學術交流,2005(1):154-164.
作者簡介:鄧夢婕,廣西民族大學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視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