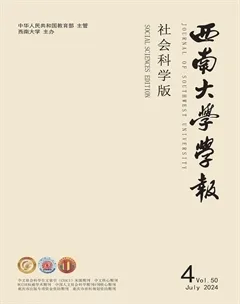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探索與發展中的社會流動圖景
摘 要:在人類現代化進程中,工業化和城鎮化等社會結構轉型是其核心內容,而社會成員在社會分工結構中進行社會流動是其必然的伴生性社會現象。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從生產方式與交往形式的辯證關系出發,揭示了現代化進程中“地域性個人”向“世界歷史性個人”轉變的基本原理,這啟示我們從社會結構現代化轉型的角度尋找社會流動的深層規律。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中國人口規模巨大且農村人口基數龐大等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流動人口的規模之巨以及管理和服務流動人口的任務之艱。在中國式現代化探索與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歷史時期基于現實國情采取了不同的流動人口調控機制,形成了社會流動的嚴控圖景、自發圖景、賦能圖景和自主圖景等縱向變遷歷程。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部署以全面深化改革來保障和推動社會流動的自主圖景,尤其是助力個人全面發展的城鄉融合圖景和區域協調圖景,這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時代課題。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社會流動;城鄉關系;全面深化改革;歷史唯物主義;新型城鎮化;國家治理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D261;D663;C9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841(2024)04-0026-13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綜述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1]。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2]。從人類現代化進程的共同特征看,社會成員在城鄉與區域間進行大規模社會流動,即社會階層流動化[3],是工業化和城鎮化等社會結構轉型中普遍且必然存在的伴生性社會現象。從中國特色來看,人口規模巨大且農村人口基數龐大以及區域與城鄉發展不平衡等現實國情,必然會形成而事實上也形成了中國社會流動的特殊圖景:作為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在社會結構轉型的歷史條件下,流動人口的規模之巨以及管理和服務流動人口的任務之艱,在人類現代化進程中前所未有。
在學術研究視域下,社會流動包括階層流動和人口流動兩個議題。1927年,俄裔美國學者索羅金出版《社會流動》一書,首次提出“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概念,用以分析社會成員在社會空間中的地位升降現象。1932年,該書在中國被翻譯為《社會變動論》并由世界書局出版,旨在“研究各個人在社會空間中的變動現象”[4]。其中,“社會流動”概念中譯時被改譯為“社會變動”,意在突出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化對社會成員生存與發展的實際影響。其后,伴隨對社會流動現象認知的深化,學界仍然更多地使用“社會流動”來翻譯“Social Mobility”,以此聚焦并解讀社會成員在社會階層結構中的位置變化。1967年,美國學者布勞和鄧肯出版《美國的職業結構》一書,旨在將社會流動與社會分層研究結合起來,并以職業為標準分析社會成員的地位排序和位次升降,建構了“布勞-鄧肯地位獲得模型”[5]。在中國,學界主要以地位獲得模型、職業生涯模型和求職過程的社會網絡模型等來解讀中國的社會流動[6],其理論內涵始于索羅金的“社會流動”概念,其實質是階層流動,主要指代社會成員的地位升降;而作為階級階層結構變遷的基本形式,其理論來源則主要是韋伯主義的階級理論。
根據奧羅姆的解釋,在韋伯看來,“階級僅僅代表在勞動力市場中具有同等地位者的整體聚合”[7]。在韋伯的《經濟與社會》等著作中,他根據社會成員在資源分配中所得份額的多寡,從財富、權力和聲望等維度分別將不同“整體聚合的同等地位者”區分為上中下三個層級。與韋伯不同,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不是從“同等地位者的整體聚合”這一邏輯來進行階級劃分,也不是對社會成員間的階層關系進行“階梯式排列”[8]。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進一步明確,“粗俗的”人(特指海因岑等粗俗文學的代表)的理智把階級差別變成了“錢包大小的差別”[9]343;而“財產關系上的不公平”[9]331,以現代分工、現代交換形式、競爭、積聚等為前提。既然不存在高低排列的階梯式階層格局,自然也就不存在上下流動的理論圖景,也就是說,某些學術話語中的所謂向上流動、向下流動以及平行流動等概念,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基本原理,而是主要來源于韋伯主義的階級理論。
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堅持“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并“始終必須把‘人類的歷史’同工業和交換的歷史聯系起來研究和探討”[10]160。從結構視角看,即便是韋伯主義的地位升降,其社會流動如城鄉居民的流動感知等,同樣也來自于城鄉資源配置、戶籍等系列制度改革所引發的城鄉結構變遷[11]等社會分工結構的變化,城鄉與區域之間的場域區隔構成阻滯社會成員合理有序流動的結構性致因[12]。這意味著盡管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沒有明確提出社會流動的概念,但其從分工結構及分工與交換的關系等角度進行階級階層分析的基本原理,隱含了社會流動的深層致因和內在規律。這要求我們從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中梳理并建構社會流動的理論邏輯,尤其是從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和區域結構等社會分工結構中尋找社會流動的基本規律[13]。同時,這也將克服僅以個體位置變化界定社會流動而忽視產生社會流動現象的結構性致因等研究中的不足,并為社會流動研究提供新的理論貢獻和知識補充。
人口流動研究始于1880年英國學者雷文斯坦對推拉邏輯下人口遷移現象的關注,主要聚焦于社會成員在收入、消費以及公共服務等勢差引力作用下所進行的地理位移。在中國,以地理學等學科為代表,主要關注人的遷移對于人口在國土空間中分布與變遷的影響,如對“胡煥庸線”的影響[14];以經濟學等學科為代表,主要關注人口遷移對勞動力要素在城鄉與區域間配置的影響;以法學等學科為代表,主要關注階層流動對司法信任水平的影響[15]。從實踐來看,不論是流動人口的能見度還是其參與度,中國正在由低流動性的“鄉土中國”形態轉向高流動性的“遷徙中國”形態[16],這構成了人口遷移對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現實影響。伴隨學界對人口流動研究的深入,學界開始使用“空間流動”“地理流動”等概念來代替人口遷移,因為“空間流動不僅是空間的位移,也是社會生活的結構化維度,可能帶來個體階層變化以及宏觀社會結構的改變”[17]。同時,如果把地方作為一個整體或作為“擴大的消費品”來看,那么,社會成員對地區的攝取是以其獲得市民身份等社會流動方式來實現的[18];而地理流動之所以具有社會流動效應,是因為地方之間在集體消費和保障居民基本公共服務權利等方面存在差異[19]。這一方面標志著學界已把地理流動或空間流動等人口流動問題納入社會流動的分析范疇;另一方面則將區域因素納入社會分工體系進行分析,并解讀其與社會流動間的相互影響關系。
綜上來看,不論是階層流動的結構性致因,還是人口遷移的社會流動效應以及區域因素的社會分工屬性,社會流動的研究符合“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等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基本原理。但在既有的學術話語體系中,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中的社會流動圖景研究目前尚接近空白狀態。那么,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中的社會流動遵循何種理論邏輯,就需要我們進行理論建構和學術創新。此外,大規模常態化社會流動來自社會分工結構的變化,而工業化和城鎮化等現代化進程是社會分工結構變遷的核心動力。這意味著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必然形塑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流動圖景。那么,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不同歷史階段,其社會流動實踐是否會呈現不同的時代圖景?中國式現代化最終又將形塑何種理想的社會流動圖景以作為“人類實現現代化的新的選擇”呢?這要求我們從理論與實踐、歷史和現實的不同維度進行實踐概括和理論總結。
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蘊含的社會流動理論邏輯
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共計7次明確提及“流動”。其中,除1處規劃“數據跨境流動機制”外,其余6處均與“社會流動”直接相關,比如“社會流動渠道”“人才有序流動”“人口流動客觀規律”“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生產要素暢通流動”等[20]。完成上述與“流動”相關的全面深化改革任務,必然涉及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及產業結構等社會分工結構的優化;而推動人的全面發展以及“推動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優化組合和更新躍升”等,構成了貫穿其中的目標主線。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關于社會流動的戰略部署,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生產物質生活本身……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10]158的理論邏輯,并如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序言中所述,“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21]530,從而規劃新征程上社會流動的未來圖景。
(一)基本規律:社會分工結構的發展會產生人的交往形式的變遷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唯物史觀的邏輯起點和歷史前提,即現實的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10]146。其中,作為“一切社會關系總和”的“現實的人”的本質,包括兩個基本方面:生產和交往。生產主要指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對自然的征服和改造;交往則是人們的相互關系,而人們的相互關系又受制于人們的物質生產活動[22]。對于分工發展產生交往變遷并引起社會組織變革的基本原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進行了論述,“游牧部落從其余的野蠻人群中分離出來”的“第一次社會大分工”,使得“經常的交換成為可能”;而手工業和農業分離的“第二次社會大分工”則“出現了直接以交換為目的的生產”;“第三次社會大分工”則出現專門從事交換活動的商人群體[21]188-194。伴隨交換等社會交往的擴大,氏族部落中“增加的人口中一部分是外來移民”[21]152,以血緣為紐帶的社會組織機制“在社會意義方面已不是最重要的”[21]132,“有決定意義的已不是血族團體的族籍,而只是常住地區了……居民在政治上已變為地區的簡單的附屬物”[21]139。
在人類社會發展歷程中,社會成員在地理空間結構和社會階層結構層面進行流動并不罕見,比如農業社會因自然災害等而發生的人口遷徙、科舉體系或軍功體系下實現階層躍遷等。但常態化的大規模社會流動現象主要發生于工業化之后的現代化進程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進行了清晰的描述,比如,“在農業領域內,就消滅舊社會的堡壘——‘農民’,并代之以雇傭工人來說,大工業起了最革命的作用”,并使得“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占優勢”[23]518;同時,“使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的歷史運動,表現為生產者從農奴地位和產業的等級制下解放出來”[23]769。也就是說,工業化生產方式打破了人類封閉隔絕的交往形式,引導社會成員在產業結構、城鄉結構等分工結構中以流動機制改變自身階層屬性,并最終推動社會成員之間的交往關系走向普遍的社會聯系。
概言之,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從生產與交往的辯證關系中,指出生產方式的發展會產生交往形式的變遷,工業化等現代化進程會產生大規模社會流動現象,而社會流動是人類社會突破封閉隔絕狀態并走向普遍社會聯系的重要動力。這種普遍社會聯系的形成,具體表現為“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10]165。這同時構成個人不斷實現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基本條件。即個人“不斷擺脫自然與他人(社會)所帶來的束縛的過程。在人尚未有充分的能力擺脫其中任何束縛的時候,人為了生存,都依附一定的共同體……隨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個體獨立生存能力的不斷增強,人就逐漸擺脫對特定共同體的依賴,獲得了獨立自主存在的經濟與社會基礎”[24]。所謂“擺脫對特定共同體的依賴”以及“獨立生存能力的增強”,具體到本文就是個人擺脫既有社會關系的束縛并尋求融入新的關系場域的社會流動過程。
(二)發展趨勢:新的社會關系形態要求新的社會組織機制與其相適應
從“地域性個人”向“世界歷史性個人”轉變,是唯物史觀對“人的現代化”的目標設定。而支撐“人的現代化”進步的深層動力在于,社會結構的現代化轉型助力社會成員突破既定社會關系的約束,并通過自主選擇勞動方式和居住地點等提升其勞動的自主性。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進行了描述,比如,“大工業從技術上消滅了那種使一個完整的人終生固定從事某種局部操作的工場手工業分工”[23]510。同時,“現代工業通過機器、化學過程和其他方法,使勞動者的職能和勞動的社會結合不斷地隨著生產的技術基礎發生變革……不斷地把大量資本和大批工人從一個生產部門投到另一個生產部門”[23]514。因此,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更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25]504。但在西方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上述社會交往形式的更新建立在資本原始積累的基礎上;而西方國家“原始積累的方法絕不是田園詩式的東西”[23]768。
因為“原始積累的秘密”是對“農村居民土地的剝奪”,以圈地運動為典型歷史事件的資本積累方式使得“大量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被拋向勞動市場”[25]737,“并且促使農村居民變成無產階級,把他們‘游離’出來投向工業”[25]745。同時,向城鎮社會流動聚集的社會成員顯然“不可能像它誕生那樣快地被新興的工場手工業所吸收。另一方面,這些突然被拋出慣常生活軌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適應新狀態的紀律”[25]754。從英國等西方國家的實踐看,對于上述問題,當局者主要以“血腥紀律”和“警察手段”進行應對:“被暴力剝奪了土地、被驅逐出來而變成流浪者的農村居民,由于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過鞭打、烙印、酷刑,被迫習慣于雇傭勞動制度所必需的紀律”[25]756。總之,西方國家工業化等現代化建設為社會成員的全面發展提供了機會前提,但其工業化等現代化實現方式是以個人異化為商品作為代價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
為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暢想以新的社會組織機制適應現代社會的關系形態,“工業生產將不是由相互競爭的單個的廠主來領導,而是由整個社會按照確定的計劃和所有人的需求來領導”[10]301。因為任由資本理性的無限擴張會造成“由盲目的規律來調節,這些盲目的規律,以自發的威力,最后在周期性商業危機的風暴中顯示著自己的作用”[21]203。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繼承者和實踐者,列寧認為,對于后發現代化國家而言,“必然要把創造高于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的根本任務提到首要地位,這個根本任務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并且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勞動組織”[26];斯大林則將現代化的起步方式總結為四種:以英國為代表的殖民掠奪方式、以德國為代表的將戰爭賠款運用于工業化的方式、以舊俄國為代表的通過借款“爬”上工業化道路以及靠本國節約來發展工業的道路,即社會主義積累的道路;而“靠本國節約來發展工業的道路,即社會主義積累的道路……這條道路是我國工業化唯一的道路”[27]。因而,不論是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還是批判資本邏輯支配下的現代化道路,要實現以人為本的現代化目標,都要求后發現代化國家探索新的社會結構轉型方式,如以國家理性而非資本理性來支配生產。這必然會形成新的社會流動圖景,尤其是本質上有別于圈地運動式的社會流動圖景,并啟示我們進行實踐總結和理論創新。
(三)理論啟示:社會流動的深層動力在于社會分工結構的轉型
物質資料的生產與交換構成唯物史觀中社會流動理論圖景的邏輯主線。在生產力相對落后的情況下,社會成員的生產方式與交換活動既受到自然條件的制約,又需要“以群的聯合力量和集體行動來彌補個體自衛能力的不足”[21]49,即依賴并受制于一定的集體組織機制。伴隨社會分工的發展所帶來的社會生產力的進步,社會成員一方面擺脫自然條件限制的能力在提高,另一方面擺脫既有集體組織機制而融入新的集體組織機制的自主性也得以增強。工業化和城鎮化等現代化進程打破了封閉隔絕的社會結構狀態并推動普遍性社會聯系機制的形成。這為社會成員以社會流動形式實現從“地域性個人”向“世界歷史性個人”的轉變提供了歷史前提。然而,西方國家對內剝削對外掠奪的現代化發展道路,一方面是個人以異化為商品作為代價而成為“自由的雇傭工人”,并造成社會成員的無序流動;另一方面則因資本理性的隨意擴張而導致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
這就要求我們在致力于工業化和城鎮化等現代化目標的同時,需要規避西方國家現代化道路的“致命缺陷”。其中,以國家理性保障有序的社會生產秩序是唯物史觀為中國實現現代化提供的理論指導。在學術研究中,對于國家理性在中國階層變遷中的關鍵作用,已在學界引起了足夠的重視,比如在國家主導的現代化發展模式下,國家政策變量成為中國社會階層變遷的核心要素,其中以“基調理論—大的政策原則—具體政策”組成的政策群構成社會流動等階層結構變遷的關鍵動因[28]。這一方面啟示我們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重要論述及政策文本等解讀中國社會流動的變遷歷程,另一方面需要我們在解讀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奇跡”的同時,深化其在保障“人的全面發展”等方面的理論認知。
三、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中社會流動圖景的歷史變遷
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起點,學術界形成了洋務運動說、辛亥革命說、中國共產黨成立說、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說、改革開放說等五種代表性觀點[29]。但總體而言,中國的現代化議題起源于西方工業文明沖擊下所產生的總體性結構危機。在救亡圖存的探索中,部分知識分子認識到工業化等社會結構轉型的強大動力,比如夏丏尊將“農業文明”向“商工文明”的時代轉化概括為“中國的現代化”[30]。作為反帝反封建的先進性革命力量,中國共產黨將工業化作為追求民族獨立的重要任務,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專門討論了“工業問題”,提出“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奮斗”[31]。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堅持以國家理性而非任由“盲目的規律”主導中國現代化道路。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圍繞黨的中心任務謀劃和部署改革,是黨領導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32]。這是我們認識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中社會流動圖景變遷的科學理論指導。
(一)工業基礎建設與社會流動的嚴控圖景(1949—1984年)
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中國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歷史前提和政治保障,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其現代化起步方式不可能走西方國家對內壓榨人民、對外殖民擴張的資本積累道路,而朝鮮戰爭等外部因素也使得新生政權放棄優先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等“起步”戰略。綜合國內外現實條件,中央選擇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毛澤東概括為“重點是用一切方法擠出錢來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33]197-198。同時,在現代化道路的規劃中,1954年,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用“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對“四個現代化”進行初步概括[33]250;進入60年代,毛澤東和周恩來“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過程中”,結合中國國情對“四個現代化”的提法進行完善,在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正式提出“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宏偉目標。“四個現代化”的提出,意味著黨中央超越了單純以工業化定義現代化的戰略認知,“更多考慮如何建立國民經濟體系的問題,也就是從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來構想中國的現代化目標”[34]。
以“共同制定的計劃”而非“盲目的規律”支配生產,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之一。在中國,“黨領導國家工作的制度”成為對該原理的重要實踐,保證了中國式現代化探索的有序進行。以“統一指揮、集中力量、協調一致地完成經濟恢復和民主改革的任務”來保證“把有限的資源、資金和技術力量集中使用到重點建設上來”[33]173-184。集中統一領導的社會整合機制,不僅有效保證了中國工業化等現代化建設的有序推進,而且避免了社會成員基于個人理性而自發進行的盲目流動。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性糧食緊缺以及城市物質資源匱乏和就業機會不足等現實國情,決定了城市難以容納農村人口的自發流動。在不同歷史時期,新生政權還采取了精簡職工等方式鼓勵城市人口“下鄉”,這同西方國家任由資本理性驅使農民“離土離鄉”的社會流動圖景有著本質區別,同時在表現形式上形成了社會流動的嚴控圖景。
外部封鎖與內部貧困等約束以及重工業吸納就業有限等限制,使得“政府不得不限制城市人口數量,近80%的人口限制在農村,留在土地上”[35]。這種通過政策機制形成的社會流動嚴控圖景,具體表現為中央人民政府1953年頒布的《關于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和1957年頒布的《關于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嚴格控制社會成員的“盲目流動”;195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賦予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不同戶籍身份,并以戶籍身份等形式嚴格控制社會成員的人口流動。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農村人口基數龐大的后發現代化國家而言,強大的國家治理能力與社會動員能力,尤其是有效的政府干預機制,是將后發潛能轉化為后發優勢的關鍵所在[36]。對于國家能力建構而言,“將流動人口定居下來(定居化)往往成為長期的國家項目——之所以是長期的,部分原因也在于這些項目很少有成功的”[37]。伴隨工業化、城鎮化等現代化進程而必然產生的流動人口,對新生政權的國家治理能力構成現實挑戰,尤其是對于國家政權如何在工業基礎薄弱以及城鎮化水平較低的條件下維持社會秩序,無疑是一個嚴峻考驗。實踐證明,以嚴控社會流動來保障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起跑秩序”,不僅避免了早期工業化國家因人口無序流動而產生的貧民窟等問題,而且有效建構了國家治理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并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
(二)城市功能優化與社會流動的自發圖景(1984—2003年)
1984年是中國社會流動圖景的轉折點,當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農村居民向城鎮轉移是“必然的歷史性進步”,相比于此前“盲目流動”的政策表述,中央對農村人口向城鎮社會流動的政策態度發生標志性重大轉折。當年5月,中央發布開放沿海城市的重大決定,奠定了“孔雀東南飛”的政策基礎;10月,國務院發布“允許農民以自理口糧身份落戶集鎮”的政策文件,在政策意義上開啟了中國農村人口大規模向城鎮社會流動的歷史序幕。相比于此前的社會流動嚴控圖景,中國社會成員開始脫離行政控制機制而開啟自發流動模式。之所以發生這樣的變化,是因為改革開放初期,黨中央針對中國的現代化道路進行了戰略性調整,并對中國社會分工結構進行了諸多優化。
1979年3月30日,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鄧小平提出:“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要使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至少有兩個重要特點是必須看到的:一個是底子薄……第二條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38]1980年,在會見英國前首相詹姆斯·卡拉漢時,鄧小平再次用“小康之家”的標準即人均年收入1 000美元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定位進行解釋,同時提出“農業機械化的道路一定要走,剩余的勞動力要轉到其他行業去”的基本構想[39]。在中國式現代化探索進程中,我們除了認識到工業基礎薄弱的現實之外,還意識到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在城鄉結構和產業結構進行轉移,被視為“必然的歷史性進步”,這也為打破中國陷入農業社會而歷久不變并停滯不前[40]的歷史怪圈找到了突破口。
如果說社會流動的嚴控圖景主要服務于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探索,那么,社會流動的自發圖景則主要基于優化城市功能等城鎮化規劃。1978年1月和4月,鄧小平針對知識青年返鄉問題和大學生就業問題,提出以調整城市結構實現城市容納更多勞動力的設想,如“重工業發展以后,是不是開辟一些就業門路,比如輕工業、服務行業,都可以用一些人”[41]261,“我們發展的領域要很好研究一下,開辟什么領域,哪些方面會增加……生產效率提升了,就逼著我們去改變結構的比例,實際上是農業工業化了”[41]296;除此之外還包括“為人民日常生活服務的行業”[41]302,要“開辟為工業、農業服務的行業”[41]359等。針對城市的功能問題,黨中央提出,“過去我們對城市功能的理解比較狹窄……一提到城市,往往只想到它是工業基地。這種認識是不全面的……城市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更重要的是為它所輻射的整個經濟區服務”[42]。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在公開演講中,將中國的城鎮化和美國的高新技術發展視為影響21世紀世界格局的關鍵因素。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主旋律,中國城鎮化之所以具有形塑中國社會結構和影響世界格局的強大動力,追溯其政策動因,緣于中國共產黨領導優化城市功能結構并有序控制流動人口的戰略規劃。
城鄉兩端的雙重變化——允許農民進城與優化城市功能,表明我國在中國式現代化探索過程中注重以容量邏輯調控流動人口。因為工業化、城鎮化等現代化進程為農村人口突破“農之子恒為農”的代際復制模式提供了機會前提;但是,作為“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允許農民進城會產生巨量的流動人口,這極有可能因突破城鎮人口容量而沖擊城鎮社會秩序。因此,除了以調整城鎮產業結構來擴充其人口容量外,我國還采取了通過發展鄉鎮企業來吸納農業富余勞動力的政策規劃。“他們離開土地而不進城,叫做‘離土不離鄉’。這和歷史上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利用各種手段剝奪農民,使他們破產,成為資本的廉價勞動力,是根本不同的。”[43]該政策在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有序流動等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是,作為人口規模巨大且農村人口基數龐大的國家,中國流動人口的規模很快超過鄉鎮企業的有限容量。基于對更高生活質量的追求,中國流動人口脫離“離土不離鄉”的政策軌道而呈現“離土又離鄉”的自發流動圖景。
(三)城鄉關系調整與社會流動的賦能圖景(2003—2012年)
農村人口大規模、自發性地向城鎮社會流動,使得政府缺乏“必要的思想準備和政策準備”[44],如何引導和管理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流動人口成為中國政府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該問題在2003年集中顯現出來:在“抗擊非典”過程中,各級政府采取各種措施勸阻農民工返鄉以防止“非典”擴散的行為,使得農民工第一次被賦予公共性身份[45]。在2003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中央明確“支持農民進城務工就業,清理和糾正針對農民工的歧視性政策和亂收費”[46];該年7月,在全國防治非典工作會議上,中央明確將管理和服務農民工群體以及保障其合法利益作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工作”被列入“進一步抓好的九項工作”之一[47]。從制度角度分析,流動人口權利保障問題產生于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體制。該體制賦予農村人口和城鎮居民兩種不同的戶籍身份,并提供兩種不同的公共服務供給機制。因而,以調整和優化城鄉關系來賦能流動人口的“城市逐夢”,不僅可以構成以人為本現代化道路的方向指引,而且為保障流動人口的基本權利提供政策支持。
作為調整城鄉關系的重要舉措,“補齊”農村居民公共服務權利短板等服務型政府建設,對于保障流動人口的基本權利具有實質性的積極支持。2002年,中央將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列入政府“十六字職能”;2005年,政府工作報告正式提出“服務型政府”的目標任務;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再次明確“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戰略目標。在服務型政府建設中,以新農合、新醫保為主要內容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建設,為農村居民提供了基本的權利保障;而保留農村戶籍身份的流動人口以“聯根式社會流動”獲得權利保障成為現實選擇[48]。時至今日,補齊農村居民權利短板并保障流動人口的基本權利依然是我們應對流動社會到來的重要任務。因為根據測算,中國當前從農村向城市遷移的鄉城流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為24.29%,在流動人口中的比重為69.66%;在城鄉流動人口內部,保留農村戶籍的流動人口比重為46.76%[49]。
除此之外,長期影響流動人口權利保障的管理問題聚焦于城市戶籍門檻,因為它增加了流動人口轉變城鄉身份與區域身份的現實難度。在2011年的戶籍制度改革中,中央對建制鎮、設區的市以及副省級城市與直轄市等三類不同規模的城市,采取由低到高的戶籍準入機制,同時在政策文本中設專章部署“解決農民工實際問題”[50]。以調整戶籍門檻為主線賦能流動人口的身份轉變,同樣構成社會流動賦能圖景的重要內容。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為中國農村社會成員突破“生于斯,長于斯”的封閉性交往機制提供了基本前提。但是,脫離既有的交往場域意味著失去原有社會網絡的支持,而如何在新的交往場域獲得基本的權利保障則是國家必須面對且需要有效回答的施政實踐問題。以問題為導向,探索并建構以權利保障為主線的社會流動賦能圖景,構成以人為本現代化道路的實踐表現。
(四)高質量發展格局與社會流動的自主圖景(2012年—)
2012年,黨的十八大勝利召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定位。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進行了戰略規劃。其中,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被確定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任務,也被視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探索與發展的“第五個現代化”。2017年,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以及同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對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特征作出重大判斷:“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51]2024年,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將“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列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同時明確將“推動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優化組合和更新躍升”作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等高質量發展的改革舉措[20]。這表明,在高質量發展格局中,現代化產業體系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技術基礎,已構成社會流動的核心支撐。
從社會流動的動因看,不同于農業社會中安土重遷的農村人口因自然災害或戰爭等而進行人口遷移,現代化進程中的人口流動主要產生于社會成員對更高消費水平、更優就業機會等美好生活的向往。2013年,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閉幕式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52]等中國夢的基本內涵。具體到社會流動,2013年,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到兩億流動群體難以享受到平等的公共服務等城市融入的“玻璃門”現象,并將其列為制約城鎮化高質量發展的現實問題[53];201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強調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重要內容,以三章篇幅專門規劃“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十三五”規劃和“十四五”規劃均將戶籍制度改革和居住證制度改革作為保障流動人口基本公共服務權利的重要舉措;2024年,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全面取消在就業地參保戶籍限制”,將“完善促進機會公平制度機制,暢通社會流動渠道”和“健全人口發展支持和服務體系”[20]作為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體系的改革任務。這表明,在新時代治國理政中,保障流動人口的自主流動權利成為中國夢的重要內容,超越了將流動人口僅視為市場要素的基本定位,強調流動人口對高品質生活的追求,構成中國式現代化的更高目標定位。
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過辛勤勞動實現自身發展的機會”[54];2019年,中央印發《關于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首次以專門性文件部署優化社會流動體制機制;2021年,中央發布《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行動方案》,保障流動人口在全國范圍內自主流動成為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的目標行動;2022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再次明確“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流動的體制和政策弊端,消除影響平等就業的不合理限制和就業歧視,使人人都有通過辛勤勞動實現自身發展的機會”[2]。2024年,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探索建立全國統一的人口管理制度”以及“健全全國統一的社保公共服務平臺……完善社保關系轉移接續政策”等改革任務[20]。這些都有力地推動了社會成員自主流動圖景的形成。
所謂自主流動,從個人角度看,是社會成員充分發揮其能動精神而選擇流動或不流動以及以何種方式向何處流動等;從社會角度看,是社會成員的流動決策具有現代化產業體系作為機會前提和容量載體;從政府角度看,是社會成員的流動行為不因生活場域的轉換而制約其獲得基本的社會支持。進入新時代,不僅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流動人口融入城市構成治國理政的政策關懷,而且鄉城流動人口的農村集體權益也有了法律保障。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不僅明確了戶籍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認定的基礎,而且也明確了因務工、經商等“暫時離開”的流動人口的核心財產權益,以避免其面臨“失地又失業”等雙重風險[55]。同時,為了“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而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部署,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已然將社會流動作為社會發展的重要表現并將其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策依據。比如,“把握人口流動客觀規律,推動相關公共服務隨人走,促進城鄉、區域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動”;同時明確提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以及“建立同人口變化相協調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務供給機制”和“建立新增城鎮建設用地指標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協調機制”等改革任務[20],這必將為社會成員的自主流動圖景提供更有力的政策支持。
四、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中社會流動的未來圖景
作為人口規模巨大且農村人口基數龐大的轉型國家,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進程,必然需要引導巨大規模的流動人口在城鄉間、區域間和產業間進行有序流動。同時,大規模社會流動事實上構成了推動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強大動力,如從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的轉變[56]。新的社會結構形態必然要求新的國家治理機制與之相適應。因而,展望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社會流動的未來圖景,一方面要求我們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城鄉融合發展與區域協調發展,以保障社會流動的合理有序進行;另一方面要求我們以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推動社會成員自主流動圖景的持續完善。
(一)理論圖景:在社會結構轉型中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唯物史觀圖景
以工業化為核心的現代化道路逐漸消除人類社會中具有地域局限性的交往形式,并推動世界歷史性交往形式的形成。從現代化的普遍規律看,工業化創造了現代化的社會交往形式,有力地打破了人類社會的封閉孤立狀態并創造了世界歷史,因而,“直到現階段,工業化仍然構成現代化的核心”[57]。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探索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將工業化作為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物質基礎;進入新時代,中國依然將現代化產業體系作為人口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支撐。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既要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維護社會公平,更好地實現效率與公平相兼顧、相促進、相統一”[58]。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部署的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實踐中,“完善促進機會公平制度機制,暢通社會流動渠道”[20]構成了推動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制度保障。以“效率與公平相兼顧、相促進、相統一”[59]為目標勾畫自主流動圖景,表明中國式現代化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踐與發展,也是對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理論否定和實踐超越;同時,中國共產黨結合基本國情長期規劃并適時調整現代化戰略,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踐創新。
(二)實踐圖景:以現實國情為基本出發點的改革與發展圖景
世界各國現代化道路的差異源于世界各地稟賦結構的差異性,而現代化的本質是改變自身支配社會變遷的稟賦結構,并進行上層建筑的適配性變革[60]。中國共產黨基于不同歷史時期的時代任務和發展需求而制定與其相適應的流動人口管理機制,最終形成了以人為本的社會流動圖景:持續系統地推進工業化、城鎮化等社會分工結構的現代化轉型,并為社會成員突破地域局限的社會流動行為提供機會前提;基于人口規模巨大,尤其是農村人口基數龐大且人多地少等基本國情,通過體制機制的適時調整來引導社會成員有序流動,并最終以現代化社會支持機制保障社會成員自主流動。然而,當前城鄉、區域、體制間的多重分割,限制社會結構進一步優化[61];縣域流動人口占比偏低等結構事實,要求我們通過結構性優化構建社會流動重大轉向的系統性方案,以構建新型城鄉關系[62]。“推動生產要素暢通流動”“完善人才有序流動機制”“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等改革任務,要求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城鄉間與區域間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并以健全人口發展支持和服務體系等系列改革機制為流動人口搭建“橫向流動橋梁和縱向流動階梯”[63]。
(三)任務圖景:優化流動社會治理的國家治理現代化行動圖景
在既有的話語邏輯中,社會流動是社會成員基于改善個人階層狀況而進行的個人決策;但是,在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體系中,社會流動是生產與交往辯證關系的實踐表現,構成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重要路徑。因而,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處理好若干重大關系”的重要論述中,將“破除階層固化的體制機制障礙,暢通社會上升通道”作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的重要任務[59]。同時,在黨中央治國理政的系列規劃中,比如在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規劃中,明確提出“健全統一規范的人力資源市場體系,促進勞動力、人才跨地區順暢流動”[64];在區域協調發展的布局中,明確“打破阻礙勞動力在城鄉、區域間流動的不合理壁壘,促進人力資源優化配置”[65];在基層治理現代化的決策部署中,明確將“流動人口管理服務”作為街道等基層組織為民服務的重要任務[66]。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把握人口流動客觀規律,推動相關公共服務隨人走,促進城鄉、區域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動”[20]。這要求我們將流動社會治理納入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行動規劃,以此形成合理、公正、暢通、有序的社會流動格局并推動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
五、結 語
從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看,社會流動是社會分工結構轉型產生社會交往機制變遷的直接表現;其中,工業化構成生產結構轉型及交往機制變遷的核心動力,城鎮化則是社會結構轉型的承載場域與容量載體。同時,歷史唯物主義要求,為了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并避免資本理性和個人理性的“盲目規律”,需要以國家理性保障“共同生產”的基本秩序。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積極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來探索中國的工業化道路和城鎮化戰略;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思維誤區,克服了后發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普遍性困境,真正找到了破解后發國家“外源現代化”歷史命題的全新思路[67]。基于后發國家及人多地少等基本國情,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歷史時期采取不同的戰略規劃,產生了不同的社會流動圖景。中國社會流動圖景的變遷與優化是中國式現代化在效率上超越資本主義且更好維護社會公平的實踐寫照;同時,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保障,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為目標,正確運用生產與交往之間的辯證關系,不僅是對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理論否定和實踐超越,而且是中國式現代化保障個人自主流動及助力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理論創新和實踐經驗。
參考文獻:
[1]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在京舉行 中央政治局主持全會 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作重要講話[N].人民日報,2024-07-19(1).
[2]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N].人民日報, 2022-10-26(1).
[3] 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增訂本)[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14.
[4] 索羅金.社會變動論[M].鐘兆麟,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6:1-5.
[5] 彼得·布勞,奧蒂斯·杜德里·鄧肯.美國的職業結構[M].李國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12-22.
[6] 李路路,朱斌.當代中國社會分層與流動研究手冊[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4:551-556.
[7] 安東尼·奧羅姆.政治社會學導論[M].張華青,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49.
[8] 莫里斯·迪韋爾熱.政治社會學——政治學要素[M].楊祖功,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116-122.
[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43.
[1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0.
[11] 黃超.制度變遷與城鄉居民的流動感知[J].社會,2024(3): 220-241.
[12] 韓宜錚.流動與區隔:農業轉型過程中人口流動與階層分化[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3(2): 38-50.
[13] 朱光磊,王通.階層與分層:中國社會成員構成研究中的兩種分析邏輯[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20(6):13-23.
[14] 王桂新,潘澤瀚.中國人口遷移分布的頑健性與胡煥庸線[J].中國人口科學,2016(1):2-13.
[15] 張曉琳.階層流動、社會公平感與中國公民的司法信任——基于CGSS 2017數據的實證研究[J].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3):46-58.
[16] 段成榮,邱玉鼎.遷徙中國形態下人口流動最新趨勢及治理轉向[J].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23(4):118-129.
[17] 馬凌,羅加威, 李錦昊.空間流動與社會流動關系研究述評[J].人文地理, 2023(6):1-7.
[18] 王寧.消費流動:人才流動的又一動因——“地理流動與社會流動”的理論探究之一[J].學術研究, 2014(10):29-37.
[19] 王寧.地方分層、人才流動與城市人才吸引力——“地理流動與社會流動”理論探究之二[J].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6):47-55.
[20] 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N].人民日報,2024-07-22(1).
[2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530.
[22] 王滬寧.政治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1-36.
[2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18.
[24] 林尚立.當代中國政治:基礎與發展[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6:3.
[2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6] 列寧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90.
[27] 斯大林選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4.
[28] 李強.試分析國家政策影響社會分層結構的具體機制[J].社會,2008(3): 54-64.
[29] 蔣英州,王創宇.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歷史起點、主要內涵與使命追求[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 (2):1-13.
[30] 韓喜平, 朱禹璇. 現代化理論的溯源與創新[J].西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3):1-7.
[31] 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0-1081.
[32] 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的說明[N].人民日報, 2024-07-22(1).
[3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1949—1978)上冊 [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197-198.
[34]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1949—1978)下冊 [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674-676.
[35] 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47-148.
[36] 夏敏.中國式現代化的密碼:后發優勢如何從潛在轉化為現實[J].理論學刊, 2023(1): 23-31.
[37] 詹姆斯·C·斯科特.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M].王曉毅,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1.
[38] 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3-164.
[3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思想年編(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310.
[40]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16.
[4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261.
[42] 于光遠.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1981—198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34.
[43] 萬里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5.
[44] 趙樹凱.農民流動與政府管理[J].經濟體制改革, 1995(3): 37-44.
[45] 徐勇.農民流動、SARS與公民保障網絡[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3(5):24-29.
[46] 陳錫文,等.中國農村改革30年回顧與展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77.
[4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397-398.
[48] 王通.聯根式流動:中國農村人口階層分化與社會流動的隱蔽性特征[J].求實, 2018(5):77-89.
[49] 王通.脫嵌式社會流動:中國鄉城流動人口市民化的制度邏輯[J].求實,2022(3):59-74.
[5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192.
[51] 習近平著作選讀: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66.
[52]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0.
[5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590.
[54]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N].人民日報,2017-10-28 (1).
[55] 楊林,袁文全.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認定規則解析[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4(3):96-106.
[56] 焦長權.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上半程與下半程[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2):22-39.
[57] 劉偉.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與內在邏輯[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3(1):1-18.
[58] 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2023年版)[M].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64.
[59] 習近平.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處理好若干重大關系[J].求是,2023(19):4-8.
[60] 林毅夫,付才輝.中國式現代化:藍圖、內涵與首要任務——新結構經濟學視角的闡釋[J].經濟評論, 2022(6):3-17.
[61] 顧輝.過渡型階層結構與社會流動轉化機制:理論闡釋與現實分析[J].浙江學刊,2023(6):81-92.
[62] 劉建娥,凌巍.中國縣域城鎮化再抉擇——社會性流動的重大轉向與系統性構建[J].社會學研究, 2023(3): 23-44.
[63] 關于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
[64]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8.
[65]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8.
[66]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
[67] 蘭洋.中國式現代化對后發國家不發展理論的超越[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3):1-9.
The Social Mobilityin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such 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s the core content,and the social mobility in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structure is an inevitable accompanying phenomenon.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veal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Regional Individual” to “Global and Historical Propertie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which inspires us to find the deep law of social mo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s a late-modernization nation,China has a huge population and a large rural population,which determines the scale of migrant population and the difficulty to manage and serve the migrant population.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dopted different migrant population control mechanisms based on its national condition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and formed a vertical change process of strict control picture,spontaneous picture,empowerment picture and independent picture of social mobility. To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will ensure and promote the independent picture of social mobility,especially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rogram and regional coordination program that help individuals develop in an all-round way,constitutes the era task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Key words: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social mobility;rel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Historical Materialism;New Urbanization;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