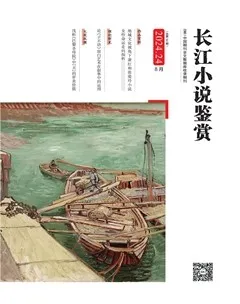論《子不語》中留白藝術在敘事中的運用
[摘" 要] “留白”是中國古代書法繪畫中所采用的一種創作手法,主要運用畫面中的部分留白,達到一種以少勝多的藝術效果。這種手法被應用在文學中就產生了文本中的“空白”,即作者未說明但隱藏在已知內容中等待讀者去探索和挖掘的部分。《子不語》在人物、敘事、環境等方面就運用了留白這一藝術手法,在塑造出眾多性格鮮明生動形象的人鬼精怪的同時,給讀者留下廣闊想象空間,極大地調動了讀者的主觀能動性和閱讀積極性,取得了“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
[關鍵詞] 《子不語》" 留白" 人物" 敘事
“留白”是中國書法中的一種創作手法,黑墨白紙,以墨色點染,并在畫面中留下一定的空白給人以想象的空間,對應哲學中老子“知白守黑”的辯證觀念,講求虛實相生,從而達到以少勝多的藝術效果。這種“留白”手法在許多文學創作中也呈現出獨特的魅力。如汪曾祺先生曾經所言“中國畫講究‘留白’,‘計白當黑’;小說也要‘留白’,不能寫得太滿。”[1]海明威也曾提出關于文學的“冰山理論”,這一理論是指冰山往往八分之一露于水面之上,八分之七匿于水面之下,展露于世人眼前的一角峰巒是隱藏在水面下冰山全貌的索引,用于文學中就是指讀者由文中所給出的確定明了的部分來想象感知作者未說明的部分。如果作品書寫太過直白味同嚼蠟,如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中總是把道理直抒筆端,則免不了有一絲刻意說教的意味;再如,《聊齋志異》把故事人物情節發展都描繪得完整全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讀者的部分想象空間,可能會使讀者感到略微乏味,而如果描寫又太過抽象與晦澀,使廣大讀者百思而都不得其意,則與作者的目的就背道而馳,同樣降低了文本的吸引力和可讀性。反之,如果把握合適的尺度,對文本做出一定程度的“留白”,則可以增加讀者的領悟與感知效果,達到“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
與著名的《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合稱為“明清三大文言小說”的是袁枚的《子不語》。游國恩曾在《中國文學史》中認為該小說:“作品內容也確乎是些供無聊消遣的鬼神怪異之談,沒有什么思想價值。”俞鴻漸則在《印雪軒隨筆》中提及:“降而至于袁隨園之《子不語》,則直付之一炬可矣。”直至近年來《子不語》才逐漸被人們所重視,出現了眾多研究成果,如閻志堅的《袁枚與子不語》、李志孝的《審丑:〈子不語〉的美學觀點》、王英志先生的《袁枚評傳》、韓石的《“惡”的展現:論袁枚和〈子不語〉》、程敬的《袁枚〈子不語〉的幽默藝術》、李莉的《淺析〈子不語〉卷五之〈奉行初次盤古成案〉》等。大家從美學的角度、語言風格的角度、敘事手法的角度、版本成書的角度或是對其中某類精怪的分析角度等進行了相應的研究和論述,而關于《子不語》中留白藝術的運用則沒有給予太大的關注。《子不語》作為一部志怪小說在一定程度上運用了這種“留白”手法,在增強故事神秘感的同時,也使得讀者有更好的閱讀體驗,從而達到“寓教于樂”的創作目的。以下我們就從敘事的角度對《子不語》中對空白藝術的運用進行論述,從文本各方面來對子不語故事中的“空白”進行研究和分析,走進《子不語》的“留白世界”,探索其中的魅力與獨特。[2]
作為小說這一文學體裁,敘事是其核心與靈魂,是最能體現作者情感表達的有機組成部分,是連接文本與現實的中間地帶。
一、敘事跳躍或敘事間隔
如《三頭人》一文中首段對于兄弟三人進入“神隱之境”的過程并未給出直截了當的描寫,而是通過周圍環境的變化來暗示本不該出現在山林曠野中的海潮江濤之聲,以及“身大如象”的黑牛。盡管文中沒有進行具體的明示,但是在此時他們其實已經進入了另一個世界中。如果直接寫明他們進入了另一個世界,敘述就變得索然無味,但如果省略掉這段描寫,后面關于三人的離奇經歷的情節發展就不自然,因此這一段作為鋪墊,使后面的情節順理成章、流暢而自然,極大激發了讀者的好奇心,同時給讀者留下了極大的想象空間。
敘事跳躍還體現在當作者在描述一個人或一件事時,突然引入另一個不相干角色的介紹,這種意義上的分離,會使情節突然中斷,從而空白就產生了,讀者也會因此產生更強烈的閱讀興趣,想要探索其中的奧妙和用意。而在這種探索中才能感悟到“空白”之處的深意和內涵。如《南山頑石》《酆都知縣》《大樂上人》《沭陽洪氏獄》《狐撞鐘》《藤花送終》等篇目。
如《藤花送終》一篇:
“吏部衙門有藤花一枝,系千年之物,古干如龍,一人不能合抱,葉覆三間堂寢,夏日尤涼,每與牡丹齊開。乾隆六年,塚宰甘公汝來,與果毅公納親選官堂上。甫唱名抽簽,而甘公薨于椅上,手猶執筆未落也。納公奏聞,上賞銀一千兩,命所屬經紀其喪。其夕,藤花盛開,結蕊發花,大香三日,較暮春時更盛十倍,不知是何征也。”[3]
故事先寫吏部衙門的千年藤花,轉而又談及吏部尚書甘汝來于選官之時病斃于衙門,上報皇帝后下令為其操辦喪事,最后又寫到千年藤花于其喪葬之夜“結蕊發花,大香三日,較暮春時更盛十倍”。從開始的藤花到甘汝來病故二者之間似乎毫無關聯,這種情節的中斷所造成的空白會使讀者陷入思考:吏部衙門是否果真有一人難以合抱的千年藤花,千年藤花與甘汝來直接又有什么聯系,甘汝來喪葬之時為何藤花會結蕊盛放,到底此為何征。當讀者對這些空白之處提出疑問并進行思考時,就會被作者的深層用意所打動。當讀者帶著疑惑去歷史中找尋甘汝來其人,會得知其為官之時恪盡職守,兩袖清風,作為一品大員,直至亡故,所留遺產不過八兩白銀,在腐敗橫行的官場里出淤泥而不染,而衙門的千年之藤就是他這一生的所作所為的見證者和守護者,所以在其去世之時,花生異象,為其慟哭。作者對故事進行了留白處理,“不知是何征也”道破不說破,使讀者在發現空白補充空白之后恍然頓悟,于無聲處感受深沉的悲憫之情。
再者如《南山頑石》一篇,故事開頭描述了主人公陳秀才于肅愍廟中卜問吉兇的神奇經歷,其被于公(肅愍)當作門生,并旁觀了肅愍與城隍的對話,最后被再三囑咐牢記“死在廣西,中在湯溪,南山頑石,一活萬年”[4]這十六字,后在李姓表弟的勸說下陪其一起到了廣西。接著故事又敘述了陳秀才在廣西與一風雅老翁的相識相知,二者日日吟詩作賦,往來親昵。此間并未提及絲毫不吉之端倪。此時就與之前的情景產生了中斷,從而產生了空白,讀者的疑問也就此產生:為何突然引入“風雅老者”,這與之前再三提及的“預言”有何關聯,和藹博學的長者如何會使陳秀才“死于廣西”,風雅老者到底是好是壞?此時這些問題會驅使讀者急于向后面的文本內容尋求答案,同時也為之后的情節發展做好了鋪墊,隨著故事的推進和發展,對老者身份的揭露和顛覆也顯得更加合理[5]。
二、敘事的分切交代
敘事的切分交代是指對電影中蒙太奇手法的運用,即把一個完整的人物或者事物,切分為若干局部用特寫鏡頭來進行展現。而體現在小說中,就是用文字來代替鏡頭,通過文字進行切分和重組,加之獨到的安排,來塑造人物營造場景。作者很少用過多的筆墨來對人物的外貌、個性、身份、所處環境、經歷(前世今生)進行集中細致的描繪,而是把這些切分開來,在情節發展中來逐一展現,袁枚就運用了這種分切交代的敘事方式。在《子不語》的敘事中,作者并不是把一個人物或一個場景一覽無余地展示在讀者面前,把讀者的想象空間全部消解,而是精心地把一個人物或場景切分開來,通過敘事的發展,時間的推進來一點點地呈現給讀者。如《鐘孝廉》一則,主人公是一位姓鐘的舉人,故事開頭以全知視角指出其生性耿直認真嚴肅的人物形象,接著利用敘述者視角的切換,由故事主人公鐘孝廉夢中驚醒,哭訴其夢中被問罪于鬼界衙門的經歷。這時由于最初的人物形象設定所產生的極大反差會使讀者產生疑問:如此耿直認真之人到底為何被帶至鬼界衙門審問?當讀者帶著疑問繼續閱讀時,故事卻并沒有立馬給出答案,而是由鬼神爺的四次審問來逐漸顛覆主人公的形象:第一次問罪,鐘孝廉述其不孝之罪——父母去世二十余年卻未安置其棺槨,鬼神爺言此罪為小;第二次問罪,鐘孝廉述其淫亂之罪——年少時奸污婢女,神仍言此罪為小;第三次問罪,鐘孝廉述其不禮之罪——總愛出口傷人譏諷他人之文,神曰:“此罪更小”;直至第四次問罪,才揭露出其被帶自此處受審的真正原因是因其不仁不義之罪——見利忘義,殺友圖才。
在這一過程中不斷重復其有重罪這一事實,把主人公所犯罪行一樁樁進行揭露,隨著時間的推進一點點透露給讀者,讀者的閱讀興趣也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增強,對答案的求知欲使其產生極大的閱讀興趣,與此同時也會跟隨主人公一同猜測故事的答案,此時讀者所知與主人公所知一致,直到最后才由鬼神差這一敘述者把答案公布出來,在解決讀者疑惑的同時又滿足了讀者的探索欲。但如果一開始就說出最終原因,就沒有一種遞進的效果和那種等待的“焦慮”和想得知答案的人迫切所形成的巨大期待以及強烈的文本吸引力。這樣的敘事獨具匠心,自始至終讓鐘某罪之根本藏而不露,在情節的推動中塑造人物的形象,緊抓住讀者的心,直至最后揭露出答案,其不仁不義淫亂不孝的形象躍然紙上,這樣的切分敘事能夠極大地調動讀者的閱讀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
三、結局的留白
《子不語》中敘事的留白還體現在故事結局的留白處理上。書中故事的結尾往往是一筆或一句,沒有長篇的議論說教,甚至對文中故事的人物或者事件都沒有一個清晰明確的交代,但這樣的留白式的結尾言有盡而意無窮,更引人深思,耐人尋味。
如《杜工部》的末句:“鬼大聲絕哭,夫人病隨愈。”《兩神相毆》的末句:“鐘本命護,自此乃改名悟。”《藤花送終》末句:“其夕,藤花盛開,結蕊發花,大香三日,較暮春時更盛十倍,不知是何征也”,以及《鏡水》的末句:“池開蓮花,瓣瓣皆作青色。”還有《黑牡丹》的末句:“花開時,數百朵,朵皆向大王神像而開,移動神像,花亦轉面向之。”這些句子甚至不能算作一個故事的結局,都是以一種潦草的交代作結,但正是這樣不辨是非的結尾給予了讀者無限的想象空間,同時增強了志怪小說的神秘色彩。所謂“若隱若現,欲露不露,反復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6],頗有“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7]之感。
四、敘事場景的留白
作為一部充滿了“怪力亂神”的志怪小說,必然少不了詭異神秘的場景塑造,而空白手法的采用則為這種塑造增添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1.“空白性”字詞的運用
《子不語》中使用了大量的“氣”“白”“霧”“光”
“茫茫”等空白性字詞,給人一種虛、淡、遠、捉摸不定的感覺,作者常借助這些特點的詞,從視覺感知入手,來打造出一幅神秘朦朧的視覺畫面。一些帶有虛淡、色淺的字詞,可以營造出一種虛實結合、無所不能的時空感,在空間上,具有渺遠幽深、神秘空靈的特點。如《酆都知縣》中知縣入鬼界時場景描述中的“入井五丈許,地黑復明,燦然有天光”,讓人不禁想到《桃花源記》中漁人進入桃花源時的場景描寫;再如《地窮宮》中主人公李昌明進入地窮宮前的所見之景“所到處,天色深黃,無日色,飛沙茫茫”[8]。
2.“夜化”場景的設置
大多數精怪都在夜晚出場,關于這種“夜化”環境,文中并未做過多的描繪與氛圍的營造,而是以少許的敘述作為骨架,搭建起陰森可怖的環境基調,再配合“月光”或“燈光”使恐懼形態化。如《趙大將軍刺皮臉怪》中“至二鼓,帳鉤聲鏘然”“燭光清冷”;《狐生員勸人修仙》中的狐生員于襄敏公夜讀西樓時悄然而至;《煞神受枷》中煞神來時也是“至二鼓,陰風颯然,燈火盡綠”;再者如《胡求為鬼球》中鬼怪現身時“夜三鼓”“明月如晝”;類似的還有《田烈婦》中女鬼現身時“日暮升堂,月色皎然”;《西園女怪》中的“一夕步月,至二鼓”;《縛山魈》中的“中秋夕”“月色大明”,此外在《馬盼盼》《蝴蝶怪》《冷秋江》等其余篇目中也有類似的場景,在這些場景中除“夜”這一環境被點明以及“燈”與“月”此類事物的安置之外,其余環境皆一筆帶過,這種留白可以調動讀者的已有的關于“鬼怪”“夜化”的經驗來完成場景的構建,給讀者留下了極大的想象空間,達到了以簡馭繁、以少勝多的藝術效果。
五、結語
關于古代文論中對留白藝術的討論也有很多,在《文心雕龍·隱秀》篇中,“夫隱之為體,義生文外,秘響旁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互”;鐘嶸的“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司空圖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所謂“不會用筆者一筆只做一筆用,會用筆者,一筆當作百十來筆用”。《子不語》的作者袁枚以盡可能少或平實的詞匯去接近事物的平常面目的風格,沒有過多繁復華麗的描繪,而是力求平凡,字里行間皆是率真、素樸,免去了生僻詞匯的刻意雕飾,語匯平實,拉近了讀者與《子不語》的距離。與此同時運用留白藝術使人物形象個性鮮明,故事情節絢爛起伏,敘事發展趣味橫生,絕不會有寡淡無味之感,反而更加引人入勝。該書作為袁枚唯一一部小說集,是其踏過萬里山河、結識四海之友的見證,其以獨特的藝術手法和廣博的取材途徑,為世人搭建起一個光怪陸離的神鬼世界,同時也為中國古典小說添上了一抹不容忽視的亮色。
參考文獻
[1] 徐新媛.論汪曾祺小說中的“留白”[J].綿陽師范學院學報,2020,39(3).
[2] (清)袁枚著,王英志注.《子不語》[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3] 涂年根.文學文本敘事空白的表述機制[J].東岳論叢,2016(11)
[4] (清)袁枚.《續子不語》[M].浙江出版集團數字傳媒有限公司,2013.
[5] 李致瑩.畫面“留白”的思考[J]藝海,2020(2).
[6] (清)陳廷悼.白雨齋詞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7] (南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8] 王柄羲.中國繪畫藝術與戲曲藝術中的“留白” [J].藝術教育,2020(3).
[9] 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M].北京:中華書局,1998.
(特約編輯 范" 聰)
作者簡介:李妍,西安外國語大學,研究方向為西方文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