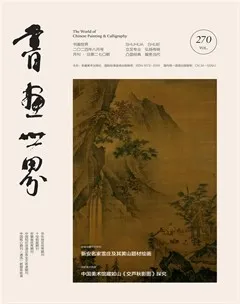“二爨”影響下的嶺南碑學審美建構


關鍵詞:嶺南;碑學;“二爨”;審美
一、“二爨”書法的審美特色
“二爨”指《爨寶子碑》和《爨龍顏碑》,二碑書刻時間較接近,故將二碑合稱。《爨寶子碑》立于東晉大亨四年,即義熙元年(405),《爨龍顏碑》立于南朝劉宋大明二年(458),兩碑前后相差53年。從書體演變上講,這一時期正是隸書向楷書過渡的重要階段,存在楷隸相雜的“合化”現象。此一時期的楷書既沒有脫離篆體平動筆法的圓轉形態,也沒有濾除隸書橫向開張的波挑筆畫,形成了平直體勢和波挑筆畫兼具的形態特征。楊守敬曾說:“真書入碑版最先者,在南則有晉、宋之大小二爨。”
“二爨”是云南邊疆書家在中原書風影響下的佳作,既有“銘石書”的共性,又有爨地的文化特色。其書風有共通性且屬同一地域、同一家族的傳世碑刻,我們將二碑放在一起探究,更能清晰地看到東晉至南北朝時期,西南邊疆書家在中原書風影響下對楷書風格樣式的探索。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盛贊“二爨”:“南碑今所見者,二爨出于滇蠻,造像發于川蜀。若高麗故城之刻,新羅巡狩之碑,啟自遠夷,來從外國,然其高美,已冠古今。”[1]806康有為所推崇的南碑傳世稀少,有其時代因素。東晉延續漢末禁碑之令,所以傳世碑刻不多。因“南碑又絕難得,其有流傳,最可寶貴”[1]804的稀缺性,在清代碑學大起、金石考據之風盛行的背景下,“二爨”之于書法史的真正意義才被激活,才會出現“較之魏碑,尚覺高逸過之”[1]806的審美認識。康有為繼承了碑學發展的成果,將對篆隸本體的研究擴大至廣泛的碑銘,尤以對魏碑的推崇意義重大。康氏言魏碑之美:“古今之中,唯南碑與魏為可宗,可宗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越,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1]826南碑因傳世稀少,也獲得與魏碑同等的評價,可見其藝術價值之高。康有為在《碑品》中將《爨龍顏碑》置于神品第一,力壓一眾北碑,成為碑學之典范。究其緣由,《爨龍顏碑》“下畫如昆刀刻玉,但見渾美;布勢如精工畫人,各有意度,當為隸、楷極則”[1]805,“晉碑如《郛休》《爨寶子》二碑,樸厚古茂,奇姿百出……皆在隸、楷之間,可以考見變體源流”[1]805。康有為贊其為“隸、楷極則”“神品第一”“正書第一”“書家鼻祖”,從這些美譽可以看出康氏對“二爨”的推崇。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書體處于隸、楷之間,可以考見字體風格的演變;二、書風符合康有為以雄強為美的書法審美觀;三、書法高古,為“隸、楷極則”,習之可上追篆、隸古法。“二爨”與其他楷法成熟的魏碑相比,其法更顯高古。拋開時間概念和地域的差別,僅從書法風格來看,“二爨”確有其獨特的書法價值。
《爨寶子碑》(圖1)用筆樸拙雄強,結體中正而不失開闔爛漫,字形或縱長端偉或方正寬博。用筆雖以方筆為主,但保留了大量的篆、隸筆意,如直線與曲線。直線使其字形穩固;曲線則增添字勢的柔和弧形之美,下垂以及斜曲的筆畫,圓暢流美,自然生動。此碑方圓曲直兼有,深得漢隸正脈。《爨龍顏碑》(圖2)較《爨寶子碑》在筆法上更顯細膩,出現了精雕細琢的楷法點畫,但在體式上仍以隸式為主,橫向舒展,疏朗有度,古意盎然。《爨龍顏碑》點畫之間呼應性極強,有明顯的輕重提按用筆,而且出現了橫畫向右上傾斜的意態。這是典型的魏碑成熟時期的“斜畫緊結”,較之《爨寶子碑》“平畫寬結”的平穩,有了體態上的變化。二碑都以隸為體,但時間較早的《爨寶子碑》保持了隸體的純粹,而《爨龍顏碑》則在隸體的基礎上強化了楷法。和而不同、各有特色才是書體演化發展的正確路徑,“二爨”表現出了不同的書法審美風尚。
二、嶺南的碑學環境
碑學是時代的產物。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書學》中曾說:“從前的人,本來并沒有所謂的‘碑學’,嘉、道以后,漢、魏碑志出土漸多,一方面固然供給幾位經、小學家去做考證經史的資料,又一方面便在書學界開個光明燦爛的新紀元。”[2]碑學與帖學之分實自清人開始。阮元在清嘉慶十六年(1811)創作的《北碑南帖論》,為早已展開的碑學運動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和支撐:“古石刻紀帝王功德,或為卿士銘德位,以佐史學,是以古人書法未有不托金石以傳者。”[3]其以碑佐史的思想為王國維提倡的二重證據法提供了考古與文獻研究的經驗積累。嶺南碑學的興盛和壯大基于嶺南本土金石遺存和外來文化的共同影響。其中以翁方綱、阮元、包世臣、伊秉綬、何紹基對粵地碑學的影響最大。他們在金石學上造詣深厚,大力推動了嶺南地區經學、文字學、金石學的發展,引領嶺南學子重振樸學之風。
翁方綱曾三任廣東學政,在粵地生活長達九年。其專著《粵東金石略》收錄了嶺南境內大量的金石碑刻,系統整理了粵地的書法遺存,填補了嶺南金石學研究的空白,開創了粵地碑學書史研究之先河。
阮元曾任兩廣總督兼任廣東學政,創辦學海堂并自任山長。其教學與研究提倡實學,重經史文理,反對已經被反復咀嚼、形義破碎的理學,以及限于程式、千篇一律的八股文風。時人評價:“阮元督粵,以粵人不治樸學,創學海堂以訓士。”[4]這與阮元重樸學、提倡考據、講求實證的學風有關。學海堂的創辦為廣東學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礎。其以經世致用為宗旨的辦學思想,不僅影響了嶺南學風,對清代樸學研究的影響也極為深遠。阮元做官,每到一地都有訪碑立著的傳統,著有《山左金石錄》《兩浙金石錄》《石渠隨筆》等金石學著作。嶺南地區出土的大量碑刻,為阮元主持編撰的《廣東通志》提供了實證,集清代嶺南史學研究之大成。故而清代學術界評價阮元:標領文壇數十年,海內尊之為學界泰斗。這樣的大學者對嶺南文化藝術體系建構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
翁方綱、阮元從金石碑刻考據研究入手,為嶺南奠定了扎實的樸學研究基礎,從書學建構上為碑派書法提供了理論支撐。咸豐年間學者李廣田大力提倡北碑,開創嶺南碑學,又由于潘存、鄧承修等人的推動,碑學漸為嶺南書家所重視。清末,康有為從理論與技法層面推進碑學研究,其《廣藝舟雙楫》是嶺南乃至整個中國碑學研究之大成。康有為書學思想的核心是尊碑,尤以魏碑為最。康有為對魏碑的研究是在篆、隸體式縱向演變脈絡上延續的,他說:“漢末波磔縱肆極矣。久亦厭之,又稍參篆分之圓,變為真書。今觀元常諸帖、三國諸碑,皆破觚為圓,以茂密雄強為美,復進為分。”[1]775-776“北碑當魏世,隸楷錯變,無體不有。綜其大致,體莊茂而宕以逸氣,力沉著而出以澀筆,要以茂密為宗。當漢末至此百年,今古相際,文質斑璘,當為今隸之極盛矣。”[1]776“南、北朝碑莫不有漢分意,《李仲璇》《曹子建》等碑顯用篆筆者無論。若《谷朗》《郛休》《爨寶子》……皆用隸體。《楊大眼》《惠感》……波磔極意駿厲,猶是隸筆。”[1]796-797可見,在南北朝的書法體式中,篆書筆意保留較多,又以隸筆增加古意。康有為云:“真楷之始,濫觴漢末。若《谷朗》《郛休》《爨寶子》……皆上為漢分之別子,下為真書之鼻祖者也。”[1]816康有為通過對篆、隸體變脈絡的分析,讓我們看到了魏晉楷書在筆法體勢中對篆、隸古法的保留,通過魏碑構建了清代碑學的宏大框架。在碑學體系中,康有為著重分析了源流演變,其中以“二爨”為代表的魏碑具有鮮明的特征。康氏碑學書法觀以樸學為底,注重書體演變的脈絡傳承和風格演變。其碑學研究往往兼具多重因素,但始終未完全脫離篆隸體對碑學的滋養,這與康有為深受嶺南金石學的影響有密切關系。由此可見,嶺南的碑學淵源是根植于樸學的,基于清代嶺南金石學研究的深厚沃土。
三、“二爨”在嶺南的接受
一個地區的審美接受與當地文化有密切聯系,爨地是珠江之源,而嶺南屬于珠江流域,從源頭蔓延而來的爨文化在地理空間上具有廣泛的延伸性,當爨文化元素與嶺南本土審美相結合,便產生了獨特的藝術語言。“二爨”的書法形態蘊含著深刻的文化內涵和高古的書法審美,具有強烈的變體意識和雜糅形態,在取法上具有延續發展的可能性。其在嶺南地區被廣泛接受是因為嶺南地區受到了近代政治、思想、文化、潮流的沖擊,具有了創新求變的精神和意識。在文化潮流影響之下,清代碑學在嶺南大興。隨著康有為等人對“二爨”的大力推崇,爨體書法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是近百年來碑學求新求變、持續發展的結果,具有審美再創造與美學再發現的意義。
李文田是嶺南早期碑學建構中的重要書家,他最早根據“二爨”碑刻風氣質疑《蘭亭序》真偽,引發了嶺南地區學者、書家對“二爨”的討論。這種對《蘭亭序》書風過于妍美與成熟的質疑并未隨著朝代的落幕而結束。1949年以后,“蘭亭論辯”再一次將“二爨”及南朝王氏墓志作為楷書體系上的重要風格代表與《蘭亭序》進行探討。雖然這種依此質彼的審美認識有時代的局限性,但引發的思考對書法審美風格的創造意義是巨大的。
在嶺南書家筆下,康有為“奇變”的書學理論賦予了“二爨”書風的新面目—取其風骨與意態。這是對“二爨”書風的繼承與創新,使得粵地碑學書法突破舊有的審美范疇,融入了粵地山水涵養的重意韻的審美偏好,使原本笨拙的字體表現出了秀雅而溫潤的骨感。粵地有書法創新的思維意識和物質條件,從陳獻章到康有為,他們在書法創作上都進行了不同時俗的探索。嶺南書家在對“二爨”的字式取法上,堅持隸、楷一體的高古本質,書法奇巧而顯異態,呈現出了別具一格的面貌。其中以嶺南書家曾習經(1867—1926)、范家駒(1882—1944)、秦咢生(1900—1990)、賴少其(1915—2000)、饒宗頤(1917—2018)等人對爨體書法的探索最具代表性。
從現今有資可考的書史記載來看,在碑版拓本流傳較為單一的時代,書法傳承多以師徒相授為主,故嶺南習爨風氣必有脈絡可考。李文田、阮元、翁方綱、包世臣為嶺南書法注入碑學基因,康有為拓而展之,使嶺南成為碑學重鎮。但嶺南早期碑學理論與創作實踐者都較少進入“二爨”的書寫本體,而是在理論體系上確立了“二爨”不可撼動的經典地位,在書寫中具體表現為對“以碑入帖”碑學觀的積極探索。誠如李瑞清在臨摹《爨寶子碑》時說:“全用翻騰之筆,以化其頓滯之習。”這種筆法對嶺南書家習碑的影響是久遠的,也正是筆法的不同使嶺南碑學產生出具有寫意性的書寫面貌。在碑帖融合觀念的影響下,早期嶺南書法的代表人物雖多尊“二爨”,但極少有人對“二爨”進行精準的實臨,多是取其意態與風神,進而融會在其他書體的創作中,增加了書法構成中元素的多樣性。從書法繼承來看,這是對爨體成果的部分借鑒。真正從書法本體將嶺南爨體風氣推向全面接受者當數曾習經和范家駒。
曾習經自幼秉承家學,聰穎過人,享譽文壇。其與康有為同鄉,深受其政治革新思想影響,又與梁啟超交往密切,在嶺南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光緒十八年(1892),曾習經考中進士,曾任戶部員外郎。他的書法深受嶺南碑學的影響,博采眾家之長,于漢魏碑版、晉唐小楷均有涉獵,尤以“二爨”書法最負盛名。其“二爨”書法取南北碑刻楷書之拙趣,以圓化方,點畫厚重,有書卷清氣。
范家駒,光緒三十年(1904)中進士,曾任法部會計司郎中。一生臨池不輟,師法漢隸魏碑,對“二爨”情有獨鐘。我們從其作品中可看出對《爨龍顏碑》字形結構的巧妙運用,字式橫向開張,筆畫含蓄有力,骨法洞達,有天然老成的氣象。
嶺南習爨書家在時代的影響下也漸漸有了審美的時代性,這是區別于嶺南早期碑學中的古典元素和習爨初始面貌的一個重要特征。秦咢生一生鐘情《爨寶子碑》,其書法(圖3)多學此碑。在他的大力推廣下,學習爨體書法的人數猛增,大量牌匾題字成為嶺南獨特的文化標識,在大眾傳播視域下實現了“爨體”書法的普及。書法拓本可歸納為圖像,具有顯著的社會傳播力,在書法傳播的審美接受過程中才能實現其藝術價值,但對書法審美的建構分析還須納入特定的歷史情境中,客觀地進行研究與探尋。最早傳入嶺南地區的《爨寶子碑》初拓本,由原云南空軍學校校長劉毅夫贈予廣東省主席陳銘樞,值李濟深壽誕時,陳銘樞轉贈李濟深,李濟深習書數年,均練習此碑。此拓本后歸李濟深侄子李然。此拓本中“鴻漸羽儀”之“鴻漸”水旁完整無缺,“道兼行葦”之“兼”字、“抽簪俟駕”之“俟”字、“春秋廿三”之“三”字、“穆穆君候”之“君”字、“在陰嘉禾”之“在嘉禾”三字、“鳴鸞紫闥”之“鳴”字尚未破損,“瀣我貞良”之“我”字亦清楚能辨,尤其是最后之“玉”字完好無損,顯為石未缺時所拓。秦咢生曾將此拓本影印出版,在當時書法資料尚不完全普及的情況下,此精良拓本的出版使爨體書法得到了廣泛的傳播,間接促進了嶺南地區書法審美接受意義上“二爨”效應的產生。
賴少其以書畫聞名于世,其書法(圖4)主要取法金農和《爨寶子碑》,以書寫性強化碑味和爨味,牢牢把握爨體創變的特點,具有鮮明的中正雅韻之拙趣。
饒宗頤的爨體書法( 圖5)注重對氣脈的承接,在典雅清麗的書卷氣中,不失奇巧拙樸之感。他曾說:“學習書法應該二王與二爨相資為用……《爨龍顏碑》及《爨寶子碑》,用筆沉厚,特有一種古拙的意念,而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書法飄逸絕倫。故此二者兼學,在二爨中求古拙,在二王中求流麗,方能不顧此失彼。”這種兼學并優的取法觀念是饒宗頤的書法指導思想,他將心中的氣韻化為筆下生生不息的綿綿勁力,展現出了學者的雅逸。這三位以爨體為基的嶺南書家,從書法審美建構的不同層面探索了爨體延伸發展的可能性,在古今元素的融會變通中展現了嶺南碑學的審美包容。
碑派書家的審美建構及其爨體書法資料在嶺南地區的傳播,帶動了嶺南書家學習爨體的風氣。在這種風氣的持續影響下,嶺南碑學的涵蓋范圍和內涵逐步擴大,構建了集金文、漢碑、魏碑、“二爨”于一體的碑學體系。
結語
作為滇中書法的代表,“二爨”延續了篆、隸體式演變下碑學線條的中實飽滿、字形的端莊雄偉。雖然處于楷、隸體態演變的歷史階段,但從魏晉南北朝廣泛的書法范圍來看,“二爨”有發展延續的確定性因素,“奇”“古”“丑”“拙”的藝術特色也符合碑學審美觀。書法風格的接受和闡釋在時代背景下因人而異,康有為對“二爨”的推崇是在他“揚碑抑帖”思想影響下的一種價值選擇,符合他變法求新的思想需求。康有為的大力推崇,最終確立了“二爨”之于碑學不可撼動的經典地位。此后,“二爨”在嶺南迅速傳播,廣為時人所喜歡,經過幾代嶺南碑學書家和理論家的共同努力,“二爨”早已成為嶺南書法的代表,成為嶺南獨特的文化標識和歷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