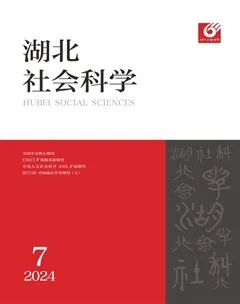批判視域中的威權民粹主義


摘要:當前西方的民粹主義研究者放棄了傳統理論左右二分的模式,而采用“威權民粹主義(AP)”這一概念,并積極引入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來分析民粹主義中的威權政治因素,探究民粹主義滑向暴力運動與極權的根源。通過對西方社會現實的考察可以發現,在造成威權民粹主義的原因中,除政治經濟環境外,心理—文化因素以及信息技術等也發揮了重要作用。西方學者認為,應當警惕民粹主義中的威權因素與極端傾向,遏制其對全球民主的腐蝕,并嘗試將其吸收、納入到西方傳統政治框架之中。然而,這些理論愿景正面臨著諸多現實阻礙。
關鍵詞:威權主義;民粹主義;美國;批判理論
中圖分類號:D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477(2024)07-0047-13
收稿日期:2024-06-01
作者簡介:吳鑫(1991—),男,哲學博士,西北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陜西西安,710072)。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人類文明新形態對馬克思主義文明觀的原創性貢獻研究”(22XKS024)的階段性成果。
①TAP:Timbro Authoritarian Populism Index.
②該調查數據自2019年之后停止更新,因此2020年至今的數據暫缺。
③詳細數據與報告可見TAP官網:https://populismindex.com.
一、“威權型”民粹主義的興起與研究現狀
民粹主義在當今實踐中往往表現出“威權政治”的特征,乃至滑向暴力、專制的極端,這種情形在全球各地已相當普遍。過去十幾年間,在拉美、東南亞以及非洲,民粹主義黨派及其領導人執政后的一系列舉措不斷顛覆民眾對民粹主義本身的認知。在西方社會,民粹主義導致的政治極化和對立也越來越突出。
從地區分布來看,歐洲是威權民粹主義上升最快的“重災區”。瑞典著名研究機構Timbro曾對歐洲民粹主義的發展歷史進行深入調查,并逐年發布“威權民粹指數”(TAP)①,根據2019年的數據②,新興民粹主義黨派在全歐洲選舉中獲得的席位比例已從1980年的10.8%上升到22.1%,其中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所占比例由1.1%上升到15.7%,超過左翼民粹主義兩倍多(后者為6.4%),2019年歐盟議會選舉中民粹主義黨派所占比例則接近24%,其中右翼民粹占七成以上。若從選民角度來看,全歐洲有26.4%的民眾在全國性大選中投票支持“威權民粹主義黨派”③。
圖1為1998年與2018年歐洲范圍內民眾向不同派別政黨的投票比例,可以看出,“威權民粹主義黨派”與自由主義黨派、綠黨的得票率呈上升趨勢,其中前者的增幅最大,社會民主黨、保守黨等傳統黨派的得票率則明顯下降。若從選舉結果來看,2010年前后,左翼與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歐洲各國議會中所占的席位同樣在迅速攀升(見圖2)。
Timbro的報告也指出,威權民粹主義政黨并不是一個統一的指稱,其內部也分歧重重并且同時存在左右兩個傾向,但其至少具有兩方面的共同點:其一,威權民粹主義政黨對憲法、法治、議會等傳統政治模式普遍缺乏興趣與耐心,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它們要求加強直接民主,減少國家機構與行政過程的緩沖、中介作用;其二,對強大的民族國家的訴求是威權民粹主義的典型特征,反全球化、反歐盟、反北約,要求建立人民的(本民族的)、具有強大能力的國家是其共同追求。自難民危機以來,威權民粹主義勢力在土耳其、匈牙利、波蘭、西班牙等地不斷增長,并日益滲透到法國、德國等歐盟核心國家。即使在民粹主義政黨尚未取得政治成果的國家,其仍然可以對主流政黨、公共話語和政策議程施加巨大的“勒索”壓力(如英國獨立黨在催化英國退出歐盟中所起的作用),在可預見的未來,俄烏沖突等外部因素將繼續加深上述危機。
與此同時,在拉美、非洲等地,威權民粹主義也在迅速發展。以南非為例,斯泰倫博斯大學(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近期的一項研究發現,過去只有少數人認為某種形式的威權政府是管理國家的好方法,但調查數據顯示,持這一觀點的人數自20世紀90年代至今增長了一倍多,2017年46%的受訪者表達了這種情緒;非洲人國民大會(ANC)等傳統政黨正在失去選民的支持,而以非洲基本運動、人民革命運動、“黑人第一、土地優先”1等為代表新興少數黨派則公開投向威權民粹主義,一些政黨甚至走向了煽動分裂、政治暗殺的極端。
在此背景下,傳統理論關于左翼民粹主義(LP)與右翼民粹主義(RP)的劃分似乎失去了理論效力,許多美國學者開始引入“威權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即AP)這一術語。正如肖恩·哈廷(Shawn Hattingh)所指出的,“盡管右翼民粹主義更容易表現出威權主義的特征,但在一些地區情況則完全相反……因此,(采用)威權民粹主義這一表達能夠打破左右之分——這一劃分往往將我們束縛于并不重要的表象之中——進而探究民粹主義自身走向權威、獨裁的根源”2。
威權民粹主義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關于英國撒切爾主義及美國里根政策的論述。安妮·芒羅-柯(Anne Munro-Kua)在20世紀90年代發表的《馬來西亞的威權民粹主義》3則是第一部系統、全面研究威權民粹主義的著作。本世紀以來,以道格拉斯·凱爾納(Douglas Kellner)、杰米哈·莫洛克(Jeremiah Morelock)等為代表的美國學者將相關研究不斷推向深入。在這之中,左翼與右翼學者都將紛紛轉向法蘭克福學派,嘗試延續其在上個世紀尚未完成的工作,并從批判理論的視角與框架出發,分析威權民粹主義的內在成因及現實影響。其中,影響較大的著作有凱爾納所著《美國噩夢:特朗普、媒體奇觀與威權民粹主義》4、莫洛克主編的《批判理論與威權民粹主義》5、艾弗·克魯(Ivor Crewe)及大衛·桑德斯(David Sanders)主編的《威權民粹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民主》6、皮帕·諾里斯(Pippa Norris)的《文化反彈:特朗普、英國脫歐與威權民粹主義》以及勞倫·朗曼(Lauren Langman)的《從不滿到動亂:今天的威權民粹主義》等。當前,威權民粹主義的概念正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接受和使用,盡管立場、觀點各有不同,但在總體上,“威權民粹主義”一般都被用來描述表現出明顯權威傾向、專制特征的民粹主義運動及政治實踐,例如使用暴力手段驅逐、迫害那些不被認為是“人民”的群體。易言之,在不明確區分左右的前提下,任何民粹主義運動若表現出某種威權性訴求、手段,或導向威權政治后果,都可納入威權民粹主義的范疇之中。
相比于多黨制國家,美國當前政治所受的直接沖擊較小,但多數美國學者及政客的共識是,威權民粹主義對美國民主的挑戰是真實的,并且這種威脅正在日益增長。斯蒂芬妮·斯坦利(Stephanie Stanley)指出,“美國歷史有著豐富的民粹主義敘事,歷史上的民粹主義思想深刻影響了當前的政治運動”7,她認為,特朗普及茶黨運動的“政治血統”(Political Lineage)可以追溯到獨立戰爭時期的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19世紀末的人民黨(The peoples party)運動、20世紀70年代的新紀元運動(New Age Movement)、里根主義等。美國著名政治歷史學家邁克爾·卡津(Michael Kazin)也曾將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林肯等人看作代表人民反抗精英的民粹主義英雄。這表明,在政治與文化傳統層面,美國自立國之初所倡導的自由、平等、獨立等理念與民粹主義有著難以分割的聯系,這也是導致當前美國社會一系列對立爭端的內在原因。
從現實來看,威權民粹主義在美國也呈現上升的趨勢。諾里斯的一項近期調查表明,大約44%沒有大學學位的美國人“希望出現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為此甚至不必費心國會或選舉”1。達里博爾·羅哈奇(Dalibor Rohac)在《美國威權民粹主義的驅動因素》一文中也指出:“威權民粹主義吸引力的上升與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下降、黨派兩極分化加劇齊頭并進……對美國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中期,五十年前,近四分之三的人口信任聯邦政府,這個數字在今天已經下降到25%以下……而即使是在(作為威權民粹主義代表的)特朗普執政的第一年,這種下降仍在繼續。”2顯然,特朗普競選連任的失敗,以及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的乏力表現并不意味著民粹主義的消退,相反,這一現象只是兩黨制穩態結構對民粹主義浪潮的暫時分流與紓解,是政治形式上對美國社會分裂、對立事實的暫時掩蓋,而這只能推遲并醞釀更大的矛盾。
二、威權民粹主義的成因:三重分析維度
1934年,霍克海默及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主要成員開始流亡美國,直到1950年研究所遷回西德,在此期間,威權政治成為學派第一代思想家共同關注的核心問題。圍繞納粹德國、蘇聯及美國的社會現實,批判理論的考察“涵蓋了權威人格的心理學批判、權威與家庭的社會學批判、極權國家的政治經濟批判以及文化轉型、社會發展中的一般性權威”,[1]形成了許多有價值的調查報告與理論著作,為相關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材料與經驗。
法蘭克福學派在美國的理論遺產經由馬丁·杰伊(martin Jay)、凱爾納、哥倫比亞學派等后學得以傳承。當前美國學者對威權民粹主義的研究也大量借用學派的思想資源,西奧多·阿多爾諾(Theodor Adorno)關于權威型人格的量化研究,以及弗洛姆(Erich Fromm)、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等關于文化、社會結構中的權威模式等是美國學者關注的熱點。在關于美國威權民粹主義的形成原因的分析中,批判理論所創立的三重分析維度,即社會學批判、心理—文化批判與政治—經濟批判被廣泛采用。
(一)政治—經濟維度
按照主流的觀點,經濟因素是某一思想與政治運動產生的根源,以往的研究也常常將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難民危機看成是世界范圍內民粹主義高漲的首要原因。但美國學者認為,經濟因素與民意調查數據中對威權民粹主義者的支持關系不大,一些新的調查也表明,造成歐洲民眾支持右翼民粹主義的原因中,文化與政治問題比經濟利益更重要。不過,這并不代表經濟因素無足輕重,只是其對權威民粹主義的影響程度與方式需要進一步考察。
1.經濟因素的“前效應”
索爾特·達瓦斯(Zsolt Darvas)等人的一項調查顯示,近三十年來,美國排名靠前的大公司高管薪酬增長了997%,遠超普通工人工資的增長速度,二者的比例由20∶1上升到了87∶1,社會整體收入不平等的差距已經接近1920年代末的峰值3。但達瓦斯的研究也表明,收入水平兩極化的拉大與選舉結果之間的關系很弱,因而不能作為因果關系的證據。此外,在收入不平等程度低得多的國家(如奧地利),以及過去十年收入不平等率下降的國家(如英國),威權民粹主義仍然呈上升趨勢。
因此,經濟因素對威權民粹主義的影響并不是通過底層或兩極分化來實現的,羅哈奇認為,這種威脅集中在中等收入階層以及技能勞動者群體之中。從實際看,經濟危機、移民涌入、全球化等帶來的威脅對高技術行業和底層工作者影響較小,前者(如工程和科學領域的高薪工作者)一般不能輕易被取代,而后者(如餐飲或保潔工作)受流動資本與產業鏈調整的影響也很小,恰恰是中間階層的工作者受到全球化與移民的沖擊最大。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投票支持特朗普的選民很大一部分來自中產階層,以及經濟、產業受到全球化影響最大的地區,這一結果支持了上述結論。
另一個重要的事實是,經濟因素對威權民粹主義的影響并不是直接的、顯性相關的,而是表現為一種“前效應”。美國經濟學家、商務部官員杰德·科爾科(Jed Kolko)指出,美國民眾對經濟及工作的焦慮主要來自未來的不確定性,這種預期性導致經濟因素對政治產生了前置影響。易言之,傾向于支持威權民粹主義以及其他極端政治派別的民眾并不都是在現實中遭遇了經濟困難,許多人僅僅是感受到了未來的不確定性與威脅。在美國文化中,工作仍然是維持社會關系和尊嚴感的重要手段,缺乏工作所帶來的絕望與負面影響是深遠的;另一方面,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以及經濟增長的模式,從美國官員到投資者、普通民眾,往往更容易受到預期因素的影響,對未來危機的擔憂有時甚至超過了現實。亞瑟·布魯克斯(Arthur Brooks)曾提出“尊嚴赤字”(Dignity Deficit)的概念,突出了未來因素對美國工薪階層心理狀態及政治訴求的巨大影響。布魯克斯指出,“尊嚴赤字是一種強大的政治資源,多數肆無忌憚的政客已經能夠熟練使用這種資源來喚起民眾的普遍的憤怒”1。
在美國,經濟因素造成的不滿還有其他潛在根源,例如教育差距與向上流動的障礙。歷史上,包括有色人種、女性、貧民等邊緣群體所接受的低水平教育限制了他們躋身上層的可能,美國大學也被詬病為精英教育的保留地。但根據WIA在2019年發布的報告,美國大學中女性占比已經超過男性,擁有大學學位的男性占總人口的比例為34.6%,女性則為35.3%,在研究生教育階段,這一比例分別為8.7%與10.4%2。該報告還指出,受教育因素影響,在過去三十年中,美國男性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力在四個維度上均呈快速下降趨勢,這包括技能獲取、就業率、職業地位與實際工資水平。與此相關的一些報告則暗示,隨著平權運動的發展以及美國教育結構的變化,在未來幾十年里,白人男性工作競爭力表現不佳的狀況可能會永久化。
即使假定上述預測基本準確,邊緣化的群體要在工作競爭與經濟地位上對白人男性取得絕對優勢仍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在現實中,經濟擔憂所產生的政治效應卻提早展現出來,勞動力市場的危機帶來的心理作用要遠大于其對社會經濟的實際影響,因此,經濟因素對威權民粹主義的推動不應被過分夸大。在較為富裕的北歐福利國家,日益壯大的右翼極端勢力所主張的反移民、反全球化,也很難歸咎于經濟因素。
2.政治兩極化與信任下降
金融危機之后的美國經濟雖然已經逐步復蘇,但其特點仍然是生產率增長緩慢和迫在眉睫的結構性變化。經濟復蘇帶來的社會利好也并不平等,某些部門和地區表現很好,而其他部門則從未回到正軌。這一現狀加劇了政治上的兩極化,很多民眾認為,危機后采取的緊急措施與復蘇政策僅僅使少數人受益,而對危機負有責任的精英也沒有受到追究。由此,政治上的“腐化精英”與人民的對立日漸凸顯,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利益集團和強大的競選捐助者能夠直接影響選舉結果,而不合理的選區劃分也限制了選舉競爭;二是政府內部缺乏直接的政治問責制,以致官僚機構能夠在不考慮公民意愿的情況下制定政策決定,在某些時期,行政部門甚至可以在沒有立法支持的情況下制定政策。
從選舉過程看,高收入群體的投票率遠超低收入者,從而進一步擴大了二者的政治影響力差異。根據統計數據,在2012年的總統選舉中,收入低于一萬美元的民眾投票率只有約47%,而收入超過15萬美元的群體投票率則達到80%以上;而在2016年的選舉中,低收入和高收入選民的登記率差距為20個百分點①。此外,選舉中的政治支出越來越集中在最富有的少數人身上,2012年選舉中花費的所有資金中,幾乎有一半來自前1%的富裕階層②,而2016年投票人口中前0.01%的捐款比例從1980年代的16%增長到40%。在2020年的選舉中,數量龐大的低收入選民成為兩黨競爭的重點,加上新冠疫情、經濟蕭條、種族主義等因素的影響,邊緣群體與貧民的政治訴求與參與度有所提高,但政治兩極化的總體格局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改變。
富裕階層的政治影響不僅體現在選舉支出與投票率上,還存在于廣泛的“政治游說”(Lobbying Politics)中。游說制度在美國由來已久,多元主義理論家認為游說行為在整體上對政治平衡與自由民主是有利的,但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利益集團的游說已經形成一個龐大的產業,其負面影響也在不斷擴大。早在2012年,凱·施洛茲曼(Kay Schlozman)等人就指出,大公司和商業利益集團的游說對政策影響越來越大,已經威脅到了民主制度本身。施洛茲曼等的調查數據顯示,代表大企業、商業集體的組織占所有游說支出的72%,而勞工組織僅占1%③。另據美國響應式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的調查發現,大公司、貿易協會和其他有影響力的組織每年花費數十億美元游說國會和聯邦機構。一些特殊利益集團在華盛頓設立了獨立的游說公司,另一些游說者則直接從事政府內部工作,表1為美國游說集團支出排名列表④。
從1998年到2022年,游說支出總額排名前列的為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美國地產商協會(National Assn of Realtors)、美國醫院協會(American Hospital Assn)和康卡斯特(Comcast Corp)等大公司或商業聯盟;上述集團在2022年的游說支出大致也排在前列,而亞馬遜、Meta、谷歌母公司Alphabet等新興科技巨頭的游說支出則是近十年才開始迅速增長,但總額仍難以超越前述大集團。美國商會歷年游說總支持接近18億美元,與此相比,過去數十年來美國所有工會總計花費不到7億美元。
在美國民眾看來,政府被組織良好的特殊利益集團所俘虜,對公民的訴求與擔憂的回應則越來越少。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等調查發現,普通美國人對政府的公共政策幾乎沒有影響力,“即使絕大多數民眾(70%—80%)贊成某項政策變化,其實際執行仍達不到預期的一半”。[2]此外,選舉制度中極端的選區劃分與無限制的競選支出助長了影響,扭曲了民主政治的進程,由此造成的結果是,政治機制傾向于將利益集中在富人身上,但將政策成本分散到整個人口上(特別是邊緣化群體),普通民眾在地區選舉中雖擁有一定的權利,但在聯邦一級沒有得到公平的代表。
與此同時,美國政治與政黨也變得更加兩極分化。民眾對美國民主的一個普遍抱怨是,主要候選人在政策立場上幾乎無法區分,這表明政黨缺乏明確的、堅定的原則。公共選擇理論對此的解釋是,為了利益最大化,政黨需要將精力集中在爭奪中間選民上。然而,近十幾年來的變化是,美國國會兩黨在一般性事務政策上變得越來越同質化,但在重大問題上的立場分歧卻正在擴大。除選舉程序外,國會的戰略分歧也是兩極分化背后的一個重要因素。由于對選民基礎忠誠度的日益關注,兩黨經歷了實質性的變化——從1970年代共和黨的南方重組開始,黨派的選民基礎越來越固化,當前的共和黨主要以南方保守白人集團、中產及以上階層為基礎,而民主黨則以中下階層、少數族裔、移民為基礎,這使得二者在重要立法上很難有達成妥協的機會。
政治兩極化以及民眾的政治無力感導致對政府信任的下降。一些學者認為,美國民眾對通過政治手段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抱有過度的、不切實際的期望,由此帶來對政府的不滿。但實際上,民眾的親身感受很容易讓他們產生如下判斷:政客們無法解決實際問題可以簡單地用黨派爭吵來解釋,即公共政策問題的解決辦法是顯而易見的,缺乏善意是取得進展的主要障礙。這種觀點帶來的一個很自然推論是,需要選舉一個無黨派的局外人(例如一個專制的民粹主義者),以便使其脫離傳統政黨斗爭與民主程序的束縛,進而專注于解決民眾切實關心的問題。這一觀點在當前的美國民眾中越來越有吸引力,由此導致了今天的超黨派政治,為威權民粹主義創造了肥沃的土壤。
(二)心理—文化維度
約瑟夫·朗茲(Joseph Lowndes)曾指出,“美國民粹主義的兩種變體中,左翼主要針對經濟精英,而右翼則主要針對文化精英”。[3]類似的,大衛·巴克(David C.Barker)等人也曾在2020年對美國民粹主義進行了一項量化研究,以考察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系數。巴克等人發現,美國的“經濟民粹主義者”(Economic Populists)群體以年輕人、女性為主,他們更加世俗、開放、人道,支持平權、進步,更加傾向于民主黨;而“文化民粹主義者”(Cultural Populists)則主要由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工薪階層、年長者構成,他們往往具有反智主義、民族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紀律主義等傾向,更加關注自身利益且不容易接受政治妥協。
巴克等人的調查數據顯示,“約12%的受訪群體表現出兩種民粹主義傾向的融合……但經濟民粹主義(EP)與文化民粹主義(CP)是完全不同、幾乎沒有重疊的兩種形態,兩個群體也幾乎沒有共同的價值觀與世界觀”。[4]在美國、拉美以及歐洲,特別是一些經濟發達、社會福利良好的國家,經濟—政治因素與心理—文化因素在民粹主義形成上所帶來的獨立影響是日漸明顯的事實,某些情況下,文化因素的作用甚至高于經濟因素。
1.心理基礎:性別、種族與身份
巴克等人的研究顯示,性別與兩種民粹主義呈現明顯的正相關,即男性更加傾向文化民粹主義,女性則相反,而前者則具有典型的威權主義色彩。可能的解釋是,男性更加在意政治身份、地位,而女性則關注具體的經濟及生活事務。另一方面,性別歧視本身對威權民粹主義也有較大影響。右翼的、文化的民粹主義往往反對墮胎、控槍、平權運動,并表現出對女性、移民等少數群體的歧視。阿巴斯·阿里扎德(Abbas Alizadeh)指出,“厭女癥是全球威權民粹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女性及其他少數群體的正當權利訴求被威權民粹主義者看成是對傳統政治秩序的攻擊”1。從現實看,威權民粹主義政黨掌權的國家都存在針對女性的不平等與壓迫政策,例如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曾明確表示,女人不能忍受政治的坎坷;歐爾班政的府所有大臣都是男性,僅有幾個黨的議員是女性。在美國,“威權民粹主義分子為自己的無知而自豪——他們目空一切地愚蠢、平庸,對受過良好教育的有色人種、移民和女性的辛勤工作感到憤慨。這種挑釁性的無知已經進入了美國人的血液中”1,這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身上尤為明顯。
性別歧視在種族與身份方面的延伸則表現為強烈的排他性。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戴安娜·穆茨(Diana C.Mutz)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對于投票支持特朗普的白人選民來說,對失去地位的恐懼是比經濟焦慮更重要的因素2。與難民危機嚴重的歐洲相比,美國的移民人口(包括穆斯林)與本土白人往往融合得很好,此外,當前美國的移民率要遠低于19世紀末邊境開放政策鼎盛時期的移民數量。盡管如此,奴隸制和種族隔離遺留下來的文化與心理影響仍然廣泛存在。凱爾納指出,“奧巴馬作為第一位黑人總統的事實激怒了許多美國人,他們的種族主義和偏見因右翼媒體和共和黨對奧巴馬政府的長期抹黑與攻擊而加劇3”。特朗普以及共和黨的選民基礎是美國本土白人,在政治宣傳上,競選團隊利用了后者對移民、種族和伊斯蘭教的焦慮。《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一項調查發現,68%的白人工人階級選民表示,需要保護美國的生活方式免受外國影響,近一半的人同意“事情發生了很大變化,以至于我經常覺得自己在自己的國家像個陌生人”的說法。在有這些焦慮的白人工人階級選民中,79%的人投票支持特朗普4。
美國心理學家弗蘭西斯·薩姆納(Francis Sumner)1906年提出了“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rntrism)”的概念,用來描述個體所表現出的排外傾向,其主要特征是在文化、習俗上機械地接受與自身相似的東西,并排斥和敵視異質性。阿多爾諾在《權威人格》中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概念,將民族中心主義界定為“團體與團體關系的一種思想體系”5。阿多爾諾發現,民族中心主義者典型的思維方式是“以公牛眼睛(那般)的同心圓來看社會”,[5](p200)他們習慣于將自己所在的或自己認同的團體看成是內團體(In-groups),而將其他的、自己不認同外部團體一律看成外團體(Out-groups),并強調二者之間的絕對區分。同時,這種意識形態可以在各種層級之間進行轉換,威權民粹主義者將美國看成是一個優越的整體,而將其他國家和民族看成是低等的、從屬的團體,然而視角一旦轉回內部,就會產生白人與其他族裔、基督教與其他教派、精英與群眾等新的對立,這導致其始終囿于偏見與狹隘之中,無法平等、寬容地對待異質性群體。
美國與歐洲民粹主義中廣泛存在的民族中心主義傾向與經濟因素有一定的聯系(例如外來群體對工作機會的擠占),但更多的則是文化、心理上的擔憂。一些美國學者指出,移民涌入正使美國種族變得更加多樣化,加上老齡化的影響,白人可能在本世紀中葉成為少數族裔。與經濟擔憂類似,即使不考慮其他因素的變化,某些趨勢或預測的結果也需要在漫長的未來才能轉變為現實,但在美國文化環境中,潛在的乃至虛構的威脅總是能在當前社會發揮強大的影響。安瑞克·伯格曼(Eirikur Bergmann)使用了“本土民粹主義”(Nativist Populism)的概念來描述民粹主義者的排外現象,塞繆爾·皮雷斯(Samuel Pires)的概念則使用“民族民粹主義”(National Populism)一詞1,類似的研究也都表明,基于性別、種族與身份差異而產生的心理—文化因素極大地促了民粹主義向威權政治的蛻變,并由此引發現實中的極端行動(如驅逐移民、政治暗殺等)。
2.文化反彈:孤獨與具象
諾里斯在其最新著作中引入了“文化反彈”(Cultural Backlash)的概念,她指出,“威權民粹主義的興起可以解釋為西方社會的傳統群體對長期、持續的社會變革所產生的文化反彈”。[6](p21)諾里斯認為,威權民粹主義在瑞典、比利時、丹麥等擁有完善福利制度的國家肆虐,并得到了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經濟上富有的人口的支持,這表明經濟因素絕不是主要原因。從文化和社會結構上看,過去半個世紀以來,西方社會的主流趨勢是日益自由、多元,對LGBT、移民、少數群體的包容,以及經濟上的全球化、文化上的世俗化,固然帶來了進步與裨益,但也導致社會與政治穩態結構的“雙重失衡”,“任何一方都不再能夠占據主導,因為自由多元才是主導”,[6](p47)這種社會劇變不僅使傳統群體(例如年長者、白人男性)感受到威脅,進而引發強烈的反應,也讓幾乎所有群體都產生了被邊緣化、孤立化的錯覺,這種多元、自由但孤獨的文化狀態使得威權民粹主義幾乎能夠從任何群體中獲得支持者。
在弗洛姆、阿倫特(Hannah Arendt)、馬爾庫塞等關于納粹主義的研究中,個體的孤獨與“逃避自由”的文化機制就被著重強調,而在當前的發達國家,孤獨已經成為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本世紀以來,極端組織所宣揚的各類意識形態都在利用民眾逃避孤獨、獲得權力感與歸屬感的心理,包括民粹主義、恐怖主義、種族主義及原教旨主義,莫不如此。按照馬克思的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存在普遍的個體異化,盧卡奇(Georg Lukács)則稱之為“物化”,這一情形隨著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必然不斷加深。孤獨的、原子化的個體在強大的“資本—技術”共生系統面前變得茫然而無力,因而產生想要逃避自由并加入到強有力的群體之中的心理沖動。阿倫特曾指出,“原子化個體的孤立不僅為極權主義提供了群眾基礎,也形成了貫徹到整個結構最頂層的原則”,[7](p273)而由孤獨個體所組成的烏合之眾往往會無條件響應極權主義者所要求的忠誠。特朗普曾宣稱,“我可以站在第五大道上朝行人開槍,而不會失去任何選民……這簡直不可思議”2,這一夸張的說法恰恰體現了支持者對其完全忠誠的心理。
面臨經濟或文化上的威脅,普通人需要尋求強大者的保護,而孤立個體所產生的群眾運動也呼喚強有力的領袖,概言之,一個具象化的“強者”是威權民粹主義本身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對于美國民眾來說,特朗普的形象似乎完美契合了這一要求,而關于美國民粹主義的研究中也無一例外地涉及對特朗普個人的心理、文化剖析。凱爾納指出,與傳統的理性獨裁者不同,特朗普是一個混亂而無紀律的人,“他被純粹的自戀、憤怒和暴力傾向驅使,但也正因為此才被視為美國政治的身份象征”。[8](p20)特朗普在美國政界展現出了迄今為止最無拘無束的自我,他不斷地炫耀自己的財富、聰明以及男性魅力,同時也展現出施虐狂的特征,例如在選舉辯論中對其他候選人肆無忌憚的侮辱,以及對警方襲擊其抗議者的無視。
然而,特朗普的這些性格特征成功吸引了大量的追隨者。如果站在理性的角度,很難理解支持者如何將一位毫無政治經驗與遠見的人吹捧為拯救美國的領袖。從韋伯(Max Weber)意義上的領袖魅力來看,特朗普被某些群體所視,正因為他具有某些創造奇跡的“優越”品質,比如讓美國再次偉大,恢復白人、男性和基督教的統治。盡管并沒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特朗普能夠實現其諾言,或真正維護其追隨者的利益,但特朗普的形象無疑滿足了威權民粹主義者在心理與文化上的多數需求,這種魅力正是由樂于接受的民眾自身所賦予的,因而,特朗普只是美國社會文化反彈的一種具象投射。
(三)信息技術的影響
互聯網平臺、大數據對政治的影響是國內外學界近來關注的熱點,但涉及民粹主義的研究并不多見。2020年Netflix出品的紀錄片《監視資本主義:智能陷阱》1討論了社交媒體在產生極端思想、制造社會對立上的危害,并從制度監管、道德約束、主體自律等方面給出了建議。關于美國民粹主義的論述中,凱爾納、朗曼及約迪·迪恩(Jody Dean)等對信息技術也有所提及,這些分析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1.對于民眾。迪恩在描述當前數字資本主義時指出,信息網絡與資本統治下的個體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個完全確定的、不受其控制的環境……系統被呈現為決定我們的過程和對象,它是某些可以觀察和描繪的東西,甚至可能是可以預測或哀嘆的東西,但永遠不會受到影響……任何個體都無法對系統產生影響”。[9]迪恩將這種現象定義為“幸存者—系統意識形態”,即高度獨立的、原子化的個體與強大的、無所不包的算法系統之間的對立。網絡系統放大了人的孤獨與逃避自由的心理效應,使其更易受到煽動性的人物或信息的影響。著名學者侯世達(Douglas R.Hofstadter)曾指出,美國民眾長期以來傾向于接受陰謀風格的敘事,這種風格喚起了強烈的懷疑感,進而導致文化動蕩,例如歷史上對光明會、共濟會及共產主義的恐慌。威權民粹主義能夠盛行,也在于其敘事方式經過信息網絡的擴大而得以廣泛傳播,烏戈·查韋斯(Hugo Chavez)等人關于“新冠病毒是中國生物武器”的言論,以及Q-Anon的信徒,都是通過宣揚陰謀論而獲得民眾的認同與支持的。威權民粹主義通過網絡傳播的各類虛假夸大信息,迎合了普通美國人的民族中心主義、個人自由主義等心理,在虛構的共同敵人(如中國威脅、戀童癖民主黨人、控制整個世界的猶太人)面前,將分散的個體意識重新整合起來,這為民粹主義運動創造了群眾基礎,但也在客觀上強化了信息網絡對人的負面作用。
2.對于政客。國內學者認為,網絡的“去中心化”對主流文化的話語權構成了挑戰,J.D.戴維森(James D.Davidson)等人則認為,信息時代將產生一大批“主權個人”(Sovereign Individual),在經濟上,“一些主權個人每年有數億美元的可投資收入,超過某些破產的國家可支配的財富”,[10](p217)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與影響可能不亞于一個國家,而在操縱信息方面,主權個人也完全可能比許多曾經的國家更加強大。顯然,去中心化帶來了國家權力的削弱,也使得一些擁有出眾天賦或巨大財富的個人脫穎而出,在政治與文化的真空地帶,任何人都有可能聚集起一批自己的信徒,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民粹主義領導人通常都具有突破傳統的獨特風格,這使其能夠更加有效地利用媒體來塑造一個強大的煽動者形象。威權民粹的一大特征便是“系統性的撒謊”,并將任何對自己不利的信息定性為“假新聞”。谷歌公布的一項分析顯示,假消息(通常融入了夸大或情感成分)的傳播速度是真實信息的六倍多,看似荒謬的“反智主義”能夠產生了巨大的現實影響,緣由即在于此。根據統計,在2016年3月,媒體公司估計特朗普獲得的媒體報道遠遠超過其共和黨競爭者,而截至6月他則獲得了價值至少30億美元的免費媒體報道。[8](p24)
關于Facebook對美國大選的影響,以及近年來美國選舉中Twitter、Tiktok的作用也有諸多討論,政客與科技巨頭的關系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但這一方面的研究需要深入到信息技術與政治結構、意識形態、話語霸權等關系的內在邏輯之中。信息網絡帶來的去中心化削弱了政府主導的政治與文化霸權,使話語主體多元化,從而助推了民粹主義浪潮,而數字資本主義系統則強化了個體人的孤獨狀態與投向強者的意愿,進而為威權政治提供了民眾基礎,此兩種機制也是導致威權民粹主義的不可忽視的因素。
三、民粹主義的多面性:現實影響與未來
2021年的國會山暴亂是美國式民主所遭受的最嚴重的一次攻擊,許多美國學者也將此事件看作民粹主義對美國政治現實挑戰的象征。長期研究內戰的芭芭拉·沃爾特 (Barbara Walter)在評論威權民粹主義時提到,“我們可能會面臨一個暴力行為分散但持續存在的時代——爆炸、政治暗殺、極端主義團體實施的破壞等行為規模相對較小,但卻更加頻繁與持久”。[11](p2)芭芭拉也指出了導致分裂、內戰的一般模式,包括:(1)民主的衰落;(2)基于民族、宗教或種族身份的日益增長的群體對立和對他者的排斥;(3)“降級”(Downgrading),即當一個占主導地位的群體面臨地位或聲望下降時,他們往往會采取暴力手段來保持權力和地位。
美國社會當前情形的發展恰恰表現出了上述三個方面的特征,這也是威權民粹主義迅速上升的原因所在。莫洛克一針見血地指明:“威權民粹主義在美國的興起是系統性政治在起作用,是政治通過媒體、法律、經濟、教育等方面的變化釋放出的‘新常態’……特朗普的崛起只是對種族、階級和性別的掠奪性政治經濟以及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中潛在的毀滅傾向的最新粗魯表達。”[12](p112)從本質上看,美國的威權民粹主義只是各種“保守復古”運動的集合,民粹主義者試圖恢復一個想象中的黃金時代,在那個時代,白人男性擁有經濟、政治及文化上的絕對優勢,他們可以輕松找到有保障的工作,獲得體面的收入與福利,其身份與地位也沒有受到挑戰。然而,隨著全球化的加速,移民浪潮、多元主義、平權運動不斷發展,由此引發的傳統群體的文化反彈,即表現為種族主義、仇外心理、同性戀恐懼癥、性別歧視、本土主義以及反智主義等,而威權民粹主義則可以看成是后者的集中體現。
另一個關鍵的問題是,民粹主義何以在實踐中普遍走向威權、專制的極端?
一種觀點認為,民粹主義沒有固定的政治主張與完整的意識形態,因而在實踐中容易被各類政治派別化用。梳理民粹主義研究史可以看到,持不同解釋的學者為數眾多,如保羅·塔戈特(Paul Taggart)認為民粹主義具有“變色龍特征”,科特·維蘭德(Kurt Weyland)將民粹主義解釋為一種策略,瑞·詹森(Ray Jansen)則將其看作一種動員手段,羅格·巴爾(Roger Barr)將其定義為一種群眾運動,除此之外,還有學者將民粹主義定義為一種話語方法或框架,如約翰·阿斯蘭迪斯(John Aslandis)、克拉斯·福雷瑟(Claes de Vreese),或者定義成一種政治風格或態度,如本杰明·墨菲特(Benjamin Moffitt)、斯蒂芬·霍瓦爾特(Steven Van Hauwaert)等。大衛·卡門斯也指出,“美國民粹主義的性質和動態尤其混亂,很多立場不同的政治人物,如麥卡錫、里根、克林頓、布什和特朗普等近幾十年來都分享了這個綽號……對于許多政治家與觀察家來說,民粹主義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只要人民喜歡它,它就是民粹主義的。”[13](p131)
相反的觀點則認為,民粹主義本身從一開始就包含著威權政治的因素。安妮在20世紀90年代就指出,“威權民粹主義一詞乍一看似乎自相矛盾,但實際上民粹主義天生就是威權主義的,因為它是一種戰略,而不是一種充分發展的意識形態。”[14](p5)楊-維爾納·穆勒 (Jan-Werner Müller)也認為,民粹主義的兩個關鍵要素是“反精英主義”與“反多元主義”,這意味著在區分人民與精英的同時,民粹主義也特別強調“人民”的界限,從而自然產生出排外、排他的傾向。因此,民粹主義在實踐中往往依靠威權型領袖或專制型政黨。穆勒指出,民粹主義走向威權政治主要是基于下述邏輯:(1)無視傳統制度體系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打破限制、實現“人民意志”的必要條件,因此,間接民主產生的國家行政自主權需要被摧毀,使政府成為人民領袖直接掌控的工具;(2)地方當局的自治被視為落實人民意志的另一個體制障礙,故而需要加強專制與中央集權;(3)司法機構的獨立性、民間社會和非政府組織、獨立媒體等一切威脅也應當被清楚,由此導致反自由、反多元的倒退行動。
面對威權民粹主義的威脅,美國應當如何應對?盡管觀點不同,但美國學者所給出的解決方案卻趨向一致——通過適當途徑分化、消解民粹主義,并將其吸收、納入到傳統政治的正常軌道中來,設想中的措施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政黨重組。部分學者認為,民主黨和共和黨需要認識到他們正處于危機,并著手進行長期性重組,同時制定管理變革的戰略。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數據,民主黨與左翼獨立人士中支持黨內重組的比例高達67%,但共和黨與右翼則僅有36%。1從歐洲的經驗看,民粹主義的崛起帶來了新黨派的涌現與傳統政黨的改組,而在美國,執政兩黨則面臨著民眾日益增長的憤怒和不信任,因此,政黨的改組和自我重塑也將變得不可避免。
第二,正視民粹主義的挑戰與訴求,推動政治與政策改革。蘇姍妮·米特勒(Suzanne Mettler)等指出:“當民粹主義者能夠合法地宣稱自己是局外人時,當人們對政治腐敗有廣泛認同的看法時,當老牌政黨刻意避免討論民粹主義者提出的問題時,民粹主義者最有可能在政治上取得成功。”[15]盡管美國兩黨制所造成的二選一困境延緩了民粹主義政黨化的進程,但絕不能因此將民粹主義看作不足顧慮的、流散的小派別,面對普通民眾對建制共識的嚴重懷疑,兩黨都需要仔細考慮其政治立場。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對政治制度進行結構性改革,以提高民選代表的響應能力和問責制(特別是反腐敗改革),以幫助重建對政府的信任。
第三,吸納民粹主義中對民主有利的積極因素,并防止其滑向威權政治的極端。民粹主義者走向暴力運動的根源在于他們認定當前制度是不可救藥的,因此往往利用大眾的挫敗感來組織摧毀行動。然而,合理、可信任的改革者也可以有效地利用民粹主義者的情緒,而不會導致反民主或反自由的極端后果。這種所謂的“好的民粹主義”以法國政治家阿德里安·阿貝卡西斯(Adrien Abecassis)為代表,他的改革舉措回應了公眾的擔憂,也消解了激進主義與極端主義。羅哈奇認為,當前美國威權民粹主義中的民族中心主義、白人至上主義等極端思潮,也可以通過久經考驗的民主價值觀和制度重建來對抗。
“威權民粹主義的興起不是美國民主功能失調的原因,而是結果……這恰恰是民主制度運作不善的表現”,[16]極端的黨派之爭、響應低下的政府、民眾的挫折感構成了威權民粹主義的驅動力,經由信息技術和社交媒體的強化而形成廣泛的文化反彈。一些學者認為,極端民粹主義的強勢不一定是永久性的,通過政治改革、文化重塑等方式,能夠恢復民主自由的傳統。羅哈奇則指出,威權民粹主義的影響不會消退,除非新一代政治領導人能提出一個可信的議程,它不僅比民粹主義的方案更能吸引公眾,并且能實際改善人們的生活。無論如何,威權民粹主義浪潮背后的因素是復雜,一些結構性的內在弊端是無法通過簡單、迅速的解決方案來根除的,要馴服、吸納威權民粹主義,將其整合進傳統政治框架之中,需要美國政府付出大量的政治努力,而在世界層面,捍衛、重建民主政治和話語則需要各國政治家、民眾與知識分子的持續參與,這也將是一項艱巨而長期的任務。
參考文獻:
[1]吳鑫.法蘭克福學派權威批判研究[D].上海:復旦大學,2020.
[2]Benjamin I. Page, Martin Gilens. Democracy in America? What Has Gone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3]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et al.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pulism[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4]David C.Barker,Ryan"DeTamble. American Populism: Dimensions, Distinctions, and Correlates[J].Global Public Policy and Governance. 2022, (2).
[5][美]西奧多·W.阿道諾.權力主義人格[M].李維,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6]Pippa Norris,Inglehart Ronald.Cultural Backlash: Trump, Brexit,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7]Hannah 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73.
[8]Douglas Kellner. American Nightmare: Donald Trump, Media Spectacle,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M].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2016.
[9][美]約迪·迪安(Jodi Dean).數字資本主義與政治主體[J].張可旺,譯.國外理論動態,2021,(1)
[10]James Dale Davidson, William Rees-Mogg. Sovereign Individual: Mastering the Transition to the Information Age[M]." New York:Simon amp; Schuster, 2020.
[11]Barbara Walter. How Civil Wars Start: and How to Stop Them[M]." New York: Crown Books, 2022.
[12]Jeremiah Morelock. Critical Theory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M].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2018.
[13]David H. Kamens.The New American Creed: The Eclipse of Citizenship and Rise of Populism[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14]Anne Munro-Kua. Authoritarian Populismin Malaysia[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6.
[15]Suzanne Mettler,et al. Democratic Vulnerabilities and Pathways for Reform[J]."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22, (1).
[16]Dalibor Rohac, et al. Drivers of Authoritarian Popu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 Primer[EB/OL].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
責任編輯"" 唐"" 偉
①數據來自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官網(https://www.nber.org)。
②Adam Bonica et al. Why Hasnt Democracy Slowed Rising Inequalit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3(3) pp.103-124.
③Kay Schlozman et al."The Unheavenly Chorus: Unequal Political Voice and the Broken Prom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587.
④數據見該機構網站(https://www.opensecrets.org/)。
Authoritarian Populism in the Critical Theory:
Leading Factors, Status and Influence
Wu Xin
(School of Marxism,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 China)
Abstract: Current populist researchers in the West have abandoned the traditional left-right dichotomy of theory, and many scholars are adopting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in order to gain insight into how populism turns to violent campaigns and authoritarianism. An examination of Western social realities reveals that that beyon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asons,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along with the effec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ll have played their important role in leading to authoritarian populism. Western scholars assume that authoritarian factors and extremist tendencies of populism should be guarded against, its corrosion of global democracy should be curbed, and these extreme ideologies should be absorbed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political frame.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actical obstacles in achieving these theoretical visions.
Keywords:authoritarianism; populism; US; critical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