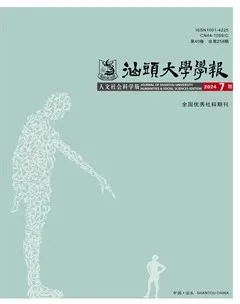將花釀蜜無復花:論集字詩的生成機制與詩體風格

摘 要:文學作品意義上的集字詩自宋代蘇軾集《歸去來兮辭》始,后世涌現出大量的以集《歸去來兮辭》《蘭亭集序》字詩為代表的詩歌創作,從經典中集字成詩成為推動文學經典化的重要傳播方式。明清文人以“詩牌”集字成詩頗具游戲色彩,展現漢字魅力的同時映射出士人娛樂文化的千姿百態。集字詩從“經典”到“游戲”的寫作模式,也引發后人對集字詩詩體風格的雅俗之爭,蘊含豐富的詩學和文化韻味。
關鍵詞:集字詩;蘇軾;清代;文人游戲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4225(2024)07-0014-08
收稿日期:2024-05-20
作者簡介:王園瑞,女,河南南陽人,文學博士,浙江農林大學茶學與茶文化學院講師。
集字早期多作為一種書法用語,主要指搜羅前人書法字跡而集成書法作品,如《徐氏法書記》所載“梁大同中,武帝敕周興嗣撰《千字文》使殷鐵石模次羲之之跡,以賜八王”[1],便是最早的集字書法。集字作為展現中國古代書法文化的一種重要現象,其影響持續至今。其實,書法文化中的“集字”現象也在悄無聲息地滲入中國古典詩歌中,兼具書法審美和識字功能的《千字文》即為“集字”進入詩歌領域帶來了啟發。清代高不騫《賜正書千字文》云“集字誰經始,成章此發端”[2],《千字文》全文為四字句,對仗工整,音韻和諧,幾與四言詩無異。真正意義上的集字詩出現在北宋,以蘇軾集《歸去來兮辭》字詩為發端。解構經典,重構為詩,成為后世集字詩的固定模式之一,并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開拓出集字詩創作的洋洋大觀之景,惜乎學界對此較少關注。本文旨在對中國傳統詩歌領域內的集字詩進行梳理,考察集字詩的發展規律和風格特點,以期揭示集字詩發展過程中的詩學內涵和文化意義。
一、文學接受視域下的經典重構
——從韻文中集字
(一)集字詩之開端——集陶淵明《歸去來兮辭》
清人陸以湉認為“集字始于東坡之集《歸去來兮辭》”[3],樊潛庵對蘇軾的集字詩評價道:“自七才子集唐,而后有集李、杜,集陶者矣,未聞有集字以成詩者。創之蓋自公始,且十律中格調嚴整,語意流麗,欲尋一毫斧鑿痕,不可得也”[4],對東坡集字詩的開創之功予以極高的肯定。蘇軾因“烏臺詩案”謫居黃州,以集字成詩的方式將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改寫成十首五言律詩,題為《歸去來集字》,這是蘇軾對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改造的首次嘗試。從整體上看,蘇軾的再創作與陶淵明原作《歸去來兮辭》所描寫的景致、生活情趣乃至抒發的情感基本上保持一致,如其一曰“命駕欲何向,欣欣春木榮。世人無往復,鄉老有將迎。云內流泉遠,風前飛鳥輕。相攜就衡宇,酌酒話交情。”[5]詩句中對具體景物和活動的描寫,幾乎是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相關內容的翻版,借陶淵明語表達自己辭官歸隱的生活理想。
自東坡開集《歸去來兮辭》中字成詩這一先例后,集字之風在南宋文人圈已產生影響。蘇軾的虔誠追隨者李綱是南渡時期學習和追和蘇詩最多的一位詩人,同時也因為對陶淵明的人格崇拜,作了相當數量的和陶詩。李綱在南渡時期作《次韻和歸去來集字》十首,次韻之語皆集于《歸去來兮辭》。稍晚時期的宋伯仁作《席上有舉東坡集歸去來字成詩十首醉中戲續一首》:“傲世欲何求,歸來已倦游。琴詩聊自嘯,丘壑復相留。問菊時攜酒,乘風或棹舟。樂天良有以,心事老田疇。”[6]雖是醉中所作,但仍得蘇軾集字詩的精髓,營造出一種寧靜恬適、樂天自然的意境。
清代集《歸去來兮辭》詩的創作較為豐富,在東坡集《歸去來兮辭》的影響下有相當數量的仿作和追和。列表如下:
從上表可知,集《歸去來兮辭》字詩整體上已擴展至更為豐富的主題和場景,呈現出日常化的寫作特點。如集字以贈別,顧光旭《和鄭蘭州集歸去來辭字十首即送歸莆田·其九》:“役役感游子,行行為問余。未尋三徑樂,欲策萬言書。春去人將老,風來云自舒。鄉關雖已遠,可以命吾車。”[7]雖取自《歸去來兮辭》,但詩歌中游子思鄉的情懷和友人贈別的囑托之意亦十分明顯。再如集字以題圖,祝德麟《集歸去來兮辭字題張愛庭東皋舒哮圖》:“富貴途非遠,田園趣可尋。問農聊策杖,撫景或攜琴。獨往松風就,有時云壑臨。乃知舒嘯者,憂樂不關心。”[8]不但畫題“集”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的“登東皋以舒嘯”字,詩作內容也選取了極富有代表意義的意象和字眼,讀來頗覺陶淵明“游在畫中”,攜琴問農,登高舒嘯,為圖畫增添了如臨其境的慢鏡頭感悟。其次,集字成詩題于畫中,也有強烈的“借古人增榮”的意味,不僅實現了詩與畫兩個維度的互相闡釋與潤色,在集字的來源與范圍方面也為詩畫插入了“第三者”的視野,豐富了詩畫的內涵。清人將這些日常生活中習見的內容用古人的話語加以重構,通過集字這一藝術化的形式,使這些日常生活中的瑣碎平庸變得空靈有味。
集《歸去來兮辭》為詩,主要因為蘇軾的首創而沾溉后世,此后的集字詩創作,雖名為集《歸去來兮辭》字詩,但實則是受到讀蘇軾詩作的直接影響,這點可以從詩題和詩序中看出。因此后世的集《歸去來兮辭》字詩包含有對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和蘇軾集《歸去來兮辭》字詩的雙重接受,名為蘇軾《歸去來兮辭》集字詩的續詩、和詩、仿詩,實則突顯的是《歸去來兮辭》中陶淵明的景語和情語。紀昀評東坡集字詩曰:“此亦借事消閑,不得謂之詩,然亦不惡。十首皆代淵明語。”[9]雖然蘇軾集字詩有“不得謂之詩”之譏,但是借淵明語,用淵明字,來澆自己心中之塊壘,幾乎成為后世集《歸去來兮辭》字詩最真實的意圖。
(二)文人雅會的追憶——集王羲之《蘭亭集序》
《蘭亭集序》因為王羲之的書法真跡,自唐代以來廣泛流傳于世,其書法價值被后世推為至高無上,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也使王羲之登上了古今無二的“書圣”地位。集《蘭亭集序》中的字進行臨摹作字帖、楹聯等書法文化,在唐代以后一直熱度不減。兩宋時期,蘭亭文化的昌盛不僅體現在蘭亭書法的日趨流行,對《蘭亭集序》的品評、研究也日益開展。這也為《蘭亭集序》的接受和改造提供了無限的可能。
首次作集《蘭亭集序》語成詩的嘗試當為南宋中興詩壇的喻良能,喻良能(1120—?),字叔奇,婺州(浙江義烏)人,自號香山居士,又號錦園先生。其好友王十朋在給喻良能的一首贈別詩《贈喻叔奇縣尉》中說:“同舍同年友,天資迥不群。詩文侵晉宋,兄弟類機云。梅市訪仙侶,蘭亭懷右軍。(自注:叔奇嘗集《蘭亭》作詩五絕)公余時過我,無酒亦論文。”[10]194詩中盛贊喻良能的詩學造詣,在王十朋“自注”中也提及喻良能作過五首集《蘭亭集序》中語而成的絕句詩。①此后王十朋作《和喻叔奇集蘭亭序語四絕》,不僅是喻良能曾作集《蘭亭》語詩的明證,也是目前現存文獻中第一首集《蘭亭集序》語詩。列之如下:
我自扁舟入越初,蘭亭已向夢中如。
崇山峻嶺至今阻,唱和詩成無處書。
群賢少長畢經過,曲水流觴憶永和。
一代風流已陳跡,世殊事異感傷多。
晤言一室許誰親,相過無非我輩人。
放浪形骸嗟老矣,仰觀宇宙尚艱辛。
茂林修竹未成往,游目騁懷聊自欣。
暢敘幽情有齊契,一觴一詠細論文[10]196。
這組詩完全是對《蘭亭序》文句的重組,可以說是引用《蘭亭集序》之語,來抒發個人之情。詩題中標明是“集蘭亭序語”,“語”可以理解為:詞語、短語,是比“字”稍微長一點的語言單位。嚴格意義上的集字詩當如上文東坡集《歸去來兮辭》,是詩中的所有的字都取自《歸去來兮辭》,限制性較大。而王十朋的集《蘭亭序》語詩,則是取其語辭而修飾之。換句話說,以集《蘭亭集序》中的“語詞”為主然后用自己的語言加以點綴使其通順完整,并賦予個人思想和情感。這是一種長于“集字”短于“集句”的特殊情況,由此推測喻良能所作集《蘭亭》五絕詩亦當如此。以王十朋所作第四首為例,“茂林修竹”“游目騁懷”“暢敘幽情”“一觴一詠”出自《蘭亭集序》的短語,其“集語”意當是此,“未”“自”“欣”“齊”“契”“文”也能在《蘭亭集序》中找到對應的字,“成”“往”“聊”“有”“細”“論”六字為作者連貫詩意而加。初讀仿佛再現了當年曲水流觴的雅會場景,實際上也契合王十朋和詩的主題,王十朋與喻良能曾在紹興蘭亭盡情唱酬,賦詩論文,成為莫逆之交。
王十朋集《蘭亭集序》之語成詩顯然與宋代詞人喜用的“隱括”手法如出一轍,基本選取經典名篇,剪裁或截取原作之語,概括原文大意,熔鑄成新的文學體裁。作為詩歌創作的兩種方法,集字與隱括雖然有著相似的表現方式和藝術要求,但是二者的區別亦非常明顯:集字詩要求所集之字皆來源于作品,即改動于“作品”之內;隱括則可以用“添”“改”等方式對原作進行改寫,改動于“作品”之外。與王十朋《蘭亭集序》集語詩不同的是明人許贊作有集《蘭亭集序》續韻成詩的七言古詩,許贊此詩也有“集語”的特點,并且絲毫未改動原文的敘述順序和主旨思想。如“‘永和九年’‘暮春’時,‘會稽山陰’春欲離。‘蘭亭’勝概勝天下,一年‘修禊事’相宜”(單引號內為《蘭亭集序》中語)。因此,王十朋、許贊之作雖不能稱為集字詩,但可以看作是集字這一藝術形式去觸碰和解讀《蘭亭集序》的嘗試,并直接啟發和影響了清代蘭亭集字詩的繁榮景象。
受王羲之上巳節“修褉事也”作《蘭亭集序》的直接影響,在上巳節游玩賞春、曲水流觴并模仿王羲之蘭亭雅集也一直是唐宋以來很有影響力的風俗文化活動,清代在上巳節舉行蘭亭雅集較之前代最為頻繁。蘭亭雅集的基本內容有修禊、飲酒、賦詩、制序、作書等,其中賦詩多是唱和、聯句、分韻或續作的形式,但在上巳節這天以集《蘭亭集序》字為詩寄情抒懷在清代尤為普遍。如顧宗泰《三月三日平伯曉舟兩學博雨吉上舍佩南茂才會于城南水亭褉飲即席集蘭亭序字成七言二首》,魯之裕《集蘭亭字和京師諸同人上巳一畆居修褉三絕句》,沈景連《上巳集蘭亭序字四律》,韋謙恒《小漪南修褉用蘭亭序集字》等,清末文人、藏書家金武祥就在其《粟香隨筆》中《集字成詩》條記載了當時創作風氣和自己的創作實踐。
右軍《蘭亭序》,今人多集字為楹聯,鮮有集字成詩者。余壬申里居,逢上巳節,戲集字成五古一首。前半首云:“昔賢不可作,稽古懷風流。山林或寄興,至樂咸猶猶。快哉風日和,娛此水竹幽。觀時一以慨,悲感亦有由。”后半首便覺敷湊,故稿中刪之[11]。
“因修洛陽禊,重憶永和春”,在上巳節集《蘭亭集序》字成詩已然成為文人間約定俗成的文化紀念。這類詩的寫作緣由大都有所說明,皆因上巳節或修褉之事的感發和引導,王羲之等人的蘭亭雅集,在特定的時間、空間留下了文學映射,成為后世文人群體的集體記憶。因此后世詩人們的文學創作對時空的選擇及其行為模式,都帶著對蘭亭雅集的記憶和再現意義。
隨著蘭亭集字詩的漸成風氣,清代也有一些蘭亭集字詩不再受時間和風俗的限制,蘭亭集字詩在規模上也不斷擴大,如顧光旭《初春游蘭亭已有述矣復集蘭亭字》,這一組詩有二十四首,近千字,如同王羲之筆下蘭亭雅集的再現,正如其詩所說:“于稽集古錄,有作會相期”,“集古”以“相期”,也是清代大多數文人對“蘭亭雅集”的推崇與追望。朱倫瀚的《蘭亭集字詩十首并序》,不僅是集蘭亭字為五言古詩十首,而且其序文也是集蘭亭字而作,可謂翻版的《蘭亭集序》。清代蘭亭文化氛圍濃厚,集字詩作為蘭亭文化的一種重要追憶形式自然有其適宜的發展環境,《吳興詩話》載:“書屏大令癸丑試長邑,以‘癸丑暮春初’命題,集蘭亭字為詩,一時和者甚眾,個體皆備”[12],不僅呈現了清代吳興地區集蘭亭詩的盛況,也反映蘭亭文化強韌持久的輻射性特征。因此蘭亭集字不僅是對王羲之《蘭亭集序》的變相模仿,也為我們如何熟練解讀與應用《蘭亭集序》的文辭提供了一種范例。
《歸去來兮辭》《蘭亭集序》以其作品的經典性開創了后世集字詩創作的典范,也奠定了集字詩以名篇佳作為集字范圍和主題的內容特征。清代詩人豐富的集字詩實踐也將《歸去來》集字詩和《蘭亭集序》集字詩發展推送至高潮和成熟階段,不僅印證著上述作品的經典性,也為經典作品的傳播擴寬了渠道。但這兩類集字詩也面臨著“通貨膨脹”的危機——由于寫詩的人多,作品數量多,規模大,導致詩歌新意不夠,價值不高。清人們為了擺脫集字素材枯竭、詩意老化的寫作困境[13],便嘗試打破這兩種日常寫作的范式,擴大了集字范圍,并有意識地從其他名篇佳作集字成詩來探索異己體驗。如趙吉士集《滕王閣序》字為詩、朱學詩集《懷仁圣教序》字為詩、彭孫貽集《桃花源記并序》字為詩、徐基集《赤壁賦》字為詩等,此類作品都是用莊重的寫作態度進行文體突破的嘗試,借以傳達“言志載道”“為事而作”的正統文學觀念,在進入尚友古人境界的同時又裝飾和點綴著詩歌題材。從文學經典中集字成詩雖然也出現了少量的“戲續”“戲作”等出于娛樂需求的題材,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經典的嚴肅性,但卻可以使這些被“二度創造”的經典更好地融入文人的日常生活和民間文化當中。
二、集會宴飲文化下的文字游戲
——從詩牌中集字
詩牌在唐代已有,亦被稱為韻牒,唐人多用詩牌集韻成詩,“韻牒始段成式,段押句好押窮韻、惡韻;其平聲好韻不僻者,書竹簡,稱為韻牒。”[14]所謂“韻牒”即為書寫不同字韻的木牌。發展到明代,詩牌內容和樣式更為豐富,詩人們開始用“詩牌”集字成詩,一時間成為文人雅士酒桌上流行的文字游戲。“近日莆用人為詩牌,削骨縱橫半寸,刻韻于上,平聲赤文,仄韻綠文,每人各分數十字,酒間集之成詩。”[15]明人王良樞還專作《詩牌譜》一書,對詩牌的制作和玩法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清代詩人趙吉士好以“詩牌”作集字詩,其對《詩牌譜》的集字成詩的規則和體式也甚是熟悉:
詩牌集字詳于吳興王良樞一譜,其式用牙牌六百扇,廣六分,厚一分,以一面刻字一面空白,曰其字聲平仄,以硃果別之,椿牌一扇長,準詩牌二刻曰詩伯,凡易陴勻為四分,每一百扇以一人為詩,伯執椿牌,內取一扇,以字畫數到某人次第取用,以紙筆令詩伯掌之,聽各人自取韻,自制題,詩成細評優劣,分碑式之外又有分韻式、立題式、可字式、借字式、較勝式、品第式、賡奇式、翻新式、和韻式、收殘式、洗荒式、疊錦式、聯珠式、合璧式、煥彩式[16]。
王良樞在《詩牌譜》中對集字成詩這一游戲過程大至定題、立意、體裁,小至用字形體、聲音、意義上的變通皆有涉及。根據詩人所抽取的漢字組合押韻成詩,就像L·R·帕默爾所說的:“漢字不過是一種程序化了的簡化了的圖畫的系統”[17],因為其圖畫性,每個漢字都是獨立的個體,所以詩人們集字便用傳統的“以意逆志”式的閱讀習慣自動組合著這些獨立的文字。看似在挑選灑落一地、錯綜復雜的漢字,實則是有其肌理和文脈可循。這些漢字按照思維的理性機制變成一種“線性序列”,這種“線性序列”就是古人詩歌中由意象構成的作詩模式。《詩牌譜》所選六百字,吳承學先生認為王良樞對“山景、水村、林泉、田野、城市、樓臺、春秋、曉暮之類相關的字眼情有獨鐘”“似乎帶有強烈的古典山水詩歌意境模式的審美傾向”[18],因此用《詩牌譜》集字成詩大多具備古典山水詩的創作風格。當然詩牌不同,其所選的漢字自然也不相同,也決定著最后集字詩的內容和風格。但從《詩牌譜》以及此后的詩牌集字詩來看,詩牌所收字韻,是中國古典詩歌創作較為常用的韻;所收意象,也是歷代詩歌中的活躍意象。漢字的優勢和特點在此得以彰顯,漢字在“集字”這種構詩方式中顯得松散又拘束,卻在成詩過程中發揮極強的自由性和延展性。這些凌亂無序的漢字,一旦映入詩人眼簾,便迅速抵達作者大腦的“知識儲備庫”,“使讀者獲致一種自由觀、感、解讀的空間,在物象與物象之間,作若即若離的指義活動”[19],最后憑借詩人的敏感度和積累量,從詩歌“意象”小元素拼合成詩歌“意境”大單元。以詩牌集字成詩,兼具漢字詩學和意象思維兩種游戲考驗,成為文人一本正經之余侑酒佐歡、點綴消閑的重要活動。
明清以來用詩牌集字大多是群體性娛樂活動,作為詩人與朋友在酒宴上的文字游戲,既有豐富宴飲活動的娛樂性質,亦有詩歌互相品評的鑒賞意味。如清人鄭熙績《夏日休園對雨集字》序文中提到:“先大父雅嗜詩詞,自制牙牌嵌韻內二千二百字,色異朱藍,韻分平仄,每當園居之暇,偕友分韻集字,以代世俗手譚之戲。每趨庭,多以此為恒課。庚申季夏下帷休園時,值有章家叔祖過訪,忽遇風雨,留飲小齋,偶出詩牌漫集七言古體一首,截鶴斷鳧之誚,固知貽笑于大方也。”[20]30與詩友談笑間,詩作優劣自現。鄭熙績《避暑平山堂舟中偕友集字》:“舟泛平山繞屬岡,招邀勝境納新涼。風飄柳影渾無暑,露衰荷衣別有香。幾處笙歌依畫艇,數聲鐘磬出僧堂。可憐車馬勞勞客,誰似吾徒逸興狂。”[20]62此詩兼具寫景、記事、書懷為一體,用字恰當,銜接自然。鄭熙績自我評價為:“項山先生集字詩有‘詩不如人好字稀’之句傳為集字佳話,吾欲以此詩質之。”[20]62雖是宴飲上的游戲之作,但蘊含著作者集字成詩構思的辛苦、布局的巧妙,在打破常規、深入開掘的同時,更致力于提高集字詩的藝術感受和表現難度,使集字詩這一游戲文學頗有競技文學的意味。
在當時頗有規模的詩社或集會中,以詩牌集字成詩也成為文人們相互交流感情、切磋詩藝的一種活動方式。吳振棫《國朝杭郡詩輯》記載了康熙三十六年(1697)的七夕宴集:“大會名流一百六十七人,以詩牌集字,用堂額相賞,有‘松石閑意’為韻,分賦五言七章,主人延賓治酒之余,即席詩成。”[21]此次集會在當時頗有影響,詩會上共作出373首五言排律詩,這些集字詩后來皆收入《寄園集字詩》中。魏象樞在《寒松老人年譜》中記載了他所參與的蘿山雅會中集字成詩的盛況:“四月,與鄉中紳士十人聯詩社,集字為詩,名曰蘿山雅會。或于山麓,或于河橋,或于園亭花陰樹下,月一與焉。詩成,小飲長談,絕不一及時事。……人十作侶,要求集字聯吟。篇不成者,讓酒三觥。席過奢者,罰錢一馬。美哉斯舉,正是歌詠太平。匯其多篇,幸將追蹤大雅,與者辭者,各宜聽之。”[22]在這樣的詩社中,文人群體間的集字詩最易見出才學、詩藝之高下,客觀上形成了一種比較的氛圍。詩社中不成文的“以詩爭勝”理念規范了集字詩的隨意性和近俗性,集字詩以往隨心所欲、涉嫌拼湊的自由性得以限制,但把玩漢字、振奮精神的娛樂性未減。
相較于集會或詩社中的“群娛”,詩人們也會“自娛自樂”,以詩牌集字這種群體性活動也逐漸轉移至個人的隱私空間。在書齋或書室中,從詩牌里挑字選韻,把玩成詩,也成為文人消遣時光、緩解孤獨的慰藉品。清初文人趙吉士的《羾青閣秋集》中有集字詩16首,“詩牌八盤,盤百字,限‘清輕迎情聲橫’韻,每盤集排律二首。”[23]501如“燒鐺聊適意,剪菊且娛情。露白舒庭艷,天低咽塞聲。”[23]501句,本自性情,對仗工整,可見吉士苦吟之工。伴隨著清代豐富的集字詩實踐,在趣味性上詩人們也有嘗試。如尹嘉銓《集字回文》:“心同素水映冰壺,閣望高山遠樹無。林杏度霞浮濯錦,野蘭霏雨滴明珠。琴清曉韻蟬分露,鶴引群棲鳳繞梧。吟細近總圍石榻,尋幽愛靜夕添壚。”即被評價為:“縷金錯彩,巧極天工”[24],因為融入了回文這一雜體因素,不僅給人以視覺上的新鮮感,讀來也充滿節奏美和藝術美。
王國維先生說:“詩人視一切外物,皆游戲之材料也。然其游戲,則以熱心為之。故詼諧與嚴肅二性質,亦不可缺一也。”[25]這一則詞話強調了詩人創作如何在“外物”與“內心”之間自在出入,游刃有余。“入”則“必以熱心為之”,而“出”則能把一切外物視為“游戲之材料”。集字詩是作者將所見漢字以熱心的態度“集”之,故而形成一種亦莊亦諧的文學樣式。如果說從“經典”中集字是沿著以“嚴肅傳承”為主干,以“戲續”“戲作”為旁枝的橫向發展脈絡的話,那么以“詩牌”集字,則是在“詼諧”外表或場景下,蘊含著詩人求新去俗的嚴謹態度,呈現出縱向的構思形態。所以不管是何種范圍的集字詩,都能看到詩人在有意識地追求“詼諧與嚴肅二性質”的統一。
三、“近俗”與“自然”:
關于詩體風格的矛盾爭論
集字詩自宋代出現以來,歷代評價褒貶不一。由于集字這一形式的通俗性和單一性,多被認為是近俗簡易之作,或是童蒙學文的練習,或是文人閑暇的娛樂,因此后世評價多有諷意。東坡集《歸去來兮辭》字為詩,即招來后世一些學者的不滿。王若虛對東坡集《歸去來辭》評價道:“東坡酷愛《歸去來辭》,既次其韻,又衍為長短句,又裂為集字詩,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爾!是亦未免近俗也。”[26]徐時棟認為:“昔坡老嘗集《歸去來辭》為詩矣,辭字繁多,捃摭既易,隨意命句,署對非難矣。且全用其文,無剪裁錘煉,即其意義亦頗雷同。”[27]集字詩之所以有如此的評價,與其寫作性質有關。有特定范圍的集字詩,受內容和主題的局限,“集”他人作品中的“字”而成,詩歌并非原創,集字詩作者只是略加改造,作了“收集”和“重鑄”的工作。如集《歸去來兮辭》中字,像“琴”“酒”“鳥”“菊”這些意象似乎總是和平淡、閑適、隱逸的生活意味掛鉤;集《蘭亭集序》中的字,“春”“亭”“管”“弦”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群賢畢至”的蘭亭雅會,這些圖畫式的漢字已經決定了詩句的意指。詩人們在拼接意象的同時又自動組合了這些“點狀”的文字,使他們不言自明地呈現出相似的意義。由于取字范圍的局限性,選辭定韻較為容易,而且意象與主題多與原作相差不大。所以徐時棟的擔憂也不無道理,從經典中集字會把詩人的思維固定在前人作品窄小的天地里,不但難以生出新意,而且很容易弄巧成拙,點金成鐵。王士禛認為:“詩集句起于宋,石曼卿、王介甫皆為之,李龏至作《剪綃集》,然非大雅所尚。近士大夫競以詩牌集字,牽湊無理,或至刻之集中,尤可笑”[28],以“詩牌”集字成詩大多是隨便拼湊所得,既不合詩律,也不符合詩教“雅正”的傳統。這樣的拼湊之詩,孩童亦能為之,清人魏象樞即與其子合作《除夕禁爆竹聲閭巷甚靜呼兒集字成詩》,所以清末文廷式在《論詩》中提到:“風雅而還讀楚辭,紉蘭佩芷不相師。烘爐自有陶鈞術,怕看人間集字詩。”[29]文廷式歷來反對詩歌的因襲拼湊,認為應該獨出機杼,自辟蹊徑,講求詩歌的創新和發展。而集字詩既不是詩人獨立自主的創作,也不符合詩歌的進步和創新,因此作為文人之間的游戲之作,宴飲助興尚可,登大雅之堂則不夠資格。
而有的集字詩則因為集字的渾然天成、恰到好處而受人稱贊。清初文人項景襄《初冬送繆天士南歸集字》“只因喧洛下,豈愿客長安”一聯,被鄧漢儀評為“自然之極”;“故人情意重,共說且加餐”一聯,被評為:“清真脫化,幾不知為集字詩”。[30]911這兩聯詩并沒有因為以詩牌集字的局限性而阻礙了詩歌本身情感的表達,是真實情感與所見之漢字的自然興會的過程。《暮春同顥亭、胤倩、岱麓、子長詣慈仁寺看海棠,集字為詩,遇健庵、端士共飲花下再賦》中有“詩不如人好字稀”句被奉為“集字場佳話”[30]911,該句巧妙自然地道出了當前作者作集字詩的尷尬處境,本應起限制作用的“詩牌”,此時也完美地順應了作者的作詩思路。清人鄭熙績《題友人張氏蓮花別墅集字》:“早秋清泛水亭邊,滿座荷香拂綺筵。高臥煙霞留石韻,遙聽歌炊接冰弦。松風忽送三山雨,柳浪還通九曲泉。野老忘機惟習靜,閑看浴鷺傍池眠。”其自我評價為:“集字中難得一氣混成,絕無補綴饾饤氣息,所以為佳。”[20]63之所以稱其“一氣混成”,是因為這些詩作不像是從詩牌中集字而作,更像是作者有感于當下,發自內心的自然創作,而恰好與詩牌中的字對應。本真的內心之語與詩牌的對應之字的欣然相遇,如緣分般美妙的契合,自然造就出集字詩“渾然天成”的神奇作用。所以集字詩在本身莊諧性質統一的同時也趨向于達到外在雅俗共賞的審美需求。吳綺在為何云壑《轉運集字詩》作序時,對集字詩的詩學性能作了明確的揭示:
夫詩緣至性,實本別才;聚腋成裘,裘合而寧知是腋;將花釀蜜,蜜成而無復為花。此豈屬乎人能,良亦關乎天巧。若乃五音迭奏,并合宮商;雜彩相宣,自成機杼。相其體制,風華不讓齊梁;攬厥篇章,大雅無傷李杜[31]。
吳綺此語強調了集字詩創作中漢字單元與詩歌整體的密切關系。“聚腋成裘”“將花釀蜜”不僅僅是字數由少到多的積累過程,更是將漢字的性質、蘊意等“天巧”范疇下的部分通過“人能”等技巧性的布局和安排,配合演奏出“五音迭奏”的宮商之曲。所謂“渾然無集字之跡”的效果,就是“天巧”和“人能”相互作用下的最高境界,全然不見“集字”這一外在因素,詩人之“藝”與漢字之“意”巧妙融合,只呈現出“蜜”,“而無復為花”。以經典集字成詩,本意就在于學習風雅之語,感受先賢魅力,雖有“附庸風雅”的嫌疑,但也顯示出集字詩最初想擺脫“近俗”之弊的努力。集字詩在發展過程中的兩種集字方式,也決定了集字詩呈現出“莊諧并重”“雅俗共賞”的風格特點,看似對立實則平衡了集字詩審美構成的失重,使得集字詩能夠穩定并長期保持這種風格特質。
結" 語
集字詩作為雜體詩的一種,有其萌發的特定的歷史土壤和實現其詩體功能的客觀需求。從“經典”中集字是集字詩自宋代初興之時的原始風貌,是在莊重嚴肅的場合下,寄托著個人心志的“雅正”之作,集字詩作為推動文學經典化的一種重要方式,其價值不容忽視。發展至明清時期,“詩牌”的風靡,集會詩社活動對集字成詩的追捧,集字詩“游戲”“娛樂”的性質愈發強烈,清代文人傳承并擴寬了宋代集字詩的范圍,表現出對駕馭漢字、組合詩意的強烈興趣和高超能力。集字在詩歌領域的成熟也促使其延伸至其他文體領域,比如明人孫李昌的集《赤壁賦》字作《點降唇》曲;清人顧子山集《歸去來辭》成《沁園春》詞,陸茨云《浣溪沙集字》、何五云《菩薩蠻夏景集字》等集字成詞,諸如此類的集字文學無不彰顯著漢字的活力。“求詩味于鹽梅姜桂之表,運詩妙于神通游戲之境”[32],詩人們以帶著鐐銬跳舞的本領在文字聲韻的譜系上嵌字填空,不但凸顯著作詩者的智慧和機趣,展示著語言文字運用“字字珠璣”的美感,而且文人們通過把玩“漢字的魔方”,在調節文人生活情趣、啟發心靈巧思方面,也起著點滴涓助的功用。
[1]張彥遠.法書要錄[M].洪丕謨,點校.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6:90.
[2]高不騫.傅天集[M]//《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第2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44.
[3]陸以湉.冷廬雜識[M].冬青,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39.
[4]溫汝能.和陶合箋[M].清光緒十八年上海五彩公司石印本.
[5]馮應榴.蘇軾詩集合注[M].黃任軻,朱懷春,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204.
[6]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全宋詩:第61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38184.
[7]顧光旭.響泉集[M]//續修四庫全書:第145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47.
[8]祝德麟.悅親樓詩集:卷三十[M]//續修四庫全書:第146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38.
[9]蘇文忠公詩集[M].紀昀,評//蘇軾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1979.
[10]王十朋.梅溪集[M]//《梅溪集》重刊委員會.王十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1]金武祥.粟香隨筆上冊[M].謝永芳,校點.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343.
[12]戴璐.吳興詩話[M]//續修四庫全書:第170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67.
[13]蔣寅.生活在別處:清詩的寫作困境及其應對策略[J].文學研究,2020(5).
[14]胡震亨.唐音癸簽[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05.
[15]費經虞.雅論[M].費密,補//續修四庫全書:第169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80.
[16]趙吉士.寄園寄所寄[M]//續修四庫全書:第119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95.
[17]L.R.帕默爾.語言學概論[M].李榮,王菊泉,周流溪,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117.
[18]吳承學.文字游戲與漢字詩學——《詩牌譜》研究[J].《學術研究》2000(7).
[19]葉威廉.中國詩學[M].北京:三聯書店,1992:15-16.
[20]鄭熙績.含英閣詩草[M]//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74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21]錢仲聯.清詩紀事[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1807.
[22]魏象樞.寒松堂全集[M].北京:中華書局,1996:725.
[23]趙吉士.萬青閣全集[M]//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
[24]尹嘉銓.偶然吟[M]//四庫全書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68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436.
[25]王國維.王國維文集·人間詞話刪稿[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169.
[26]王若虛.滹南詩話[M]//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514.
[27]徐時棟.煙嶼樓文集:卷二[M]//續修四庫全書:第154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47.
[28]王士禛.王士禛全集[M].濟南:齊魯書社,2007:4603.
[29]文廷式.文廷式詩詞集[M].陸有富,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19.
[30]鄧漢儀.慎墨堂詩話:卷二十一[M].北京:中華書局,2017.
[31]吳綺.林蕙堂全集[M]//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255-256.
[32]揭傒斯.詩法正宗[M]//續修四庫全書:第169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47.
(責任編輯:徐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