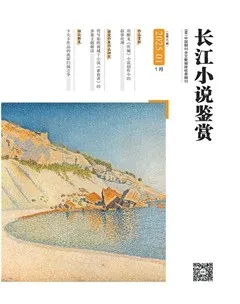論殷健靈的少女成長問題書寫
[摘要]青春期少女心理成長書寫拓寬了成長小說的書寫邊界,有關兩性發育、融合教育題材的作品也豐富著21世紀以來成長小說對中國少女成長多元樣貌的呈現。殷健靈的成長小說《紙人》《哭泣精靈》《橘子魚》等展現了青春期少女身心遭受的創傷以及她們的成長蛻變,深受少年讀者青睞。其作品給予青春期少女心靈上的啟迪,為她們的成長提供借鑒,同時對少女文學寫作產生重要影響。
[關鍵詞]殷健靈" "成長" "少女形象
[中圖分類號] I207.4" "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5)01-0033-05
一、緒論
少女時代是女性生命周期中一個非常關鍵的階段,在女性的個體成長軌跡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成長小說,尤其是針對少女成長的書寫,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與學術價值。少女群體在成長過程中的獨特思維方式與生理特征,使得她們對成長的感知更為敏銳。這種敏感性不僅體現在她們對自我身體變化的關注上,如初潮所帶來的羞澀感,更體現在她們對外界評價與異樣目光的感知上。這種因敏銳的感知能力而產生的敏感細膩的心理變化,為成長小說中的少女成長書寫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20世紀80年代,青春文學創作熱潮興起,影響到成長小說的創作,青春期少女的成長歷程以及心理轉變得到更多關注。少女作為作家無法回避的書寫對象,她們成長中的美麗與迷茫得到展現。少女形象和少女成長的書寫在成長小說領域擁有了獨立的發展空間。然而,不同的作家在創作中會呈現出不同的風格。與大多作家對少女成長和少女形象的階段性聚焦描寫不同,殷健靈的作品展現的是少女的成長鏈條,對于少女成長的關懷多借由文中充當“擺渡者”的角色與少女們的交往活動展現出來。在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少女成長擺渡”可理解為:引導少女在成長過程中正確看待心靈上的創傷或挫折,用一種外界的力量幫助她們克服困惑和痛苦,最終實現自我成長和心理重建。在此基礎上,殷健靈的作品引導少女去開發自身的潛力,找尋自我救贖的勇氣,懂得他者陪伴的意義。在內外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殷健靈筆下的少女角色通常能夠實現從“含苞待放”到“落落大方”的成長蛻變。
二、撫平心理創傷
深入剖析殷健靈的作品對于少女心靈創傷的撫慰作用前,我們必須先明確成長與心靈創傷的共生關系。
心理學家卡爾·榮格(Karl Jung)強調,心理創傷往往隱藏在日常生活的點滴之中,或明顯或隱晦地影響著個體的心理發展和行為表現①。在少女成長的旅途中,心靈的創傷往往通過多種復雜且微妙的方式表現出來,這些表現形式構成我們理解和援助她們的基礎。莫迪凱·馬科斯(Mordecai Marcus)在《什么是成長小說》一文中對成長小說進行了歸納:成長小說展示的是年輕主人公經歷了某種切膚之痛的事件后,改變了原有的世界觀或性格,或兩者兼有;這種改變使他們擺脫童年的天真,并最終將他們引向一個真實而復雜的成人世界[1]。在這個過程中,儀式本身的重要性相對較小,但必須證明這種變化對主人公會產生永久的影響。莫迪凱·馬科斯將成長小說的關鍵詞歸納為“年輕的主人公”“經歷切膚之痛”的轉折點,最終引向“成人世界”。“經歷切膚之痛”作為少女成長的轉折點,為成長籠罩上一層揮之不去的悲傷。
1.淡化對死亡的恐懼
生命的輪回是自然界中再正常不過的現象,每個人都會經歷生命終點的洗禮。然而,對于一個正在成長中的少女,死亡的概念仍然顯得陌生而遙遠。在過去的歲月里,由于成長小說的特殊讀者群體,“死亡書寫”一直備受爭議。然而,隨著死亡教育的普及,越來越多的成長小說作家開始關注這一主題,嘗試以成長小說的形式描繪死亡。殷健靈的作品在這類題材中獨具魅力,作家沒有對死亡進行生硬解釋或梳理,而是選擇用溫暖的陪伴和美好的回憶來淡化死亡帶來的恐懼。散文集《愛——外婆和我》是殷健靈在真切感受親人離世的深切悲痛后的真情流露,記錄了作者和外婆數十年相互陪伴的點點滴滴。書中前半部分的基調十分溫暖,講述殷健靈在外婆的陪伴下度過的幸福童年生活。外婆對這個并沒有血緣關系的小孫女極盡寵愛:會容忍小孫女不肯洗澡、學大人說臟話、發脾氣,甚至縱容她含著滿口巧克力入睡。后半段則用大量筆墨書寫步入高齡的外婆慢慢衰老,一步一步走到生命盡頭:逐漸衰老的外婆摔倒后再也不能像剛搬家時那樣毫發無傷地站起來了,她慢慢變得茫然、遲滯,甚至患上阿爾茨海默病,最后永遠離開了“我”。在殷健靈的筆下,這些關于外婆衰老和死亡的記憶帶給讀者的似乎并不是恐懼,反而有種陽光灑在身上的暖意,就像作者談及這本書時所說的:“寫完后我發現,那個瓶塞被拔掉了,負面情緒疏解了,我得到了一種安慰,也告慰了外婆。”殷健靈以成人的視角書寫這段經歷,給予那些與曾經的她一樣恐懼親人離世的少女以情緒支持,教會她們如何用記憶挽留過去的溫暖,理性面對親人逐漸衰老時可能會產生的遺憾。
2.擁有自我救贖的勇氣
長篇小說《哭泣精靈》通過禍福相生的意蘊,塑造了一個在困境中實現自我拯救的典范形象米粒。米粒的心靈創傷源于家庭環境的不和諧。剛上二年級、年僅9歲的米粒不能理解媽媽為什么要搬出去住,爸爸為什么不去把媽媽追回來。小說詳盡地描繪了米粒在成長過程中遭遇的挫折,通過描寫米粒倔強的目光和紅腫的眼睛等細節展現父母離異帶給米粒的創傷和痛苦。小說結尾,米粒沒有哭,她似乎哭不出來了,在這個過程中米粒收獲了成長,并拯救了自己。丁冬的幫助使米粒在與現實相對照的另一個世界找到了與相親相愛的爸爸媽媽生活在一起的另一個“自己”,并懂得愛與珍惜的意義。兩個世界的經歷使米粒堅強成熟起來,她不再沉迷于另一個世界中家的美好,也不再執著于讓現實世界中關系破裂的父母重歸于好,她坦然接受父母離異的事實,破碎的心靈也在自我療愈后結了一個如花朵一樣的痂,在沒有任何損傷的父愛和母愛的呵護下繼續快樂地長大。
少女在成長過程中,不僅要應對家庭離異的創傷,還會遭遇多種心靈層面的挑戰與打擊。這些心靈創傷如同結痂的傷疤,隱喻著成長需要經歷的痛苦,付出的代價。然而,殷健靈的作品以其深刻的洞察力與人文關懷,如同《哭泣精靈》中的仙人丁冬一般,為少女們提供心靈的指引和慰藉,給予少女在成長過程中拯救自我的勇氣和力量。
三、指引身體的成長
少女在成長過程中,身體發育常常給她們帶來各種煩惱。我們常常在少女讀物上讀到關于青春期少女厭惡和恐懼身體發育的文章。《意林小小姐》就是一本深受少女喜愛的讀物,少女讀者在讀后感中講述了“大姨媽”來臨時的不適,表達了厭惡之情,甚至表示因同齡異性的打趣感到自卑和困惑。但是在殷健靈的作品中,青春期發育被描繪成美好的事物,這種描繪有助于少女們更好地認識自己,接納自己。
1.乳房和初潮
青春期女孩的生理變化,首先從乳房的發育開始,即乳房的隆起。這其中的每一個階段都會給少女們帶來前所未有的新奇體驗,有時還會伴有強烈的羞恥感,這種羞恥感往往由同齡異性的他者帶來。《紙人》中,與秋子同齡的莫克因為有著較為早熟的性自覺,多次對秋子的乳房發出不懷好意的疑問,“長著那東西重不重”,并以看到秋子羞紅的臉為樂趣。為沖淡社會文化背景下關于女性乳房發育給少女們帶來的羞恥感,殷健靈的作品對少女身體發育過程的描寫帶有一定的神圣色彩,這種神圣性主要是通過對少女乳房發育的象征物——花朵的選擇體現出來。在長篇小說《米蘭公寓》中,殷健靈用一朵花的成長過程來象征少女乳房的發育,“蓮蓬的生長暗示了整個生命的過程,蓮花凋謝,蓮蓬生長;蓮蓬敗落,蓮子成熟,新的生命開始了……孕育著蓮子的蓮蓬恰如眾多生命的種子,恰似少女含苞的乳房”,從女性乳房的生理意義角度帶領少女們重新認識自己的身體。
月經初潮也是少女青春期身體發育的重要標志。殷健靈在作品中也多次描寫這個過程,為了幫助少女更好地接納這種自然的生理現象,她還專門寫了同名散文小說《初潮》,“那年冬天,大雪紛紛揚揚,數日不停。我從寂靜的黎明醒來,雪的折光使床單的顏色更為鮮明,床單的中央,開放著一朵暗紅色的小花,那是我第一次生命的潮汐”[2],唯美而溫暖。
2.他者影響下的自我成長
在殷健靈的作品中,少女角色的自我認知過程不僅是一段自我發現之旅,更是一系列內心沖突、自我疑問和自我肯定的循環往復。少女們探索自我內心世界的同時,往往會得到家人、朋友,甚至陌生人的陪伴和支持。
處于成長過程中的少女經事少、閱歷淺,特別在乎他人對自己的評價,從而產生自我認知困惑,常常是在經歷了種種內心掙扎后,才能完成對自我的正確認知。通過深入剖析殷健靈的作品,我們得以洞察他者的陪伴在少女自我認知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在殷健靈的文學世界里,他者形象呈現多元化的形態,主要囊括了年長同性他者、同齡友人以及年長異性他者等三種類型。其中,年長同性他者尤為顯著地影響了少女的自我認知與成長過程。
年長的同性他者不僅是影響少女的重要力量,更是少女在精神層面的支柱和成長道路上的指導者。少女往往對年長同性他者懷有崇拜之情,這種情感不僅促進少女對自我的深刻理解,更教會她們如何正視自我,接納自我。年長同性他者的言行舉止、溫柔的肢體接觸,成為少女成長過程中的重要參照和心靈滋養。作者通過描繪年長同性與少女在成長路上的心靈溝通和相互理解,展示了少女在遭遇挫折和困惑時,年長同性他者的陪伴與鼓勵如何幫助少女重拾自信,找回自我價值。在《紙人》中,丹妮作為一個同性長者的形象,貫穿蘇了了的整個少女時代,她安撫了蘇了了因偷看表姐身體產生的羞恥感,引導她認識自己,幫助她正確看待同齡異性的舉動,用更為成熟的心態去理解秋子的死亡。丹妮這一角色充分展現了年長同性他者在少女成長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殷健靈的作品充分展示了年長同性他者對少女成長的深遠影響。年長同性他者作為榜樣和心靈的引導者,能幫助少女更好地認識自己,接納自己,并在這個過程中找到歸屬感和自我認同。
四、殷健靈少女成長問題書寫的現實意義
1.展現更真實的少女成長
“人物形象是小說的主心骨,衡量小說成功與否的關鍵就看其人物是否逼真,形象是否飽滿。”[3]少女成長小說自然是以各種不同的少女作為小說的主要人物形象。不同于以往作家塑造的有著極強批判色彩、高揚青春激情的少女形象,殷健靈筆下的少女形象大多帶有作家本人的影子。我們了解殷健靈的成長經歷后會發現,她少女時代的履歷堪稱完美,她本人是完美適應傳統教育的好學生,是父輩眼里的驕傲,也是同齡孩子的楷模。如此完美的成長經歷使得殷健靈在塑造人物形象時必然會被這種思維定式所限制,故而“懂事乖巧”就成為她筆下一部分少女形象的標簽。大多這種類型的少女,在心理敏感而又脆弱的青春期里常常備受煎熬。長篇小說《玻璃鳥》中,少女在升入中學后,在一種莫名其妙的緊張壓力下總是控制不住幻想自己將來會成為一個深受大家歡迎的孩子,一個乖巧可愛的“好孩子”。“我已經學會區分哪些欲望是合理的,哪些欲望是不合理的,然后,我學會了克制。”[4]殷健靈接受采訪時也說過:“我并不滿意自己的少女時代,如果讓我重頭來過,我會怎樣呢?我會更張揚天性;我會勇敢表達我需要愛;我會剔除束縛做一個完完全全的自己。”[5]可以說這種追求“乖巧懂事”的乖乖女,是作家殷健靈自我成長軌跡和價值觀的投射,也是當下社會傳統教育理念規訓下的少女典型。正是因為意識到這一點,殷健靈圍繞這類少女的“修女式”成長塑造了另外兩類與之相對的少女群體。一類是圍繞在追求“乖巧懂事”的少女們身邊,熱情似火、天真開朗、充滿著旺盛生命力的少女形象;另一類是與乖巧少女完全相對的叛逆少女,她們性情乖張、叛逆沖動、脾氣暴躁,幾乎是和傳統教育相悖的典型,她們代表在青春期不愿被管教的那一類少女,她們大多因為不正確的引導最終走向生命的終結。《橘子魚》中,少女艾未未從出生起就同父親生活在一起,父親冷漠寡言,艾未未無法和他交流自己的心事。不同于《玻璃鳥》中害怕精致美麗的羊毛衫引起他人注視的“我”,艾未未恨不得將自己裝扮成一只花孔雀,她開始嘗試著用外部的改變來吸引周圍人的注意,對傳統教育規章下的“好孩子”規則嗤之以鼻:把自己的頭發染成跟周圍同學格格不入的藍綠色;在寒冷的冬天堅持穿一條單褲,還一定要把一節腳腕露在外面;故意在考試的時候發揮失常。這種習慣性的自我放縱使得她過早品嘗青春禁果,并為此付出一定代價。顯而易見,這類少女形象與前者形成鮮明對比,她們不再是懂事聽話、善于隱藏克制的好好學生,而是為了引起他人注意敢于張揚自我的叛逆少女,殷健靈筆下的這類少女形象顯然帶有濃重的規勸意味。
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底色,少女們在成長過程中所要面對的問題也日新月異,殷健靈從不同的角度塑造出一個個獨特的少女形象,使其作品具有了跨時代的教育意義。
2.對少女嚴峻生存現實的觀照
傳統文化中,性教育的保守使得家長們在教育孩子時對“性”話題盡量閉口不談,加上學校生理教育課程缺失,互聯網成為青春發育期的孩子獲取性知識的唯一渠道,但互聯網上的性知識往往參差不齊。作為一名女性作家,殷健靈認為處于青春發育期的少女相較于男孩更加敏感和脆弱,這些未經篩選的性知識可能會導致少女對“性”的認知產生偏差,于是作者決定通過文學創作指引少女們正確面對青春期的各種挑戰。由于性教育缺失導致的少女媽媽問題,是觸動殷健靈創作小說《橘子魚》的一個重要動因。她在這本小說的后記《美麗的泅渡》中說:“少女媽媽成為現今社會的新問題,‘性’從諱莫如深的圈囿中走了出來,甚至有了泛濫之勢。在某種意義上,它比性禁錮更可怕。”殷健靈以彌補少女性教育缺失為創作目的,通過書寫性格、經歷不同的少女媽媽相同的悲劇命運,勸誡青春期的少女正確對待“性”。小說《橘子魚》中,作者以雙線并進的形式為我們展示了艾未未與夏荷的成長軌跡,以及盛曉虹與秋子的悲慘結局。小說中,艾未未與夏荷都順利地度過了成長之河中的波瀾,而幫助和引導艾未未正確對待性行為,化解艾未未對于性恐懼的正是成年后的夏荷。殷健靈正是通過對夏荷與艾未未、盛曉紅與秋子兩組少女媽媽相同經歷不同結局的書寫,凸顯當今社會正確合理性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相較于教育者的刻意隱瞞導致少年男女通過其他的途徑,去獲得有關這一問題的信息,進而有可能對這一問題形成有誤差的認識[6],不如通過健康的性教育引導少女獲得性生理和性心理的正確認識。
五、結語
殷健靈在20多年的文學創作生涯中,始終保持著一絲不茍的寫作態度,為我們創作了一部又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她的少女文學創作具有鮮明個性,主要集中于少女的成長問題書寫[7]。其對于少女內心世界的細膩描繪,讓我們看到了少女們在成長過程中經歷的迷茫與掙扎。殷健靈的作品中,少女成長問題往往與家庭、學校、社會等多方面因素緊密相連。在家庭中,少女們面臨父母的殷切期望以及復雜的家庭環境等多重壓力;在學校中,她們則需要應對學業壓力、人際關系等挑戰;在社會中,她們更是需要面對性別歧視、社會期望等種種問題。這種深入骨髓的書寫方式,使得殷健靈的作品具有極強的感染力,引起廣大少女讀者的情感共鳴。此外,殷健靈的少女成長問題書寫還體現了深切的人文關懷。作家關注少女們的內心世界,傾聽她們的心聲,理解她們的困惑與掙扎,在她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她對少女的關愛與鼓勵,也看到她對少女未來發展的期許與祝福。這種人文關懷使得殷健靈的作品具有一種溫暖而感人的力量,給予讀者啟示和力量。
殷健靈的少女成長問題書寫獨特而深刻,其作品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和深遠的社會意義,值得深入探究。
注釋
① 榮格學派心理學家唐納·卡爾謝曾在《創傷與靈魂》一書中提及,成長過程尤其是童年的創傷經驗,會在兒童的潛意識中形成一個矛盾的保護機制,這個保護機制會以天使、神仙教母、可靠穩重的男性等方式出現在內心幻想或夢境里,向兒童保證會提供絕對的安全與保護,然而隨著兒童日漸長大,這份保護也變成可怕的牢籠,天使會威脅創傷幸存者不可以隨便相信別人,因為這世界上到處充斥著可能會傷害他的怪物。
參考文獻
[1] 芮渝萍.美國成長小說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2] 殷健靈.紙人[M].武漢:湖北少兒出版社,2007.
[3] 王瑞祥.兒童文學創作論[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4] 殷健靈.玻璃鳥[M].南京: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2009.
[5] 殷健靈.紙人[M].南昌: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00.
[6] 沈約.成長的陣痛——談殷健靈作品中對少女問題的書寫[D].金華:浙江師范大學,2009.
[7] 杜妍.殷健靈少女文學創作研究[D].長沙:湖南師范大學,2020.
(特約編輯" 張"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