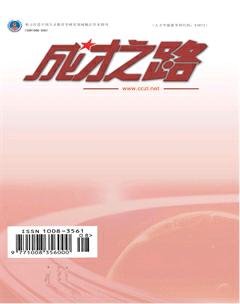四個優化提高信息技術課堂效率探研
高太山
摘 要:在教學實踐的基礎上,從優化教學設計、優化教學過程、優化教學手段和方法、優化教學評價等角度出發,探討了提高信息技術課堂教學效率的方法,從而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
關鍵詞:信息技術;課堂效率;四個優化;全面發展
中圖分類號:G633.9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3561(2016)23-0096-01
信息技術是特教學校的一門基礎性課程,在教學中,教師要在知識與技能、過程和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等方面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為實現這一目標,教師必須要提高課堂教學效率。而如何提高信息技術課堂教學效率,是擺在信息技術教師面前的一項重大課題,也是一個既古老又常新的話題。從多年的教學經驗來看,殘疾學生學習信息技術會取得什么樣的效果,主要取決于教師對課堂的掌控情況,教師要從優化教學設計、優化教學過程、優化教學手段和方法、優化教學評價等角度出發,科學地利用課堂環節提高課堂效率。
一、優化教學設計
教學設計是教師設計課程的依據,主要包括教學目標、教學重點和難點、教學方法、教學過程、時間分配等環節。可以說,提高信息技術教學效率的一個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優化教學設計。優化教學設計,最重要的是優化教學三維目標。教學三維目標的優化要按照特殊教育學校信息技術教學目標和任務來進行,這既是素質教育和新課程改革的要求,也是符合殘疾孩子受教育的任務型導向。在信息技術教學中,教師要使學生在知識、技能、能力、情感態度、價值觀等方面達到預定的目標,從而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例如,在講授“書寫環保倡議書”這一課時,教師首先要明確本節課的三維教學目標。一是知識目標:啟動Word,輸入文字、正確換行。二是能力目標:通過學習讓學生認識Word軟件的窗口組成,能熟練輸入倡議書內容,并能保存倡議書。三是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目標:第一,形成嚴謹、科學的學習態度;第二,養成保存文件的好習慣。
二、優化教學過程
教學過程是一種預設的程序結構,具體地說,是教學活動的啟動——發展——結束在時間上連續展開的程序結構。教學過程作為一種特殊的認識過程,也是一個全面促進學生身心發展的過程。要優化課堂教學過程,必須要打破傳統的條條框框的束縛,打破所謂的固定程序化。教師要縝密地進行全面思考,要充分考慮教材情況、學生情況、教學設施設備情況,并結合教師自身知識儲備的特點,圍繞三維教學目標設計教學過程。設計教學過程,要做到既合理又科學,二者缺一不可,只有這樣,才能較好地把握好教學節奏,才能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另外,優化教學過程中要注意,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并把兩方面進行有機結合,進而才能關注所有學生的發展和進步。
三、優化教學手段和方法
教學手段和教學方法有相似之處,但它們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意義,不能混為一談。優化教學手段需要教師有效地掌握以多媒體課件為核心的現代化信息化教學手段,并加以合理利用。可以利用信息化教學手段直觀性強的特點,把抽象的化學知識具象化,進而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教學方法多種多樣,傳統的“滿堂灌”“填鴨式”教學已無法適應素質教育和新課改的要求,因此必須優化教學方法。優化教學方法要根據不同的課題進行,而不是拘泥于某一種方法,教無定法便是最好的優化教學方法。情景教學法、情感教學法、演示實驗教學法、案例教學法等教學方法,都可以有選擇性地拿來使用。例如,信息技術是一門實踐性強的課程,有些概念較為抽象,學生不易理解,需要把抽象的問題具體化、形象化,這就需要用到情景教學法。總之,優化教學方法要根據相應的教學內容來完成,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提高教學效率的目的。
四、優化教學評價
教學評價包含多重因素,這里的教學評價主要指課堂上教師對學生表現的評價。教與學的過程是一個辯證統一的過程,因此,在教學過程中要積極倡導一種良好的師生關系,這種關系主要表現為民主、和諧、平等。要維持這一良好的關系,教師要格外注重對學生的評價,既要重視定性評價,也要重視定量評價。課堂上,教師一方面要盡量了解學生掌握知識的情況,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學生的情緒變化和反應。因此,只有對學生的表現采取積極正確的評價,使學生得到應有的尊重,才能激發學生學習信息技術的積極性、主動性。
五、結束語
綜上所述,實現較高的課堂效率,是保證特殊教育學校信息技術課程教學質量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前提條件。想方設法提高特殊教育學校信息技術課堂教學效率,是信息技術教師孜孜追求的目標,需要師生雙方的共同努力。教師要從優化教學設計、優化教學過程、優化教學手段和方法、優化教學評價等四個角度出發,引導學生開展形式多樣的學習,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進一步提高信息技術課堂教學效率,是需要引起教師重視的,也是值得期待的。
參考文獻:
[1]陳詩琦.提高信息技術課堂教學有效性策略探討[J].寧德師范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14(03).
[2]孔令領.淺談如何提高信息技術課堂效率[J].教育實踐與研究,2013(09).
[3]薛利娟.如何提高中學信息技術課的課堂效率[J].內蒙古教育,201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