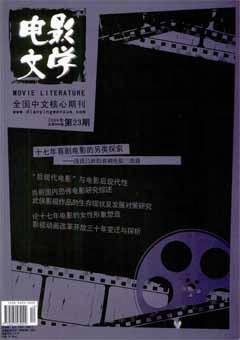十七年喜劇電影的另類探索
趙瑞鎖 賈 月
[摘要]呂班是新中國喜劇電影的拓荒者之一。他執導的喜劇三部曲《新局長到來之前》《不拘小節的人》《未完成的喜劇》是中國喜劇電影史上的經典作品。本文通過分析呂班喜劇電影中對意識形態的表現,重復、移植、巧合等喜劇手法的運用來重新審視和評價這位新中國喜劇電影的重要導演。
[關鍵詞]諷刺;意識形態;喜劇技巧
電影與生俱來就帶著喜劇的色彩。在這種集合了聲畫光影的藝術形式誕生之初,它最主要的表現形式便是喜劇片,如最為人們熟知的盧米埃爾兄弟制作的電影《水澆園丁》,便利用生活中常見的水管向人展示了電影天生具有的喜劇性。因為喜劇片有利于電影討好觀眾和贏取票房,早期的中國電影多以喜劇為內容。20世紀30年代。國家危亡導致電影加強了意識形態功能。左翼電影人開始了揭露社會黑暗,表現小人物困苦生活的悲、喜劇創作。加年代,以《太太萬歲》和《烏鴉與麻雀》等為代表的喜劇承載了電影工作者對當時社會的人文批判。總之,動蕩不安的社會局面和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造成了中國喜劇電影一以貫之的譏諷時事的特點,成為中國喜劇電影特有的民族風格。
新中國成立后,無論從哪方面說。喜劇電影的創作似乎都應該延續此前的輝煌,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在1949—1955年的中國電影史上,除去一些具有喜劇因素的影片之外,整整7年沒有拍攝過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喜劇片。這種情況在中外電影史上實屬少見。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缺乏產生喜劇的社會文化生態環境是最主要的因素。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幾個年頭,人們都沉浸在周圍戰爭頻發、政治運動不斷的社會氣氛中,人們的審美意識重心在于追求強烈的戲劇沖突與體現沉重的情感。喜劇很難進入文藝家的審美視野。直到1956年,由于戰爭的結束、“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的提前完成、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等一系列鼓舞人心的社會現象出現之后,整個社會的文化環境才呈現一種較為寬松的局面。在這樣的背景下,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影響下,電影界才有勇敢者出來一試身手。他就是呂班。
在經歷了批判《武訓傳》、批判俞平伯、反胡風、內部“肅反”等一連串運動后,電影界的創作活動比較寥落。1956年,在雙百方針的號召下,電影局提出了“三自一中心”(自由選材、自由組合、自負盈虧與以導演為中心)的重要主張。這一主張為藝術家自由發展自己創作提供了一定的空間。幽默開朗的呂班與相聲演員侯寶林、馬三立、編劇何遲等人組成了“春天喜劇社”,積極籌備著屬于他的喜劇電影。
1956年,呂班拍攝了他著名的兩部喜劇電影——《新局長到來之前》和《不拘小節的人》。作為新中國諷刺喜劇的試水之作,這兩部電影在當時社會的反響不錯。呂班針砭時弊的喜劇不僅給觀眾帶來了笑聲。同時還引起了強烈的共鳴。1956年和1957年前后。《大眾電影》等刊物以大量的篇幅介紹呂班的喜劇創作,《新局長到來之前》的劇照占據著刊物大量版面,各種與之呼應的文章也隨之而出。但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電影的問題并不是其藝術成就上的高低問題。而是其政治立場是否正確的問題。一部電影的命運與文藝界的評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呂班拍攝《新局長到來之前》和《不拘小節的人》這兩部電影時所持有的溫和批判態度,雖然在他的第三部喜劇電影《未完成的喜劇》得到了延續。但這部電影卻遭到了嚴重的批判。1958年5月,中央電影局召開創作思想躍進會議,批評《未完成的喜劇》是一部“徹頭徹尾的反黨反人民的毒草”,導演呂班也被批評為是“電影界的敗類”。粉碎“四人幫”之后,呂班的錯案才得到改正,由他導演的電影也被重新評價。《新局長到來之前》被視為開拓新中國喜劇領域的創作。
一、對意識形態表現形式的探索
研究十七年電影中的喜劇片類型,首要的一點,是不能回避其中的意識形態屬性。按照好萊塢喜劇電影的制作觀點,存在于故事結構中的喜劇因素并不要求有具體的主導動機來將各個事件拼湊在一起,甚至不要求所敘述事件以任何方式與故事發生聯系,而純粹處于喜劇效果的考慮放棄敘事的完整。因此,一切荒誕情節樣式以及偶發性、隨意性在喜劇創作中都是允許的,并且能為喜劇創作帶來極大的靈活性。但在呂班的喜劇創作中,這種純為喜劇效果而設計的情節不再出現。其喜劇效果的取得,不依賴于荒誕離奇的情節事因以及隨意、偶發性事件的大量穿插。相反,卻是完全建立在嚴密的敘事結構以及因果性動機的設置上。喜劇性場面始終沒有脫離開敘事而獨立發揮作用。影片《新局長到來之前》,牛科長牛大海的可笑之處,正是由于“牛大海想極力討好新局長”這一大“因”的設立。或者說,它存在于牛大海的主導動機之內。《不拘小節的人》緊緊圍繞李作家與女青年的數次見面做文章,為的就是后面兩人明白對方身份之后,女青年對李作家道德行為的批判。影片前后邏輯的發展是相當緊湊的,從而排斥了一切敘事情境之外的喜劇性因素,達到了意識形態循序潮進的教育功能。
呂班的這三部喜劇電影全部針對現實,反映人民內部矛盾。導演在批判那些落后人物、丑惡思想時,非常注意適度,并非像《未完成的喜劇》中那位文藝評論家那樣,將人與周圍的環境全都“一棒子”打死;而是將落后人物置于光明、正面的社會環境之中,讓他們接受社會的改造。《新局長到來之前》的張局長、蘇玲,《不拘小節的人》中的敏英姐妹,都是積極健康的社會力量,他們構成了“邪難壓正”的社會環境。在《未完成的喜劇》中,雖然影片內套的三個小故事表現的是揮霍浪費、自吹自擂、不孝敬父母等社會“歪風”,但影片中的喜劇創作者們已經表明了他們嘲諷的態度。亞里士多德說過,“喜劇要嘲諷‘比我們差的人”。三個小故事的創作者們都是社會正面力量的代表,而三個小故事所表現的歪風惡習在影片中明顯處于被諷刺批判的弱勢地位,是比社會大多數人差的人。
呂班的喜劇三部曲為新中國的喜劇電影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創作提供了具體的參照。隨著《未完成的喜劇》被扣上“毒草”的帽子,新中國的喜劇電影也開始了另一個方向的探索——以歌頌代替諷刺。《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等被人稱之為“社會主義新喜劇”的電影,雖然讓觀眾在笑聲中感受到了新時代的召喚,但一味地歌頌卻使得喜劇失去應有的現實意義。因此,20世紀60年代的喜劇,在歌頌中融合了呂班喜劇電影中審慎溫和的嘲諷,才有了《李雙雙》《大李、老李和小李》等更接近喜劇本質、貼近生活的電影。
二、在喜劇技巧上的嘗試
呂班作為新中國第一個開始喜劇創作的電影工作者,為了應對當時的社會形勢。他進行喜劇電影創作的第一要件就是要“穩當…‘收斂”,不能有無味的噱頭,不能太夸張,不能流于“鬧劇”。但即便是在受到種種限制的情況下,呂班還是自覺地為贏得觀眾笑聲而繼續探索。
呂班營造喜劇情節的方式主要有三種:重復、移植和巧合。
重復手法在喜劇情節中用得很多,而重復的事件本身
并不一定產生滑稽與幽默,甚至是平淡無奇的,但當它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時,構成一組結構相似的動作段落時就有可能好笑了。《新局長到來之前》有幾個人物輪番登場誤認張局長為修房的張老板的一場戲:先是牛科長大吹其與張局長是老戰友一同打過游擊,繼而崔庶務指使“張老板”快去修房以應付張局長的檢查,接著傳達室小青年又來責備張局長為何偷偷溜進來。接連不斷的三段相似噓頭重復強調,不僅不會使情節渙散,反而使整段劇情銜接得更為緊密,增加了笑的密度。重復手段以本身滑稽或不滑稽的單個事件組成,因重復性而生成一定的喜劇效果說明,喜劇片中相同或相似的情景反復出現,既是劇情敘述上的需要,又可通過視覺上的重復,達到內容上的強調,以引起觀眾的注意。咀嚼體味其中的內涵意蘊。得到應有的審美愉悅。
移置是喜劇作品中另一種運用廣泛的手法。移植是指兩組事物角色性質位置的互換使用,一組事物用的是另一組事物的屬性,而另一組則用了這一組的屬性,實質是兩組事物屬性的顛倒替代使用,由此引發意外的喜劇效果。身份的調換產生的喜劇效果對觀眾而言,是一種有意的期待,觀眾處于知情者的優越地位俯視角色間的“智斗”把戲。而對于《新局長到來之前》中張局長被當做修房的張老板這一角色身份的調換而言,觀眾也是以期待的心理看牛科長一伙是如何在新局長面前展露其真相的。這里喜劇的歡快感正是產生于知情與不知情的人物真假雙重身份之間,是對立的“知”與“不知”相互作用的結果。真真假假的關系構成了移置方式的喜劇效應,而觀眾心理期待的急切性更強化了這種喜劇效果。《新局長到來之前》是無意中張冠李戴、認錯了人物的身份。有意的移置是人與環境整個關系的錯位,是更為廣泛的移置。而無意的移置則屬誤會。從誤會的無意性起因中不難發現產生誤會的前提是讓兩個事物碰巧相遇或相合。《新局長到來之前》沒有事先約請姓張的老板,就不會有后面錯認新來的張局長的誤會。不論有意的還是無意的移置,在喜劇片情節的構成中都是不可缺少的要素。
“無巧不成書”。中華民族對戲劇性、故事性的偏愛歷來彌久,巧合無疑有助于故事的戲劇性,所以是文藝作品中最慣常的使用手法之一。故事情節較曲折的文藝作品,往往要借助“巧”字:人物關系及命運發展,事態的前因后果,矛盾的產生、發展與結局,諸如此類常常帶有很強的偶然性。正是這種巧合,大大增強了故事發展上的奇妙色彩與藝術魅力。簡言之,巧合是以人物出乎意料的奇遇或事情、細節的湊巧相合,使沖突以激變方式展開,造成波瀾與懸念。在其他文藝種類體裁的創作中也有“巧合”,但喜劇電影的“巧合”要巧得情趣,巧得有意蘊。而且它往往也參與構建喜劇的情節。《不拘小節的人》的喜劇性就主要體現在巧合上。李作家來某市的主要目的是講座,但李作家還有一個私人目的:見一位只鴻雁傳書卻從未謀面的女文學愛好者。李作家“不拘小節”的不良行為,如在汽車上扔果皮、在公園里亂摘花朵、在圖書館毀壞書籍、在劇院大聲喧嘩,每次都因為編劇的巧妙安排而被素昧平生的女青年遇上。李作家原本希望給女青年一個好印象,卻因為自己的“不拘小節”而惹怒女青年。而觀眾是一切巧合的且擊者和知情者,雖然猜到結局是不良行為的人要被拋棄,卻也樂得看到這樣的巧合繼續下去。
在電影完全為政治服務的年代,組織敘事的因素是主流意識形態,電影創作者們只有遵循這一前提。才能進行創作。呂班作為新中國眾多“帶著腳鐐跳舞”的電影導演中的一員,用他對喜劇電影的熱愛和嘗試為新中國電影的豐富繁榮做出了貢獻。雖然喜劇創作最終釀成了導演命運的悲劇,但歷史最終還予呂班和其作品應有的評價,他的電影也被后人重新重視并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