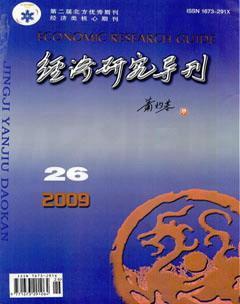完善民事訴訟法律監督的幾點思考
臧玉龍
摘要:為強化檢察機關對法院民事審判的法律監督,必須賦予檢察機關實施法律監督最基本的“知情權”,結合《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以及當前人民檢察院在行使民事抗訴權時受到的制約,并就當前民事抗訴制度中存在的缺陷,以及如何進行完善民事訴訟法律監督制度,從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強化法律監督權的角度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民事訴訟;民事訴訟法;法律監督
中圖分類號:D915.2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26-0243-02
檢察機關是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其對民事審判活動的法律監督主要表現為對已生效的民事裁判提起抗訴。2008年4月1日生效的《民事訴訟法》盡管對民事抗訴制度進行了部分修改和完善,抗訴情形增加為13項加一款,但民事抗訴制度的原有缺陷依然存在。結合《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以及當前人民檢察院在行使民事抗訴權時受到的制約,筆者就當前民事抗訴制度中存在的缺陷,以及如何進行完善民事訴訟法律監督制度,從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強化法律監督權的角度,提出幾點意見。
一、對未生效的民事判決、裁定無權抗訴,導致民事抗訴權不完整,限制了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權的行使
《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院只能“對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抗訴,對沒有生效的判決、裁定無權抗訴。這種事后監督模式排除了檢察院其他監督方式和手段,是將《憲法》賦予檢察院的完整法律監督權在民事檢察方面予以割裂,是對檢察院法律監督權的限制。對于“事后抗訴權”,有學者將之歸因于民法中的“不告不理”、“誰主張誰舉證”、“自愿原則”和“處分原則”,認為做為國家公權力的檢察機關抗訴權不宜過深介入,否則將會侵犯民事主體的“處分權”等私權利。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有待商榷。首先,民事訴訟中的私權處分是相對權而不是絕對權,不得因私權處分而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以及其他公民、法人等民事主體的合法利益。在司法實踐中,民事主體的私權處分行為也往往會涉及對國家公權利、公共利益的侵犯,仍然具有檢察機關代表國家進行監督(包括抗訴)的必要性。其次,從抗訴制度的設置以及抗訴權的本質分析,民事抗訴與刑事抗訴制度沒有本質區別,都是對適用法律是否正確的監督,不應因刑事案件、民事案件的區別而有事前事后監督之分。再次,我國現行的民事抗訴制度主要學習和引進了前蘇聯民事訴訟模式,隨著我國法治建設不斷完善和法學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們應該按照科學發展的觀點,敢于用批判的眼光和視角審視分析現有民事抗訴制度的缺陷和不足,對缺失的制度予以完善。
筆者認為,應當賦予檢察院在民事訴訟中完整的法律監督權,取消事后監督的限制。或者對《民事訴訟法》第179條規定的13種抗訴情形區別對待,分為事后抗訴和可以事前抗訴兩種情形區別對待。例如,對發現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一旦發現,檢察院立即可以提出抗訴,不必等到判決、裁定生效后再提出抗訴。
二、監督渠道不暢,民事抗訴權難以有效行使,制約了法律監督效果
《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院對已經生效力判決、裁定,發現有抗訴情形的應當提出抗訴。但《民事訴訟法》中卻沒有規定檢察院“如何發現”和“如何有利于檢察院發現”。筆者認為,監督手段缺失是民事法律監督制度設置中的一個重大缺陷,客觀上導致了檢察院在民訴案件監督中的消極、被動地位,對民事案件難以實現及時、全面、有效監督,嚴重制約了檢察機關對民事案件的監督效果。例如,《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法院民事判決書、裁定書副本向檢察院報送制度,也沒有賦予人民檢察院的調閱卷宗權,實踐中經常出現法院工作人員因存在抵觸情緒,不配合檢察院調取卷宗情況發生,既加大了監督的難度,又降低了司法效率,浪費了司法資源。因此,信息來源有限、渠道不暢、權力缺失成為民事抗訴案源枯竭,監督工作難以開展的主要原因。
筆者認為,為強化檢察機關對法院民事審判的法律監督,必須賦予檢察機關實施法律監督最基本的“知情權”應建立法院民事判決書、裁定書副本向檢察院報送制度,暢通民訴案件的監督信息渠道,使檢察機關及時、充分了解法院的民事案件信息,能夠通過判決、裁定及時、充分了解案件情況,對符合抗訴條件的案件提出抗訴。同時,應明確授予檢察院調取法院民事案件卷宗的權力,在檢察院向法院調取卷宗時,法院必須準許和配合,從而暢通監督渠道,減少工作阻力。
三、應完善檢察機關的抗訴情形,確立對損害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民事行為的抗訴權
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規定了檢察院可以提出抗訴的13種情形與當事人申請法院再審的情形完全相同,忽略了檢察院抗訴與當事人申請再審的區別,客觀上淡化了檢察院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的地位和職能。筆者認為,申請抗訴和申請再審是法律賦予當事人的兩種法律救濟途徑。從當事人的角度,無論是申請檢察院抗訴還是申請法院再審,其目的都是為了啟動審判監督程序,維護自身利益。因此,現實中,在雙方當事人認為各自利益實現的情況下,雙方提出抗訴申請或者再審申請的可能性極小。這意味著,在當事人雙方皆大歡喜,實現各自利益的情況下很難啟動抗訴程序。然而,當事人雙方皆大歡喜,實現各自利益的情況下是否就意味著該案件在實體和程序上都不會存在問題,不存在法律監督的必要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審視、分析民事訴訟,我們不難發現,盡管民事案件是解決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糾紛,但有時民事案件仍然會涉及到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公共利益。比如,民事案件的主體有時會是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國有企業,民事案件的標的也可能是國有財產或集體財產。不排除會出現民事案件當事人之間通過調解、協商等方式達成一致,而損害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情況發生。檢察院是法律監督機關,負有維護國家利益的法律職責。筆者認為,對損害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民事判決、裁定,應當賦予檢察院抗訴權,即使雙方當事人都不申請抗訴或再審,檢察院依然有權提出抗訴。
此外,法律應賦予檢察院在特定情況下對民事調解書的抗訴權。《民事訴訟法》182條規定,“當事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調解書,提出證據證明調解違反自愿原則或者調解協議的內容違反法律的,可以申請再審。經人民法院審查屬實的,應當再審。”根據這一規定,當事人對“調解協議的內容違反法律的民事調解書”可以申請再審。但是,法律規定檢察院只對“生效的判決、裁定”可以抗訴,卻未規定對“民事調解書”可以提出抗訴。這就意味著,對以調解書方式結案的民事訴訟,檢察院無權提起抗訴。但在司法實踐中不排除調解書中損害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情況發生。比如,作為民事訴訟一方當事人的機關、團體、國有企事業單位為實現某種目的,犧牲國家利益,以求的與對方當事人進行調節。因此,筆者認為,賦予檢察院代表國家對損害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民事調解書抗訴權,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四、應限制法院將抗訴案件移交下級院審判的自由裁量權,維護抗訴的嚴肅性
《民事訴訟法》第188條規定,“有本法第179第一款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情形之一的,法院可以交下一級人民法院再審。”而第181條第二款規定,“因當事人申請裁定再審的案件由中級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審理。最高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裁定再審的案件,由本院再審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審,也可以交原審人民法院再審。”188條和181條含義明確但邏輯上存在問題。根據第188條,接受抗訴的法院對檢察院提出的民事抗訴案件符合第179條第一款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情形之一的,既可以自己審理,也可以移交下級院審理,具有自由裁量權。從該條可以看出,如果接受抗訴的法院是中級法院,該法院有權將案件移交它的下級法院,即基層法院(不排除該案件的一審法院)審理該起抗訴案件。然而,根據181條第二款,又明確了當事人向法院提出再審的請求被采納后,案件一律由中級人民法院以上的法院審理,排除了基層人民法院審理再審案件的可能性。至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檢察院提起抗訴的案件,如果符合第179條第一款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情形之一的,基層人民法院可以審理,而同樣是第179條第一款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情形之一的,如果是由當事人向法院申請而被裁定再審的,則必須由中級以上的人民法院審理。同樣的情形,卻由于提出主體的不同,產生不同的處理結果。這種做法,既使得立法上出現矛盾,也與上級檢察院抗訴制度的立法精神和宗旨悖離,嚴重影響了檢察機關抗訴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筆者認為,對抗訴案件應一律由提出抗訴的同級法院審理,不得發回下級法院尤其是基層法院審理。從而實現提高審判效率、節約司法資源、維護審判權威性和檢察機關抗訴嚴肅性的多重效果。
五、應確立對執行程序的監督權,對法院的執行程序實施有效監督,完善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權
執行程序是民事訴訟的重要環節,關系到法律的實施效果和當事人合法權益能否得以實現,其重要性毋庸質疑。根據“有權利就應有監督”的法學基本原理,既然存在執行權,就應同時設置一種權利對之進行監督和制約。就現存的法律制度而言,法院的執行權主要通過法院內部上級對下級的監督,檢察院對執行程序的唯一監督手段是對執行中的違法問題制發檢察建議。由于《民事訴訟法》中沒有規定檢察建議的法律地位,實踐中,對于檢察機關的檢察建議法院往往不予接受,這就致使對法院的執行程序缺乏一種外部的、獨立的、更加有力的監督。“每個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僅依靠內部監督的弊端顯而易見。在近年來被查處的司法機關工作人員職務犯罪中,法院執行人員占有較大比例,很多案件觸目驚心,監督不利是一個重要原因。檢察院是國家的專門法律監督機關,其職責就是代表國家行使法律監督權,《中共中央轉發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關于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初步意見》中要求“明確人民檢察院對民事、行政訴訟的法律監督的范圍,完善相關程序”。中央政法委在2005年專門下發了《關于切實解決人民法院執行難問題的通知》強調,“各級檢察機關要加大對人民法院執行工作的監督力度”。然而,修改后的《民事訴訟法》仍然沒有將本應屬于檢察院對法院執行程序的監督權授予檢察院,著實令人費解。
筆者認為,應當賦予檢察機關對民事案件執行程序監督權,明確檢察建議(或意見)的法律地位,強化檢察機關在民事執行程序的監督實效,從而進一步規范和促進法院的執行行為,解決法院執行難、執行亂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