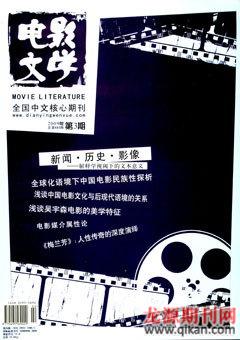充溢悲憫拍眾生
史言喜
[摘要]人們多認為謝晉電影和中國政治的關系密切,甚至認為謝晉電影是為主流政治服務的,是主流政治話語的代言品,而我們往往忽略了謝晉的電影中一直貫穿著的人文關懷。事實上,謝晉電影寄寓著他一貫的人文理想和人道主義追求,從人文關懷角度解讀謝晉電影,會發現謝晉電影無論是主題選擇、電影人物形象塑造,還是敘事風格特征等,無不充溢人文關懷精神。
[關鍵詞]謝晉,電影,人文關懷
“人文主義”在《辭海》中解釋為:“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代表新興資產階級文化的主要思潮。指貫穿于資產階級文化中的一種基本的價值理想和哲學觀念,即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和人道主義。它強調以人為‘主體和中心,要求尊重人的本質,人的利益,人的需要,人的多種創造和發展的可能性。人文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其主流是市民階級反封建、反中世紀神學和禁欲主義的新文化運動。”文學、電影等藝術形式所說的“人文”主要指人的本質、使命、地位、價值、個性發展、個人的自由和幸福等的一切現實要求,“人文關懷”也即關注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自由平等、人的解放乃至人的生存困境、人的欲望。
早期的中國電影有兩個傳統:上海電影傳統和延安電影傳統。延安電影傳統是革命的和政治的,上海電影傳統是民主的和人文的,出身于“世代書香之家”、在重慶和上海受到藝術和電影的啟蒙教育的謝晉接受的主要是上海電影傳統影響,家庭出身、文化熏陶、藝術修養、師承關系都必然會給謝晉打上深深的人文關懷的烙痕。他前期拍攝的《女籃5號》、《紅色娘子軍》、《舞臺姐妹》、《春苗》既歌頌新中國、歌頌革命,同時也有對個人命運、感情和幸福的關注,即使是傳達主流政治話語,也依然在某些方面保留其人文思想和人文主義追求。《青春》、《啊!搖籃》則更明確地表達了他的人文思想和人道主義關懷。改革開放以后,謝晉從他一貫的人文思想和人道主義追求出發對傳統的主流政治(“文革”政治)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人文關懷使得他的影片對傳統主流政治話語(階級斗爭、革命專政等)提出了強烈的批判,這種批判在其經典作品“‘文革三部曲”(《天云山傳奇》、《牧馬人》、《芙蓉鎮》)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集中體現。1986年開始的“謝晉模式”討論以后,謝晉進一步發展了人道主義和人性關懷的主題,弱化了政治的主題,拍攝了《最后的貴族》、《清涼寺鐘聲》、《啟明星》、《老人與狗》、《女兒谷》等。就像人們所普遍觀察到的:謝晉將他一貫對現實社會熱點主題的關注,讓位于對更具普遍性和永久性的人性主題的關注,將中國題材擴大為國際題材。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從社會使命感上升到人類使命感”。
謝晉電影獲得最大成功是在80年代初、中期,當他拍出《天云山傳奇》、《牧馬人》、《芙蓉鎮》的時候。這三部反映現實政治的作品中無不滲透著謝晉的人文關懷與人道主義追求,也正是人文關懷喚起了社會的深層需求,因而引起廣泛而強烈的回應,為推動中國傳統主流政治向現代轉換、推動當代中國政治和文化的往前發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因此,我們可以說,謝晉電影的主題是他持之不懈的人文關懷。
如果說一位成功的電影導演必然有著一以貫之的精神追求、文化特征與價值取向,有著某種濃重的情懷,那么,電影人物形象塑造也就必然能夠體現某種鮮明的、帶有顯著特質的共性特征。謝晉電影中的女性形象就有著明顯的共性特征,她們身上傳達出謝晉特定的人文和道德話語,這些不同類型卻有著共同文化心理特點的女性是謝晉人文關懷精神的寄寓與體現者。謝晉自己說過:“我這個人對人情、人道主義的作品是比較喜歡的。”“人情、人性、人道主義、‘文學是人學,這些觀點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爛了的。即使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也被潑上了‘修正主義的污水。然而這恰恰是文藝中標最重要的東西,是文藝規律中很重要的部分,違背了這個規律,是不可能創作出感人的作品來的。”或許正是基于這種認識,謝晉電影中的女性并不完全是“性”的符號,更是其人文和道德理想的“符號”。她們不是好萊塢式的欲望對象,而是謝晉理想中的道德楷模。謝晉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并不主要側重對女性“身體”和“部件”的展示,而是通過她們的身體語言,傳達其特定的人文和道德話語。她們身上集中了中國傳統女性的諸多優良品德,她們美麗動人、善良淳樸、溫柔賢惠、忍辱負重、吃苦耐勞、心靈手巧、聰明能干,符合普通民眾對女性的審美需求與道德要求。通過這些女性形象,謝晉把他的人文和道德理想感性化、具體化了。而觀眾通過對這些女性形象的觀賞,在愉悅和“快感”之中吸收的則是謝晉的人文和道德理想。
在謝晉“‘文革三部曲”里,女性不僅是男主人公的妻子,更是他們精神上的母親。《天云山傳奇》中,風雪彌漫的山路上,馮晴嵐艱難地拉著板車把落魄無助的羅群接回自己的住處,猶如一位胸懷博大的慈祥母親義不容辭地接回為社會與政治所放逐的兒子。當羅群獲得平反、被社會與政治重新認可的時候,馮睛嵐卻像一個把兒子撫養成人的母親,默默倒下。離開了人世。影片中出現了一組極富歷史滄桑感的深沉的畫面:馮睛嵐青年時代的照片,冒著青煙、剛剛熄滅的蠟燭,掛在竹竿上穿了多年的破毛線背心,打著補丁的花布窗簾,馮晴嵐生前走過的小木橋……這是謝晉用他的鏡頭語言譜寫的對女性、母親、母愛的深情頌歌。《牧馬人》中的許靈均是既被資產階級家庭拋棄又被無產階級放逐的雙重棄兒,因為李秀芝的出現才揚起了生命的風帆。李秀芝具有“地母”的特征,她是許靈均精神上的母親,不僅善于持家,而且以她特有的善良與溫柔消解了許靈均政治上的放逐。她說:“我從結婚那天起就為他平了反。”許靈均在乎反以后之所以能夠斷然拒絕生父要他出國繼承財產的要求,顯然是因為他實際上已經在草原上的牧民和李秀芝那里找到了“父親”和“母親”。關注傳統的家庭模式、道德標準、倫理觀念、價值觀念、謀生手段、生存方式乃至人性深處蘊藏著的生命本真反應、人的情感經驗才能讓人物有血有肉,馮晴嵐、李秀芝,宋薇等眾多女性都是謝晉電影成功的女性形象。
謝晉電影還著意把女性塑造成平凡的普通人,進行非英雄化的處理。馮晴嵐雖是一個有著堅定信念和堅強性格的知識女性,卻只是小山村里的一名普普通通的小學教師,她默默無聞,命定似的成了羅群的保護神。與馮晴嵐相比,李秀芝更是連革命信念都無從談起,她只是個為了生存而背井離鄉的逃荒女,她的“階級覺悟”低到對眼前這場急風暴雨式的“文革”運動全然不覺的程度,把許靈均的右派這一“大政治問題”看成是“誰沒有錯,改了就好”的一般錯誤,她甘愿與許靈均結合也只是因為本能地感到“他是好人”,對可能帶來的后果卻渾然不知。謝晉電影中的女性就像大地上隨處可見、生命力異常頑強的小草那樣普通和平凡,然而這些女性身上卻閃耀著人性的光輝,她們活得那樣艱難,然而又是那樣的坦然。這些女性在特殊歷史時期血淚斑斑的生活場景,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深深觸動我們內心
傷痛的同時也讓我們感觸到導演心中那一份溫情和蒼涼。這些女性表現的是導演對“人”本身的終極關懷,寄寓著導演對“人”的充分發展的美好愿望。謝晉的人文關懷在表現普通女性在凄楚命運面前無怨無悔、善良樂觀、甘于犧牲奉獻的作品中,尤為彰顯,因為“人文精神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一種寶貴的精神財富。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就是人文精神不斷確立和發展的過程”。他甚至旗幟鮮明地標榜其影片承載著哲理提升的意義。他認為,“作為一名真正的藝術工作者,不但要有藝術感覺的創新精神,更應該具有社會責任感,創作出真正具有精神價值、人文關懷,在觀眾中產生震撼、經得起歷史檢驗的作品”。因此,他的影片充滿了人性、人情、人道主義精神。謝晉電影即使在表現社會悲劇、生命悲劇、民族悲劇的同時,還刻意去表現許多美好的東西。他坦言:“我拍影片更多地追求美育作用、警示作用,希望對祖國、對人類貢獻美!”
電影說到底是一種藝術,其內涵的傳達經由一定的藝術形式而實現。所以對其美學風格、敘事視角的選擇和把握也是十分重要的。電影作品的敘事視角指敘述者或人物從什么角度觀察故事,用“誰”的眼光呈現世界。敘述的人稱一定程度上說明導演的敘述態度,而敘述態度決定和反映導演灌注在作品中的敘事情感。魯迅先生說過,悲劇是將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而悲劇一旦用兒童的視角來表現,就會格外讓人心靈震撼。文軒先生認為兒童眼光“與那些爛熟的成年狀態相比,他更多一些質樸無華的天性,更多一些可愛稚拙和迷人的純情。當一個嬰兒用了他清澈的目光看這個世界時,他必要省略掉復雜、丑陋、仇恨、惡毒、心術、計謀、傾軋、爾虞我詐……而在目光里剩下的只是一個藍晶晶的世界,這個世界十分清明,充滿溫馨”。謝晉似乎偏愛兒童視角,但當我們探究他作品中兒童視角的共同點時會發現,他是用兒童視角來凈化現實的污濁與丑陋、荒唐和虛偽,以期讓生活呈現出藝術化、童真美的特點。胡適說:“道德教育的最高目的是要人人都能行善去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一般。”兒童視角的選擇就恰恰起到了勸人向善的道德教育、人文教育作用。電影《牧馬人》中許靈均平反后,補發了500元錢,當秀芝數錢時,兒子好奇地問:“媽媽,爸爸哪兒弄來這么多錢啊?”秀芝感嘆地回答:“當了二十年‘老右補的。”兒子聽后,非常認真地說:“媽媽,長大我也要當‘老右,掙好多好多錢,給你買雙皮鞋。”這一處細節,是通過不諸世事孩子的言行,向觀眾演示了那一段被扭曲的歷史是多么不堪回首,孩子哪里知道那其中的辛酸。于是,歷史的影像和話語再一次引起人們心靈的戰栗。
語言是思想的外衣。電影導演對生活的認識,他的贊賞或針砭、熱愛或悲憫都會體現在作品的影像敘述和語言中,形成作品的張力,引導觀眾從欣賞的愉悅與傷痛中感知生活的冷暖、世態的炎涼、人物內心的柔軟或堅硬,甚至觸及我們忽略了的命運的自我愚妄和人性傷害。謝晉電影是擅長講故事的,但更喜歡用戲劇化的方式、詩化的敘述技巧來完成故事情節敘事和人物形象塑造。用謝晉自己的話說:“電影能不能使人看后久久不能忘懷,除了作品寫了性格鮮明的人物和主題思想帶有深厚的哲學意味外,還要看作品有沒有詩意。導演挖掘作品的主題思想時必須找出作品中間的‘詩,哪怕埋藏在作品內部,卻澎湃著巨大生命力的作品內部的詩。作品要有光輝,必須要有詩,也就是必須要有浪漫主義。”于是,謝晉電影總是力圖表現出雙重的語境——社會大環境的悲劇、困境和無奈;人倫小環境的詩意、溫情和美好。
謝晉創作的主流電影主題嚴肅,質樸,但創作手法和表現技巧并不保守。他主張“用獨特的慧眼去發現特別的表現手段,捕捉獨特的東西”。影片既要內容真實,形式又要藝術化。也就是說,他的影片蘊含著一種“唯美”的風格。這里說的“唯美”,不同于脫離社會現實、忽視內容和意義的“唯美主義”。謝晉的電影是一種常規的敘事,不刻意追求形式技巧,但他的電影敘事卻是流暢的,鏡頭語言是精巧而獨特的。謝晉的電影語言有多種表現元素,如聲畫造型、時空交替、內心旁白、細節渲染等手法,帶給觀眾一種視覺上的美感和藝術享受,同時又給人一種昂揚向上的、溫暖人心的情感撫慰。影片《芙蓉鎮》中男、女主人公被勞動改造,天不亮就起來掃大街,當時他們竟然心血來潮,揮動著掃把。踩著華爾茲的節拍跳起“掃街舞”,這不能不說是創作者有意安排和設置的一個戲劇化場景。它是對當時社會現實的一段虛構再現,以近乎“戲謔”、類似于文學上“反諷”的手法,使觀眾忘卻了當時社會現實的種種苛刻,跟隨他們去享受片刻的、實際上早已被剝奪了的歡娛和自由。這種“苦中作樂”、在生活重壓之下對生活和人生的樂觀態度,飽含著創作者的深沉思索和一往情深的“悲天憫人”的情懷,是謝晉電影生涯一以貫之的人文關懷的價值取向的具體體現與自然流露。因此,謝晉電影傳達的不止是美學觀念、審美情感,還有社會心理的剖析、人生的感悟、價值思索以及哲理意義的提升等人文主義的豐富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