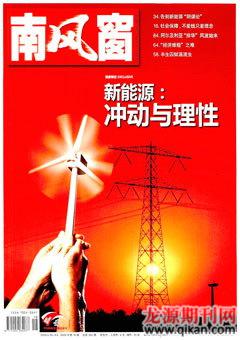西藏鄉(xiāng)鎮(zhèn)建設(shè)反思
傅景亮
在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特別是社會(huì)轉(zhuǎn)型階段,西藏的社會(huì)矛盾開始凸顯。社會(huì)矛盾與族群矛盾開始結(jié)合在一起,特別是社會(huì)矛盾轉(zhuǎn)換為族群矛盾的可能性增長(zhǎng)。從而使得民族地區(qū)的矛盾愈益復(fù)雜化,社會(huì)矛盾和族群矛盾的相互強(qiáng)化對(duì)西藏鄉(xiāng)鎮(zhèn)基層政權(quán)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壓力。藏地處中國(guó)的西南部,具有獨(dú)特的歷史地理價(jià)值。西藏建設(shè)的情況如何直接關(guān)系到邊疆的安全與穩(wěn)定,經(jīng)過多年特別是近年來中央、西藏和各個(gè)援建省份的共同努力,西藏鄉(xiāng)鎮(zhèn)建設(shè)有了長(zhǎng)足的發(fā)展,特別是自去年“3·14事件”之后,西藏明顯加快了政治、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各個(gè)方面的建設(shè)步伐。
筆者在調(diào)研中發(fā)現(xiàn),在內(nèi)地大部分鄉(xiāng)鎮(zhèn)基層政權(quán)出現(xiàn)弱化的趨勢(shì),西藏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行為中規(guī)中矩,究其原因,西藏地區(qū)的鄉(xiāng)鎮(zhèn)政府具有獨(dú)特的激勵(lì)機(jī)制和約束機(jī)制,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西藏地區(qū)的安全與穩(wěn)定,同時(shí)又需要加強(qiáng)西藏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治理創(chuàng)新能力。
獨(dú)特的激勵(lì)機(jī)制與約束機(jī)制
在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特別是社會(huì)轉(zhuǎn)型階段,西藏的社會(huì)矛盾開始凸顯,并且與族群矛盾開始結(jié)合在一起,特別是社會(huì)矛盾轉(zhuǎn)換為族群矛盾的可能性增長(zhǎng),從而使得民族地區(qū)的矛盾愈益復(fù)雜化。社會(huì)矛盾和族群矛盾的相互強(qiáng)化對(duì)西藏鄉(xiāng)鎮(zhèn)基層政權(quán)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壓力。
西藏地區(qū)的鄉(xiāng)鎮(zhèn)政府具有不同于內(nèi)地的激勵(lì)機(jī)制和約束機(jī)制,激勵(lì)機(jī)制和約束機(jī)制并存,而且在某種程度上相互轉(zhuǎn)換,既推動(dòng)了西藏地區(qū)鄉(xiāng)鎮(zhèn)政府建設(shè),又產(chǎn)生了一定的制約作用。
首先是社會(huì)性因素。西藏民主改革推動(dòng)了其現(xiàn)代化的步伐,如今大部分鄉(xiāng)鎮(zhèn)都呈現(xiàn)出一片現(xiàn)代的景象。在江孜縣達(dá)瑪節(jié),筆者注意到各個(gè)角落無不充斥著現(xiàn)代化的商品,包括物質(zhì)產(chǎn)品和精神產(chǎn)品。但是,西藏的現(xiàn)代化仍然遠(yuǎn)遠(yuǎn)滯后于內(nèi)部地區(qū),最主要體現(xiàn)在社會(huì)結(jié)構(gòu)方面。可以說,社會(huì)結(jié)構(gòu)既有現(xiàn)代性的一面,又有傳統(tǒng)性的一面,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表面的現(xiàn)代化掩飾不了西藏社會(huì)骨子中的傳統(tǒng)性。如何有效地汲取傳統(tǒng)的資源,有效地應(yīng)對(duì)傳統(tǒng)權(quán)威的挑戰(zhàn),如何才能推動(dòng)現(xiàn)代性因素的成長(zhǎng),成為鄉(xiāng)鎮(zhèn)政府必須考慮的問題。
其次則是價(jià)值性因素。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賦予了民族自治地區(qū)專有的自治權(quán),毋庸置疑,中國(guó)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的確推動(dòng)了民族地區(qū)的發(fā)展。但是,民族區(qū)域地區(qū)的自治仍有其限度,特別是一些具體的政策和措施妨礙了自治權(quán)的實(shí)施,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其發(fā)展。對(duì)于西藏地區(qū)而言,如何通過完善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保護(hù)自然資源和生態(tài)環(huán)境,促進(jìn)西藏地區(qū)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文化的發(fā)展,從而保護(hù)少數(shù)民族的合法權(quán)益,則直接涉及自治與發(fā)展雙重價(jià)值的合理界定。
再次則是體制性因素。一般而言,內(nèi)地鄉(xiāng)鎮(zhèn)政府呈現(xiàn)為一種“經(jīng)濟(jì)壓力型體制”,即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是內(nèi)地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工作中心,也是衡量鄉(xiāng)鎮(zhèn)政府工作的主要指標(biāo)。相對(duì)而言,西藏鄉(xiāng)鎮(zhèn)政府則更多是一種“政治壓力型體制”,政治要求和因素成為西藏鄉(xiāng)鎮(zhèn)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其原因昭然若揭:達(dá)賴集團(tuán)以及西藏極少數(shù)分裂分子一再制造事端,無論在國(guó)際還是國(guó)內(nèi)層面上對(duì)國(guó)家的統(tǒng)一和安全產(chǎn)生了極端的影響,直接影響到西藏地區(qū)的安全、穩(wěn)定與發(fā)展。安全與穩(wěn)定是發(fā)展的前提,沒有安全與穩(wěn)定何談西藏的發(fā)展?政治要求必然成為各級(jí)政府的首要任務(wù)。基于“政治壓力型體制”的要求,鄉(xiāng)鎮(zhèn)政府在行政體制上也往往形成“行政一權(quán)威型體制”,行政管理工作延續(xù)著傳統(tǒng)的權(quán)威型方式,通過行政權(quán)威的強(qiáng)有力約束推動(dòng)鄉(xiāng)鎮(zhèn)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
最后則是族群性因素。西藏主要以藏民為主,約占130多萬人口中的95%,還有其他民族如漢族、珞巴族、維吾爾族等。中國(guó)各民族之間長(zhǎng)期以來相互交往融合,從而鑄造了中華民族大家庭。但是族群在文化象征、宗教信仰、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等方面仍然存在差異,族群之間的差異是歷史和文化造就的。基于族群象征的差異性是自然的,但是,西藏族群關(guān)系卻呈現(xiàn)為復(fù)雜化的格局。
一則歷史事件的遺留因素,西藏解放和民主改革觸動(dòng)了一部分舊勢(shì)力的反動(dòng),如達(dá)賴集團(tuán)一再貶低和扭曲中國(guó)的民族政策,在海外生事。二則西藏所處的歷史地理位置,眾所周知的“麥克馬洪線”導(dǎo)致了中國(guó)西藏問題的國(guó)際化,對(duì)中國(guó)的西南部邊疆的安全與穩(wěn)定造成了重要的影響。三則宗教因素的作用,西藏歷史上實(shí)行政教合一制度,西藏民主改革則開啟了宗教世俗化的進(jìn)程,然而宗教在西藏根深蒂固的地位始終影響著政治發(fā)展。制度、政策與關(guān)系
制度理性化是現(xiàn)代國(guó)家和社會(huì)的必然要求,具體表現(xiàn)為結(jié)構(gòu)合理化和功能分化。西藏地區(qū)鄉(xiāng)鎮(zhèn)政府在制度建設(shè)、政策創(chuàng)新以及處理與社會(huì)的關(guān)系方面都能夠有所為有所不為。
西藏地區(qū)鄉(xiāng)鎮(zhèn)政府機(jī)構(gòu)設(shè)置與內(nèi)地似乎并無二致,鄉(xiāng)鎮(zhèn)黨委、政府和人大三大塊,不同機(jī)構(gòu)承擔(dān)著不同的職能。但是,由于西藏獨(dú)特的政治經(jīng)濟(jì)條件,鄉(xiāng)鎮(zhèn)機(jī)構(gòu)設(shè)置又具有其獨(dú)特性。如基于安全與穩(wěn)定的考量,“維穩(wěn)”工作始終是西藏各級(jí)政府的首要工作,“反對(duì)分裂、維護(hù)穩(wěn)定、促進(jìn)發(fā)展”成為鄉(xiāng)鎮(zhèn)黨委的工作重心,一般都是由鄉(xiāng)鎮(zhèn)黨委書記親手抓,并成立專門的工作組,由鄉(xiāng)鎮(zhèn)主要領(lǐng)導(dǎo)組成,村級(jí)單位的一項(xiàng)重要使命就是輔助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維穩(wěn)工作。
長(zhǎng)期以來,人才問題一直困擾著西藏地區(qū)的鄉(xiāng)鎮(zhèn)政府建設(shè),援藏干部的到來無疑是雪中送炭,援藏干部豐富的行政經(jīng)驗(yàn)和改革經(jīng)歷對(duì)于推動(dòng)西藏的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一大批具有高學(xué)歷的人才從內(nèi)地源源不斷地注入西藏,日喀則市幫佳孔社區(qū)主任就頗為自豪地告訴筆者,有一名畢業(yè)于清華大學(xué)的碩士在他們這里勤奮地工作。藏族干部、援藏漢族干部和在藏漢族干部形成了多層次的干部群體,干部隊(duì)伍的年輕化、高學(xué)歷和專業(yè)化是鄉(xiāng)鎮(zhèn)政府工作的人才保障。當(dāng)然,如何有效地整合不同的干部力量也是鄉(xiāng)鎮(zhèn)政府工作所要面臨的重要課題。
西藏鄉(xiāng)鎮(zhèn)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也有其獨(dú)特的經(jīng)驗(yàn)。為了培養(yǎng)藏族黨員和干部,西藏鄉(xiāng)鎮(zhèn)政府普遍建立了“雙培雙帶”制度,其核心內(nèi)容就是把農(nóng)牧民致富帶頭人中的優(yōu)秀分子培養(yǎng)成黨員或村干部、把黨員和村干部培養(yǎng)成致富帶頭人,堅(jiān)持黨員和村干部帶頭致富、帶領(lǐng)群眾共同致富。通過致富能手和黨員干部的結(jié)合,既推動(dòng)了鄉(xiāng)鎮(zhèn)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又有助于黨的隊(duì)伍建設(shè),黨的模范作用和影響悄無聲息地影響到普通農(nóng)牧民。
在經(jīng)濟(jì)方面,西藏地區(qū)的鄉(xiāng)鎮(zhèn)政府也進(jìn)行了多種多樣的嘗試。江孜縣江孜鎮(zhèn)黨委書記班久來自于農(nóng)民家庭,就讀于日喀則農(nóng)學(xué)院,對(duì)農(nóng)牧工作非常熟悉,他在基層工作的十幾年中進(jìn)行了大膽的探索,推行了“農(nóng)區(qū)畜牧業(yè)政策”、“村民合作社”、“農(nóng)畜產(chǎn)品專賣點(diǎn)”等政策措施,有力地推動(dòng)了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贏得了廣大農(nóng)牧民的贊譽(yù)。值得稱道的是,這些政策的制定一方面是建立在鄉(xiāng)鎮(zhèn)領(lǐng)導(dǎo)干部調(diào)研的基礎(chǔ)上,另一方面則是充分發(fā)揮農(nóng)牧民的積極性,鄉(xiāng)鎮(zhèn)政府往往征求和采納農(nóng)牧民的建議,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政策的科學(xué)化和民主化。
鄉(xiāng)鎮(zhèn)政府直接服務(wù)于
農(nóng)牧區(qū),村級(jí)單位構(gòu)成了鄉(xiāng)鎮(zhèn)政府工作的主要對(duì)象。西藏村級(jí)單位近些年來普遍實(shí)行了村民自治。西藏拉薩市堆龍德慶縣東嘎鎮(zhèn)南嘎村在2005年舉行了村委會(huì)主任直選,1280名選民參加了選舉,村民投票選舉出一位德高望重的村委會(huì)主任。在該過程中,鄉(xiāng)鎮(zhèn)政府在選舉組織、設(shè)備、人員和投票過程中扮演了“守夜人”的角色,保證了選舉有條不紊地進(jìn)行。
為農(nóng)牧民提供公共服務(wù)是西藏地區(qū)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基本職能。西藏具有獨(dú)特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條件,公共服務(wù)的內(nèi)容也具有其特殊性。如惠及千家萬戶的“安居工程”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西藏大部分農(nóng)牧民的居住問題,如何推動(dòng)安居工程則是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又一工作主題。根據(jù)堆龍德慶縣羊達(dá)鄉(xiāng)的一份資料顯示,該鄉(xiāng)3年內(nèi)完成了750戶安居工程建設(shè)任務(wù),其中貧困戶55戶,放牧民定居戶8戶。3年的安居工程總投入資金9296.44萬元。
治理與創(chuàng)新
以治理的視角審視西藏地區(qū)的鄉(xiāng)鎮(zhèn)基層政府建設(shè),顯然,改革開放已經(jīng)為鄉(xiāng)鎮(zhèn)基層治理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鄉(xiāng)鎮(zhèn)政府所具有的激勵(lì)機(jī)制和約束機(jī)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邊疆地區(qū)的安全與穩(wěn)定,但是若要保證西藏地區(qū)的長(zhǎng)遠(yuǎn)發(fā)展還需要改變治理方式和創(chuàng)新機(jī)制。
政治要求是歷史地形成的,是國(guó)家統(tǒng)一、邊疆安全的內(nèi)在需要。政治要求從政治高度上對(duì)西藏鄉(xiāng)鎮(zhèn)基層政權(quán)建設(shè)予以規(guī)約,然而不能簡(jiǎn)單地去理解此種政治要求。政治要求著眼于安全與穩(wěn)定,從長(zhǎng)遠(yuǎn)看來則是基于發(fā)展的要求,特別是社會(huì)的全面發(fā)展。只有社會(huì)的全面發(fā)展才能從根本上保證邊疆的安全與穩(wěn)定。政治要求從質(zhì)的方面規(guī)定行政管理工作,然而,政治與行政并不相同,前者是國(guó)家意志的表達(dá),后者則是國(guó)家意志的實(shí)現(xiàn),有其自身的規(guī)律可循,因此政治與行政的適度分離則是西藏鄉(xiāng)鎮(zhèn)基層政權(quán)治理方式轉(zhuǎn)變的首要前提。
西藏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治理還需從政府主導(dǎo)型向社會(huì)主導(dǎo)型轉(zhuǎn)變。行政權(quán)威型治理方式仍然是一種傳統(tǒng)的治理方式,即自上而下的、以領(lǐng)導(dǎo)意志為核心的治理方式。在此種治理方式中,社會(huì)力量的參與是有一定限度的,領(lǐng)導(dǎo)的工作態(tài)度和方式直接決定了治理的效果。政府主導(dǎo)型治理方式在現(xiàn)代化初期特別是中國(guó)特殊的國(guó)情中具有其合理性,但是隨著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變遷,政府必須重視社會(huì)自身的治理,社會(huì)治理越來越多地承擔(dān)政府的某些公共功能,從而實(shí)現(xiàn)政府主導(dǎo)型治理方式向社會(huì)主導(dǎo)型治理方式的轉(zhuǎn)變。鄉(xiāng)鎮(zhèn)政府在治理模式的轉(zhuǎn)變過程中向服務(wù)型政府挺進(jìn)。
西藏地區(qū)鄉(xiāng)鎮(zhèn)政府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嘗試了不同的政策創(chuàng)新,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政策創(chuàng)新有其特色,即體現(xiàn)為政策性創(chuàng)新模式。一般而言,政策性創(chuàng)新是基于某些領(lǐng)導(dǎo)的主觀意識(shí),鄉(xiāng)鎮(zhèn)主要干部往往根據(jù)自己的判斷進(jìn)行試驗(yàn)性的政策,缺乏系統(tǒng)的考慮,往往成本很高,而且具有不穩(wěn)定性。政策性創(chuàng)新也是基于專業(yè)要求,西藏地區(qū)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政策創(chuàng)新大部分都是專業(yè)性非常強(qiáng)的,其適用范圍非常狹窄。此外,政策性創(chuàng)新缺乏配套政策,政策性創(chuàng)新或者因缺乏配套政策而夭折,或者與其他政策相沖突從而導(dǎo)致其他問題。因此,必須實(shí)現(xiàn)政策性創(chuàng)新向制度性創(chuàng)新轉(zhuǎn)變,即建立創(chuàng)新性機(jī)制,群策群力,以合理、科學(xué)和民主的方式進(jìn)行創(chuàng)新,從而取得最大的創(chuàng)新成果。
當(dāng)然,西藏地區(qū)鄉(xiāng)鎮(zhèn)政府治理方式的轉(zhuǎn)變和制度創(chuàng)新能力建設(shè)還需要很多基礎(chǔ)性工作,如建立合理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推動(dòng)市場(chǎng)化建設(shè),提高城鎮(zhèn)化程度,繼續(xù)宗教世俗化的進(jìn)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