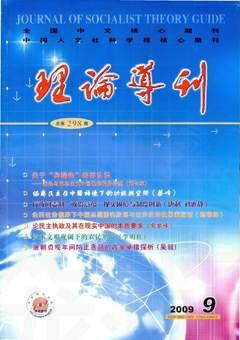文學在人的需要系統中的價值定位
王秋麗
摘 要:文學作為用語言表達的情感化、形象化的人文意識,是為了滿足人追求真善美的需要,作為人的“發展的需要”的核心部分的審美需要而存在并顯示其價值的。文學與經濟、政治以及哲學人文科學在價值方面的不同,決定了文學在人的需要系統中的價值定位,即文學的價值是把認識價值和教育價值包孕在娛樂價值之中的感染性的、綜合的審美價值,是一種精神價值,一種自由的人文價值。
關鍵詞:文學;人的需要;審美價值
中圖分類號:I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09)09-0017-03
(一)
價值既是一個經濟學概念,也是一個哲學和美學概念。對于經濟學意義上的價值概念,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是從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入手進行討論的。而對于哲學和審美意義上的價值概念,馬克思則在別的著作中,就對象與人的需要之間的價值關系,作過一系列至今仍頗具經典性的論述。他說:“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1]406“是人們所利用的并表現了對人的關系的物的屬性”;“表示物的對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屬性”,“實際上是表示物為人而存在”[2]139-326。
馬克思在以上的幾句話里,主要強調了三點:其一,價值體現的是對象與人的需要之間結成的關系,即價值關系;其二,對象與人的需要之間其所以能結成價值關系,是因為該對象確實具有滿足人在某方面需要,因而對人有用,或者使人愉快的某種屬性,我們可以稱之為價值屬性;其三,對象及其價值屬性表明,它是屬于人的,它為人而存在,而且僅僅只是為人而存在。
綜上所述,從哲學和美學意義上來說,所謂價值,是指對象具有的能滿足人在某方面需要的某種內在屬性。
這里我們談人的需要,是指人作為“類存在”的普遍性需要,而不是個體人的隨便哪一種需要。在個體的人那里,并非其一切需要,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都應當給予滿足。個人的需要,如果超越了社會法律、政治或者道德的底線,就屬于不合法或者不合理的需要,也就不應當給予滿足。因此,從正面立論,價值是指對象能滿足人的需要的某種屬性;但不能從反面立論,并不是凡能滿足人的需要者,就一定有價值。
哲學和美學意義上的價值概念,是和人的需要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的。作為一種重要的人文藝術形式,文學的存在,對于人而言,其作用不可或缺。人的生活需要文學,離不開文學,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那么,文學可以滿足人在哪方面的需要?也即,文學和人的需要之間,建立的是一種什么樣的價值關系?
人作為如恩斯特·卡西爾在《人論》中所說的利用符號進行文化創造的動物,簡而言之即所謂文化的動物,其生命的整個需要,乃是一個包括從生理到心理,從物質到精神、從形而下到形而上的方方面面的復雜系統。對于這樣的一個復雜系統,弗洛伊德僅僅將其歸結為本能(性本能與自我本能,生的本能與死的本能)。弗洛伊德在把人的需要問題動物化、欲望化、無意識化和病態化的同時,也把人的需要問題極大地簡單化了。大概正是有感于此,美國學者、被譽為心理學“第三思潮”(第一思潮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學,第二思潮指華生的行為主義心理學)代表人物的馬斯洛,提出了由低級到高級,一層層遞進的人的需要層次(也叫需要等級)理論。(如圖所示)

開始,馬斯洛只是論列了諸如人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愛與歸屬需要和自尊需要等幾個層次的基本需要。這樣的論列,比之弗洛伊德的本能論,大大前進了一步,但上述需要,恰如馬斯洛在此之后所言,它們都只是因缺乏產生的需要,即所謂“缺乏性需要”:一旦缺乏它們,就可能引起疾病;滿足它們,就可能免于疾病;恢復它們,就可能治愈疾病。僅僅從這些“缺乏性需要”中,還看不出人之為人的超越意向來。馬斯洛在上述幾個層次的“缺乏性需要”之上,又提出了為人所特有的積極健康的自我實現的需要。正是這種自我實現論,以及作為人在自我實現之后的心理體驗的描述的巔峰體驗論,使馬洛斯大有別于弗洛伊德和華生等前輩心理學家,成為“第三思潮”的領軍人物。[3]為了使人的自我實現需要,以及這一需要得以滿足時油然而生的巔峰體驗不至于被架空,馬斯洛又在《通向一種關于存在的心理學》一書里,論證了其位置介于人的基本需要與自我實現需要之間,代表著人的存在價值的,被他稱之為“發展的需要”。[4]51-52魯迅當年論及人的需要:“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其中第一點“生存”、第二點“溫飽”,大致相當于馬斯洛所謂基本需要,而第三點“發展”, 與馬斯洛講“發展的需要”也是不謀而合的。魯迅只是點到為止,不曾就“發展”二字作進一步的展開。魯迅留下的空白,馬斯洛加以填補。按其設計,在“發展的需要”這一層次上,容納著人對包括真善美在內的多方面的精神追求。至此,馬斯洛創造的人的需要層次的理論,開始呈示出作為一個心理學的科學體系的整體輪廓。
馬斯洛認為,在通常情況下,人的需要是按照由低級到高級的層次,一層層地被激發起來的。也即,一個人只有在滿足了最低層次的需要之后,他才可能產生緊挨著這一層次的更高一個層次的需要。馬斯洛又提醒人們,不要過分拘泥于人的需要層次,因為這中間多有例外。特別在一些心理健康者那里,他們可以憑借自身心靈的超越功能,在某一方面或某幾方面的基本需要尚未得以滿足的情況下,跳過若干層次,徑直去追求發展的需要,以及自我實現的需要的滿足。馬斯洛通過對上述超常規情況的論證闡述,使其關于人的需要層次理論,越發地趨于縝密、完善。
(二)
如果以馬斯洛的人的需要層次理論為坐標,文學之于人的價值究竟應該如何定位,問題也就不難解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文學作為用語言表達的情感化、形象化的人文意識,它完全是為了滿足人追求真善美的需要,亦即作為人的“發展的需要”的核心部分的審美需要而存在,而顯示其價值的,因此,文學的價值也就必然應該是,而且只能是審美價值。
為了說明這一點,下面將拿文學與社會生活的各層面作一番價值方面的逐一比較。關于社會生活的層面結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通常將其劃分為生產力、生產關系以及經濟基礎、政治法律制度與社會意識形態等四個層面;普列漢諾夫的《唯物主義史論叢》將其區別為生產力、生產關系、社會制度、精神道德狀況以及社會意識形態等五個層面;而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則將其簡化和概括為經濟、政治和文化等三個層面。這里,我們以毛澤東的“三層面論”作為文學和社會生活各層面進行價值比較的參照。
首先,拿文學與經濟的價值作一比較。經濟作為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生產部門,其產品不管是工業產品、農業產品,還是其他行業的產品,都是用來滿足人的基本需要,尤其是其中的生理需要的種種物質產品。因此可以說,經濟所創造的完全是物質價值。文學與經濟不同,它從事的并非物質生產,而是純粹的精神生產。詩歌、小說或戲劇、影視文學作為文學的精神產品,與人的基本需要,尤其是生理需要之間,談不上什么滿足不滿足的價值關系。為什么望梅可以止渴,畫餅不能充饑呢?就因為所望的梅畢竟是物質產品,而所畫的餅,充其量只是與文學產品一樣的精神產品。魯迅先生的話:“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跑了。”道理正在于此。文學的精神產品,雖然不能滿足人的基本需要,尤其生理需要,但它們卻可以超越人的缺乏性需要,在存在的意義上,滿足人的發展的需要,更具體地說,是滿足人追求真善美的精神需要。由此而論,較之經濟層面提供的物質價值,文學體現的只能是一種精神價值。
其次,再拿文學與政治進行價值的比較。政治作為經濟的集中體現,處在上層建筑的核心部位。它既是社會的立法者,同時又是社會的執法者和司法者。它可以通過帶有強制性的權力,以及作為這種權力的標志的法律法規和行政條文,通過一整套的國家機器,管理國計民生,以保障全社會的生產和生活能夠和平、安全、有秩序地進行。因此,政治管理給人直接帶來的是安全需要、歸屬需要和尊重需要等基本需要的滿足;同時從間接的意義上,它對經濟的管理,也能轉化為某種可見的物質效益,從而給人帶來生理需要的滿足;對文化的管理,還能轉化為某種精神效益,從而給人帶來發展需要以及精神需要的滿足。概而言之,它給人帶來的是一種全方位的管理價值。和政治層面這種以權力的強制性表現出來的管理價值根本不同,文學與有著追求真善美的精神需要的人之間的價值關系,完全建立在共同的人文情懷和共同的精神旨趣的基礎上。一方面是文學的寫作者,另一方面是文學的接受者和欣賞者,他們的結合是不帶任何強制性的靈魂的自由結合。恰如列寧宣稱:“無可爭論,文學事業最不能做機械的平均、劃一、少數服從多數。無可爭論,在這個事業中,絕對必須保證有個人創造性和個人愛好的廣闊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廣闊天地。”[5]163正因為文學在本性上是自由的,而且它所展示的主要是人文意識,所以,其體現的精神價值,如果深究之下,乃是一種自由的人文價值。
最后,再拿文學與同處于文化層面的哲學人文科學作一番價值方面的比較。文學體現的是精神價值和人文價值。哲學人文科學就價值而論,也是如此。這是文學與哲學人文科學作為人學的共同之處。 所不同者,哲學人文科學運用抽象的思想與概念顯示其精神價值和人文價值,重在以理服人,而且它們給人的,往往不是單一的認識價值(如哲學),就是單一的教育價值(如宗教、道德);而文學則是將思想與概念包孕在情感與形象的系統之中,重在以情(感情)感人、以形(形象)動人,給人的是把認識價值和教育價值包孕在娛樂價值之中的綜合的審美價值。為什么我們平時看一本小說與聽一場講座,常常會有不同的感覺。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區別于哲學人文科學思想和概念式的、單一的認識價值或教育價值,文學的價值,乃是一種感染性的、綜合性的審美價值。
在作了三個層面的價值比較之后,我們確認文學的價值是一種不同于經濟的物質價值的精神價值;一種不同于政治的管理價值的人文價值;一種不同于哲學人文科學的單一認識價值或教育價值的審美價值。我們作這樣的比較和確認,對討論文學的價值形態,無疑是非常必要的。恰恰是文學與經濟、文學與政治、文學與同屬文化層面的哲學人文科學在價值方面的這些不同,才決定了文學在人的需要系統中的價值定位。無論在任何時代,也無論在任何民族、任何國家的社會生活里,文學都是不可或缺的,也都是不可取代的。
(三)
誠然,文學的審美價值,在滿足人的需要的輕重緩急的程度上,和經濟的物質價值、和政治的管理價值,甚至和同屬于文化層面的哲學人文科學的認識價值或教育價值,都難以作等量齊觀。因為經濟、政治,也包括一部分人文意識形態(如道德等)所能滿足的人的需要,作為缺乏性需要,大多屬于基本需要。有如馬斯洛所論,一旦這些基本需要不能予以滿足,對個人而言,就會產生疾病以至死亡;對社會而言,就會發生災難以及動亂。相對地說,文學所能滿足的人的審美需要, 是人在解決了生存和溫飽問題之后,為使精神方面有所發展才提出來的一種超越性需要。就它對于人的重要性與緊迫性而論,肯定不能和前述基本需要相比擬。然而,我們切不可因為它對人不那么重要與緊迫,就將其置于可有可無的地位。文學離不開人的生活,人的生活也同樣離不開文學。我們不能設想,一個民族、一個時代,倘若連最廣義的文學都沒有,那將是一番多么可怕的圖景!十年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幫”推行封建專制主義,我國的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包括文藝在內的整個精神文化生活,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饑荒。此種后果,大家從劉心武的小說《班主任》、張弦編劇的電影《被愛情遺忘的角落》中可見一斑。不管是小說中的宋寶琦和謝惠敏也好,也不管是電影中的小豹子和存妮也好,他們都是精神上的畸形者。上述這些人物,就天性而論,各有其愛美之心。但是,歷史卻把他們安排在了一個所謂“沒有詩歌,沒有小說,沒有戲劇,沒有散文”的“文革”時代。既然他們作為讀者無書可讀,無美可審,文學沒有給他們提供能夠滿足其追求真善美需要的可能性,那么,由此而產生精神上的畸形,產生從人性到動物性的退化,自然是在所難免了。
本文一開頭所引用的馬克思關于價值概念的論述,其中有一句話特別地耐人尋味:價值“表示物為人而存在”。馬克思在此強調的是以人為本,或者說人本主義的價值尺度。為什么在“文革”時期,會產生諸如宋寶琦和謝惠敏,以及小豹子和存妮這樣的悲劇呢?除了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原因之外,在文學價值問題上自覺不自覺地放棄了人本主義的尺度,也是很要緊的一個方面。作為我國古代主流話語的儒家文化,基于其政治、道德的功利主義,往往把詩和文學的價值定位于“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論語·陽貨》);或者“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毛詩序》);或者“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白居易:《與元九書》)等等上面。[6] 受儒家功利主義價值觀的影響,加之形成于革命戰爭時代的傳統文藝思想慣性作用等,我們過去很長一個時期,也更多地將文學的價值取向,由為人民服務、為工農兵服務完全推論和引導到為政治服務、為階級斗爭服務的方向。在這樣的語境中,文學的價值本位,也便不由自主地發生了挪移:從人的本位逐步變成為政治本位、階級斗爭本位等等。真善美被當作資產階級的奢侈品,假丑惡就乘虛而入大行其道。在攪亂了的價值尺度的指揮下,文學界一度有如當年狄慈根形容的那架“發瘋的鋼琴”,除了無休止地散播極“左”的政治噪音以外,再不可能從事像樣的審美創造了。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我們今天講文學的審美價值,就是要讓文學回到人的本位,說得更明確一點,回到能滿足人追求真善美的需要的審美本位上來。經濟也罷,政治也罷,同屬文化層面的哲學人文科學也罷,它們作為與文學比鄰而居的社會生活共同體的各個組成部分,完全可以向文學發出這樣那樣的召喚,施加有形無形的影響。但這所有的一切,都必須建立在尊重文學的人本位、尊重文學的審美本位這一價值尺度的基點之上。 倘能如此,我們偉大民族的文學復興,應該是指日可待的。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馬斯洛.自我實現的人[M].三聯書店,1987.
[4]戈布爾.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M].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5]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學[M].人民文學出版,1980.
[6]中國美學史料選編(上)[M].中華書局,1980.
[責任編輯:黎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