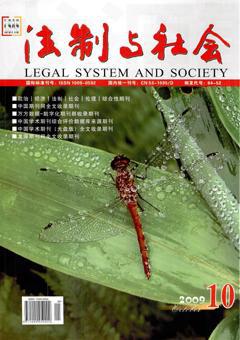人民監督員制度試行中存在問題研究
張爍鈴 任 亮
摘要作為列入中央司法改革文件的人民監督員制度,是檢察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從實踐出發,對該制度試行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簡要分析與研究。
關鍵詞人民監督員 制度設計 司法改革
中圖分類號:D926.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592(2009)10-167-02
人民監督員制度是檢察改革的一個部分,是檢察院對自偵案件的部分環節增加外部監督渠道的一種嘗試。從江蘇省于2005年10月擴大該項制度試點工作以來的實際效果來看,雖然取得了一定的社會效果,但與設立該制度的預期目標還是有一定的差距。有人認為“實行人民監督員制度目的在于加強對檢察機關查辦職務犯罪工作的外部監督,從而使檢察權在正確的軌道上運行”①但是如果人民監督員制度僅僅是停留在書面上而少有實施。那么其制度制定的目的再多么美妙也只能是紙上談兵,這種制度本身也就成了一種作秀之舉。因此,筆者以為提高人民監督員案件監督率,是測試、檢驗人民監督員制度的設計是否科學、正確的極為重要的方面,也是檢察機關試行人民監督制度中應試圖解決的關鍵所在。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楚問題的成因。那么造成人民監督員案件監督率低的原因是什么呢?依筆者所見:
一、制度設立目的與具體規定設計存在矛盾
人民監督員制度設立的目的是,既引入了對自偵檢察權外部監督的機制,增加了自偵檢察權的社會透明度;又賦予了這種監督的主動性和強制性特征,使這一監督上升到法定程序的高度,從而提高了監督的公信力。這個目的,在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實行人民監督員制度的規定(試行)》(以下簡稱《規定》)中設定的案件監督范圍、監督程序以及總則的有關條款中均可體現。如《規定》第二條第一款列明“人民檢察院查辦職務犯罪案件,實行人民監督員制度,接受社會監督”,第十三條第一款規定“人民監督員對人民檢察院查辦職務犯罪案件的下列情形實施監督:1.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決定;2.擬撤銷案件的;3.擬不起訴的。”第十四條又規定人民監督員發現人民檢察院在查辦職務犯罪案件中具有“五種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出意見。這些規定均鮮明的體現出了人民監督員對自偵檢察權監督的主動性和強制性特征,充分反映出設立人民監督員制度的目的。
但是《規定》及后來最高人民檢察院作為配套措施而形成的《關于實行人民監督員制度的規定(試行)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在某些規定設置上,卻并未完全體現制度設計的目的,特別在啟動監督程序的條件上或加以限制,或空泛而不具備操作性。較為明顯的是“對不服逮捕決定”的監督啟動條件的設限。首先,啟動監督程序必須是犯罪嫌疑人有明確的不服逮捕決定的意思表示;其次,必須提出申辯理由,第三,偵查監督部門維持逮捕決定的。如《規定》第十八條中規定,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決定的,除了向承辦案件部門提出外,還須附申辯理由,雖然《意見》第三條對申辯理由作了細化的規定,但仍未跳出設限的框架。由于這種監督是有條件的,所以無疑加大了啟動監督的難度,導致了對這類案件引入外部監督的可能性降低。這種限制設計可能是出于慎重考慮,但《規定》的設計者可能沒有認識到檢察院自偵檢察權的行使中,逮捕案件占了絕大多數。不可理解的是人民監督員制度設計者為何要對這一塊主要的監督領域設定門檻。從另一方面看,對“三類案件”的監督,是兩個不同內容的監督。對逮捕案件的監督,是對檢察權是否濫用、犯罪嫌疑人的人權是否得到保護的監督;對撤銷案件、不起訴案的監督是對檢察權是否懈怠的監督。兩種不同性質監督的啟動,卻設計為兩種不同的啟動條件,恰恰證明了制度設計的矛盾性。
二、告知制度設計的合理性有待提高
《規定》第十八條中規定: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決定的,應當自告知之日起五日內向承辦案件部門提出,并附申辯理由,承辦部門應當立即將犯罪嫌疑人的意見轉交偵查監督部門。偵查監督部門應當另行指定承辦人審查并在三日內提出審查意見。維持原逮捕決定的,偵查監督部門應當及時將書面意見和相關材料移送人民監督員辦公室。從規定中可以看出,要啟動這類案件的人民監督員監督程序必須有三個先決條件:一是必須是犯罪嫌疑人對逮捕決定提出異議;二是提出的異議必須有適格的理由;三是偵查監督部門另人審查后,否定異議成立的。在目前人民監督員制度試行中,不僅是社會,甚至于檢察人員中對其知之甚少、了解不深,而且這種情況還將相當一個時期存在,要讓犯罪嫌疑人的救濟行為符合上述三個條件的要求,進而啟動監督程序,就必須有極為嚴謹、合理、科學的告知程序和內容,但《規定》在這方面顯得粗糙和欠缺。
具體的表現為:1.權利的告知缺乏明確具體的內容。《規定》在如何告知上僅有第十八條和《意見》第五條作了相應的規定。十八條規定:案件承辦人在第一次訊問時,應當將《逮捕羈押期限及權利義務告知書》交犯罪嫌疑人,同時告知其如不服逮捕決定可以要求重新審查。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決定的,應當自告知之日起五日內向承辦案件部門提出,并附申辯理由。第五條規定:“送達《逮捕羈押期限及權利義務告知書》時,應當在告知書第二聯副本上注明‘如不服逮捕決定的,可以要求重新審查”,“不服逮捕決定的意見可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提出。”從這些告知內容上就可以看出,其過于簡單。一是缺少告知載體,《逮捕羈押期限及權利義務告知書》并非為人民監督員制度設計的。二是缺少告知內容,使犯罪嫌疑人很難把握。2.權利行使的法律后果交待不清。權利行使后的法律后果,直接影響到犯罪嫌疑人是否行使該權利。《規定》在告知內容上將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決定行為的法律后果,定為“可以要求重新審查”,這一表述存在兩個問題:一是界定不準確。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決定的法律后果不光是“重新審查”,其最終的法律后果從設立人民監督員制度本身來說,就是啟動人民監督員監督程序。“重新審查”只不過是啟動人民監督員程序的前置條件,是該程序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將“重新審查”作為不服逮捕決定行為的法律后果,是不準確的,至少是不完整的。二是表述的內容沒有體現人民監督員制度,將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決定的情形,納入人民監督員制度,是該項制度的主要內容之一,因此在告知犯罪嫌疑人權利時,必須明確的將這種權利與人民監督員制度之間的關聯性告訴犯罪嫌疑人,而《規定》和《意見》在告知內容上,沒有體現這種關聯,“可以要求重新審查”與人民監督員制度之間是什么關系,從《規定》和《意見》的相關表述中是無法弄清的。目的決定行為,如果犯罪嫌疑人對自己行為的目的也不知所以然的話,又如何會采取這種救濟手段去啟動人民監督員制度呢。3.告知的主體設定不科學。現有的人民監督員制度在對不服逮捕案件的告知設定上,采用了由案件承辦部門告知的方法,《規定》第十八條規定:由案件承辦人在對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訊問時,“告知其如不服逮捕決定可以要求重新審查”,并另規定“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決定的,應當自告知之日起五日內向承辦案件部門提出”,這種告知主體的設定,從試行的結果看其不科學的弊端已彰顯出來。因為犯罪嫌疑人提出不服逮捕的意思表示是啟動人民監督員監督程序的首要要素,其是否作出這種意思表示,與告知的方法、內容有很大的關系。對如何運用告知方法,如何掌握告知內容的深度,其主動權全部在承擔告知任務的主體上,告知主體如果懈怠告知或不正確告知,必然影響到被告知人的行為取舍,致使其不能正確的運用人民監督員制度所賦予的救濟權利。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認為,啟動人民監督員監督不服逮捕案件的程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告知主體。但是,現有的制度設計,又將這重要的角色賦予了與被監督內容有直接關聯的案件承辦人(部門),而從法理上講,案件承辦人(部門)在人民監督員制度中是被監督者的身份,恰恰是本應在這個環節中回避的主體。試想,案件是我偵查的,逮捕的申請是我提出的,現在要詢問當事人對此有無意見,有意見的話就將對我所辦的案件進行審查,那么我會用什么樣的方法、什么樣的態度來詢問當事人呢?所以這種告知主體的設定弊端十分明顯,而且極為滑稽。從試行的實踐看,上述的分析也并非空穴來風,許多告知人因為身處被監督的地位,對人民監督員制度或不了解,或有顧慮,不是對被告知人的有關提問不能正確解釋,就是在告知時,千方百計的采用防止被告知人作出“不服”意思表示的所謂技術處理的做法。如過分強調“申辯理由”這個附著條件要求。曲解“重新審查”的含義,致使被告知人因不了解人民監督員制度或不懂“不服”的法律后果,或害怕重新偵查,而放棄了“不服”的決定。事實上,“那些表示服從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在偵查后期或審查起訴階段翻供的占大多數,而認為自己沒有犯罪事實或認為證明自己實施犯罪行為的證據未經查證或不實的,也不在少數”。②這一不爭的事實,說明告知質量對是否啟動人民監督員監督程序至關重要,而告知主體的偏差必然導致告知質量難以保證。
三、過于簡化的“五種情形”規定,使適用存在困難
人民監督員制度對列入人民監督員制度范圍內的工作,除了“三類案件”外,還將人民檢察院查辦職務犯罪案件中具有的“五種情形”納入了人民監督員制度的監督范圍,并將這“五種情形”列為除“三類案件”外的另一個主要監督內容。但是對這樣一個主要監督范圍,《規定》中涉及的相應規定則過于簡單,其表現在:1.從體例看條文設置不平衡。整個《規定》共三十九條,除其中十四條規定了屬于監督范圍的情形(即“五種情形”)外,只有第二十八條交待了人民監督員依照十四條的規定實施監督的,由人民監督員辦公室負責辦理。《意見》共十八條,只有第十七條規定了對人民監督員的建議、意見的管理由人民監督員辦公室負責這一條相關條文。條文的設置上明顯偏輕,與對“三類案件”條文設置的數量相比極不對稱,很容易讓人懷疑人民監督員制度中將“五種情形”列入監督范圍的設計是應景之作。2.內容上空洞無物,不具操作性。作為人民監督員制度唯一的兩個法律依據性文件,《規定》和《意見》僅就“五種情形”的界定及監督意見的流轉職能部門作了規定,其他內容竟然絲毫未涉及;另外,除了對“五種情形”的范圍規定的較為詳細外,對如何監督、如何操作沒有具體的規定。《規定》第二十八條僅作了“人民監督員辦公室負責收轉材料,督促相關部門辦理,并及時反饋處理意見”的表述,《意見》第十七條僅規定為“相關部門應當將人民監督員的建議、意見的辦理結果書面告知人民監督員辦公室,人民監督員辦公室應當進行跟蹤督辦,并向人民監督員反饋結果。”對于人民監督員通過什么形式提出意見、建議,提出意見、建議的法律后果是什么,相關部門如何辦理人民監督員的意見、建議等內容和程序均未作出相應的規定。既然《規定》和《意見》是一個程序和實體相結合的準法律文件,那么對“五種情形”監督的規定又是如此簡單,完全不能形成一個操作體系,所以對“五種情形”的監督率幾近于零也就不足為怪了。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上述三個方面是造成人民監督員個案監督率低的重要原因。由于人民監督員制度畢竟是一項司法改革的試探性舉措,所以出現這樣的問題和偏差也是正常的,以上問題的出現需要我們以改革的態度,科學、合理、積極地去使之完善。
注釋:
①張林楓.人民監督員制度的理論依據與立法問題.江蘇檢察研究.第89期.
②徐蔚敏,孫杰.完善操作程序實現剛性監督.江蘇檢察研究.第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