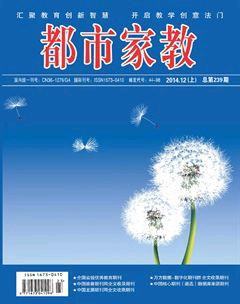思維導圖在職業中專英語教學中的應用
蘇書
【摘 要】思維導圖是一種可視化的知識表征工具,是一種具有放射性思考的具體化方法。自思維導圖被成功引入高中教學領域以來,在教育教學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目前,職業中專英語教學中的詞匯量、信息量豐富,語法學習結構復雜,課文及篇章的閱讀量加大,并且寫作的體裁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這對職業中專英語教師及學生是一種挑戰。本文就如何將思維導圖工具引入職業中專英語教學中,輔助英語教學,全面提高教師的教學效率和學生的學習效率做出探討。
【關鍵詞】思維導圖;職業中專英語教學;應用
近年來,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思維導圖在教學中越來越具有應用價值,它為職業中專英語教學的方法改革帶來了新的飛躍與轉變。我國在課程標準中明確強調職業中專英語教學必須采用有效的教學工具,激發與培養高中學生的英語學習興趣,使職業學校的學生掌握一定的英語基礎知識和聽說讀寫的技能,以此來形成一定的綜合語言能力。目前,隨著英語在我國對外開放中重要性的不斷提高,職業中專英語教學中將學生詞匯量的擴大、信息量的擴大、知識面的拓寬等作為主要的教學改革方向。英語單詞量也由過去的3000個增加為5000個。在實際教學中,主要存在著語法知識難以識記、理解,閱讀的篇章信息量大、句型不好判斷、文章的整體框架結構不容易把握等問題。寫作逐漸呈現出結構的復雜化、題材的多樣化等特點,這些都對職業中專英語教學與學生的學習提出了新的挑戰。
思維導圖作為一種可視化的知識表征工具,將一種放射性的思考實現了具體化的思維方式與方法。在英語教學中,用可視化的思維導圖將英語的知識點進行有效的組織與整理,從而為教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形成一個完整的知識體系結構,這對學生更加直觀的提供豐富的英語語境、促進學生的學習,幫助學生更好地背誦與記憶單詞,掌握語法、把握文章的寫作脈絡等提供了有力的幫助。本文將通過思維導圖在高中英語單詞教學、語法教學、閱讀教學的引入來研究其在高中英語教學中的應用,并努力探索思維導圖對職業中專英語教學中深遠影響。
一、思維導圖在職業中專英語詞匯教學中的應用
在職業中專英語教學中,詞匯教學是一個難點內容。很多學生的英語單詞在記憶方面存在困難,不能很好的掌握科學的單詞記憶方法。而英語單詞的學習情況直接決定著學生的閱讀與寫作能力,學生所掌握的詞匯量越大,在閱讀中遇到的閱讀障礙就越小,而在寫作中也會出現很多能夠獲得高分的亮點詞句。對于單詞的思維導圖的教學設計,首先,教師可以引導學生將具有相同前綴的單詞畫出相應的思維導圖,對那些已經學過的單詞入手,作為新舊單詞之間的交叉連接,將這些新舊單詞做一個成功的導入鏈接。第二,課后,學生根據課堂上教師給出的思維導圖進行適當的補充與完善,從而進一步加深對所學新單詞的記憶、認識、理解、正確運用。多年的教學實踐經驗表明,小組合作是一項十分有效的學習方式。第三,完成對思維導圖的繪制后,教師可以通過教師評價、學生自評、小組互評的方式來對各小組的完成情況進行評價,以此來提高學生對思維導圖的使用積極性與學習英語單詞的信息。
二、思維導圖在高中英語語法中的應用
職業學校的學生對于英語語法的學習還存在一定的障礙,如果一個學生的英語語法掌握的較好,那么他就不會對閱讀中出現的各種難句、長句產生畏懼情緒,更會對寫作中的時態、句型產生畏難情緒。教師可以先將學生已經掌握的兩種時態和新學的時態的結構書寫、總結在黑板上,在認真觀察這些時態的基本構成后找到中心點,用方框表示出動詞的不同時態,并用分支表示出每種時態的標志、結構、例句等。在學生的努力與教師的有效指導下,共同完成對語法思維導圖的繪制。同樣,教師仍然可以采取思維小組合作的形式來提高學生對思維導圖的理解與使用頻率。課后,學生在根據自己繪制的思維導圖進行補充、修改、擴展,通過對比二者之間的差別來加深對新講授語法知識的理解與運用。這一看似簡單的過程,其實蘊含著豐富的內涵。學生在教師的引導與幫助下通過對思維導圖的繪制在頭腦中建立起了系統的知識網絡,有助于學生對各種時態的深刻理解與掌握,并且不容易混淆。
總之,將思維導圖工具引入到職業中專英語教學中,不僅使學生容易記憶教師的講課內容,而且可以幫助教師對所講授的內容從整體上做出把握,使得教師、學生的思維更加清晰,學生亦能夠通過對自己思維導圖的繪制輕松地完成教學內容。同時,教師在通過對學生設計的思維導圖過程的觀察,進一步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與其內心的思維活動,及時為學生的不良學習習慣做出糾正。我們堅信,只要我們認真探索、銳意教改就一定能夠創造出更多的、有價值的、有益于職業中專英語教學的切入點,全面提高職業中專英語教學的效果,使我國的英語教學邁上一個新的臺階。
參考文獻:
[1]紀曼然.思維導圖對于英語詞匯教學的啟發[J].當代教育論壇,2010(01)
[2]師海紅.運用思維導圖提升英語自主學習能力[J].英語教師,2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