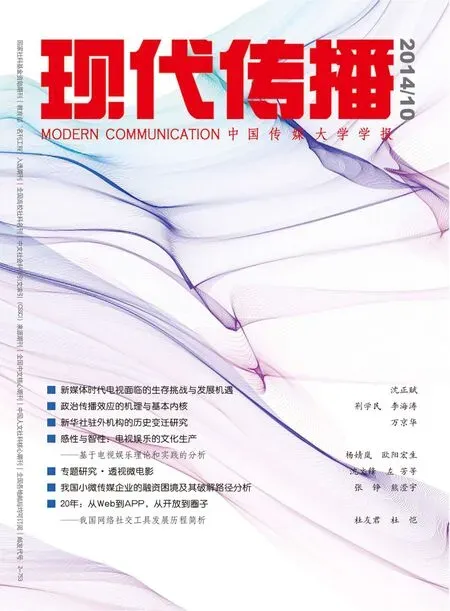影像話語流變與認知“微電影”的新視角*
■ 杜志紅
影像話語流變與認知“微電影”的新視角*
■ 杜志紅
“影像話語”,指構建影像的思維方式和組接方式所共同形成的話語表達,它直接決定了影像的類型和風格,會成為一個時代影像生產和影像審美的風向標。隨著時代社會的變遷,貶抑或推崇某種影像話語的審美習慣和情感態度也會發生不同程度的流變。
這種影像話語的流變意味,近年來在影像宣傳推介或曰“影像說服”領域表現得尤為搶眼,這就是“微電影”現象的火爆態勢。一方面,在社會實踐領域,由于新媒介技術的發展,各種類型的“微電影”粉墨登場,各種創作實踐主體紛繁復雜,各種性質的評比賽事層出不窮,呈現出一種熱鬧而無序的狀態;另一方面,在學術研究領域,關于“微電影”概念的認知和“微電影”現象的研究,也爭論不斷、眾說紛紜。有人質疑這個名詞的科學性,認為它是一個“不靠譜的概念”;①有人認為微電影“生于惡搞”,后又受制于廣告商,單一的盈利模式導致微電影必將“死于廣告”。②
以上的爭議和質疑表明,對于微電影的基本概念、身世和身份等,還缺乏一個明確的認知,需要影視研究領域給予認真的關注和探討。本文將微電影的興起放置在“影像說服話語流變”的視角下進行考察,或許可以獲得一種對微電影本質特性和身世來歷的新的認知視角。
一、兩種蒙太奇思維與影視形態的構成
構建影像的思維方式和組接方式,影視專業術語稱之為“蒙太奇”。一般來說,蒙太奇分為兩大類型,即對列式的“表現蒙太奇”和連續式的“敘事蒙太奇”。前者著重于內在的聯系,在操作過程中,往往會根據某個主觀意圖或思想,把分別拍攝于不同時空中的鏡頭按照寫論文的邏輯而非講故事的邏輯來進行編排;后者著重于時間的順序、動作的連貫和情節的連續,一般用來講述一個具有完整情節的故事,帶有敘述的客觀性。
在一百多年影視發展歷程中,蒙太奇的思維、藝術和技法逐步成熟。盡管有時這兩種組接方式會在一部影視作品中被同時使用,甚至有難以區分的情況出現。但是以兩種蒙太奇思維方式形成的影視節目形態,卻仍然有著較大的區別。
以連續的動作組接為主的敘事蒙太奇,逐漸主要被用以創作故事片,以至于到后來,故事片甚至逐漸成為人們心目中“電影”的代名詞。“今日西方電影家制造的影片中絕大部分都是故事片,都是以表現‘敘事’為目的的,這是一個明顯的事實。”③
而表現蒙太奇,由于更能滿足對于主觀思想和理念的傳達,則很快成為宣教思維主導下的的影像話語選擇。在這方面,蘇聯的電影理論可謂集大成者。蘇聯蒙太奇學派主要代表的愛森斯坦認為,蒙太奇最重要的特點是可以通過“兩個鏡頭的對列以及它們的內在沖突產生第三種東西,即對所描繪的事物進行思想評價的契機,通過它的特殊功能來闡明思想。”④在他看來,兩個鏡頭之間的沖突是產生新的意義的根源,也是電影藝術的基礎。蒙太奇是操控觀眾思想的一個有效的工具。另一個代表人物維爾托夫,則更是對“藝術中的故事情節本身攻擊不遺余力,斥之為資產階級反革命的‘美學雜碎’,認為故事只會使人脫離現實而不是面對現實。”⑤
或許由于有著這樣的認識基礎,蘇聯在推翻沙皇統治、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過程中,“很快意識到電影的認識和宣傳功能,對它進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并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下。”⑥列寧在1921年關于電影的指示中說,“它應該是形象化的政論,它的精神應該符合于我們蘇維埃優秀報紙所遵循的路線。”⑦后來,“形象化政論”成了蘇聯理論家解釋為關于紀錄片的定義,即“電影的解說優先于畫面,發展到極端狀態便是文字統攝畫面,甚至可以直接以理論為題材,用電影的方式論述一種理論觀點。”⑧
新中國影視在發展歷程中更多學習了蘇聯的電影理論。1949年前后,蘇聯電影工作者把“形象化政論”的創作理念帶入中國,很快成為后來中國影像工作者多年遵循的權威觀念,“‘形象化政論’一直是新聞紀錄電影創作的指導原則,成為我們公認的創作傳統。它既包含影片的內容,又標志著影片的樣式。”⑨
上世紀90年代,盡管我國影視界曾掀起以紀實美學為追求的影像觀念變革,但是由于“形象化政論”壟斷中國影像主流形態的時間長達40年之久,以至于在影像創作者、意識形態管理者和普通觀眾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美學觀念和思維慣性。在影視屏幕上,不僅很少看到以連續的敘事蒙太奇為結構的故事化廣告,而且在各級領導、影視工作者、觀眾心目中,只要提到用以影像說服的專題片、宣傳片、廣告片,大家就自然地會選擇表現蒙太奇的思維方式,這基本上成為近年來我國影視美學中對于影像說服性話語的一種本能認知。
二、微電影:影像說服話語中的敘事蒙太奇回歸
正是在上述的背景下,微電影的出現讓許多人眼前一亮。加上數字攝錄設備的小型化、低廉化,以及傳播終端的多元化,傳統的以表現蒙太奇為主的叫賣式廣告,已難以在新的網絡和新媒體觀看環境中實施強制傳播,更難以激發起人們的觀看興趣。當以敘事蒙太奇方式來講述一種商品的故事時,人們自然地將這種影視類型與電影故事片相類比;同時,由于其長度和規模較小,而且出現在由微博和社交媒介所營造的碎片化媒介接觸時代,就自然地被冠以“微”字,出現了“微電影”這樣的概念。
因此,微電影的火爆景象,看似是一種新鮮事,其實是對影像說服領域中長期存在的“表現至上”或“敘事抑制”現象的一種逆反:影像說服話語中的表現蒙太奇長期占據主流、而敘事蒙太奇遭受擠壓和抑制的格局,終于在新傳播技術塑造的媒介環境中受到沖擊,敘事蒙太奇以微電影的方式在影像說服話語中強勢回歸。換句話說,微電影的出現,正是影視說服話語發生流變的結果。也可以說,正是由于敘事蒙太奇的強勢回歸和影視說服話語的流變,促成了微電影的風生水起。而這種回歸和流變,與影像媒介的本性和人類的天性之間存在著天然的契合性與親和力。
有學者早就指出,影像媒介的本性與敘事性話語方式具有天然的契合性。“首先,影片的表達面是由形象性符號構成的……因此銀幕上的形象表現,按其本性即傾向于敘事性的表現。其次,銀幕上的影像都是運動的。一切對象,包括靜止的風景,在有攝像機拍攝以后,都在事件延續中被記錄下來,并參與變換。”⑩這一影像本性,也為更多的電影學家所認同。克拉考爾就指出:“銀幕形象傾向于反映出自然物象中含義模糊的本性。”(11)巴贊進而認為,現實含混性尤其是指人類行為意義的含混性。觀眾可以通過探索角色行為動機而逐步卷入情境,這也給予演員發揮表演潛力以更大的可能性。“表現蒙太奇由于過分嚴格地‘組織’了觀眾的知覺,因而在銀幕畫面中就消除了多義性。鏡頭含義過于明確,反而使觀眾沒有想象的余地了。”(12)這也基本上揭示了以說服性文字為主導的影視作品何以令人生厭甚至反感的原因。
敘事性話語方式,與人類的天性之間也有著天然的契合性。人類是故事的動物,聽故事是人類的天性,因為“故事提供了過去與現在、他人與自己的一種聯系”,“是人類構筑精神世界的特殊方式,人類正是通過故事來理解世界、理解自身,理解過去、現在與未來的。”(13)故事在被敘述過程中,可以自然而然地展現生活的邏輯和神秘的命運感。因此,即使是帶有商業性質的微電影,也因為將商品信息或者品牌理念巧妙地融入故事中,而減弱了可能招致的反感。
此外,敘事蒙太奇,是訴諸觀眾情感的視覺說服手法。它將抽象的符號化的情感因子變為日常生活中具體可感的情感宣泄載體。美國廣告大師托尼·施瓦茨指出:“最好的政治廣告對觀眾什么都沒有說。它們僅僅觸動了觀眾的情感,并且提供了一個讓他們宣泄這種情感的語境。相對于觸動了觀眾心弦的廣告,那些試圖向觀眾傳遞信息的廣告怎么都要遜色一些。”(14)而對于這一點,訴諸理性、指向主觀表達的表現蒙太奇無法勝任,只能采用訴諸感性具有戲劇性的敘事蒙太奇。
三、故事敘述應是認知“微電影”概念的核心
目前,不論在影像創作,還是在觀看者認知方面,“微電影”概念常常與“微視頻”“DV作品”“數字短片”等概念混亂使用,在一些作品發布、宣傳推廣的新聞報道中,一些宣傳片被冠以微電影的名頭發布;一些由政府、協會、行業、地區等主辦的所謂“微電影大賽”,往往在作品征集時,將劇情片、紀錄片、MV、VCR,甚至動畫片等都囊括其中……這些現象,都造成了“微電影”概念的無限泛化和混亂。
同時,在理論認知方面,有的局限于對微電影一些表象的描述,或做一些削足適履的框定,比如“微時長”“微投資”“微周期”等等;而一些爭議和討論中所使用的微電影概念,則各有各的對象指稱,因而造成理解上的偏差和不必要的誤會。
綜合上述的分析,本文認為,微電影最根本的特點不在于碎片化傳播和短時播放,而在于它敘事策略的轉向:從表現蒙太奇向敘事蒙太奇的轉換。微電影可以說是一種小型的影像說服的敘事藝術,這應該是關于微電影的本質的一個基本定義。這個定義可以把微電影與微視頻分開,同時也與一些沒有故事性的形象宣傳片、廣告片、MV等分開,從而為建立起自己的本體性確立框架。換句話說,判斷一部微型影視作品是不是“微電影”,應首先看它是不是以敘事蒙太奇的話語方式講述一個故事。至于所謂“微時長”“微投資”“微周期”等等描述,則只能算是關于微電影概念的外延式表述。而這樣的認知,對于指導和組織微電影的創作,提升微電影的整體藝術水平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即微電影必須從敘事創意和話語策略上確立著力點和藝術追求。
注釋:
① 劉一賜:《五問“微電影”》,http://techorange.com/2012/03/05/micro-movie。
② 陳新焱、周馮燦:《微電影:生于惡搞,死于廣告》,《南方周末》,2012-04-02。
③⑤⑩(12) 李幼蒸著:《當代西方電影美學思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176、154、102頁。
④ 何蘇六著:《電視畫面編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頁。
⑥ 俞虹:《蘇聯蒙太奇學派》,《當代電影》,1995年第1期。
⑦⑧⑨ 張同道、劉蘭:《格里爾遜模式及其歷史影響》,《電影藝術》,2008年第4期。
(11) [德]克拉考爾著:《電影的本性》,中文版,中國電影出版社1981年,第88頁。
(13) 潘知常:《講“好故事”與講好“故事”(上)——從電視敘事看電視節目的策劃》,《東方論壇》,2006年第6期。
(14) [美]布萊恩·麥克奈爾著:《政治傳播學引論》,殷祺譯,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頁。
(作者系蘇州大學鳳凰傳媒學院副教授)
*本文系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資助項目“新媒介與文化傳播研究”(項目編號:2014SJB538)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