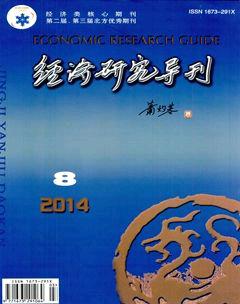以人為本理念下的城市公共服務體系建設
楊劉軍
摘 要:中國城市社區傳統的政府——企業包攬式的公共服務體系,在改革開放深入推進階段,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的快速發展和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服務需求。然而,20世紀80年代推進的城市公共服務體制改革過于市場化,使得原本具有公益性的城市公共服務體系向效益和利潤傾斜,“為人民服務”的口號流于形式。當前,以人為本理念深入人心,但市場化和公益性的矛盾卻是中國城市公共服務體系的癥結,而只有“政府購買服務”新模式才能從根本導航解決上述問題。
關鍵詞:公共服務;政府購買;以人為本;體系建設
中圖分類號:F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08-0060-02
一、當前中國城市公共服務體系的癥結
(一)城市公共服務體系的公益性傳統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于對蘇聯模式的借鑒,中國基本建立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城市公共服務體系,本文稱為“傳統城市公共服務體系”。這一體系有三方面的特點:其一,傳統城市公共服務體系的主體是政府。計劃經濟時期,絕大多數城市人口,只要具有勞動能力,就會被安排一定的工作,政府通過各種類型的企業將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輸送到普通民眾手中。其二,傳統體系的供給途徑是企業。因為當時,中國在勞動就業領域實行“低薪酬、廣就業”政策,當時城市居民享受公共服務主要通過企業和崗位來實現,公共服務的大部分資源在當時是政府來配置的,政府將這些資源分配附屬在具體崗位上,所以,城市居民首先就是“單位人”。其三,傳統體系的理念是“為人民服務”,其價值基石是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因此,當時人們能夠在實踐中真真切切地為了集體而做出犧牲,城市居民之間,特別是一個企業的員工之間形成了一種“大家庭”的關系模式,互幫互助。
總的來說,中國傳統的城市公共服務體系是一種以政府為主題、通過企業(單位)來實施的普遍的、就業型體系。這種體系因為是政府和企業包攬式的服務,因而具有較強的公益性,它也像計劃經濟一樣,在特殊時期確實因為能夠體現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而發揮過巨大的作用。
(二)市場化改革以來對公益性的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政府職能的轉變,傳統體制下政府通過行政方式配置公共服務的弊端日趨顯現,“自我服務,漠視公共需求;工作效率低下,浪費公共資源;固守成規,缺乏創新;服務意識薄弱,態度傲慢。”[1]因此,城市公共服務體系改革勢在必行。20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了一系列的城市公共服務的社會化改革,其初衷是希望改革傳統體制中政府過于包攬的行政管理方式。
事實證明,中國在20世紀末的城市公共服務體系改革是有缺憾的。表現在:第一,以住房和醫療為代表的民生領域內的主管部門,過于關注自身利益,將城市居民自身的利益拋之腦后,導致群眾意見相當之大;第二,隨著中國社會集團日益分化,“社會貧富分化直接導致了城市中形成了諸多的弱勢群體”[2],而公共服務體系在很長一段時間沒有關注這些人的利益;第三,普通民眾的服務需求始終得不到積極的回應,社會化改革要求政府和各部門一切向經濟效益看齊,這就有可能會忽略群眾的呼聲。
二、城市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必須堅持公益性
(一)公益性是城市公共服務的根本屬性
從學理性的角度來看,公益性是公共服務的根本屬性。顧名思義,公共服務就是面向公眾提供的各種與其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服務項目,其內涵是國家和政府履行的一種對于公眾的服務職能,其外延卻相當寬泛,包括衣食住行醫等幾大塊在內,但是概而言之,公共服務必須面向普通大眾[3]。根據西方經典的政治學原理,政府作為每一個社會成員的代言人,在其設立之初就與人民形成了一種契約關系,人民將權力和權威賦予政府,而政府則具有保護公民、服務公民的不可推卸的職責,而向公民提供他們必需的公共服務,則是政府職責的應有之義。
如上所述,公共服務必須面向普通公眾,因此公益性就成為公共服務的根本屬性。公共服務的公益性具備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方面,公益性表現在城市公共服務的受惠人群必須確保為大多數城市居民,當然,本文不是指傳統戶籍制度下的城市居民,而是包括一切自愿在城市中就業、生活、休閑的人口;另一方面,公益性還表現在城市公共服務必須實行公共決策、群眾民主參與的程序,當前,有越來越多的城市,實施公共服務項目決策和改革的聽證會制度,暫且不談個別的暗箱操作,這也是一種制度上的進步。以上兩方面,即城市公共服務的受眾和參與力量的大眾化,說明了它的公益性本質。
(二)堅持公益性與解決民生問題相契合
正是因為中國20世紀末在城市公共服務領域實行的市場化改革使得對計劃經濟下行政性的資源分配方式矯枉過正,才使得城市公共服務走向了違背人民意愿、片面地追逐經濟效益的錯誤道路。新世紀伊始,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執政以后,針對現實的問題,提出了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的執政理念。在這一理念的指引下,中國正在逐漸糾正以往的過失,政府也將執政的著力點慢慢地從追求GDP的增長向解決民生問題轉變,執政理念的轉變和執政著力點的轉向。這恰恰說明了中央政府已經認識到,公益性才是公共服務的根本屬性,必須以解決民生問題為契機,大力弘揚公共服務的公益屬性。
它們二者的關系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堅持公共服務的公益性,與堅持以解決民生問題為執政重點,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它們都是政府在有限的能力下,最大化地滿足人民、特別是社會弱勢群體的需求,這也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其次,它們二者的出發點也是一致的,公益性堅持了人民群眾的受眾地位,因而是以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作為自己的出發點,而解決民生問題也是為了急人民之所急、予人民之所欲,出發點同樣是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再次,堅持公益性和解決民生問題,都必須統領在科學發展這一新的執政理念之下,因而二者也是具有一致性的。因此可以說,堅持城市公共服務體系的公益性,就是堅持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然而,“只有創新公共服務供給模式,提升城市政府公共服務能力,才能真正地滿足社會公共的需。”[4]endprint
三、政府購買服務是解決既存矛盾的關鍵
(一)政府購買服務堅持了公共服務的公益性
“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同公共服務不到位、基本公共產品短缺之間的突出矛盾,暴露出我們現行制度安排的某些缺陷,并對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5]因此,順應這種要求,對中國城市公共服務體系進行模式創新,成為了一種必然。“政府購買服務”是一種較為新穎的值得探索的模式。
公共服務的產出并不是一股力量就能完成,在整個公共服務體系中,理應包含政府的支持、指導和監督、社會民間力量廣泛而深入的參與以及市場機制在其中的穿針引線。因此,構建一個包含政府、社會和市場三方面的公共服務體系,是政府購買服務的前提。其中,政府為公眾提供公共服務應該要通過“委托——購買”的方式加以實現的。在現階段,政府將服務公眾的職責通過財政全額撥款的方式分派給社會服務組織,在這些組織實施服務過程中和完成后,政府組織相關專家對其進行監督和評估,判斷社會福利組織是否準確、及時、有效地完成了任務。社會服務組織作為政府“委托——購買服務”模式的社會活動主體,直接對政府負責,也直接面向公眾實施專業化服務,因而成為整個公共服務體系的關鍵。
(二)政府購買服務有效地融入了市場競爭思維
由上可知,“政府購買服務”模式中,委托人和購買人是政府,受委托人和出售服務者是社會服務組織,但是,二者作用的發揮卻離不開市場這一第三方機制的作用。歷史表明,西方國家在公共領域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后,提升了公共服務質量、降低了公共服務成本,“這種做法對于中國當前的城市公共服務改革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作用”[6]。只有政府、服務組織和市場三方聯動,整個公共服務體系才能運轉正常。市場機制運轉的具體途徑,其實也就是整個公共服務體系的實施機制——政府購買服務。
隨著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公眾對公共服務將會有巨大需求,而雖然滿足公眾需求是政府的職責,但政府不具有專業服務能力,于是通過“委托——購買服務”方式,用政府財政支持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服務供給,社會服務組織要想提升自身在市場中的競爭力,只能通過市場競爭,不斷吸納專業人才以提升實力,將服務順暢地輸送到公眾那里。概括而言,新的城市公共服務體系應該努力創造“政府主導、社會主辦、市場主動”的局面。
概括而言,中國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后,長期的政策慣性導致城市公共服務體系日漸落伍;但是20世紀末的市場化改革又矯枉過正,以住房和交通為代表的諸問題未得到根本性解決。針對新發展階段的社會現實,政府購買服務既堅持了公共服務的公益性,也吸納了市場競爭的效益優勢,因此成為中國城市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一個未來發展方向。
黨的十七大指出,我們要實現新階段的可持續發展,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實現這一目標的前提手段就是要以創新的思維積極構建中國新的城市公共服務體系,而其中政府購買服務模式已經代表了一種新的舉措和新的嘗試。政府購買服務也全面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理念,與時代發展主題保持一致。究其原因,我們不僅要關注當前的問題,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滿足社會公眾對服務的當下需求,也要以歷史為鑒,實現可持續性的科學發展,關注代際公平,將構建中國城市公共服務體系的眼光放得更為長遠,不能像以往制定政策那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應當制定長期性、規范化的制度和政策體系,為后世造福。
參考文獻:
[1] 周云圣,朱歡.城市公共服務市場屬性研究[J].計劃與市場探索,2003,(6):57-58.
[2] 孫立平,等.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的結構變遷[J].中國社會科學,1994,(2):47-62.
[3] 金南順.城市公共服務的三個基本問題[J].城市問題,2005,(6):56-58.
[4] 劉雙良,等.城市公共服務社會化的困厄及其解圍[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08,(1):111-113.
[5] 遲福林.公共服務不足凸顯“短缺”矛盾[J].人民論壇,2007,(8):18-20.
[6] 任立兵,李冰.中西城市公共服務比較分析[J].東北財經大學學報,2007,(4):63-66.
[責任編輯 李 可]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