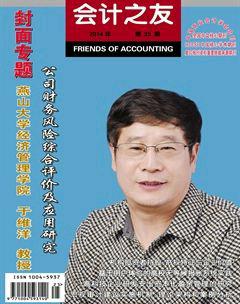經營風險:風險導向審計中“風險”的應有之意
朱廣印++張瓊+王治
【摘 要】 我國引入風險導向審計后,學術界從不同角度形成了不同的風險導向審計觀。文章探討了風險導向的關鍵風險概念及其關系,提出構成風險導向審計中“風險”應有之意的條件,并以此為基礎對不同的風險導向審計觀進行評析,得出經營風險是風險導向審計中“風險”的應有之意的結論。
【關鍵詞】 風險導向審計; 風險概念體系; 經營風險; 重大錯報風險
中圖分類號:F23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937(2014)25-0097-05
一、引言
自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引入風險導向審計以來,國內學術界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了探討,形成了有關風險導向審計的不同觀點,主要包括:
1.審計風險觀:風險導向審計在對審計風險進行系統的分析與評價的基礎上,制定審計戰略及適合的審計計劃。在注冊會計師認為審計風險已經控制在可接受水平范圍內時,就可以發表審計意見(胡春元,2001)。
2.訴訟風險觀:基于審計主體受法律訴訟而遭到損失的可能性來定義審計風險(王廣明、沈輝,2001),該觀點將“風險”理解為審計主體可能受到的訴訟風險(或稱法律責任風險)。
3.重大錯報風險觀:認為風險導向審計應以評估是否存在重大錯報風險為中心,并把對該風險的評估貫穿于審計的全過程(張龍平等,2004)。
4.舞弊風險觀:財務報表審計應以判別企業管理層舞弊風險為導向,以管理層舞弊為導向進行審計才能保證通過審計揭露管理舞弊的效果(王澤霞,2004)。
5.經營風險觀: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是在系統觀的指導下以經營風險作為審計導向,綜合“由上至下”和“由下至上”兩種方法對被審計單位進行全面審計(謝榮、吳建友,2004)。
正確認識現代風險導向審計中“風險”的含義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從理論上說,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模式是現代審計學的重要內容之一,如果對現代審計理論中的重要內容存在不同甚至矛盾的認識,顯然不利于現代審計理論的完善;從實踐上講,運用不同的風險導向審計觀,其審計重點、審計資源的分配等各不相同,實現審計目標的效率與效果也大相徑庭。
筆者認為,厘清現代風險導向審計中“風險”的含義,至少應明確以下兩個問題:(1)風險導向審計模式中關鍵風險有哪些?它們之間的關系如何?(2)作為風險導向審計模式中“風險”應有之意的風險應滿足哪些條件?
二、風險導向審計中關鍵風險之間的關系
(一)風險概念體系
風險導向審計涉及眾多的風險概念,它們構成一個完整的風險概念體系(圖1)。
如圖1所示,信息風險、審計業務風險、審計風險、重大錯報風險、檢查風險和經營風險處于關鍵位置,共同構成了這個體系的骨架。
信息風險和審計業務風險是社會審計服務供求的重要決定因素。信息風險指的是會計信息及相關信息存在不準確的可能性。存在重大錯報的會計信息會使信息失去原有價值,甚至產生誤導,致使投資者作出錯誤的判斷并因此遭受損失。審計業務風險是指特定業務的承接而受到損失的不確定性,有訴訟風險、信譽風險、利潤受損風險等表現形式。根據理性經濟人經典假設,對業務風險和收益的權衡是判斷是否承接審計業務的決策關鍵。而正是這種風險收益權衡的結果決定了社會審計服務的供給量。
注冊會計師承接審計業務后,主要有三種原因導致其遭受損失:未遵守業務約定書、出具不當審計意見以及特定審計業務關系。注冊會計師在審計業務中不遵守審計業務約定書條款的可能性稱為違約風險;注冊會計師對其審計的財務報告出具不恰當意見的可能性稱為審計風險①;注冊會計師雖然在審計報告中出具了恰當的審計意見,但由于其與被審計單位之間存在審計業務關系而受到損失,這種風險稱為審計業務關系風險。審計風險是導致審計業務風險的重要原因,控制審計風險的關鍵是控制審計業務風險(A.A.阿倫斯等,1991)。這就確定了審計風險處于概念體系的中心地位。
企業經營風險與重大錯報風險二者存在密切的關系。正是經營風險的存在,使得重大錯報風險才有了基礎和源頭,甚至可以說前者驅動了后者的產生。鑒于經營風險與重大錯報風險之間關系的重要性,下面著重探討經營風險與重大錯報風險之間的關系,闡述重大錯報風險的形成機理。
(二)重大錯報風險的形成機理
經營風險是指企業經營無法達到預期目標的可能性,可分為戰略風險和經營流程風險。戰略風險是指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和易變性致使企業經營目標無法確定達到。為應對戰略風險,企業管理層通常會設置包括戰略管理、核心經營和資源管理等在內的經營管理流程。經營流程風險是指來自企業內部各經營流程的威脅。管理層通過設置內部控制來應對經營流程風險。內部控制包括戰略、管理和經營流程三個不同的控制層級。內部控制本身有其固有缺陷性,不可能消除所有的風險,我們稱之為控制風險。因此將控制風險定義為內部控制無法有效地降低企業經營風險的可能性②。為了能夠對企業風險應對措施及其效果進行有效控制,管理層應建立可靠的信息系統并選擇適當的監測變量。管理層采取風險應對措施后仍然無法控制的風險部分,形成剩余風險。可以用下式來表達經營風險與剩余風險的理論關系:
剩余風險=經營風險③×控制風險
雖然存在剩余風險,但并不意味著必然導致出現重大錯報,事實上財務報表的重大錯報也并非全部來自于剩余風險,但二者確實存在明顯關聯④(汪壽成、劉明輝,2007)。重大錯報的產生有兩大原因,那就是“錯誤”和“舞弊”。從形成機理來看,“錯誤”是主客觀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主觀因素包括會計人員的道德素養、業務水平和心理偏差⑤等;客觀因素包括不確定性的外部政治、經濟環境和企業本身的復雜性等。客觀因素往往與剩余風險有關,剩余風險與產生錯誤的主觀因素結合就可能導致財務報表重大錯報。例如,企業經營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管理層沒有能夠采取有效的應對措施就會形成剩余風險,而存在剩余風險的情況下,如果會計人員不顧這種變化的存在仍然沿用過去的會計估計,就可能導致財務報表重大錯報。事實上,財務報表中產生重大錯報的可能性無法從根本上加以消除。這是由于導致錯誤的主客觀因素無法根本消除。這些因素包括非常規項目和會計估計必須存在,內部控制也有其局限性,如會計人員的心理偏差行為等因素。與“錯誤”的客觀性不同,“舞弊”則是故意使用虛假信息等欺騙手段謀求獲取不當利益的行為。注冊會計師在審計業務中重點關注“侵占資產”和“虛假陳述”。endprint
剩余風險與對財務信息做出虛假報告之間存在密切聯系。首先,剩余風險可能導致企業無法實現經營目標,甚至會導致企業破產。面對嚴格的市場監管和社會各方壓力,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管理層往往存在通過財務報表舞弊對其經營和財務狀況進行粉飾的動機或壓力。其次,企業管理層擁有的特殊地位與權力,往往可以輕易繞過內部控制直接或間接地操縱會計信息。換言之,兩權分離形成的委托—代理關系成就了管理層財務報表舞弊的機會。最后,如果不夠誠信和自律,管理層完全可以找到舞弊的借口。
經營風險與重大錯報風險的關系如圖2所示。
三、作為風險導向審計中風險應有之意的“風險”應滿足的條件
從圖1可以看出,經營風險——重大錯報風險——審計風險——審計業務風險——信息風險構成了風險導向審計的風險鏈。在這一風險鏈中,哪個環節是風險導向審計中“風險”的應有之意呢?這涉及到界定作為風險導向審計中風險應有之意的“風險”應滿足的條件。筆者認為,作為風險導向審計中風險應有之意的“風險”至少應滿足四個條件:(1)由于風險導向審計是一種審計模式,所以以該風險為導向的風險導向審計必須與審計模式性質不矛盾;(2)以該風險為導向必須與審計模式中“導向”一詞的真正含義不沖突;(3)以該風險為導向的審計能夠體現該審計模式的特征,能將風險導向審計與其他審計模式相區分;(4)該風險是審計工作的“牛鼻子”,以該風險為導向開展審計工作能更加有效地達到審計目標。在這四個條件中,后兩個條件的含義是明確的,而人們對構成前兩個條件的審計模式的性質和審計模式中“導向”一詞的含義卻有不同認識。下面著重討論這兩個問題。
(一)審計模式的性質
審計目標、范圍、重點和程序等的組合構成了審計模式。審計模式規定了資源的分配、風險的控制方法、程序的規劃、證據的收集和結論的形成等方面(劉明輝,2007)。審計模式究竟是為了發現舞弊或重大錯報,還是為了發現并報告舞弊或重大錯報?這涉及到對審計模式性質的認識。審計三方關系為理解風險審計模式的性質提供了基礎。
審計三方關系由預期使用者(信息需求方)、責任者(信息提供方)和注冊會計師(信息鑒證方)組成。預期使用者與責任方共同確定了責任方應提供何種信息以及如何提供信息,預期使用者與注冊會計師共同確定了審計應達到的目標,而注冊會計師與責任方共同確定了應使用的審計模式。審計目標取決于在特定審計環境中預期使用者的需求及注冊會計師的能力等因素。隨著審計環境的改變,預期使用者的需求及注冊會計師的能力也會發生改變,因而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審計目標的具體內容是不同的。能否實現審計目標取決于注冊會計師在審計中能否發現舞弊或重大錯報以及對發現的舞弊或重大錯報能否進行報告。能否將發現的舞弊或重大錯報如實進行報告取決于注冊會計師是否具有獨立性,而能否發現舞弊或重大錯報則取決于注冊會計師所采用的審計模式。西方國家一般將我們所說的審計模式稱為審計方法(Audit Approach)。從本質上講,審計模式是發現舞弊或重大錯報的方法,而不是報告舞弊或重大錯報的手段。
(二)審計模式中“導向”的含義
理論界之所以會出現形形色色的風險導向審計觀,對審計模式中“導向”一詞的理解分歧是重要原因之一。有人按中文字面意思將“導向”理解為“引導的方向”,也有人將其理解為審計工作的“切入點”。筆者認為,對“導向”一詞的理解應遵循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原則,而不能僅按中文意思來理解。
審計環境不斷發生著變化,審計模式也發生著改變,從最初的“賬項導向”演變為“內控導向”,再演變為“風險導向”。從英文來源來看,不同模式中,“導向(Oriented)”與“基礎(Based)”是同義的。“Oriented(導向)”的詞根是“Ori”,來源于拉丁文,有“太陽升起”、“起源”、“最初”之意。這說明審計模式中的“導向”就是審計工作的起始點。在審計模式中,“導向”、“基礎”和“起始點”三者具有相同的含義。
在賬項導向審計中,審計計劃的立足點、實施審計工作的切入點和收集審計證據的著重點均與會計賬目有關,因此稱之為賬項導向審計。在內控導向審計中,審計計劃的立足點、實施審計工作的切入點和收集審計證據的著重點均與內部控制有關,因此稱之為內控導向審計。在風險導向審計中,審計計劃的立足點、實施審計工作的切入點和收集審計證據的著重點均與風險有關,因此稱之為風險導向審計。
四、有關風險導向審計觀評析
筆者以上述條件為標準,對學術界存在的有關風險導向審計觀進行評析。
(一)審計風險觀評析
首先,審計風險觀與審計模式的性質相矛盾。審計風險是指注冊會計師有可能對所審計的財務報表出具不恰當審計意見。這里實際上包括兩種情況:一是缺乏必要的勝任能力,未能發現財務報表存在的重大錯報;二是缺乏必要的獨立性,雖發現重大錯報但未能恰當報告。將風險導向審計的“風險”視為審計風險,實際上是將風險導向審計的性質定位為發現重大錯報與報告重大錯報的方法,這混淆了審計方法與審計獨立性的界線,與審計模式的性質相矛盾。
其次,審計風險觀與審計模式中“導向”一詞的含義相沖突。審計模式的演進過程是審計重心逐步前移的過程。在風險導向審計中,審計重心已前移至對導致重大錯報的各種因素的了解和評估上,審計各環節均與導致重大錯報風險的因素相聯系,而審計風險既非計劃審計工作的立足點,也非實施審計的切入點,更非收集審計證據的著重點。可能有人認為,審計中所收集的審計證據都是圍繞著降低審計風險來進行的,因而審計風險就是收集審計證據的著重點,這種說法實際上混淆了收集何種證據與為何收集證據的界限。從圖1可以看出,審計風險與重大錯報風險及檢查風險并不是處于同一個層次上,將審計風險看成是收集審計證據的著重點,無助于揭示問題的實質。
再次,審計風險觀無法體現風險導向審計的本質。任何一種審計模式都是制定審計計劃、執行審計程序、收集審計證據,以提高發表正確審計意見或結論的可能性。換言之,任何一種審計模式都是為了降低發表錯誤的審計意見或得出錯誤的審計結論的可能性。盡管賬項導向審計與內控導向審計沒有明確提出審計風險的概念,但在降低發表錯誤的審計意見或得出錯誤的審計結論的可能性這一點上,它們與風險導向審計并無二致。審計風險概念及其模型的提出,只不過是使注冊會計師由被動接受審計風險變為主動控制審計風險。因此,審計風險觀無法使風險導向審計與其他審計模式明確區分開來。endprint
最后,審計風險觀無法有效地實現審計目標。審計風險并非審計中其他風險的源頭,無法成為風險導向審計的立足點。而且審計風險觀沒有強調風險評估是審計環節中必經的程序。根據審計風險模型,要使風險控制在可容忍水平,注冊會計師不妨通過調整審計風險要素中的一個或幾個來實現。如果按照傳統的風險模型,注冊會計師可不對固有風險進行評估,而直接將其確定為100%,轉而對控制風險進行評估,并以控制風險的評估來確定檢查風險水平,這實質上退回到了內控導向審計。事實上,內控導向審計的效率與效果均劣于風險導向審計,這也正是內控導向審計向風險導向審計演進的原因。
(二)訴訟風險觀評析
首先,訴訟風險觀將風險導向審計的“風險”視為訴訟風險,實際上是將風險導向審計性質定位為發現錯報、報告錯報和應對訴訟風險的一種審計方法。顯然,對風險導向審計的審計模式和自然屬性定位是矛盾的。
其次,訴訟風險觀與審計模式中“導向”一詞的含義相沖突。訴訟風險是審計業務風險的一種,它本身不是審計中其他風險的源頭,無法作為風險導向審計的起始點或基礎。
再次,訴訟風險觀無法體現風險導向審計的特征。從某種意義上講,訴訟風險是審計模式的一個外生變量,它更多地受客戶特點及社會法律環境等的影響。將訴訟風險作為風險導向審計中“風險”的含義,無法揭示風險導向審計的特征。
最后,訴訟風險觀無法有效地實現審計目標,以訴訟風險觀指導審計實務也是有害的,它會導致注冊會計師只關注訴訟風險而忽視發現重大錯報。
(三)重大錯報風險觀評析
重大錯報風險觀將重大錯報風險視為風險導向審計中的“風險”,實際上是將風險導向審計定位為發現重大錯報的方法,這與審計模式的性質并不矛盾,但重大錯報風險仍不是風險導向審計中“風險”的應有之意。
首先,盡管對重大錯報風險的評估是實施風險導向審計的核心,但“核心”并非“基礎”或“起始點”。從重大錯報風險的形成機理(圖2)可以看出,重大錯報風險本身是由其他風險決定的,并非審計中其他風險的源頭。在風險導向審計中,審計實施的全過程和關鍵點均與導致重大錯報風險的源頭有關。
其次,重大錯報風險觀無法體現風險導向審計的特征。在財務報表審計中,任何一種審計模式都是為了發現重大錯報,都將發現重大錯報作為審計工作的核心,而要發現重大錯報,當然離不開對重大錯報風險的評估。與其他審計模式不同的是,風險導向審計明確注冊會計師必須運用風險評估程序對導致重大錯報風險的各種因素進行了解和分析,在此基礎上評價重大錯報風險,而其他審計模式則沒有明確注冊會計師必須運用風險評估程序。因此,是否對重大錯報風險進行評估并非風險導向審計與其他模式的區別,重大錯報風險觀無法使風險導向審計與其他兩種模式明確區分開來。
最后,重大錯報風險觀無法有效地實現審計目標。重大錯報風險并非審計中風險的源頭,它本身是由導致重大錯報的因素決定的,離開了對導致重大錯報風險源頭的了解與分析,無法對重大錯報風險做系統的分析與評估,也就無法有效地實現審計目標。注冊會計師在審計中的視角對其審計判斷和審計行為具有重大影響。重大錯報風險觀容易使注冊會計在審計中采用簡化主義認知模式,將注冊會計師的視角引向會計視角,而非戰略系統視角,難以得出正確的審計結論。
(四)舞弊風險觀評析
舞弊風險觀將舞弊風險視為風險導向審計中的“風險”,實際上是將風險導向審計定位為發現重大錯報的方法,這與審計模式的性質并不矛盾,但舞弊風險仍不是風險導向審計中“風險”的應有之意。
首先,舞弊的出現通常與動機、機會、借口有關,未能有效控制的經營風險(剩余風險)給舞弊提供了動機。從圖2可以看出,舞弊風險本身是由經營風險等因素決定的,它并非審計中其他風險的源頭,無法成為風險導向審計的基礎。因此,舞弊風險觀與審計模式中“導向”一詞的真正含義相沖突。
其次,盡管審計目標幾經演變,但對舞弊的關注始終是審計目標的重要內容。發現舞弊是任何一種審計模式的重要內容。舞弊風險觀無法體現風險導向審計的特征,無法使風險導向審計與其他兩種模式區分開來。
最后,舞弊風險觀無法有效地實現審計目標。現代審計的目標是降低錯報風險,增強財務報表的可信性。舞弊只是導致重大錯報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錯誤也會導致重大錯報。由于企業經營過程中會出現非常規事項、會計信息生成過程中會存在會計估計、內部控制總會存在制約,以及各種心理啟發等導致錯誤的因素無法完全消除,也就不能完全消除可能的“錯誤”造成的重大錯報;同時,并非所有的舞弊都導致財務報表的重大錯報。因此,舞弊風險觀有以偏概全之嫌,以舞弊風險觀指導審計實務無法有效地實現審計目標。
五、風險導向審計中風險的應有之意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經營風險才是現代風險導向審計中“風險”的應有之意。
首先,以經營風險為導向與審計模式的性質不矛盾。風險導向審計正是透過經營風險分析,評價重大錯報風險,然后確定和執行審計財務報表程序,旨在發現財務報告中存在的重大錯報,因而是一種發現重大錯報的審計方法。
其次,以經營風險為導向與“導向”的含義不沖突。從圖1和圖2中可以看出,經營風險是審計中其他各種風險的源頭或基礎。在風險導向審計中,計劃審計工作的出發點、實施審計的突破點和收集審計證據的關鍵點均與經營風險相聯系。
再次,以經營風險為導向體現了風險導向審計的本質特征。審計模式的演變過程是審計重心逐步前移的過程,從以賬項為重心經以內部控制為重心到以經營風險為重心,正是審計重心前移的體現。
最后,以經營風險為導向能夠加強審計目標的實現。經營風險是重大錯報風險的根源,是審計中其他各種風險的基礎,識別經營風險是控制審計中其他風險的關鍵,以經營風險為導向展開審計工作,抓住了審計工作的“牛鼻子”;以經營風險為導向使風險評估程序自然而然地成為審計中的必經程序,為重大錯報風險的評估奠定良好的基礎,有利于正確評估重大錯報風險;以經營風險為導向有利于在審計中使用不同認知模式,將注冊會計師的視角引入戰略系統視角;以經營風險為導向,有利于在全面了解企業經營的基礎上,通過經營風險——控制風險——剩余風險的分析,形成對會計報表的合理預期。●
【主要參考文獻】
[1] (美)A.A .阿倫斯,等.當代審計學(上)[M].張杰明,文善恩,等,譯.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1:110-252.
[2] 蔡春,等.現代風險導向審計論[M].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6:2.
[3] 胡春元.風險基礎審計[M].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26.
[4] 劉明輝.審計與鑒證服務[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9.
[5] 唐建華.風險導向審計思想的歷史演進[J].審計研究,2009(2):79-83.
[6] 王廣明,沈輝.試論供給導向的風險基礎審計[J].會計研究,2001(12):51-54.
[7] 王澤霞.論風險導向審計發展創新——管理舞弊導向審計[J].會計研究,2004(12):49-54.
[8] 汪壽成,劉明輝.論經營風險分析的審計意義[J].中國注冊會計師,2007(10):69-72.
[9] 謝榮,吳建友.現代風險導向審計理論研究與實務發展[J].會計研究,2004(4):47-51.
[10] 張龍平,李長愛,鄧福賢.國際審計風險準則的最新發展及其啟示[J].會計研究,2004(12):76-81.
[11] Larry F. Konrath. Auditing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 A risk analysis Approach[M].West Info Access,1993:150 .
[12] W. R. Knechel. Auditing:Assurance &Risk[M].South Western College Publishing,2001:1,3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