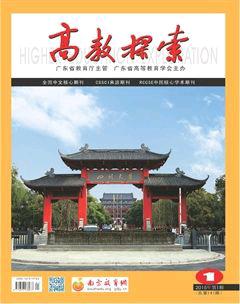粵港高校合作辦學(xué)的制約因素分析
王璐
摘要:雖然社會各界對粵港高校合作辦學(xué)的呼聲很高,但是兩地合作的具體實施卻進(jìn)行得異常艱難,多種因素制約著兩地教育合作的開展。歷史文化背景、社會意識形態(tài)和制度環(huán)境、資源稟賦、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差異性等背景因素在為粵港高校合作創(chuàng)造條件的同時,思想上的顧慮、政策上的缺位、體制上的差異、文化上的沖突、財力上的不濟(jì)、研究上的缺乏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制約著合作辦學(xué)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
關(guān)鍵詞: 廣東;香港;高校;合作辦學(xué);制約因素
香港高校的教育質(zhì)量在國際上享有盛譽(yù),自然也受到國人的推崇。2007年《北京考試報》在新浪考試頻道所做的“上大學(xué),報北大清華還是選香港高校”調(diào)查顯示,3100多人中65.48%的人認(rèn)為香港高校要好于北大、清華等內(nèi)地名校。香港高校先進(jìn)的教學(xué)理念(占45.17%)、全英語授課(占23.42%)、更容易出國深造(占12.91%)等都得到了調(diào)查對象的認(rèn)同。[1]同時數(shù)據(jù)還顯示,社會各界都非常支持和看好粵港兩地高校的合作辦學(xué),廣東的家長也非常渴盼能引進(jìn)香港優(yōu)質(zhì)的教育資源。香港中文大學(xué)副校長徐揚(yáng)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透漏,早在2006年夏,中文大學(xué)在提出深圳合作辦學(xué)方案的前后,曾在深圳乃至廣東地區(qū)經(jīng)過長時間的獨立調(diào)查,99.8%的受訪者認(rèn)為有必要合作辦學(xué),99%的受訪者認(rèn)為深圳要支持香港中文大學(xué)在深辦學(xué)。[2]調(diào)查還顯示,很多深圳家長(逾82%)愿意送子女到香港就讀大學(xué),并愿意每年為此承擔(dān)2-5萬元(31%的家庭),甚至10萬元以上(3.4%的家長)的費用。 [3]
雖然社會各界對粵港高校合作辦學(xué)的呼聲很高,但是兩地合作的具體實施卻進(jìn)行得異常艱難,多種因素制約著兩地教育合作的開展。歷史文化背景、社會意識形態(tài)和制度環(huán)境、資源稟賦、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差異性等背景因素在為粵港高校合作創(chuàng)造條件的同時,思想上的顧慮、政策上的缺位、體制上的差異、文化上的沖突、財力上的不濟(jì)、研究上的缺乏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制約著合作辦學(xué)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
一、思想上的顧慮
香港雖然一直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由于經(jīng)歷了100多年的殖民時期,有著與內(nèi)地截然不同的政治、經(jīng)濟(jì)與文化背景。而香港與內(nèi)地在文化及意識形態(tài)上的差異使得中央政府在處理內(nèi)地與香港之間的關(guān)系時非常謹(jǐn)慎,甚至有時顧慮重重,陷入“兩難”的境地,兩地高校在教育合作上也瞻前顧后,疑慮頗多。在兩地合作辦學(xué)中,參與各方思想上的顧慮在很大程度上阻礙香港與內(nèi)地教育合作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這正如Robert在歐洲國家跨境教育合作案例分析中所言,雖然在跨境教育合作中,政治不再粗暴地干涉教育合作,但總體上仍舊是教育合作的一個阻礙因素。[4]
維護(hù)國家統(tǒng)一和主權(quán)完整是一個國家和政府最根本的利益所在。建國后,中國政府一直將早日完成國家統(tǒng)一作為最重要的國家利益。為確保香港的順利回歸,中央政府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和平統(tǒng)一,一國兩制”的戰(zhàn)略方針,并在教育合作上作出一系列努力。如采取措施增強(qiáng)香港青年對祖國和中華民族的認(rèn)同感,以促進(jìn)香港主權(quán)和人心回歸的同步實現(xiàn);重視和支持香港學(xué)生到內(nèi)地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學(xué)習(xí),并多次調(diào)整收費標(biāo)準(zhǔn)及有關(guān)政策;支持內(nèi)地學(xué)生到港校深造,不斷擴(kuò)大香港高校到內(nèi)地招收學(xué)生的地區(qū)范圍與權(quán)限等。
但在高校合作辦學(xué)方面,中央政府卻一直沒有賦予香港高校“一國”之內(nèi)的國民待遇,而更多地出于“兩制”的考慮,僅賦予香港高校一定的優(yōu)惠和靈活。畢竟,高校在國家中的地位舉足輕重,是經(jīng)濟(jì)的發(fā)動機(jī)、文化傳統(tǒng)的保護(hù)者、個人潛能的開發(fā)者、公正的社會秩序的創(chuàng)造者、國家聲望的象征以及知識的源泉。教育主權(quán)的維護(hù)很大程度上是國家主權(quán)的維護(hù)。中央政府一直擔(dān)心國外(境外)教育機(jī)構(gòu)的獨立辦學(xué)會侵犯國家的主權(quán),并且此種擔(dān)憂由來已久。早在1949年建國之前,我國就不允許任何國外(境外)高校在國內(nèi)建立獨立的校園。2006年后,中央政府在目睹了地方中外合作辦學(xué)“泛濫”所帶來的各種亂象和教育質(zhì)量下滑后,對中外合作辦學(xué),包括境外合作辦學(xué)更是心存顧慮。但為了提高國內(nèi)大學(xué)的辦學(xué)水平,吸引優(yōu)秀的教育資源,滿足潛在的需求,加速中國國際化和激勵創(chuàng)新,中央政府仍舊積極支持合作辦學(xué),只不過審批更加謹(jǐn)慎,并且不允許國外(境外)高校到內(nèi)地獨立辦學(xué)。最新籌辦的香港中文大學(xué)(深圳)雖盡力爭取,但仍舊是以合作辦學(xué)的模式落地。
二、政策上的缺位
首先,中央政府下放給地方政府的權(quán)限和政策不足。當(dāng)前,從社會經(jīng)濟(jì)、文化的長遠(yuǎn)發(fā)展出發(fā),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視本地教育的發(fā)展。從自身人緣和地緣優(yōu)勢出發(fā),同境外名校的合作辦學(xué)也被政府視為提高本地區(qū)教育發(fā)展的重要選擇。《珠江三角洲地區(qū)改革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明確表示要“支持港澳名牌高校在珠江三角洲地區(qū)合作舉辦高等教育機(jī)構(gòu),放寬與境外機(jī)構(gòu)合作辦學(xué)權(quán)限,鼓勵開展全方位、寬領(lǐng)域、多形式的智力引進(jìn)和人才培養(yǎng)合作。”為提高自身辦學(xué)水平,廣東高校在政府的支持下紛紛做出“攬英才不差錢”的壯舉,而且廣東政府開放辦學(xué)“引進(jìn)來”的誠意與決心遠(yuǎn)不止于此,在“引才”之余,還向境外、海外名校“引制度”、“引模式”,追求“原汁原味”。事實上,廣東政府并不滿足于粵港高校間的合作辦學(xué),而是希望中央放權(quán)允許港校到粵獨立辦學(xué)。盡管近年來多方呼吁,且香港科技大學(xué)、香港大學(xué)、香港中文大學(xué)等院校已與深圳市政府簽署合作辦學(xué)備忘錄,并先后提出獨立辦學(xué)的意向,然而受相關(guān)法律制約,無法進(jìn)入實質(zhì)性操作階段。港校以合作辦學(xué)的方式落戶廣東也是無奈之舉。
其次,高校間合作已在積極開展,但地方配套政策尚未完善。粵港澳三地的高等教育一直有著交流與合作的傳統(tǒng),但原來的合作大都是禮節(jié)性(表層)的、局部(零星的)的、自生自滅(非制度化)的,很難形成綜合的、突破性的效應(yīng)。CEPA(《內(nèi)地與港澳關(guān)于建立更緊密經(jīng)貿(mào)關(guān)系安排》)的簽訂需要將大珠三角高等教育合作上升到深層的、全面的、長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制度化的層面。[5]《粵港澳合作協(xié)議》的簽訂更是使各界看到了粵港合作辦學(xué)的美好前景。但目前粵港兩地的教育合作同經(jīng)濟(jì)合作一樣,由于很多具體的措施仍未配套,都面臨著“大門開啟、小門未開”問題。比如港校的國民待遇身份、稅收、兩地教師的來往簽證等問題都亟待解決,廣東省政府加緊出臺相關(guān)政策勢在必行。相比之下,上海市早在 1993 年就已經(jīng)頒布了《上海市境外機(jī)構(gòu)和個人在滬合作辦學(xué)管理辦法》,粵滬兩地間合作辦學(xué)發(fā)展的差距自是必然。
再次,除了內(nèi)地要開放相應(yīng)政策外,香港也要打通關(guān)隘。深圳高等教育民間關(guān)注組成員金心異在呼吁中央允許港校到內(nèi)地獨立辦學(xué)的同時指出,香港方面也需解放思想,打通兩地教育資源的配置。他說:“如果完全是深圳政府掏錢辦分校,香港高校教育資源不能與深圳共享,這也限制了進(jìn)一步合作的可能性。”他認(rèn)為,目前深港在中小學(xué)教育資源配置上已經(jīng)有所突破,在高校合作方面也應(yīng)如此。[6]
三、體制上的不適
香港高校雖然有著享譽(yù)世界的辦學(xué)水平,但高校領(lǐng)導(dǎo)和教育主管者也對自身高等教育的發(fā)展前景憂心忡忡。他們認(rèn)為地域狹小、生源有限、高校林立都是限制港校發(fā)展的因素。讓香港高教界尤其擔(dān)心的是,如果不能依托內(nèi)地這個巨大的資源寶庫,不能參與到內(nèi)地經(jīng)濟(jì)與社會建設(shè),香港高校就有被邊緣化的危險。加之,粵港地域鄰近,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水平相差不大,廣東高等教育整體水平又有所欠缺,在合作辦學(xué)上港校有著“比較優(yōu)勢”,因此到粵辦學(xué)得到港校的青睞。
但就香港各大學(xué)而言,到粵辦學(xué)機(jī)遇與挑戰(zhàn)并存。由于擔(dān)心觀念和體制上的不適應(yīng),多數(shù)港校在合作辦學(xué)上很是猶豫。首先,香港實施校董會制度和“教授治校”,是一種學(xué)術(shù)內(nèi)行的自主管理,在專業(yè)設(shè)置、學(xué)位數(shù)額上也有著較大的自主權(quán)。而內(nèi)地高校管理體制的行政色彩較濃,高校辦學(xué)自主權(quán)難以全面落實。雙方在辦學(xué)體制和辦學(xué)理念上也存在一定差異。按教育部規(guī)定,香港高校在內(nèi)地辦學(xué)必須采用合作辦學(xué)的方式,這使得香港高校頗為頭痛。加之,港校在目睹了浸會大學(xué)與北京師范大學(xué)之合作由于觀念和體制的原因面臨重重困難時,紛紛表示沒有興趣到國內(nèi)合作辦學(xué),想獨立辦學(xué)。但目前粵港高等教育合作是在國家制定的《中外合作辦學(xué)條例》框架下進(jìn)行的,即使是項目合作也必須通過教育部的嚴(yán)格審查,難度較大,更不允許境外教育機(jī)構(gòu)單獨辦學(xué),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合作辦學(xué)的發(fā)展。
四、文化上的沖突
“文化距離”的概念是雷金·羅斯特琳那首先提出的。她認(rèn)為文化距離是母國與東道國之間那些一方面能夠創(chuàng)造知識需求,另一方面又阻礙知識流動,進(jìn)而導(dǎo)致阻礙其他方面資源流動的要素的總和。文化距離就是各國不同文化特征的差異程度。[7]“文化距離”和“心理距離”實質(zhì)上一致。[8]百年殖民史導(dǎo)致的粵港兩地的文化距離,甚至文化沖突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兩地合作辦學(xué)的發(fā)展。
當(dāng)代香港文化,是百多年來中華傳統(tǒng)文化同英國殖民主義文化相互碰撞、沖擊,又相互滲透、融合的產(chǎn)物,是中西文化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交融的多元混合體,是文化的多元并存,沒有一種文化明顯居于主導(dǎo)地位,不同文化影響社會生活的不同層面,互相之間存在一定的分隔。中上階層,如政府公務(wù)員、專業(yè)界人士、企業(yè)管理人員等,由于接受西方教育的時間較長,接觸西方文化及生活方式的機(jī)會較多,西方文化對他們的影響很深。對于社會中下層來說,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則較深。[9]
在粵港高校合作辦學(xué)中,港方合作人員主要是高校教師和管理人員,均為高級知識分子,這類人群都屬香港中上階層,都有國外留學(xué)背景,接受西方教育的時間長,重視“公平、自由、法治”等香港“核心價值”,西方文化深入其心,可以稱得上是西方文化的代表者。因此在粵港合作過程中,他們與內(nèi)地合作高校管理者之間出現(xiàn)的沖突,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中西文化沖突在某些方面的細(xì)化表現(xiàn)。整體上的文化差異可能會給合作帶來活力,但細(xì)化到管理技術(shù)和具體操作層面的文化差異和沖突卻會給合作帶來阻礙。從整體上來講,東西文化差異明顯,在日常合作辦學(xué)的過程中,就會表現(xiàn)為辦學(xué)理念、處事風(fēng)格、管理手段和方法的差異,以及港方辦學(xué)機(jī)構(gòu)對內(nèi)地管理體制和集權(quán)式管理方式的不適和抵觸,稍有輕視或者處理不當(dāng),就會嚴(yán)重影響兩地合作辦學(xué)的正常開展。
實際上,我們應(yīng)該清醒地認(rèn)識到,雖然香港文化與內(nèi)地文化有著諸多沖突,但不容置疑,香港文化的根仍然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主要是由儒家思想、東方宗教文化(主要是佛教和道教)和民間風(fēng)俗文化這三方面交錯融合而成,傳統(tǒng)文化深植于香港文化之中 。[10] 目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有著文化融合所需的強(qiáng)大的政治支柱;香港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中又日益擴(kuò)大了與內(nèi)地的密切合作與互惠互利,物質(zhì)基礎(chǔ)也與日俱增;加之,粵港同處嶺南,同講粵語,同屬共同的嶺南文化圈,文化的同根性更強(qiáng),因此發(fā)揚(yáng)文化之共性及同根性,多些溝通和了解,多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問題,化解沖突和矛盾并不是難為之事。
五、財力上的不濟(jì)
由于目前粵港合作辦學(xué)存在“大門剛啟、小門未開”問題,很多具體的措施仍未配套,比如港校的國民身份待遇、稅收問題、兩地教師的來往簽證等問題都未解決。一方面,粵港合作辦學(xué)機(jī)構(gòu)不僅享受不到內(nèi)地高校所有的免稅待遇,還要被征收一定的企業(yè)所得稅,負(fù)擔(dān)沉重。另一方面,香港由于不允許本地資金用于港土之外的投資,兩地教育資源的配置沒有打通,高校教育資源不能共享,完全由廣東省政府或者某一高校掏錢辦分校,必將限制合作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
粵港合作辦學(xué)機(jī)構(gòu)和項目的財政困境有目共睹。雖然合作機(jī)構(gòu)或項目的學(xué)費與國內(nèi)大學(xué)(一般每年是五六千元)相比,收取相對較高(珠海聯(lián)合國際學(xué)院的學(xué)費目前每年6萬多元,中山大學(xué)土木工程專業(yè)就讀費用按人民幣3萬/年收取),但如果真正按照香港高校的教學(xué)要求和質(zhì)量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專業(yè)建設(shè),別說是對于完全靠學(xué)費運作的珠海聯(lián)合國際學(xué)院,就是對于有著充足資金支持的中山大學(xué)來說恐怕也是不足夠的。正如聯(lián)合國際學(xué)院前常務(wù)副校長郭少棠所言:“雖然學(xué)費較高,但成本更高。”這點也可從中山大學(xué)粵港合作項目的開展中得到印證。訪談中得知,2006年中山大學(xué)除提供的公共設(shè)施之外,撥付應(yīng)用力學(xué)與工程系的34.6萬元用于教師課酬、學(xué)生學(xué)習(xí)輔導(dǎo)費、青年教師培訓(xùn)費等。由于合作辦學(xué)項目要求全英教學(xué),招聘教師按國際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門檻較高,但該院卻不能支付足以吸引高素質(zhì)人才的工資待遇,致使該學(xué)院開辦之初的3年內(nèi)僅成功招聘到一位固定編制教師。另外,學(xué)校雖然撥付20萬元的專項經(jīng)費用于專業(yè)實驗課程建設(shè),但有關(guān)專業(yè)實驗室的建設(shè)仍然沒能實現(xiàn)與香港大學(xué)設(shè)備體系的接軌。
六、研究上的缺乏
美國羅伯特·伯恩鮑姆認(rèn)為,在任何領(lǐng)域內(nèi)政策制定者與政策研究者之間都普遍存在隔閡。[11]研究人員認(rèn)為很多問題需要在充分研究的基礎(chǔ)上才能作出好的決策,而實際工作者卻認(rèn)為學(xué)者們的研究對他們沒有用。羅伯特認(rèn)為這一問題主要是由研究者和實際工作者所受到的教育培訓(xùn)、經(jīng)驗及觀察世界的方法的差異造成的。學(xué)者和實踐者兩者各自擁有自身的特質(zhì),而特質(zhì)之間又是互補(bǔ)的,如何實現(xiàn)兩者的融合呢?最好的方法莫過于兩種角色集于一體,即管理實踐者同時也是其實踐問題的研究者。
在中外合作辦學(xué)領(lǐng)域,管理實踐者同時又是研究者的實例雖然不多,但還是有的。上海就有很好的也是最成功的案例,市教委的歷代管理者中不乏學(xué)者。筆者通過對“中國期刊全文數(shù)據(jù)庫”中外合作辦學(xué)研究者的身份來源分析看出,廣東和上海省市級教育管理者參與實踐研究的情況有著很大差異。1997-2011年間,上海關(guān)于跨境教育的79項研究中有16項來自市教委及其下屬管理機(jī)構(gòu),如上海市教育評估院等,占研究總數(shù)的20%。2012-2014年間雖然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但168項研究中仍有20項來自市教委及其下屬管理機(jī)構(gòu),占研究總量的12%。這批研究者均是跨境教育工作的管理者,甚至是主抓該項工作的相關(guān)領(lǐng)導(dǎo),如張民選(原教委副主任)、王奇(教委副主任)、江彥橋(國際交流處處長)、李亞東(評估協(xié)會秘書長)等擁有教授身份、甚至博士研究生學(xué)歷,屬跨境教育研究的專家,擁有良好的科研能力和水平。學(xué)者的視野,加之身處上海所擁有的國際眼光使得他們深知研究對于實踐的巨大指導(dǎo)和推動作用。為了給本地跨境教育提供一個寬松、良好的政策環(huán)境,上海市教委成立課題組,多次到歐美國家進(jìn)行專題考察,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xùn),形成了一套可行的實施辦法,不僅為本地的合作辦學(xué)實踐提供指導(dǎo),還為兄弟省份提供了借鑒。也許正是這批擁有學(xué)者特質(zhì)的管理者才促成了上海市長期以來跨境教育的大發(fā)展。再看看廣東,1997-2014年間關(guān)于跨境教育的研究成果僅有1篇來自教育管理部門(深圳)。與上海相比,廣東在跨境教育發(fā)展及其研究上的差距不言而喻。
參考文獻(xiàn):
[1]孫巖.對香港高等教育的解讀[J].青年探索,2008(1):93-96.
[2]南都網(wǎng).用十年為深圳辦世界一流名校[EB/OL].http://gcontent.oeeee.com/91d7/9d7311b
a459f9e45/blog/f00/b49091.html.2010-09-03.
[3]鮑文娟.深圳擬引進(jìn)香港高校到當(dāng)?shù)鬲毩⑥k學(xué)[N].廣州日報,2009-08-04.
[4]Robert D. Osborne.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 Collaboration in Europe: Lessons for the“Two Irelands”? [J].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2006,41(1).
[5]陳昌貴,余群英.走進(jìn)大眾化[M].廣州:暨南大學(xué)出版社,2005.55.
[6]羅莎.港校來深辦學(xué)難在哪里?[N].南方日報,2010-09-15.
[7]覃玉榮.中國—東盟跨境民族文化產(chǎn)業(yè)發(fā)展與合作——基于文化距離的探究[J].廣西社會科學(xué),2012(11):168-171.
[8] Lee. D. J. The Effect of Cultural Distance on the Relation Exchange Between Exporters and Importers: the Case of Australian Exporters[J].Journal of Global Marketing,1998(11).
[9]黎熙元.香港:多種文化并存的社會[J].中山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1997(3):12-16.
[10]周毅之.從香港文化的發(fā)展歷程看香港文化與內(nèi)地文化的關(guān)系[J].廣東社會科學(xué),1997(2):18-22.
[11](美)羅伯特·伯恩鮑姆.大學(xué)運行模式——大學(xué)組織與領(lǐng)導(dǎo)的控制系統(tǒng)[M].別敦榮譯.青島:中國海洋大學(xué)出版社,2003.7.
(責(zé)任編輯鐘嘉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