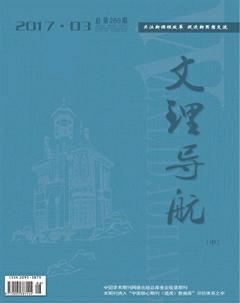談小學數學教學中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
李敏燕
【摘 要】數學思維能力的培養是小學高階段數學教學的重要任務之一,對小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有著重要的作用。所以要想提升數學課堂教學效率,教師就必須針對學生的思維能力進行培養,使學生養成良好的思維品質。
【關鍵詞】小學數學教學;培養;思維能力
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是現代學校教學的一項基本任務。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知識激增,知識的更新加快,隨之對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要提高年輕一代的素質。不僅要教給學生現代科學技術知識,而且要把學生培養成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創新的人,從而強調教學要注重發展學生的智力。從心理學角度來看,智力的核心是思維能力。思維能力增強了,智力水平也就提高了。
如何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促進學生思維的發展,是小學數學的重要任務之一。數學本身邏輯性較強,根據學科的這一特點,把數學知識作為培養學生邏輯思維能力的題材,寓思維訓練于教學之中,關鍵在于在教學中加強知識發展過程的教學,引導學生掌握獲得知識的思維全過程。那么,如何在小學數學教學中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接下來結合多年的實踐談談幾點看法:
一、新舊知識聯系,發展學生思維
數學知識具有嚴密的邏輯系統。就學生的學習過程來說,某些舊知識是新知識的基礎,新知識又是舊知識的引伸和發展,學生的認識活動也總是以已有的舊知識和經驗為前提。我每教一點新知識都盡可能復習有關的舊知識,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識來搭橋鋪路,引導學生運用知識遷移規律,在獲取新知識的過程中發展思維。
例如在教加減法各部分的關系時,我先復習了加法中各部分的名稱,然后引導學生從35+25=60中得出:60-25=35;60-35=25.通過比較,可以看出后兩算式的得數實際上分別是前一個算式中的加數,通過觀察、比較,讓學生自己總結出求加數的公式:一個加數=和-另一個加數。這樣引導學生通過溫故知新,將新知識納入原來的知識系統中,豐富了知識,開闊了視野,思維也得到了發展。
二、善于捕捉靈感,學會舉一反三
靈感是一種思維能力,是在不斷實踐和積累知識的基礎上,瞬間產生的一種創造性的思路,是一種質的飛躍,它的產生往往伴隨著突破和創新,在教學實踐中,教師要有意識的捕捉學生學習中出現的靈感,鼓勵學生大膽想象,對于有創意的想法,教師要及時給予肯定,同時,還要變換角度或者通過對比等方法去引導學生的數學靈感,讓學生感受到解題的挑戰和樂趣,并能舉一反三,不斷進行對比和聯系,形成觸類旁通的能力,全面靈活的運用數學技能,越過常規邏輯去找出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
比如這道題“將下列分數3/5、7/8、1/9、2/3按從小到大的順序排列”,從題中可以看出,如果按照傳統的思維模式,將個分數的分母進行通分比較,則顯得比較麻煩,因此,在教學中,教師不妨引導學生另辟蹊徑,從同分子分數的角度出發,將這幾個分數化簡為具有相同分子的形式,然后再進行判斷。在教師的引導下,學生們會煥然大悟,找出了更加簡便的比較方法,同時,還培養了學生創新意識。
三、教師創設情境,激活思維動機
愛因斯坦曾經說過:“教育應該使提供的東西,讓學生作為一種寶貴的禮物來享受,而不是作為一種艱苦的任務要他負擔。”教學中,教師應巧妙地創設問題情境,讓學生產生迫不及待地要獲取新知的積極情感,激活學生的數學思維。任何缺乏情感的教學活動,非但不能促使學生積極主動地學習,反而會導致學生厭學。
有這樣一道題,讓學生討論:一個長方形,長減少一米,寬增加一米,它的面積和周長會發生怎樣的變化?這一提問,使學生對問題本身發生了極大的興趣,大家憑感性回答,答案不一,且都不能講清道理。學生都迫切想知道正確答案,抓住這啟迪思維的最好時機,讓學生舉例說明。在學生講明道理后,進一步提問:“如果你按照這樣的變化去思索,能發現什么規律?”這時學生興趣更高,經過小組討論探求,很快說出結論:在周長相等的情況下,長與寬越接近,面積越大;長與寬相等時,面積最大;周長相等的長方形和正方形,正方形面積較大。由于我不斷設置問題情境,引疑誘導,整個學習過程中,學生情緒高漲,思維潛力得到深層開發,感覺自己的聰明智慧,體驗到成功的快樂,從而更積極主動地探求知識,與此同時,思維的深刻性也就得到了培養。
四、精心設計課尾,調動學生思維
課堂教學的結束階段是整個課堂教學過程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是將知識系統化、條理化、網絡化,從而加深對知識的理解,減輕記憶負擔的重要環節。精心設計的課尾,對進一步發展學生的數學思維和創造能力具有巨大的作用。因此,在教學中要求教師注重課尾的設計,巧妙借助課尾的教學設計活動,或前后響應、或設置懸念、或辨析比較、或進行活動游戲,帶領學生再掀創造思維的高潮。
例如:在教學“約數和倍數”的課尾,教師對學生從容地說:“同學們,快要下課了,我們一起來做一個游戲,好不好?”(學生齊答“好!”)“這個游戲的名叫‘動腦筋離課堂。游戲的規則是這樣的:老師出示一張卡片,如果你的學號卡片上的數是它的倍數,你就可離開教室。走的時候必須先到講臺前,大聲說一句話,再走出教室。你說的一句話,可以是‘幾是幾的倍數、幾是幾的約數或‘幾能被幾整除其中的任意一句。”通過精心設計的課尾活動,學生鞏固了知識,教師檢查了學習效果,還能幫助學生糾正錯誤和提供個別輔導,發揮了學生的創造性,達到一舉多得。如此設計課尾,學生已不僅僅停留于快樂思維狀態,而是進入真正思考的創造境界。
總之,在教學過程中培養和發展學生思維能力是教師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數學教師根據數學學科的特點,因材施教,使學生對數學產生興趣后主動思考積極思維。學生學的生動活潑。學生思維能力的提高,也是學生素質健康發展的體現。
【參考文獻】
[1]王志紅.在小學數學教學中培養學生思維能力方法初探.《教育實踐與研究》,2009(1)
[2]包錦學.如何在小學數學教學中培養學生思維能力.《都市家教月刊》,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