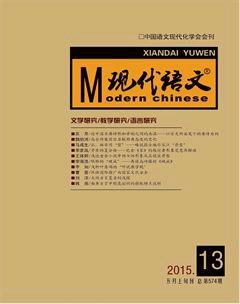新歷史語境下的“中國形象”解讀
摘 要:新歷史語境下對歷史的書寫已跳脫出意識形態局限,轉而從更宏闊的視野中去把握歷史。在這種把握和審視中,不僅有“中國”這個所謂的“自我”,“西方”這一“他者”也已融入其中,并成為作家反思歷史的重要參照。相應地,現代性也就成為作家撫觸、反思歷史時無法避開的一大命題。換言之,作家對歷史的重述始終伴隨著對我國現代化進程的主動思索,而且回望歷史有時就是為了更好地思索我國未來的現代化之路。
關鍵詞:新歷史語境 “中國形象” 《古船》 現代中國 思考
歷史需要書寫,而回望和書寫的方式卻不盡相同。
對中國近現代史尤其是革命歷史的書寫,除了革命歷史題材小說那種“在既定的意識形態規限內,講述既定的歷史題材,以達成既定的意識形態目的”[1]的敘寫方式以外,上世紀80年代還興起了一種以“第三視角”[2]來敘寫歷史的創作動向。這種所謂的“第三視角”既不著力于頌揚共產黨人的奮戰抗敵,也較少正面肯定國民黨在抗戰中的作用和貢獻,而多以平凡人物,尤其是平凡的小人物為描寫對象,講述置身歷史大潮中的平凡人那種近乎本能的反抗和應征,陳忠實《白鹿原》、張煒《古船》便屬此類作品,莫言的《紅高粱》更是以土匪“余占鰲”作為作品中心人物。本文據以展開討論的新歷史語境就主要是從歷史敘述角度而言的。角度不同,透過視角所濾得的影像相應也就存在天壤之別。
如果說,50-70年代那些在既定意識形態規限內講述“歷史”的作品旨在“為新的社會、新的政權的真理性做出證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動對歷史既定敘述的合法化”[3],那么對這一視角的偏離甚至回避則意味著作家思維重心的移位,表明他們已經跳脫意識形態局限,轉而從更宏闊的視野中去把握歷史。在這種把握和審視中,不僅有“中國”這個所謂的“自我”,“西方”這一“他者”也已融入其中,并成為作家反思歷史的重要參照,相應地,現代性也就成為作家撫觸、反思歷史時無法避開的一大命題。換言之,作家對歷史的重述始終伴隨著對我國現代化進程的主動思索,而且回望歷史有時就是為了更好地思索我國未來的現代化之路。如果說政治意識形態引領下的宏大敘事主要論證了新生政權的合法性,向世人展示了一個充滿活力的新政權形象,那么新歷史視野下的國家形象又是怎樣的呢?或者說,這類作品又塑造了怎樣的國家形象呢?
一
為便于討論,本文擬以作品《古船》為例做具體討論。
作品《古船》講述了洼貍鎮人長達半個世紀的苦難歷史,中華民族曾經所遭遇的土地改革、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災難都悉數在洼貍鎮上演。對于抗風險能力趨于零的洼貍鎮百姓而言,每一次微小的生存挑戰都是一種不堪回首的苦難經歷,在忍耐、硬抗這些不是辦法的辦法中,他們艱難地捱過了一個又一個春秋。
作品主人公隋抱樸是作家精心塑造的一位苦難親歷者代表。幼年時期的他,曾親眼目睹過用一根鐵絲串起四十二人的肩胛骨,見過年輕小伙子被扔進火堆活活燒死,見過地主女兒因為父親逃跑而被無辜打死,打死后被剝光衣服吊在樹上,同時陰部還被插上胡蘿卜;如果這些尚不足以震撼抱樸,那么抱樸自己及整個隋家的遭遇足以令其徹底讀懂苦難的涵義。土改時兄妹三人一次次地被調查;妹妹含章被趙家“德高望重”的長者趙炳蹂躪;家族產業粉絲制造廠被仇人趙多多奪去;后母茴子的死對抱樸的觸動更是毀滅性的,母親斷氣后還被趙多多撕得赤身裸體,并從頭到腳被撒滿尿……目睹了這些慘絕人寰的悲劇事件,抱樸沒有進行冤有頭債有主的追討,但內心卻留下了永久的裂痕,這從他對感情生活的態度中便可見出。抱樸一生中接觸的女性有三個:桂桂、小葵、鬧鬧,作品集中描寫了抱樸與小葵間的愛情,一個在生活面前似乎毫無生氣的木頭人,也曾在一個雷電交加的夜晚爬窗戶與小葵私會,但他的行動也僅此而已,并未再前進一步。等待多年未果后,小葵嫁給了跛四,得知小葵嫁人消息的抱樸痛不欲生,但也僅僅將這種悲傷深深刻在心底,并未從行動上去挽回。他絕望地說,“老隋家的這一輩兒人可以有愛情,但不可以有婚姻。”[4](P60-61)這是抱樸為隋家人念的咒兒,也是對自己的愛情、婚姻的一種定位。可想而知,這種意念支撐下的愛情、婚姻不可能完滿。
盡管對自己的人生毫無期望,但傳統宗法觀念教他懂得對家族、對洼貍鎮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隋家的起起伏伏、洼貍鎮的聲望、盛衰時時牽動著他的心。當家族利益的實現要以犧牲洼貍鎮人的利益為代價時,他會堅決地站在道義立場選擇保全洼貍鎮,這從弟弟見素同他商量奪回洼貍粉絲大廠的談話中便可看出。見素覺得粉絲大廠應該姓隋,因為洼貍鎮的粉絲制造業是隋家祖輩人做起來的,所以它理應歸老隋家后人來經營,而現在卻落入仇家趙多多手里。對于這個問題,抱樸說:“它誰的也不是。它是洼貍鎮的。”[4](P39)不僅言語上,行動上抱樸也是這樣做的,作為洼貍鎮公認的粉絲制作手藝最精湛的人,他沒有與趙多多爭奪粉絲大廠所有權,而是甘心呆在磨房里做著機械性的加料工作,每次“倒缸”時,作為洼貍鎮唯一可以讓粉絲起死回生的人,他都竭力救場,替粉絲廠挽回損失。按理說,憑借著精湛的粉絲制作技術,他完全可以置趙多多于死地,從而輕松奪回粉絲廠,但是,看過太多災難的他不愿讓洼貍鎮人再次經受苦難,它覺得洼貍鎮人經受的苦難已經夠多了。隋抱樸內心這種強烈的人道主義情懷使得這一形象充滿人性光輝。
但是,人道主義不是一味容忍主義。在改革開放的總背景下,商品經濟全面發展起來,趙多多學會了偷工減料,以次充好。對于這種現象,隋抱樸內心充滿了自責,從父輩身上遺傳下來的強烈的懺悔意識使得他覺得自己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覺得對不起洼貍鎮人。此時的他才將趙多多置于自己的對立面來與之對抗。最后,在粉絲廠面臨破產之時,他毅然決然地擔任了粉絲加工廠的總經理,并開始控訴趙多多等人的罪行。一個活的隋抱樸終于站起來了。
有人曾說,“張煒筆下的人物,一方面俗緣太深,苦痛連連;另一方面,這些人中間真正稱得上優秀的分子,又有一種不屈的天性,暗中指引他們經常走出人群的渾濁和喧囂。”[5]本文以為,用這句話評價隋抱樸這一形象倒十分恰切。
二
關于隋抱樸這個形象,有研究者認為其可貴之處在于其艱難的蛻變和探求過程上。在這種蛻變和探求中蘊含了深邃的歷史和文化反思,“通過他的變化,揭示現實的改革、開放生活對人性的再造,對于人格的增值,對于黑暗的邪惡勢力的致命打擊,對于一切美好、善良、正直、以至于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切新生的積極因素的催發。”[6]所以,研究者發出這樣的感慨,“沒有現實的改革,開放,可以肯定,不但沒有《古船》這樣的巨構,就連抱樸一類人物,也必將永生永世蹲在那個磨道里。”[7]
本文十分贊同論者的看法,抱樸的內心蛻變是外在社會情勢變遷的結果,也可以說,抱樸個人內心的掙扎與成長映現了我國普通百姓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心靈成長史,折射出我國社會生活領域曾經發生的劇烈甚而致命性的各種變遷。不可否認,這些社會領域的變化曾經為百姓帶來了種種傷害,有時甚至是流血犧牲。但是,如果沒有曾經這一次次摻雜著血與淚的嘗試,很難預料,我們的國家、人民還要在黑暗中前行多久。當然,歷史沒有假設。而且很慶幸,經過三十多年的摸索,我們終于找到了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并成功進入了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的新時期。
另外,抱樸這一形象的意義還在于它象征著中華民族自近代以來所遇到的一切。可以說,他是中華民族的一個縮影和典型代表。自西方這一強勢“他者”的到來打開國門的那一刻起,我們就艱難地走上了現代化之路。然而,幾千年因襲的封建痼疾不可能因為外來者的進入而自行痊愈,相反,有了他者的牽引和比照,我們民族身上的問題才顯得愈發明顯和亟需治愈。通過小說我們讀到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宗族觀念十分明顯。與西方對自由、獨立之現代個體的追求相反,人們內心的宗族觀念仍然十分強烈,小說開頭曾描寫過一個地震場景,當時人們為避開余震來到空地,隋不召環視空地后發現,“差不多都是同一族人湊在一塊兒,哪里人密集,哪里就會是一個家族。隋、趙、李分成了三大攤兒,老老少少都聚在一塊兒。也沒有人召集他們,這完全是地皮的力量。”[4](P10)這種不約而同而近乎本能的宗法力量仍然在無形中鉗制著人們的思維,成為中國發展前進中的摩擦力。這種觀念在抱樸的弟弟隋見素身上也相當明顯,它一輩子處心積慮想要做的就是打倒趙多多,奪回粉絲大廠,原因在于祖輩發展起來的事業絕對不能落到外姓人手里。這種宗族觀念既不利于現代獨立個體之養成,也于商品經濟發展無益,因而在現代社會的發展中,這也許是我們需要反思的重要一點。第二,小農思想嚴重。從普通百姓的角度看,對于現代工商業是持抗拒態度的,文中反復出現的對粉絲作坊的回憶就承載著敘述者對傳統社會小農經濟的留戀。總之,我國要實現真正的自由、平等、獨立,要走向富強、文明,還需要革新舊有思想觀念,重樹民族之魂。
三
最后一個值得我們討論的問題是,以新歷史視角創作完成的《古船》,建構了怎樣的國家形象呢?
正如名稱所表明的,這部小說探討了一艘古老的船舶如何重新駛向大海,走向世界的問題,易言之,我們這個曾經揚帆遠航、英姿颯爽的古老東方大國該如何定位自己并重新加入世界行列呢?關于這個問題,先知們已經思考了一個多世紀,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在思索著。小說對國家形象的建構主要是通過以下幾個意象隱喻出來的:《海道針經》《共產黨宣言》《天問》古城墻。《海道針經》是一本航海指南,船舶的航向是依據它來做出判斷的,由此可見其重要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伴隨蘆青河河道的逐年變窄,古船失去了賴以出航的水域,無水之舟何談航行之法,所以,對于正在崛起的中華民族而言,指導其前行的指路明燈必不可缺,但有些不再合時宜的主張、準則也是需要根據具體情況作具體取舍的。古城墻之“古”顯而易見代表了頑固守舊的舊事物,是嚴重阻礙中國前行的守舊力量,需要適時清除來為發展掃清障礙。《天問》代表了掌舵人的迷茫,像中國這樣一艘超級巨輪到底該駛往何處,每一次的追問都代表著有識之士對中國未來的主動思索。《共產黨宣言》這個比較容易理解,是指導當代中國前行的必備寶典,當然,每個國家的具體國情不同,對宣言的解讀和操作方式也會不同。在抱樸看來,這是一部“過生活”的書,當然,我們不能把過生活當成個人的事情,那樣為了自己就會去拼命,結果又會給洼貍鎮人帶來災難。這是以全局為重,以全中國百姓為對象所思考的一種過生活的方法。總之,他以最素樸的方式理解著馬克思主義中關于人性、人道主義等核心價值和信條,比照國家發展階段來思索祖國未來發展之路。
總而言之,小說《古船》所展現的是一種正在崛起中的國家形象。雖然不乏封建頑固勢力的阻擾,雖然中國傳統文化中精華與糟粕同在,但是,傳統文化孕養下的仁慈、善良也正是我們走向現代化,尤其是經濟現代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寶貴品質。
拋開宏大敘事的新歷史主義視角,講述歷史時雖少了正史的那種嚴肅與宏闊,但卻更加真實而生動。
注釋:
[1]鄭萬鵬:《當代中國文學的第三視角——<白鹿原>、<紅高粱>的思潮意義》,中國文化報,2012年12月18日。
[2]黃子平:《革命·歷史·小說》,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頁。
[3]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大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頁。
[4]張煒:《古船》,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
[5]郜元寶:《“意識形態”與“大地”的二元轉化——略說張煒的<古船>和<九月寓言>》,社會科學,1994年,第7期,第69頁。
[6][7]丁彭:《論隋抱樸——兼與黎輝曹增瑜同志商榷》,小說評論,1988年,第1期,第79頁。
(李營營 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 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