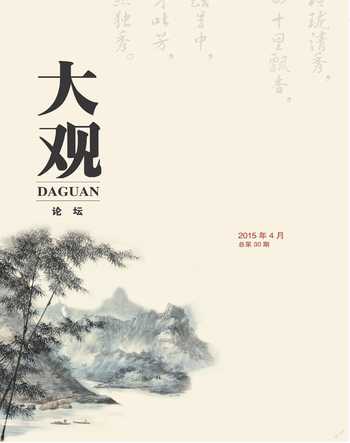從《文心雕龍》“神思篇”淺談文學創作
和曉祎
摘要:人類是有情感的動物。也許貓狗等動物也有感情,可它們永遠學不會思考——而人類正是因為懂得思考,才能對一切客觀的事物賦予自己獨特的情感,建起屬于自己的一片文學天空。《文心雕龍》中的“神思”,談的就是關于人們文學創作時的思維活動。
關鍵詞:靈感;神思;文學創作;情感體驗
日本著名私小說作家芥川龍之介在其短篇小說《戲作三昧》中寫過這么一句話:“靈感跟火毫無二致,不懂得籠火,即使點燃了也會立即熄滅的……”說的就是人們靈感閃現時,如果能保持“虛靜”狀態,頭腦清醒、精神貫注,接著產生“思理為妙,神與物游”①的感受,用自己的意志控制住滾滾而來的“靈感”,言語才能流匯成文章。古代教育學者韓愈在《答李翊書》中也有“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來矣。”②的話語。
“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字制體,大小殊功。”③劉勰指出,有些人寫文章寫得快且好;有些人寫得好但很慢,是由于個人的天分不同或文章體制不同造成的。雖然有作者的自身原因,但更重要的是“難易雖殊,并資博練”④。有時創作者創作文學作品,常會遇到瓶頸不知如何下手,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平日的經驗不夠豐富以及素材貧乏所造成。故只有“書讀百遍”才能“其義自見”,做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韓愈同樣提出了類似的說法,即“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⑤這里的“氣”有人說指的是“道德”,筆者不以為然。
誠然,先秦時孟子提出的“氣”是指自我修養達到一種較高的精神境界,也就是個人的道德修養;但到魏晉時期,曹丕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著名論斷,他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⑥這里他把“氣”引入創作批評之中。但他這里的“氣”,基本上是就作品所體現的創作主體個性而言的。于是韓愈所說的“氣”應當是二者的有機結合與發展——作為一個創作者,的確是需要有很高的道德修養,他的言論才能夠讓世人信服;而且需要飽讀詩書,具很高的文化素養,正如我們現在所講的“氣場”一般,作者的寫作風格是能夠被讀者所感受到的。不然像學問淺陋的只是寫得慢的人,才疏學淺光靠寫的快的人——這些類型人在寫作上無法有所成就。
韓愈在《答李翊書》中還提到,他剛開始寫作是“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⑦何言“譽之則以為憂”?因為文章若是被人贊美的話就說明還是存在著很多世人的觀點。再后來,“然后浩乎其沛然矣”,最終他進入創作“沉思”狀態,于是從相反方向對文章提出詰難、挑剔,平心靜氣地考察它,直到辭義都純正了,后才放手去寫——也就是一個文章的修改過程。韓愈雖主張學古即“文以載道”,但他并沒有抹殺“文”的“個性”。“學古”,正是為了反對六朝以來的千篇一律的駢儷文風;“載道”,正是為了傳達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志。而按劉勰的說法,韓愈的文章才是真正做到了“風骨”——“唯藻耀而高翔,故文筆之鳴鳳也。”⑧
劉勰認為,“風”是作品藝術感染力的根源,作者情志氣質的外在表現,要是遣詞造句正直挺拔,那么文章的骨力自然就形成了;意氣俊發爽朗,文章的風貌就清朗了。“情采”和“風骨”二者可謂相輔相成、相互影響。新銳小說作家郭敬明當下可謂如日中天,但作為一名男性,那綿軟如“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文筆,遣詞造句纏綿悱惻,時常用一些“嬌喘”、“呻吟”之類的與自己形象不符的辭藻,實在沒有所謂的“風骨”,好似患了軟骨病的人,永遠只能癱在床上,嗅不到一絲活力與生機。而在當下這個“娘化”了的時代,男女之間的界限仿佛越來越模糊,因此早已分不出什么“婉約”還是“豪放”,逐漸趨于中和的狀態。
文章的“骨架”就如人類的骨骼一樣永遠必不可少。文學作品的內容不能只為尋求新鮮的寫作手法而故意“制造”情感。文學創作是站在人的生命體驗與審美感受以及對社會生活給予人文關懷的立場上的,它對客體世界的認識、感悟與表現,都帶有濃厚的主體性或主觀性。所以,創作者不能只是為了氣勢的宏偉或是篇章的華美而去堆砌一些華而不實的辭藻。“賦”這種太過于重視格式和形容詞的文章現在逐漸衰亡的原因也正由于其自身對“情感”的不重視:情感是需要自然流露的,而不是嵌入條條框框。誠如劉勰言:“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既形,英華乃贍。吳錦好渝,舜英徒艷。繁采寡情,味之必厭。”⑨為何《詩經》久盛不衰,就因質樸而真切抒發情感的文章最能夠深得人心。
當主體在觀察一件事物的時候,已經在不可避免地改變著這個觀察對象了;即是說,讀者閱讀某個文本,也就改變著這個文本。“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樣的“誤讀”在文學中司空見慣。不僅是讀者誤讀,作者在寫作時也并非完全明白自己的創作意圖,由于作者在創作作品之前和之后都不處于“創作狀態”,因此無法斷言自己的作品是否還會具有未知的外延空間。
文學創作其實與一個著名物理概念“薛定諤之貓”很相似——貓的生死是打開盒子前的“客觀存在”,又決定于打開盒子后的“觀察”,這種觀察不是發現,而是決定。正像哈姆雷特所說:“是死,還是活,這可真是一個問題。”作者在進行文學創作時也是同樣狀態:“靈感”出現在作者腦海里,一旦形成文本,發表之后,其他可能性不復存在。這只“貓”在作者進行創作的過程中是存在著無數可能性的,或許是死,或許是活,又或許是半死不活的狀態…因此不但對作者來說是個“打開箱子的過程”,對讀者來說更是個開箱的“結果”,每個人打開箱子的方式不同,則造成結果不同。所以,文學創作和閱讀中都存在著無限的可能性,而結果怎樣,就要看創作者和接受者究竟如何運用它。
【注釋】
[1]①③④⑧⑨ 劉勰:《文心雕龍》,2008出版。
[2]②⑤⑦韓愈:《答李翊書》
[3]⑥曹丕:《典論·論文》
【參考文獻】
[1]劉勰.文心雕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朱立元.美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3][日]芥川龍之介.羅生門[M].江蘇:譯林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