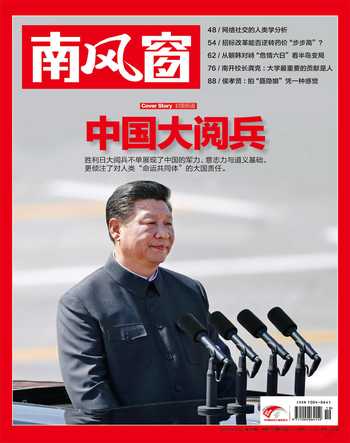不要叫醒那個裝睡的人
韋星
今年8月,是我第二次深入接觸城管這個群體。第一次是在去年5月。此前多年,我對城管有深刻偏見。每當看到城管打人的視頻,我會轉發,并附上憤怒的評價和嘲諷。那時,我感覺城管存在的“價值”,就是不斷砸掉底層人的飯碗。后來,和底層人接觸多了,和城管接觸多了,我逐漸修正自己的看法。
率先改變我傳統偏見的,是一個叫任騫的小伙子。他是個80后,在進入城管系統以前,是一名選調生。任騫是武漢市江岸區城管委的一名執法人員。去年采訪時,認識了他。他也是《南風窗》的讀者,對《南風窗》不盲從、保持理性、克制的公允觀點,很是贊賞。有了好感之后,彼此也有了深入交流的欲望。
有干勁,而且為人實誠的任騫,給了我很深的印象。他進入城管工作,多少帶有年輕人的沖動和理想主義—他想著通過自身努力,改變別人對城管的看法。在第一次跟隨隊伍執法時,任騫小心謹慎、默不作聲地跟在后面。第一次暫扣小販的東西,他于心不忍。因為小販在城管面前不斷哀求說,“自己不知道這里不能擺,是第一次到這里來擺的”,“謀生不易,希望放我們一馬”……這次執法讓任騫內心很震撼,也很矛盾:城管怎么這樣?

后來,接觸的小販多了,任騫明白了怎么回事,也慢慢融入城管,并真正成為這個群體中的一員。如今的他,每天都重復著和前輩們一樣的事情。“城市不需要管理嗎?除了教育、暫扣,還有更好的辦法吧?”任騫的疑問,也是一個群體的困惑。
后來,他也會對小販的哀求麻木,因為面對城管執法,小販大都說謊。比如“第一次到這里街道擺賣”,事實上,他們每天都來。當不斷勸離都無效時,才是暫扣物品。
可處罰沒帶來多大效果,因為小販生意的利潤也不低。較高的利潤,使得小販將這些好消息,不斷傳給家鄉的親戚。因此,街頭的小販宗族化傾向十分明顯。為搶到好地段,霸到好位置,他們甚至聯合起來對抗另一撥小販。一切都變得殘酷,“底層”相互傾軋的新聞,也因此從不缺席。
沖突發生時,一個人,特別是媒體,是應該有底層情懷,但不能被情緒綁架。所有立場,應是居于客觀事實之上。比如一個人違法了,就應該按照法律來辦,法律如何規定就如何施行,不能因為他的身份而影響判決。但在今天,更多的是拒絕談論是非,只求互相站隊,并在情緒上大肆渲染。
我已過了容易激動的年齡,但主要是隨著采訪深入,我越來越發現:讓我極度反感和憤怒的事件,很少了。
不是因為我麻木,而是對同類題材和階層深入接觸之后,我能更好地去理解人,理解事件發生的背景,以及可能被潛藏的真相。所以,我不追逐熱點,不再就熱點事件發表武斷性的結論。因為真相往往在拐角處,我不想再度自我打臉。
真的,偏見往往源于無知。比如臨時工的話題,以前,一旦城管和小販有沖突,官方總說對方是“臨時工”。對此,我堅決反對強調對方是臨時工的身份,因為不管是什么身份,錯了就是錯了。
但很多人關注的焦點是:對方究竟是不是臨時工?一開始,我也認為,官方是在找臨時工頂罪,后來發現真的是臨時工。
因為城市化過程中,涌現出很多行業,分工也在細化,需要管理的領域在增多。比如城管,上世紀80年代以前,商品經濟落后,幾乎沒有什么小販。隨著商品經濟發達,進城務工潮涌動,出現大量小販,城管才應運而生。可城管編制遠遠不夠。以武漢市江岸區城管委直屬一中隊為例,包括領導都得上路執法。此外,還得聘請150多個協管員幫忙干活,否則根本管不過來。在廣州,全市城管執法人員3000多人,但協管員的人數,要在此基礎上,再翻倍。
既然臨時工的比例多,遑論素質等因素,他們發生問題的概率,也會更多一些。但人們不愿意相信這些,他們也不想管這些,他們只認為:在事件沖突發生后,只有憤怒批判體制,批判公權力,才是“熱血好男兒”,才是占據道德最高地,才是代表正義的一方。這種人,也是在“裝睡”。
可是,憤怒地打掉一切再重來,我們的社會就會變好嗎?無知可以原諒,但裝睡的那個人,怎么叫,都是喚不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