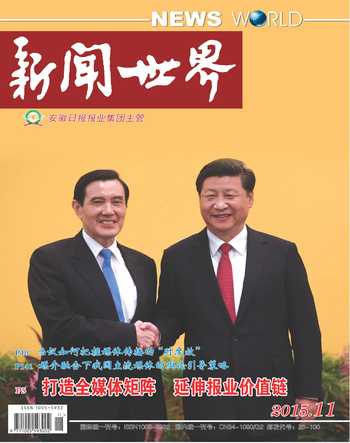簡(jiǎn)析《新聞學(xué)》對(duì)報(bào)紙代表輿論與創(chuàng)造輿論的論述
焦建
【摘要】徐寶璜先生的《新聞學(xué)》一書堪稱中國(guó)新聞傳播領(lǐng)域的經(jīng)典著作。本文通過回顧《新聞學(xué)》一書的成書過程與主要貢獻(xiàn),重點(diǎn)分析了其“報(bào)紙代表輿論”與“報(bào)紙創(chuàng)造輿論”的觀點(diǎn),認(rèn)為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民眾的意見表達(dá)渠道得以拓寬,報(bào)紙代表輿論的功能有所減弱,但信息過載的情形使報(bào)紙創(chuàng)造輿論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關(guān)鍵詞】徐寶璜 新聞學(xué) 互聯(lián)網(wǎng) 輿論
一、徐寶璜新聞思想的源頭
徐寶璜先生是中國(guó)著名的報(bào)刊新聞工作者、新聞學(xué)者、新聞學(xué)教育家,其新聞思想涉及新聞理論、新聞實(shí)踐、新聞事業(yè)的經(jīng)營(yíng)管理等多個(gè)方面。徐寶璜撰寫的《新聞學(xué)》一書,包含了其主要的新聞思想,在中國(guó)新聞教育和學(xué)術(shù)史上占據(jù)著極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國(guó)新聞傳播學(xué)領(lǐng)域的經(jīng)典著作。
1912年,北京大學(xué)畢業(yè)后,徐寶璜官費(fèi)留學(xué)美國(guó),進(jìn)入紐約州立林業(yè)工程學(xué)院學(xué)習(xí),1914年轉(zhuǎn)入密歇根大學(xué)繼續(xù)學(xué)習(xí)。在密歇根大學(xué)學(xué)習(xí)期間,徐寶璜曾選修過一門叫做“基礎(chǔ)報(bào)紙寫作”的暑期課程,對(duì)密大同期的其它新聞?wù)n程及學(xué)校當(dāng)時(shí)主要的新聞教育項(xiàng)目也有所了解。他親身體驗(yàn)到在美國(guó),新聞已成為大學(xué)中的一種專門科目,大學(xué)開始承擔(dān)起培養(yǎng)報(bào)紙工作者的任務(wù)。他把這樣的認(rèn)識(shí)、理念和新聞教育比較具體的形式和內(nèi)容都帶回了中國(guó),帶入了北大;在種種因緣際會(huì)之下,開啟了中國(guó)新聞教育和新聞學(xué)研究的新篇。
二、《新聞學(xué)》的成書過程與再版情況
1916年,徐寶璜學(xué)成歸國(guó)后,先任北京《晨報(bào)》編輯,繼任北京大學(xué)教授兼校長(zhǎng)室秘書。
徐寶璜《新聞學(xué)》一書的成書過程較為復(fù)雜,1918年9月到11月,《東方雜志》刊載了先生的第一稿,暫以《新聞學(xué)大意》為題名;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學(xué)新聞研究會(huì)召開成立大會(huì),徐寶璜以《新聞紙之職務(wù)及盡職之方法》為題演講,這就是《新聞學(xué)》第二次修訂稿的開篇;1918年10月到12月以及1919年3月,《北京大學(xué)日刊》和《北京大學(xué)月刊》刊載了先生的第二稿,發(fā)表時(shí)僅有各章節(jié)名而沒有使用總篇名;1919年11月到12月,《新中國(guó)》刊載第三稿,使用《新聞學(xué)》這一正式題名;1919年12月6日,《新聞學(xué)》由北大出版部出版,為第四稿。徐寶璜四易其稿,在這一過程中不斷深化對(duì)新聞學(xué)基本理論問題的認(rèn)識(shí)及思考。
1924年,東方雜志社出版《新聞事業(yè)》一書,內(nèi)含兩部著作,分別為徐寶璜的《新聞學(xué)大意》和胡愈之的《歐美新聞事業(yè)概況》,兩篇文稿均為他們各自在《東方雜志》上發(fā)表的舊作。
1930年,徐寶璜逝世,年僅37歲。1930年10月,再版的《新聞學(xué)》改名《新聞學(xué)綱要》,由上海聯(lián)合書店出版發(fā)行。此后,該書又在1932年、1934年和1937年再版過三次;1989年,被納入《民國(guó)叢書》再次出版;1994年,徐寶璜誕辰100周年,《新聞學(xué)》一書再一次由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發(fā)行;2008年以來,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時(shí)代文藝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又對(duì)該書進(jìn)行了再版。
三、《新聞學(xué)》的主要內(nèi)容及貢獻(xiàn)
1919年出版的《新聞學(xué)》,正文部分共14章,約6萬字,先生從新聞學(xué)的定義人手,對(duì)報(bào)紙工作的性質(zhì)與任務(wù),以及報(bào)紙的采訪、編輯、評(píng)論和發(fā)行等方面的問題,進(jìn)行了理論結(jié)合實(shí)踐的探討。
徐寶璜在寫作的過程中,借鑒中外、古今新聞理論成果與新聞傳播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形成了較為系統(tǒng)的新聞學(xué)原理框架和體系,在新聞學(xué)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xiàn),為各個(gè)新聞學(xué)問題的考察與研究提供了一個(gè)宏觀系統(tǒng)的藍(lán)本。蔡元培為《新聞學(xué)》作序,稱之為“在我國(guó)新聞界實(shí)為‘破天荒’之作”。邵飄萍主持的《京報(bào)》曾這樣評(píng)價(jià):“在中國(guó)新聞學(xué)史上,有不可抹滅之價(jià)值,無此書,人且不知新聞為學(xué),新聞要學(xué),他無論矣。”黃天鵬將徐寶璜稱為“新聞教育第一位的大師,新聞學(xué)界最初的開山祖”。
四、政府如何應(yīng)對(duì)輿論
徐寶璜先生是在美國(guó)接受的新聞教育,其《新聞學(xué)》一書中的觀點(diǎn)多源于西方,書中有諸多精彩的論述,但對(duì)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的新聞現(xiàn)實(shí)而言很難說是完全適用的。然而,先生所論及的一些問題,至今仍是新聞學(xué)界和業(yè)界重點(diǎn)關(guān)注和探討的熱點(diǎn)問題。
徐寶璜先生提出新聞的職務(wù)有六種——供給新聞、代表輿論、創(chuàng)造輿論、輸灌知識(shí)、提倡道德和振興商業(yè)。在這里,徐寶璜引用了西方的觀點(diǎn):“新聞紙者,國(guó)民之喉舌也。”對(duì)這個(gè)觀點(diǎn)他表示贊同,他指出:“新聞紙欲盡代表輿論之職,其編輯應(yīng)默察國(guó)民多數(shù)對(duì)于各重要事之輿論,取其正當(dāng)者,著論立說,代為發(fā)表之。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無愧矣。”先生在此特別強(qiáng)調(diào)了報(bào)紙要“默察多數(shù)國(guó)民之輿論”,體現(xiàn)了其對(duì)報(bào)紙公共屬性、報(bào)紙為公共利益服務(wù)之新聞?dòng)^念的認(rèn)可。同時(shí)他也認(rèn)識(shí)到了新聞紙所受到的來自政府機(jī)構(gòu)、商業(yè)組織等方面的控制,以及這些控制所帶來的后果,“新聞紙亦社會(huì)產(chǎn)品之一種,故亦受社會(huì)之支配。”“吾國(guó)政府,對(duì)于輿論,素不重視,且封閉報(bào)館之事,時(shí)有所聞,遂致新聞紙為保存自身計(jì),常不敢十分代表輿論。”相比之外,“歐美各國(guó)之政府,大抵均重視輿論,一政策之取舍,一事之興革,往往視輿論為轉(zhuǎn)移,不僅于國(guó)會(huì)中求輿論之所在,且于重要新聞紙之言論中,覘輿論之趨向。”在此,先生通過對(duì)比中外政府對(duì)待輿論的不同態(tài)度,強(qiáng)調(diào)了報(bào)紙代表輿論的重要性。
截至2015年6月,我國(guó)網(wǎng)民規(guī)模達(dá)6.68億。如此龐大的網(wǎng)民規(guī)模,囊括了社會(huì)的各個(gè)階層。互聯(lián)網(wǎng)極大地拓寬了民眾的意見表達(dá)渠道,輿論不再需要通過報(bào)紙等傳統(tǒng)媒體來呈現(xiàn),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不同的個(gè)體基于各自不同的立場(chǎng)和利益訴求發(fā)出自己的聲音,使言論表達(dá)呈現(xiàn)出明顯的多樣化特點(diǎn)。民眾可以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自由地討論政府事務(wù),使其對(duì)政府的意見與建議暴露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其中不乏對(duì)政府的批評(píng)之聲,這是互聯(lián)網(wǎng)出現(xiàn)之前的時(shí)代所難以想象的。
面對(duì)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批評(píng)之聲,政府該如何作為?按照老舊觀念去刪帖和堵塞已經(jīng)難以實(shí)現(xiàn),并且一味地打壓又會(huì)進(jìn)一步激化民眾的不滿情緒從而導(dǎo)致過激行為的產(chǎn)生。如果民眾的意見難以表達(dá)、不良情緒難以排解,就會(huì)造成社會(huì)問題的淤積,長(zhǎng)此以往必將爆發(fā)更大的社會(huì)危機(jī)。如果對(duì)民意始終采取“堵”的辦法,那么就將無法化解國(guó)內(nèi)一直存在的由于民意不暢而造成的制度性的不穩(wěn)定因素。
互聯(lián)網(wǎng)為民眾提供了意見表達(dá)的渠道,客觀上也提供了不良情緒的排解通道,這種不良情緒的排解通道在很大程度上充當(dāng)著安全閥的角色。面對(duì)意見環(huán)境的改變,政府需要做的是轉(zhuǎn)變思路,考察批評(píng)聲背后的社會(huì)訴求,而不能肆意剝奪民眾探討公共事務(wù)的權(quán)利,不能壓制民眾探討公共事務(wù)的欲求和熱情。
五、主流媒體的輿論引導(dǎo)
在“代表輿論”之外,徐寶璜先生還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創(chuàng)造輿論”這一觀點(diǎn)。他認(rèn)為,“新聞紙不僅應(yīng)代表輿論也,亦應(yīng)善用其勢(shì)力,立在社會(huì)之前,創(chuàng)造正當(dāng)之輿論,而納人事于軌物焉。”在列舉了世界各大新聞社與國(guó)內(nèi)《蘇報(bào)》、《警鐘報(bào)》、《民呼報(bào)》等例子后,先生提出創(chuàng)造輿論的三種方法:
“一為登載真正之新聞,以為閱者判斷之根據(jù)。”在對(duì)新聞的第一職務(wù)“供給新聞”的論述中先生已經(jīng)提到:“輿論之以正確詳細(xì)之事實(shí)為根據(jù)者,必屬健全,若所根據(jù)者并非事實(shí)則健全之輿論無望矣。”事實(shí)判斷是價(jià)值判斷的基礎(chǔ),只有在真實(shí)、全面的事實(shí)材料的基礎(chǔ)上,做出的判斷才是有價(jià)值的,根據(jù)片面事實(shí)所做出的判斷價(jià)值較小,在某些情況下甚至?xí)鸬椒醋饔谩_@就涉及到“事實(shí)”與“真相”的關(guān)系問題。相比之下,事實(shí)只是存在意義上的概念,表明事情是真實(shí)存在的,但可能只是事件的某一個(gè)方面,并不全面;而真相是更為全面的事實(shí),能較為全面地反映事件的整個(gè)發(fā)生、發(fā)展過程。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徐寶璜也指出:“夫新聞之為事實(shí),無待贅言,但事實(shí)真相,往往不易探得。”忠于事實(shí)、追求真相,是新聞從業(yè)者應(yīng)有的基本新聞理念。
“二為訪問專家或要人,而發(fā)表其談話。”由于民眾對(duì)一些較為復(fù)雜的問題往往缺乏必要的認(rèn)知和判斷能力,因此就需要專業(yè)人士就這些問題給出建議,以供民眾參考。
“三為發(fā)表精確之社論,以喚起正常之輿論。”強(qiáng)調(diào)來自報(bào)紙內(nèi)部編輯人員的意見引導(dǎo),先生同時(shí)提出了對(duì)編輯人員的要求——“純潔之精神,高尚之思想,遠(yuǎn)大之眼光。”
互聯(lián)網(wǎng)極大地拓寬了民眾的意見表達(dá)渠道,報(bào)紙代表輿論的功能有所減弱,但信息過載的情形使報(bào)紙創(chuàng)造輿論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新聞媒體所提供的信息可以分為兩類,事實(shí)判斷與價(jià)值判斷,其中,價(jià)值判斷是對(duì)事實(shí)更深層次的把握和分析,并在此基礎(chǔ)上提供觀點(diǎn)和建議。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信息過載的情況更為嚴(yán)重,主流媒體的價(jià)值就在于為受眾整合、梳理這些雜亂無章的信息,為人們提供冷靜而深刻的分析,這就需要分析和判斷能力,需要更多的相關(guān)領(lǐng)域?qū)I(yè)人士的加入,此外,媒體自身也要不斷地學(xué)習(xí)和請(qǐng)教,竭力為受眾提供更多有價(jià)值的判斷。
強(qiáng)調(diào)新聞媒體對(duì)受眾的輿論引導(dǎo),其中必然涉及到引導(dǎo)的方向問題,這就關(guān)涉到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的判定問題,也就涉及到價(jià)值觀問題。筆者認(rèn)為,作為社會(huì)公器的新聞媒體,要兼顧堅(jiān)守與創(chuàng)新,始終站在社會(huì)發(fā)展的前沿,引導(dǎo)民眾更清楚地認(rèn)識(shí)社會(huì)、做出判斷,這是新聞媒體的影響力與行業(yè)價(jià)值所在。
責(zé)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