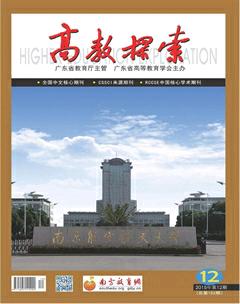論通識教育視野下的文學經典教育*
哈迎飛++周忠昊
收稿日期:2015-10-09
作者簡介:哈迎飛,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周忠昊,廣州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廣州/510006)
*本文系廣東省高等教育教學改革項目“文學通識課教學方法改革研究”(項目編號GDJG20141129)、廣東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大項目“現代化進程中文學經典的認同作用研究”(項目代號2014WZDXM021)、廣州市教育系統創新學術團隊項目“文學經典與文學教育”(項目編號13C05)的階段性成果。
摘要:文學經典作為通識教育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對提高整個民族的文化素質具有重要的意義,但如果忽視了作為專業課的文學經典教育與作為通識課的文學經典教育的差異,也很容易走進將通識課降為簡化版的專業課的誤區。本文認為,通識教育視野下的文學經典教育應突出“通”的原則,強化教師的通識眼光、教學的通才意識和學生的通透之樂。
關鍵詞:通識教育;文學經典;課程建設
經典離不開闡釋,闡釋是經典獲得不朽生命的基本條件之一,文學經典作為通識教育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對提高整個民族的文化素質和文化品格意義重大。目前,很多高校在通識教育中都把文學經典作為通識課程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就實施的情況看,有些課程受到學生的歡迎,也有一些課程流于形式。據筆者調查,造成這一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很多老師沒有意識到作為通識課的文學經典教育與作為專業課的文學教育重心不同。應該說,專業課老師承擔通識課教育教學任務,對提高通識教育的專業水準非常有益,但專業課老師從事通識教育,出發點是專業,落腳點卻是通識,把通識課變成降低了標準的專業課,不利于通識課程的建設與發展。為了更好地闡釋這一觀點,本文擬以中國現代文學經典的通識教學為個案,就文學類通識課程的建設原則進行深入探討,以期對我國通識教育的改進和提高有所貢獻。
一、以通識的眼光激活經典的研究
雖然受考核機制的影響,一般來說,絕大多數高校老師尤其是年輕老師更愿意把時間優先投入到更有挑戰性的前沿課題研究中,而不是通識教育上,但由于通識課能超越專業領域限制,打破學科壁壘,彌補專業教學之不足或局限,完善和改進專業教學并促進科研,所以也有很多資深的教師對通識教學充滿熱情。不過,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既有聯系,也有差別。以“中國現代文學經典導讀”課程為例,盡管中文系也要講授這門課程,但老師一般會較多地從文本產生的語境和文學史的維度解讀作品,而在通識課中,任課教師首先面臨的問題是,今天我們為什么要讀這些經典?而要講清楚這個問題,就不能就作品論作品,而必須與時代對話、與生活對話,與學生的心靈對話。對話的結果,是讓經典接地氣,而接上地氣的經典又激活了我們對經典的研究,這是一個非常有價值和意義的正循環。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文認為,通識教育和經典教學無論對學生還是對教師都是大有裨益的,正如武漢大學著名哲學家郭齊勇在談到經典教學時所指出:“我們的文科教學和研究生培養,除學科交叉整合不夠外,我感到最不足的是忽視引導學生讀經典。我們幾十年來一般習慣于用各種‘概論加‘通史(或專史)來代替原典,近十多年來我們更是忙于拼湊各種通論、概論的體系,現買現賣。把這些東西灌輸給學生,遠不如引導學生自己直接去接觸原典來得深厚。古今中外的學術經典著作具有深長久遠的滋潤作用,給人以創造性的熏炙和不斷反芻的空間,是用不枯竭的源頭活水……問題是我們的學生不會讀書,不會讀原典。我們需要想一些辦法,通過各種方式,按不同層次的學生的程度,引導他們直接與本專業和相鄰專業的經典相溝通。這比讀那些三轉手、四轉手的或拼湊的東西要意味深長得多。”[1]多年的教學實踐告訴我們,引導學生閱讀經典,無論是對高素質人才培養,還是對前沿的學術研究都是功德無量的。
通識教育對于經典研究具有一種特別的激活力,正如馬克思談到古代經濟研究時所說:“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反過來說,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2]在某種意義上,今天的我們之所以比過去更能體驗和感受民國文學經典的奧秘,原因也正在這里。民國文學在當下走紅和熱銷,絕不是偶然的。以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小說《邊城》為例,長期以來,人們認為這部作品表現的是作家理想中的優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但是《邊城》的魅力又不是一個“美”字所能道盡的。很多人讀完《邊城》后去鳳凰實地考察和體驗湘西生活,發現遠比不上沈從文的小說美,為什么呢?因為小說里的生活方式,作為遠逝的過去,已經永遠不可能再回來。我們讀這部經典,事實上讀到的是一種“回不去”的生活,沈從文的成功就在于他對這種再也回不去的生活的進行了詩意的呈現和表達,從而成為保存在我們心底的一張珍貴的照片。
現代社會節奏之快、壓力之大、流動性之強以及物質之繁榮、商品之層出不窮和信息之源源不絕等,是《邊城》世界里的人想象不出來的。在《邊城》里,人們沒有迫不及待要完成的任務,沒有馬不停蹄要追趕的前程,沒有競爭的壓力和生存的焦慮,這種生活,身在其中時,它的單調和清貧常常是現代人難以接受的,但是,當現代人犧牲了閑暇,提高了效率,終于獲得了所希望的財富與機會卻發現沒有從容享受它的時間和心境時,“慢生活”的渴望也會油然而生,就像愛因斯坦所說:“我強烈地向往簡樸的生活,并且時時為發覺自己占用了同胞過多的勞動而難以忍受。”[3]雖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愛因斯坦那樣為了自己占用了同胞過多的勞動而難以忍受,但是,對簡樸、安閑而豐腴的生活的幻想卻是現代人揮之不去的心結,所以《邊城》對現代人魅力無限。
·課程與教學·論通識教育視野下的文學經典教育
就經典教育而言,理解現在常常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解釋過去。站在當代生活的立場審視《邊城》,你會發現那個世界不僅詩意而且寧靜,因為一切皆為習慣所支配,所以生活在這小城中的人很少為明天焦慮和緊張。現代人的生活被時間所拘役,已經很難體會單是活著的快樂是怎樣的,單是呼吸、單是走道、單是張眼看聳耳聽的幸福是怎樣的,但是,時間在《邊城》里卻失去了它在現代社會的威力。《邊城》里的時間是自然化的,如“初五大清早落了點毛毛雨”[4],“祖父回家時,大約已將近平常吃早飯時節了”[5],“黃昏來時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6]等,而時間在現代社會通常是被精確計算和表述的,如早上五點鐘起床、晚上7:25分開會等等,所以生活在《邊城》世界里的人沒有現代人“趕時間”、“時間就是金錢”的觀念。時間的可計量化,是現代人精神焦慮的一個重要來源。劉易斯·芒福德曾在《技術與文明》一書中以鐘表為例說明,從14世紀以來,鐘表是如何把現代人變成了遵守時間的人、節約時間的人和現在被拘役于時間的人的。[7]尼爾·波茲曼指出,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學會了漠視日出日落和季節更替,因為在一個由分分秒秒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權威被取代了。[8]相對于金錢對人的奴役,時間對現代人的奴役更加深刻,也正因此,當我們在《邊城》的世界里重溫那種簡單而從容的生活時,我們的感動常常難以言傳。《邊城》的世界有星星、月亮、山花、翠竹、鳥雀和各種炒菜的氣味,這種本真的生命體驗,在沈從文筆下,是那么有質感,而在現代社會里,由于知識累積代替了感性體驗,人的生活越來越遠離自然,也越來越缺少存在的真切感和現場感。走進《邊城》,我們就好像魚歸大海,鳥回天空,又活了過來,對河水,對夕陽,對拉船人,對小山村,都十分溫暖地愛著!總之,《邊城》的世界是我們每個人都體驗過的“童年”夢境,我們都是從那個世界走出來的,所以,一見到她,我們就能立刻認出她。
當然,經典作為時代的產物,也有可能使當下的讀者感覺不適應,或是語言表達方式上的不習慣,或者是描寫對象的隔膜,或者是題材的不新穎,所以,經典需要闡釋,闡釋有助于消除隔膜,激活想象,但闡釋并不是照本宣科。闡釋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有效地激活學生與經典對話的興趣,而要激活學生的經典閱讀興趣,就絕對不能關起門來自說自話。理解現在,與時俱進,是成功解讀經典的不二法門之一。
二、“高大上”與“接地氣”缺一不可
通識教育既不是精英教育,也不是常識教育。它不是為了擴大學生的知識面,讓學生什么都知道一點點,而是為了通過對最根本和基本的問題的思考,鍛煉學生的思辨能力,提升人性境界、塑造理想人格、培養純正趣味,最終提高學生的思想覺悟、精神品質和人文素養,雖然它的起點很低,有時候甚至不設門檻,但它的境界很高。不是所有的課程都能納入通識教育課程體系的,也不是所有的課程都要求通俗易懂的,好的通識教育必定具有“高大上”的品質。據筆者觀察,大凡受到學生歡迎的通識課程,大都在“高大上”與“接地氣”兩個方面的結合上做得比較好。所謂“高大上”是指課程的內容具有經典品質,所謂“接地氣”是指課程的教學方法能夠貼近學生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具有可聽性和對話性。對通識教育來說,教師一方面要抓住“高大上”與“接地氣”之間的辯證關系建構教學原則,另一方面也要有通才教育的意識和眼光。
眾所周知,經典與流行讀物的最大區別在于,它經得起重復閱讀。正如意大利著名作家卡爾維諾在《為什么要讀經典》中所說,經典是每次重讀都好像初讀那樣帶來發現的書;經典也是一本即使我們初讀也好像是在重溫我們以前讀過的東西的書。[9]經典不老的秘密在于它能與時代對話,只要你仔細聆聽,你便能發現,經典中有你最關心的、甚至是最時尚的內容,而一旦你聽到了,發現了,你就會發自肺腑地感謝那些創作了這些偉大作品的人類靈魂工程師。
傳世的經典,是人類精神世界的護身符。以曹禺話劇《雷雨》為例,這是中國話劇成熟的標志性作品。它明顯地受到希臘命運悲劇的影響,也明顯地有莎士比亞式的性格悲劇和易卜生社會悲劇的意味。劇中八個人物,個個性格鮮明生動。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雷雨》第一次以話劇的形式在較大的思想容量和深刻性上寫出了中國人的家庭悲劇,而且是三代人的家庭悲劇:上一輩——周樸園和他的母親,這是母子層面的家庭悲劇;這一輩——周樸園和蘩漪,這是夫妻層面的家庭悲劇;下一輩——周樸園和周萍、周沖、魯大海,這是父子層面的家庭悲劇。
作為悲劇的核心人物,周樸園的身上既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思想,又有封建專制思想。因為前者,他年輕時敢于公開和侍萍同居。因為后者,他的反抗和覺醒又是不徹底的。周樸園的“始亂終棄”既造成了侍萍的悲慘命運,也給自己留下了終身的遺憾和傷害。拋棄侍萍后,周樸園還有兩次婚姻,但都不幸福。蘩漪是周樸園的第二任妻子,比周樸園年輕20歲,但周樸園始終不喜歡她。
周樸園年輕時可以到德國留學,但卻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他遵從家人的安排,但是,性格卻越來越暴戾、冷酷、專制、不近人情,而且一生沒有得到應有的幸福。我們都知道,人不能給別人自己所沒有的東西。作為一個被剝奪了自己真愛意愿的犧牲品,周樸園的內心有一個永遠無法愈合的傷口,他自顧尚不暇,哪有心思“愛”別人?又怎么能給人家“愛”呢?周樸園的暴戾與冷酷與他的包辦婚姻有著直接關系。曹禺寫出這一點,是很不簡單的,他筆下的周樸園不僅是所有悲劇的總源頭和最大的偽君子,而且也是封建禮教的受害者。劇本非常大膽也非常深刻地寫出了惡人的委屈與悲劇,不僅使周樸園的形象更加真實、深刻、豐滿,而且使劇本反封建的主題一下子提升到動人心魄的高度,堪稱大手筆。眾所周知,善人的悲劇值得同情,但惡人的懺悔或許更值得深思。《雷雨》作為百年中國話劇第一戲,常演不衰,絕不是偶然的。
作為強勢父親,周樸園身邊有兩個兒子,但一個懦弱,一個幼稚。現在很多人關心男孩教育的問題,討論為什么男孩子越來越柔弱?有一種觀點認為原因在于他們從幼兒園開始就被女性包圍了,小學,老師是女的,中學,老師又是女的,所以,男孩子越來越女性化,就像賈寶玉,非常女性化。但我們可以想一下,是誰把賈寶玉推向了賈母和王夫人的?固然,賈母溺愛孫子,王夫人寵愛兒子,但有賈政那樣的父親,賈寶玉不倒向賈母,也會倒向其他的女性。在這個劇本中,周萍從小失去母親,又長期不在父親身邊,如果說他的懦弱是父愛缺失造成的,那么,周沖的幼稚則是父親過于嚴厲,不近人情的結果。需要強調的是,周沖的幼稚中有善良、純真的詩意,而這恰恰是母親蘩漪影響的結果。在周萍、周沖生活的時代,學校的男老師至少比現在的中小學多,但他們照樣成為了“問題男生”,所以,男孩子越來越柔弱的背后,是文化的問題,不是性別問題。
魯迅在五四時期提出“今天我們怎樣做父親”[10]的問題,《雷雨》實際上寫出了一個典型的中國強勢父親的失敗人生。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呼吁:“救救孩子!”《雷雨》則進一步豐富了這個主題,提出要“救救男孩!”《雷雨》寫的是一個將近一個世紀以前的中國家庭悲劇,但是,它所反映的問題,卻相當鮮活,是中國家庭中的很多問題:父子對抗、夫妻隔膜、母子沖突、婚外戀、私生子、舊情人、見異思遷、不負責任等等,在這部作品均有涉及。它沒有答案,卻可以讓我們長久討論和思考,就像一個超級有趣的游戲,讓人走進以后永不厭倦。正因此,我們認為,讓“高大上”的經典“接地氣”應該成為通識課教學的自覺追求和努力的目標,而“高大上”的經典要接好地氣,老師一定要有通才教育的意識。
三、生命原則與情感導向
作為普通高校,文學通識教育在課程建設上還應該把握以下兩個關鍵點:一是生命原則,二是情感導向。
尊重生命,道理很簡單,但近年來發生在社會上的一些惡性案件也提醒我們,由于長期以來的應試教育過分強調成績和分數,甚至把分數當成評價學生的事實上的唯一標準,而忽視和淡漠對學生的生命教育,很多學生生命意識淡薄,令人擔憂。
生命是神圣的,也是容易受到傷害的。我們不能隨意傷害無辜者,也不能隨意殘害生命。我們要善待他人,也要善待自己,不能視生命為兒戲,更不能將生命降格為牟利的工具,認識上的誤差,常常會導致不可挽回的生命傷害。以老舍先生的經典小說《駱駝祥子》為例,為什么在虎妞死后,祥子反而墮落得更快了呢?客觀地說,虎妞難產而死,對祥子既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也是一次意外的解脫。他還那么年輕,重新開始一點不晚,何況,他還遇到了曹先生那么好的主人,憑什么得知小福子死后,他就要自暴自棄呢?雖然他喜歡小福子,但小福子的家累太重,他原先就不是特別想娶她。在一切都要好起來的時候,祥子突然撒手不干了,原因就在于,他想不通要強有什么用?當初,他要強,是因為想買車。后來,他發現要強不一定能買上車,他就開始猶豫了。
透過祥子的悲劇,我們看到,人生僅有物質的理想是遠遠不夠的,如果吃苦、忍耐、奉獻、委屈都變成了獲得財富的手段,本身并沒有獨立的價值和意義,那么,一旦期望落空,它就很有可能使人因為失望而立即走到反面去,就像祥子,前半生拼命苦干,后半生拼命墮落。祥子把買車視為自己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11]。其實,買車的理想,即使實現了也并不能保證生活的幸福,虎妞就是典型。同時,車可以買,也可以丟或壞。老舍先生筆下的祥子悲劇對于我們今天在職場上打拼的年輕人非常有啟示意義。
過去人們習慣認為,美德在窮人的身上比在富人的身上更易保持,但是,透過這部作品,我們看到,美德在窮人身上一樣甚至更不容易保持。為什么呢?因為貧窮會遮蔽人的眼睛,讓人看不到自己身上真正的財富在哪里,就像祥子,他不知道身上最大的財富不是他曾經擁有的那輛車,而是他從鄉下帶來的那種淳樸、上進、節儉、自律的品性,就像老舍所說:“他沒什么摸樣,使他可愛的是臉上的精神”[12]。當他在城市的打拼過程中,把這件最可寶貴的財富像倒洗澡水時連著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的時候,他離萬劫不復的地獄也就真的是不遠了。
大學生正處在成長的關鍵時期,“我是誰?”“我走向何方?”“人生有什么目的?”“為什么一定要有理想?”等是大學本科生在心智發展過程中具有本體論意義的根本問題。大學生關心社會,同時又比較偏激;渴望愛情,但又受不起委屈;盼望成功,但又十分脆弱。復旦大學林森浩投毒案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在宣判前的記者采訪中,林森浩談到自己之所以這樣做,就是因為“看不得室友黃洋整天高高興興的”。當記者問在看守所等待宣判的時間里他是怎么度過的?林森浩回答:“一直在看書,主要是一些文學經典。因為我覺得以前讀理工科的書太多,這方面讀得少。我感覺我的思維有點‘太直,就是不懂得拐彎。有時候容易不考慮事情的后果,不考慮別人的感受。”[13]文學經典可以幫助大學生更好地認識自我,但目前很多大學生并不太明白為什么必須選修人文經典教育課程,相當多的同學是抱著混學分的心態走進選修課室的。應該說,這里既有學生的覺悟問題,也有經典教育課程自身的教學方式要改進的問題。好的通識課,可以啟迪心智,蕩滌靈魂,引導學生用一種新的方式去看,去聽,去感受,去思考。越是經典,越能召喚沉睡者,指引迷失者,為異化的人性提供精神的呵護和心靈的滋養。用德波頓的話來說就是:“最好的書能清楚地闡明你長久以來一直心有所感,卻從來沒辦法明白表達出來的東西。”[14]經典文學可以幫助我們把未知的自我認出來,從而更好地理解自己、平衡心理,成熟而理性地處理生活、學習、感情與家庭的關系,這是目前在中國高校開展經典文學通識教育特別有現實意義、特別有戰略價值的地方所在,也是高校專業課老師從事通識教育特別有意義的地方所在。
參考文獻:
[1]郭齊勇.面向21世紀的哲學教育[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66.
[2]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
[3]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文錄[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5:2.
[4][5][6]沈從文.邊城[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29,34,54.
[7]劉易斯·芒福德.技術與文明[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9.
[8]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9]卡爾維諾.為什么讀經典[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3-4.
[10]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129.
[11][12]老舍.駱駝祥子[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36,5.
[13]復旦投毒案一審被判死刑[N].中國青年報,2014-02-19(7).
[14]阿蘭·德波頓.身份的焦慮[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