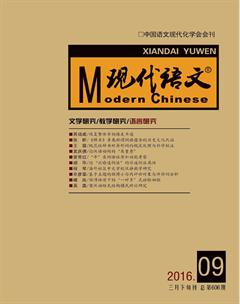《釋名》親屬稱謂詞語蘊含的歷史文化內涵
摘 要:《釋名》親屬稱謂詞語作為承載文化的重要方式,反映了《釋名》時代的歷史文化內涵:第一,體現漢代嚴格的宗法制度與尊祖敬宗的家族觀念;第二,體現漢代的繁雜的婚姻禮俗與獨特的婚姻制度;第三,體現漢代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會隨著角色的變化而轉變,呈現出雙重性和不平衡性的特點。
關鍵詞:詞語 釋名 親屬稱謂 文化內涵
《釋名》是一部用聲訓方法推求事物命名由來的訓詁學專著,在中國語言學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是中國詞源學第一部專著。《釋名》成書于東漢末年,作者劉熙,全書八卷,二十七篇。《釋名》以聲訓為主,訓釋親屬稱謂詞語時,不僅指明詞義,更著重探究詞語間音義的聯系。親屬稱謂詞語作為承載文化的重要方式,像一面鏡子,映射著漢代復雜的親屬關系。這里我們通過《釋名·釋親屬》所記錄的親屬稱謂詞語,對漢代的宗法制度與家族觀念、婚姻制度和婚姻形式以及漢代婦女的地位進行初步探究。
一、宗法制度與家族觀念
《釋名》親屬稱謂詞語作為承載文化的重要方式,反映了《釋名》時代的歷史文化內涵。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從某種意義上講,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封建社會產生的宗法制有其合理的一面,對當時社會穩定、人民生活安定,有著一定的積極作用。家國一體的宗法制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以嫡長子繼承制為基礎,以子繼父、兄統弟、嫡統庶為內在結構,用來尊祖敬宗、維系親情。
漢民族有著很強的家族觀念,十分重視血緣關系,家族是人們由婚姻和血緣關系聯結而成的社會集合。“家”是人們心中具有超強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避風港。家族中的每個人都不是一個孤立的個體,與不同層次上的血緣親屬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具體表現為家族中以父系為中心,脈絡分明、長幼有序、內外有別。
(一)以父系為中心
《釋名》中親屬稱謂以父系為中心,強調父系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釋名·釋親屬》:“父,甫也,始生己也。”劉熙將“父”定義為“始生己”,從根源上闡釋血緣關系從“父”開始,體現以父系為中心的家庭觀念。《釋名》中對祖輩親屬稱謂詞語主要有“祖”“王父”“曾祖”“高祖”,對孫輩親屬的稱謂詞語有“孫”“曾孫”“玄孫”“來孫”“昆孫”“仍孫”“云孫”。由此可見,《釋名》中的親屬稱謂詞語,以父親為中軸線向上為“及祖、曾祖、高祖”,由子而下為“及孫、曾孫、玄孫、來孫、昆孫、仍孫、云孫”,構建了整個親屬稱謂系統的框架。與父親相關親屬的稱謂詞語劃分細致,僅對父之兄弟的稱謂詞語就有5個,按照長幼,有“伯父、仲父、叔父、季父”,還有一個對父之長兄的尊稱“世父”。《釋名·釋親屬》:“父之兄曰世父,言為嫡統繼世也。又曰伯父,伯,把也,把持家政也。”指出在龐大的家族中,父親的哥哥即家族中的嫡長子“世父”有著嫡統地位,享有絕對的財產繼承權,父親死后則由嫡長子繼承,這一方式使得其他人會因為自己的身份不會對家族財產覬覦,更加牢固地保持家族的穩定。為了維護父系中男性的地位和身份,不僅區別父系和母系,還在父系中區別男女,形成一套以父系為中心的家庭觀念。對父之兄弟的稱謂詞語有“伯父、仲父、叔父、季父”,對父親的姊妹的稱謂只有“姑”。對其他親屬稱謂的區別也都是以男性為基點,如與母親相關親屬的稱謂先列出母之兄弟,再列出母之姊妹,對母親的兄弟并沒有分出大小,僅用“舅”一個稱謂詞語。與男性配偶相關親屬的稱謂有“夫之父”“夫之母”“夫之兄”“夫之弟”,與女性配偶相關親屬的稱謂比較籠統,有“妻之父”“妻之母”“妻之姊妹”“妻之兄弟”。簡而言之,在這種家族觀念下,就可以根據親屬稱謂詞語確定其在家族內的地位,辨別身份,并能知曉他們所享有的權利。
(二)脈絡分明
按著現代親屬分類標準,可將親屬稱謂系統分成“親屬的總稱、祖輩、父母、夫妻、子女、兄弟姊妹、孫輩”這七大類。各大類之間的區分十分嚴格,絲毫不相雜糅。同一個輩分、同一個性別,因為所屬的類別不同,稱謂詞語也不相同,如父之兄弟稱“伯父”“仲父”“叔父”“季父”,母之兄弟通稱“舅”;父之姊妹稱為“姑”,母之姊妹稱為“姨”;在子輩中,父之兄弟之子女稱為“姪”,母之姊妹之子女稱為“甥”;在孫輩中,姪之子稱為“歸孫”,甥之子稱為“離孫”。脈系分明的親屬稱謂詞語,體現家族中以血緣關系區分親疏,規定了家庭內部成員遠近的血親、姻親。《釋名》親屬稱謂系統脈絡分明、劃分細致,體現了漢民族對親屬關系的重視,注重維系親屬關系,使得親屬間的關系更為協調與穩定。
(三)內外有別
在漢代,親屬關系內外有別。在家族中,“宗親”即內親,是針對父系親屬來說的,宗親的范圍專指屬于“己身”的這個家族,姓氏相同,女子沒有出嫁以前算是內親。“外親”即非宗親,包括母系親屬以及已經出嫁的姊妹。《禮記·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宗親有同樣的姓氏,屬于同一父系親屬。又《爾雅·釋親》:“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爾雅》時代已經開始把母系、妻系與宗族相區分。
為了區分宗親和外親,與之相對應,親屬稱謂詞語也內外有別,區分開了男子一系的男性親屬和女子一系的男性親屬。如把兄弟之子女“姪”與姊妹之子女“甥”相區分,把姪之子“歸孫”與甥之子“離孫”相區分,通過改變稱謂區分家族中宗親與非宗親。這種區分是有必要的,因為從父系世系來看,嫁到別的家族的女性宗親及其后代子孫,已經不屬于“自己”家族了。這也體現出家族觀念以血緣關系區分親屬遠近。
(四)長幼有序
《釋名》中對父親兄弟按照長幼進行嚴格的區分,如“父之兄曰世父”“父之弟曰仲父”“仲父之弟曰叔父”“叔父之弟曰季父”。對兄弟的稱謂詞語有“兄”“弟”,《釋名·釋親屬》:“兄,荒也;荒,大也。”“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用“大”訓釋“兄”,用次第的“第”訓釋“弟”說明兄比弟早出生,兄長弟幼。對姊妹的稱謂詞語有“姊”“妹”,《釋名·釋親屬》:“姊,積也,猶日始出,積時多而明也。”“妹,昧也,猶日始入,歷時少尚昧也。”用“積”訓釋“姊”,用“昧”訓釋“妹”,解釋“姊”比“妹”早出生,接觸的事物多,對事物分析更加明朗。
班固《白虎通·姓氏》對“伯、仲、叔、季”有詳細論述,這四個詞語的出現與一年四季相關。“伯、仲、叔、季”等排行,標志著長幼有序,在周代就已經開始廣泛使用。這種排序是漢代家族觀念的中長幼有序的體現。首先,這種排序表明了宗主繼承者之間的關系。其次,區分血緣集團內的分支間關系,否則親屬關系就會被打亂。家族觀念的制約下,輩分要比長幼更為重要,在一個家庭中,首先看輩分,然后論長幼,即使舅舅的年齡小于外甥,但舅舅的輩分要比外甥高,所以我們要按輩分稱之為舅舅,而不能以平輩稱謂論之。漢語親屬稱謂詞還嚴格區分親疏和長幼,長幼有序是中國人一直遵循的倫理規范,家庭中長子享有優先繼承權,弟妹們亦要遵循“事兄如父”“長嫂如母”的道德準則。
同輩之間親屬稱謂詞語對長幼區分十分細致,同輩男性中年齡大的稱“兄”,年齡小的稱“弟”,女性中年齡大的稱“姊”,年齡小的稱“妹”。兄弟之妻中年長的稱“長婦”,年齡小的稱“少婦”。父系中根據長幼分為“伯父”“仲父”“叔父”“季父”,長者為尊,所以長者稱為“伯”,“伯”代表著“大”,有特權。《釋名·釋親屬》:“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為荒也。”在同輩兄弟中間,年長者為兄,故為大。《釋名·釋親屬》:“弟,第也。”弟由“次第”引申為“其次”。這是同輩之間,不同輩分之間的區分也是層次分明,中國人注重輩分,祖、父、子、孫按長幼順序,不能越級。
親屬稱謂系統與漢民族的社會文化有著密切關系,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宗法制度將人倫關系作為調節社會人際關系的主要方式,孟子認為教育有助于人們“明人倫”,宗法制度使這種規范內化于心。親屬稱謂詞語是漢民族家庭觀念在語言上的表現,最直接、最敏感地反映出漢民族的文化價值取向。人們形成尊宗敬祖的意識,認識到家族對于發展生產的重要性。農耕經濟社會人們通過宗族來劃分集體,親屬稱謂詞語更是直接記錄了一個家族如何井然有序地管理家庭成員。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說到西方社會的人際關系比較明確,好比“捆柴”,界限劃分明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團體結構。但是中國的社會結構“就好象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的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①每一個人都有自己所在的“圈子”,但是每一個“圈子”波及的人是不一樣的,可以通過“圈子”來區分他們的親屬關系。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親屬關系網,這個網的中心就是自己,自己的親屬關系網可能會與其他人的有交叉,但是不可能完全相同。家族觀念中的尊宗敬祖意識,就是將“圈子”中的人緊緊團結在一起,結成族群力量,同一個親屬稱謂系統中的人們有著同一個祖先,祭拜祖先已不能簡單看作家庭內部的禮儀活動,實際上是一種凝聚家庭成員精神的活動。他們通過隆重的祭祖活動凝聚族群力量、組織和團結族人。他們還通過修建家譜維系家族關系,形成龐大的親屬關系網,保持家族血脈的延續。在一個大家庭中,個人的權利不被強調,對家庭的責任和義務十分重要。家族觀念中每個人的行為不只是個體的行為,而是與整個家族的整體利益息息相關。同理,上升到國家層面,家國同構的理念使中華兒女愛國如家,這種理念具有強大的社會凝聚力,把家族興衰同國家命運緊密相連,這對現在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有進步意義。
宗法制體現的家庭觀念對家族和睦社會安定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即使后來把這種宗法意識強化到極致出現了一些消極影響,它們的存在也有合理成分。我們不能一味地排斥,要辯證地看待宗法制度與家族觀念,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孟子說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正是由家族觀念推及社會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從家庭和睦到社會安定團結、統一有序,從家庭凝聚力到社會向心力。建設和諧社會必須從中汲取營養,這是中國文化中的重要精神特征也是當今社會家庭美德的文化淵源。
受家族觀念的影響,在漢民族的潛意識中認為同一家族之間的關系比外族要親密。因此,有些親屬稱謂詞語不僅用在具有親屬關系的成員之間,還用在一些沒有親屬關系的社會成員之間,形成漢語親屬稱謂詞語的泛化。如“叔、哥、姐、弟”等,大量地使用于本該使用社會稱謂的人際關系中。漢語親屬稱謂詞語的泛化使人與人之間交往親切,縮小距離感。
二、婚姻禮俗與婚姻制度
在古代社會,婚姻有著重大意義,婚姻制度被看作基礎社會制度。一切的社會關系由此而推展出,也被作為親屬關系的起點和紐帶。漢代是古代婚姻發展的重要時期,漢代在繼承先秦禮俗的基礎上,將婚姻禮俗發展得更加系統與完善,形成了古代婚姻禮俗的基本規范。親屬稱謂詞語承載著大量的社會文化信息,不僅清楚地顯示了漢代家庭、婚姻的內部結構,還反映了當時的婚姻禮俗與婚姻制度。本文力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釋名》親屬稱謂詞語出發,探尋漢代獨特的婚姻禮俗和婚姻制度。
(一)婚姻禮俗
“婚”,《釋名·釋親屬》:“婦之父曰婚,言壻親迎用昏,又恒以昏夜成禮也。”“婚”本身是個后起字,原本作“昏”。“姻”,《釋名·釋親屬》:“壻之父曰姻。姻,因也,女往因媒也。”《禮記·昏義》孔穎達疏:“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陰來陽往之義。”“女”為陰,男為“陽”,男方在黃昏去女方家里迎親,而女方隨男方而行,故“婚姻”為“陰來陽往”。《白虎通·嫁娶》:“婚姻者,何謂也?昏時行禮,故謂之婚也,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婚”指女方家即婦家,“姻”指男方家即夫家,父親為一家之主,故《釋名》中“婚”作“婦之父”,“姻”作“壻之父”。文獻中提到的黃昏迎親,可以追溯到上古時期的搶婚習俗。搶婚,男子看上某個女子經常在黃昏時候趁其家人沒有防備,用掠奪方式強娶女子為妻。張亮采在《中國風俗史》中提到過這種野蠻的搶婚習俗,由于男子沒有得到女子及其親屬同意,女子對男子懷恨在心。《詩經·小雅·我行其野》:“婚姻之故,言就爾居。”即便是結為夫妻,同住一屋,那又怎么樣,這里只是個居住的地方,并沒有“家”的含義。后來,雖沒有搶婚習俗,但是有些地方娶妻仍然沿用這種習慣,在夜間迎娶。
《釋名·釋親屬》:“婦之父曰婚,言壻親迎用昏,又恒以昏夜成禮也。”其中提到男子昏夜迎親,女子的父親送親,男女雙方在昏夜完成婚禮,說明婚禮在《釋名》時代已經存在。《禮記·郊特牲》:“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婚禮,萬世之始也。”婚禮被認為是萬世萬物的開始,舉行婚禮為了向眾人宣布雙方已經建立婚姻關系,需要履行各自的權利和義務。反之,如果沒有婚姻之禮,夫妻生活則不美滿。《禮記·經解》:“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因此,婚姻禮俗變得十分重要。漢代男女婚姻關系的確定需要一定的儀式,這些儀式是為鞏固男女雙方關系而形成的,也是經過社會的認可和監督的,形式上更加復雜、隆重。
《釋名·釋親屬》:“壻之父曰姻。姻,因也,女往因媒也。”漢代男女雙方婚姻的締結需要媒人作中介。媒人是婚姻禮俗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人們把媒人締結婚姻看作應當遵守的道德規范。《詩經·齊風·南山》:“娶妻如之何,非媒不得。”孟子認為沒有媒人的婚姻是卑賤的。劉向在《新序·雜事》提到:“婦人因媒而嫁。”男女雙方締結婚姻需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白虎通·嫁娶》:“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佚也。”桑弘羊在《鹽鐵論·大論》中說:“故士因士,女因媒。”他把媒人比作推薦賢士的人,因為男女雙方在結婚前互相不認識,男女雙方的才能與相貌全憑媒人來說,由此可見媒人在婚姻關系確立中的重要性。
《釋名·釋親屬》:“婦之父曰婚,言壻親迎用昏,又恒以昏夜成禮也。”《釋名》提到漢代“六禮”中的“親迎”。“六禮”最早記載于《儀禮·士昏禮》,漢代班固在《白虎通·嫁娶》中詳細記載了婚儀程序“六禮”,即“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具體來說,“納采”是男方派媒人去女方家提親,“問名”是女方同意后詢問女子姓名與八字,“納吉”是占卜吉日,“納征”是宣告正式訂婚,“請期”是男方把迎娶吉日告知女方征求同意,“親迎”即結婚當日男方迎親和女方送親。“親迎”是漢代婚姻程序中的最后一個環節,指的是男方到女方家里迎娶新娘。男子“親迎”體現了對夫妻感情的重視,表示對新娘的尊重與愛護之心。《禮記·郊特牲》:“男子親迎,男先于女,剛柔之義也。”《白虎通·嫁娶》:“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禮記·哀公問》:“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漢代的婚姻禮節程序繁雜,體現漢代對婚姻關系的重視,進而更加重視由婚姻關系聯接的親屬關系。
(二)婚姻制度
《釋名·釋親屬》:“耦,遇也,二人相對遇也。”“耦”是指“配偶”,劉熙訓釋為“二人相對遇”。《釋名·釋親屬》:“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夫為男君,故名其妻曰女君也。”夫為“男君”,嫡妻為“女君”,兩個親屬稱謂詞語相對稱,可見漢代夫妻關系已經有一夫一妻的雛形。《釋名·釋親屬》對“天子之妻”有不同的稱謂詞語,“天子之妃曰后”“天子妾有嬪”。天子有正妻“后”,妾為“嬪”。由此可知,漢代處于人類婚姻家庭發展的一夫一妻多妾制階段,即一個男子與若干女子建立婚姻關系,僅一人為正妻,其他皆為妾。《禮記·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此之盛德。”
《釋名·釋親屬》:“妾,接也,以賤見接幸也。姪娣曰媵。媵承事嫡也。”“姪娣”是古代諸侯貴族女子出嫁,對從嫁的妹妹和姪女或同姓女子的通稱。《公羊傳·莊公十九年》:“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媵”與“姪娣”相同。古代諸侯女兒出嫁時隨嫁的人。后亦用以稱妾。漢代的婚姻形式表現媵妾婚。封建諸侯結婚時,新娘有八名陪嫁,稱為“媵”,這些“媵”即未來的妾。馮漢驥在《中國親屬指南》中詳細解釋了這種婚姻形式:“封建諸侯以下述方式來接收這些媵:新娘和八名媵被分成三組,每組三人;第一組包括新娘、新娘的一位妹妹或同父異母的妹妹——‘娣以及新娘哥哥的一位女兒‘姪,這三位女子構成最基本的一組;與新娘同姓的另外兩個封建諸侯國各提供一名‘媵、一名‘娣和一名‘姪,因此總共為三組九位女子。”②“媵”的地位十分低下,對于新娘來說“媵”是陪嫁,處于從屬地位。《釋名》對“姪”的訓釋也體現了姑姪同侍一夫。《釋名·釋親屬》:“姑謂兄弟之女為姪。姪,迭也,共行事夫,更迭進御也。”“迭”有“輪流交換”之義,《釋名》用“迭”訓釋“姪”,說明姪女與姑母輪流侍奉同一夫婿,姑姪同夫。又《釋名·釋親屬》:“母之姊妹曰姨,亦如之。《禮》謂之以母,為娣而來,則從母列也,故雖不來,猶以此名之也。”“姨”是對母之姊妹和妻之姊妹的稱謂詞語,母之姊妹作為陪嫁來到夫家,兒女稱母之姊妹“從母”,即“隨之而來的母親”,對姊妹之夫稱之為“私”,即“自己的、私人的”,從這三處可見漢代有姊妹同婚的現象。《釋名》這樣訓釋是有理有據的,古代文獻資料中也有關于姊妹同夫的記載。西漢時期景帝王皇后與其女弟共同入宮,趙飛燕姊妹同侍漢成帝;東漢時期章帝竇皇后“與女弟俱以選例入見長樂宮”等等。這些婚制多見于漢代封建貴族中。一夫多妻,除了妻、媵之外,還有地位更加低下的妾。《釋名·釋親屬》:“妾,接也,以賤見接幸也。”“庶,摭也,拾摭之也,謂拾摭微陋待遇之也。”“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夫為男君,故名其妻曰女君也。”妾不僅比男子地位低下,而且還低于正妻的地位。
《釋名·釋親屬》中“夫之父曰舅”“母之兄弟曰舅”“夫之母曰姑”“父之姊妹曰姑”。《釋名》收錄的“舅”不僅是對丈夫的父親的稱謂,還是對母親哥哥的稱謂;“姑”不僅是對丈夫母親的稱謂,還是對父親的姐姐的稱謂。《禮記·內則》:“婦事舅姑(公婆)如事父母。”《釋名》收錄的親屬稱謂詞語“舅”“姑”反映了漢代流行表兄妹通婚的習俗,即交表婚。交表婚指男子與自己父之姊妹或者母之兄弟的子女締結婚姻的習俗,中國的交表婚又稱“姑舅表婚”。當男子娶舅父的女兒或者姑母的女兒為妻,女子亦以舅父的兒子或者姑母的兒子為夫,妻子稱丈夫的父母自然是“舅”“姑”,男子稱妻子的父母分別為“外舅”“外姑”。后來不再盛行表兄妹通婚,便采用“公婆”稱丈夫的父親母親,而不再用“舅姑”。《白虎通·三綱六紀》中也將“舅姑”訓釋為“夫之父母”。《爾雅》中給出了足夠的證據加以佐證,《爾雅》將親屬稱謂分為“宗族、母黨、妻黨、婚姻”四類,并且將父之姊妹之子、母之姊妹之子、姊妹之子和姊妹之夫歸為“妻黨”,把不屬于姻親的親屬放到“妻黨”中。這種分類方式清楚明晰地表明《爾雅》時代確實存在交表婚現象。
三、漢代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
漢代女性生活在封建社會初期,她們的地位呈現出雙重性和不平衡性。一方面,封建禮制尚未完善,封建倫理道德觀念還沒有全面滲透到社會的各個方面,漢代中期還有遠古時代遺留的尊母風俗。這些因素使得漢代婦女在家庭內部的地位相對于封建社會后期較高;另一方面,董仲舒提出的“三綱五常”開始束縛女性的獨立意識。由于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漢代女性開始由被動變為主動,有意識地使自己的行為符合儒家倫理道德規范。可以說漢代女性地位的雙重性與不平衡性,使得漢代在中國女性史研究上的地位至關重要,這個時期的女性帶有強烈的漢代風貌。
《釋名》是漢代的重要訓詁學著作,所收錄的親屬稱謂詞語中,與婦女有關的親屬稱謂詞語有30多個,是探討漢代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第一手材料。《釋名·釋長幼》:“女,如也,婦人外成如人也。故三從之義,少如父教,嫁如夫命,老如子言。”劉熙對“女”的訓釋,明確指出女子一生中的三種不同身份,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稱謂。未出嫁為“女”,出嫁為“婦”,生子后為“母”。漢代女性在家庭中基于不同身份,權利和義務也不相同。基于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會隨著角色的變化而轉變,本文把婦女分為母親、妻子、女兒三種不同的角色加以敘述,以此來研究漢代女性的家庭地位。
(一)母親的地位
《釋名·釋親屬》:“母,冒也,含生己也。”“母,含生己也”與“父,始生己也”形成對稱。“冒”本義“帽子”,由“帽子”義,引申出“蒙蓋”之義,蒙上蓋住即有保護的意思。孩子未出生之時,母親將嬰兒含蒙于腹中保護之,孩子出生后也如保護傘一樣,時刻保護著孩子。有關母親在家庭中的地位,班固《白虎通》提到,“三從”乃是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但高世瑜的《說“三從”——中國傳統社會婦女家庭地位漫議》對“三從”中的“從子”有自己的想法,“‘從子是‘三從中最沒有意義的一項,由于家庭中長幼人倫之序高于男女兩性之別及對“孝道”的重視,相對于母權而言,‘從子只是一種規范女性總體地位的大原則,極少實行。”③從中國古代社會的現實來看,“父親死后,母親則代表其人格”,④母親在家中繼承了丈夫生前的權威,還有家庭事務的最終決定權。漢代注重“以孝治天下”,提倡“孝治”,漢武帝設舉孝廉科作為選官的標準之一,通過“孝”穩定社會秩序,鞏固封建統治。據《漢書》《史記》記載,漢代對母親十分尊重,從皇家貴族到平民百姓,無不如此。全國和地方對孝悌褒獎次數極多,社會形成尊母的風氣。《史記》中記載漢文帝在母親病重時為母嘗藥;梁孝王為母親病情擔憂,寢食難安。許智銀在《漢代人的母親情結》中說:“漢代人對母親懷有深深的崇敬之情,統治者或神化母親,或尊母親以封號,或厚葬母親,民間則為母親盡孝服喪。漢代人為了維護母親的形象往往殺死侮辱母親的人,對母親的話言聽計從,盡心奉養母親。統治者所頒行的法令法規促進了母親情節的深化,社會輿論對母親情節的強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⑤由此可見,漢代母親在家中有一定的地位,她們的意愿一般都能得到尊重。然而,兒子對母親的孝順和尊敬只是局限在家庭中,女性的社會地位沒有得到改變,男尊女卑的社會等級秩序仍然存在,如果女性的社會地位沒有獨立,就不能與男子享有同等的社會權利。可見,母親在家庭中的權威地位只能是相對的,而且是短暫的。
(二)妻子的地位
《釋名·釋親屬》:“妻,齊也。”《說文》:“妻,婦與夫齊者也。”《白虎通·嫁娶》:“妻者,齊也。與夫齊體。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釋名》《說文解字》《白虎通》都用“齊”訓釋“妻”。說明漢代夫妻關系較平等,妻子在家中有較大的權利。由于中國傳統社會經濟基礎是小農經濟,“男耕女織”的生產模式中,男子承擔家庭經濟的主要任務,女性從事家務勞動,當好丈夫的賢內助,無形中提高了女性在家中的地位。《周易》作為最早闡釋男女地位的著作,它提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周易》將男女闡述為乾坤,它把人的性別與天地陰陽聯系在一起,足見對男女關系的重視。漢武帝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也闡述了男女關系,他認為“天地之陰陽當男女,人之男女當陰陽,陰陽亦可以謂男女,男女亦可以謂陰陽”“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他將男女關系與陰陽聯系起來,承認了“陰助”的作用,要陰輔助于陽,妻輔助于夫。“男外女內”“男主女輔”的陰陽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女性的輔助地位。“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夫為男君,故名其妻曰女君也。”“君”在漢代成為對人的尊稱,用“女君”稱嫡妻,也可以看出漢代對妻子的尊重。《漢書》記載張敞為妻子畫眉;《孔雀東南飛》中劉蘭芝和焦仲卿夫妻恩愛,《后漢書》中梁鴻和孟光相敬如賓等等。從中可見漢代夫妻之間不是尊卑的主從關系,在家庭中妻子的地位與丈夫較為平等。
“三從”嚴格規定了女性“既嫁從夫”,依附于男子,沒有被看成一個獨立的個體;“三綱”強調“夫為妻綱”,妻子要對丈夫的話絕對服從。《釋名》中出現的對女性配偶的稱謂詞語有“女君”“妃”“后”“夫人”“內子”“命婦”“妻”“嬪”“妾”“姪娣”“媵”“匹”“耦”“嫡”“庶”“寡”16個。對不同階層的男子的配偶的稱謂詞語也不一樣。“天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卿之妃曰內子”“大夫之妃曰命婦”。《釋名·釋親屬》:“大夫之妃曰命婦。婦,服也,服家事也。夫受命于朝,妻受命于家。”大夫的妻子稱為“命婦”,從字面義看,受命于人的已婚女子,劉熙從聲訓的角度,將“婦”與“服”聯系在一起,闡釋了婦人以“服從”為天命的特點,規定大夫受命朝廷,君為臣綱,妻子受命于家庭,夫為妻綱,一家之主又為丈夫,強調妻子對丈夫的服從自然且合理。
(三)女兒的地位
《釋名》收錄的親屬稱謂詞語僅有“女”一例,而且放在《釋長幼》篇目中。《釋名·釋長幼》:“女,如也,婦人外成如人也。故三從之義,少如父教,嫁如夫命,老如子言。青徐州曰娪。娪,忤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然也。”
史書中有不少記載,漢代女兒在家庭中常常被寄予厚望。漢代的呂后、鄧太后少時深受父親器重,“事無大小,輒與詳議”。漢武帝時平民女子衛子夫封為皇后,有歌謠傳唱“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女子被寄予厚望入宮為后,為家族爭取榮耀,這是漢代女性得到社會認可的表現。不僅如此,普通人家的女兒在家中多是得到家人的關心、疼愛。《史記·陳丞相世家》說陳平的妻子雖然多次出嫁,在家仍然得到父輩疼愛,父輩為她的婚事親自到陳平家查看,說明了身為人女的女性在家庭中仍然受到一定的重視。《禮記·曾子問》:“嫁女之家三夜不熄燭,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其間描繪出女子出嫁時父母對其不舍,女子對父母十分依戀的情景。
《釋名·釋親屬》:“嫂,叟也。叟,老者稱也。叟,縮也,人及物老,皆縮小于舊也。”《釋名》中還能看出漢代女性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是相對的、有條件的。婦女作為“嫂”,面對丈夫的弟弟時,才能找回自己女性的尊嚴。《說文·女部》:“嫂,兄妻也。”從“嫂”字形來看,“嫂”字另一半是“叟”,源自對老人的稱呼“叟”,“女”是其意符,代指女性。用“叟”訓釋“嫂”是對嫂的尊重,其旨在將“嫂”提升到與父母一個輩分,提高“嫂”的地位。現仍有“長嫂如母”的說法,這與“嫂”字的內涵是分不開的。劉熙將“嫂”與“叟”聯系起來,尊稱“嫂”為長者,也有這層意思。漢代有些女性在同一家庭的女性中地位不平等,地位低下或年幼的女性要服從地位高于自己或年長的女性,先嫁到夫家的兄妻的地位要比弟妻稍微高一些,“少婦謂長婦曰姒,言其先來,己所當法似也。”“長婦謂少婦曰娣。娣,弟也,已后來也。”由此可見,漢代不僅男女之間地位不平等,而且同為女性,地位也不平等。
注釋:
①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頁。
②馮漢驥《中國親屬稱謂指南》,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第46頁。
③《光明日報》,1995年11月20日。
④馬新《兩漢鄉村社會史》,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317頁。
⑤許智銀《漢代人的母親情結》,《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2004年第5期。
參考文獻:
[1][清]王先謙撰集.釋名疏證補[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2]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3]周振甫.詩經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0.
[4][漢]鄭玄注.禮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5.
[5][清]陳立撰.吳則虞校.白虎通疏證[M].北京:中華書局,1994.
[6]胡奇光,方環海.爾雅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7]費孝通.鄉土中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8]蘇新春.文化語言學教程[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6.
[9]馮漢驥.中國親屬稱謂指南[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
[10]殷寄明.“姑舅、姑嫜、公婆”淺釋[J].中國語文,1996,
(1).
[11]許智銀.論漢代人的母親情結[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4,(5).
[12]胡士云.親屬稱謂研究[D].廣州:暨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1.
[13]王琪.上古漢語稱謂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6.
(張昕 山東曲阜 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 27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