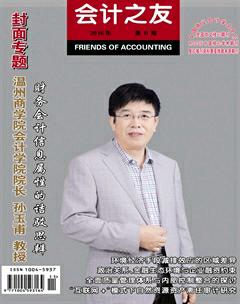審計委員會研究框架:文獻評述與展望
2016-06-23 15:56:59劉李福鄧菊香
會計之友
2016年11期
關鍵詞:公司治理
劉李福++鄧菊香
【摘 要】 2002年至今,我國審計委員會制度已經執行了10年有余,而國外審計委員會發展至今將近80年歷史。上市公司普遍設立審計委員會,有效地發揮了內部監督治理與外部協調職能,對于完善公司治理機制具有重要的推動意義。然而,隨著我國上市公司后股權分置改革的推進,新的代理沖突不斷出現,在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的進程中,有待重新審視審計委員會及其職能發揮。如何完善審計委員會制度,必將成為健全公司治理機制的重要內容。文章以文獻評述的形式,從審計委員會的內涵、職能、有效性及治理機制等方面,系統地梳理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并結合法律體系特征,比較審計委員會與監事會等內部監管機構的異同,以期為審計委員會制度的完善提供對策建議。
【關鍵詞】 審計委員會; 公司治理; 代理沖突; 后股權分置改革; 監事會
中圖分類號:F23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937(2016)11-0112-04
一、引言
隨著我國上市公司后股權分置改革的逐步深化,新的代理沖突不斷出現,制約了我國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的步伐,而利益相關者權力制衡結構逐漸失去平衡,進一步加劇了組織層面、業務層面、人員層面與道德層面的風險,從而降低了企業整體經營績效質量(廖理等,2008)[ 1 ]。基于兩權分離所產生的代理問題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與基礎,如何解決管理層代理行為中的利益沖突,一直是股東監管與管理層行為“博弈”的實質(Adolf Berle & Gardiner Means,1932;Jensen & Mecking,1976)[ 2-3 ]。隨著兩權分離公司……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商(2016年33期)2016-11-24 18:41:47
商(2016年33期)2016-11-24 18:33:46
商場現代化(2016年26期)2016-11-21 23:39:24
知音勵志·社科版(2016年8期)2016-11-05 04:45:20
人間(2016年26期)2016-11-03 19:15:03
時代金融(2016年23期)2016-10-31 13:23:15
時代金融(2016年23期)2016-10-31 12:49:23
現代經濟信息(2016年19期)2016-10-20 17:35:38
現代經濟信息(2016年19期)2016-10-20 16:55:41
中國市場(2016年33期)2016-10-18 13:4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