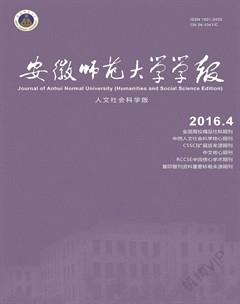思想政治教育的話語轉(zhuǎn)換及其路徑
關(guān)鍵詞: 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話語;話語轉(zhuǎn)換路徑
摘要: 話語問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內(nèi)生性問題,決定性地影響著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的話語轉(zhuǎn)換,就是教育者根據(jù)時(shí)代背景和教育情景的特點(diǎn)和要求,根據(jù)受教育者的需要和習(xí)慣,調(diào)適和改變自己原有的話語方式,用受教育者更愿意和能夠接受的話語來表達(dá)和傳遞教育內(nèi)容,以增強(qiáng)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實(shí)效性。當(dāng)前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路徑轉(zhuǎn)換主要包括:政治話語的學(xué)理化,學(xué)理話語的通俗化,通俗話語的趣味化,以及書面話語的口語化,剛性話語的柔性化,熟悉話語的陌生化等。
中圖分類號(hào): G641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 A文章編號(hào): 10012435(2016)04039707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ourse;discourse transformation path
Abstract: The discourse problem is the inner natur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has a decisive influence on the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ers to that educator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era background and educational situation, according to the needs and habits of educatees, adjust and change their original mode of discourse, and deliver education content with the words which educatees are willing and able to accept, to 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owadays, in the path of the dis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ainly includes: political discourse to theory, theoretical discourse to popularization, popular discourse to interest, and written discourse to colloquialism, rigid discourse to flexibility, and familiar discourse to strangeness.
話語問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內(nèi)生性問題,這個(gè)問題處理得好不好,直接影響著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1]為了更加貼近受教育者的需要和特點(diǎn),教育者要自覺地對(duì)自己的話語方式進(jìn)行調(diào)適和轉(zhuǎn)換,以實(shí)現(xiàn)與受教育者的話語對(duì)接。
一、思想政治教育話語轉(zhuǎn)換的特殊重要性
思想政治教育在通常情況下是用話語來進(jìn)行的,而個(gè)別情況下的非話語的運(yùn)用也必須與話語相聯(lián)系。話語的運(yùn)用是一個(gè)復(fù)雜的工程,其中重要的一個(gè)問題是話語的轉(zhuǎn)換。思想政治教育的話語轉(zhuǎn)換,就是教育者根據(jù)時(shí)代背景和教育情景的特點(diǎn)和要求,根據(jù)受教育者的需要和習(xí)慣,調(diào)適和改變自己原有的話語方式,用受教育者更愿意和能夠接受的話語來表達(dá)和傳遞教育內(nèi)容,以增強(qiáng)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實(shí)效性。
話語轉(zhuǎn)換是思想政治教育話語運(yùn)用中的應(yīng)有之義。因?yàn)椋枷胝谓逃哂迷捳Z來表達(dá)和傳遞思想時(shí),它的表達(dá)已是屬于思想的“第二次”表達(dá),即經(jīng)過了轉(zhuǎn)化的表達(dá)。思想理論觀點(diǎn)的形成需要話語表達(dá),這個(gè)表達(dá)屬于“第一次”表達(dá),它的唯一要求是清晰準(zhǔn)確地表達(dá)出這個(gè)思想觀點(diǎn)本身。它所面對(duì)的是思想本身,它要處理的是特定思想與其語言表達(dá)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而思想政治教育的話語是在此基礎(chǔ)上的第二次表達(dá),即將已經(jīng)形成的思想理論經(jīng)過話語的轉(zhuǎn)化,來向教育對(duì)象進(jìn)行傳播或傳遞,因此它所面對(duì)的主要不是思想本身,而是教育對(duì)象,它所要處理的是思想內(nèi)容、受教育者的需要和話語表達(dá)三者之間的關(guān)系。好的教育者不能簡(jiǎn)單地照本宣科,而是必須根據(jù)受教育者的情況和需要,調(diào)整表達(dá)思想的方式,實(shí)現(xiàn)從第一次表達(dá)的原初話語向第二次表達(dá)的新話語轉(zhuǎn)換。
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初話語是作為其教育內(nèi)容的思想理論本身的話語,比如理論著述的話語,政治文獻(xiàn)的話語,學(xué)科體系的話語等。在宣傳教育過程中,這種話語需要根據(jù)教育教學(xué)的需要作出調(diào)整和改變,改變后的就是教學(xué)話語或轉(zhuǎn)換后的新話語。沈壯海提出過思想政治教育的“內(nèi)容Ⅰ”和“內(nèi)容Ⅱ”,以及從前者向后者的轉(zhuǎn)換。[2]81他認(rèn)為,學(xué)科內(nèi)容有其內(nèi)在的邏輯結(jié)構(gòu),據(jù)此邏輯而呈現(xiàn)的內(nèi)容是原有內(nèi)容即“內(nèi)容Ⅰ”,出于教育教學(xué)需要而編寫的講義內(nèi)容則是轉(zhuǎn)換后的內(nèi)容即“內(nèi)容Ⅱ”。將這樣的提法運(yùn)用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話語及其轉(zhuǎn)換中來,就可以將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初話語稱為“話語Ⅰ”,將面向教育對(duì)象而轉(zhuǎn)換過的話語稱為“話語Ⅱ”。其實(shí),從思想政治教育的“內(nèi)容Ⅰ”向“內(nèi)容Ⅱ”的轉(zhuǎn)換本身就包含有從“話語Ⅰ”向“話語Ⅱ”的轉(zhuǎn)換,而且某種意義上可以歸結(jié)為這種話語的轉(zhuǎn)換,因而內(nèi)容本身畢竟是更穩(wěn)定的。
從理論上講,思想政治教育的話語轉(zhuǎn)換有兩種:一種是由于內(nèi)容本身的轉(zhuǎn)變而引起的話語轉(zhuǎn)換。如果思想政治教育的內(nèi)容發(fā)生了重大的轉(zhuǎn)變,特別是內(nèi)容體系發(fā)生了重大轉(zhuǎn)變,那么話語當(dāng)然也隨之改變。這種話語的轉(zhuǎn)換本身就是內(nèi)容轉(zhuǎn)換的一部分。恩格斯曾經(jīng)說過,科學(xué)上的每一次劃時(shí)代的發(fā)明和發(fā)現(xiàn),都伴隨著術(shù)語上的革命。這其實(shí)就是話語上的轉(zhuǎn)換。這種轉(zhuǎn)換往往具有根本性。另一種是在內(nèi)容本身沒有發(fā)生大的改變的情況下,出于教育教學(xué)的需要而實(shí)行的話語轉(zhuǎn)換。這種轉(zhuǎn)換實(shí)質(zhì)上是教育者所施行的話語調(diào)整,以使其更加適應(yīng)于當(dāng)下教育的需要。
在這兩種情形中,對(duì)我們來說更重要的是第二種,即調(diào)適性轉(zhuǎn)換。因?yàn)椋覀冞@里所講的話語轉(zhuǎn)換有一個(gè)前提,那就是話語所要表達(dá)的思想內(nèi)容本身的穩(wěn)定性,是在共同的思想內(nèi)容的基礎(chǔ)上如何選擇更好的話語表達(dá)的問題。因此,在這里話語轉(zhuǎn)換并不意味著拋棄原有的話語。這里有一種程度上的區(qū)別和伸縮空間。而程度上的大小是與宣傳教育的直接與間接有關(guān)的。在直接教育的場(chǎng)合,完全可以適用第一種話語。比如,對(duì)于黨內(nèi)的教育特別是干部教育來說,原原本本地學(xué)習(xí)馬克思主義,學(xué)習(xí)黨的領(lǐng)袖有關(guān)論述,這里基本不存在話語轉(zhuǎn)換的問題。因?yàn)楸旧淼哪繕?biāo)就是讓黨員干部原原本本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話語和我們黨的基本話語,并用這套話語來表達(dá)思想和認(rèn)識(shí)。但如果是對(duì)黨外普通民眾的宣傳教育,特別是對(duì)那些不熟悉和不習(xí)慣馬克思主義和黨的語言系統(tǒng),甚至對(duì)這些話語有一定逆反心理或偏見的群眾,只能進(jìn)行間接的甚至滲透式的教育。在這樣的情況下,思想政治教育者就不能照搬原有話語,而必須加以轉(zhuǎn)換,使之成為更容易為人們所接受的話語。
但是,不論是直接宣傳還是間接宣傳,不論是在怎樣程度上需要話語轉(zhuǎn)換,對(duì)于思想政治教育者來說,首先必須熟悉掌握原有的話語系統(tǒng),在此基礎(chǔ)上才能談得到話語的轉(zhuǎn)換,也才有可能實(shí)現(xiàn)從這種話語向另外話語的轉(zhuǎn)換。
二、思想政治教育話語轉(zhuǎn)換的基本路徑
談到話語轉(zhuǎn)換,必須涉及從什么話語向什么話語轉(zhuǎn)換的問題。這個(gè)問題應(yīng)該屬于話語轉(zhuǎn)換的路徑問題。轉(zhuǎn)換的路徑是多種多樣的,并不是只有一種路徑。對(duì)于不同的路徑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概括,本文認(rèn)為基本的路徑主要有以下三個(gè)方面。
1. 政治話語學(xué)理化
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一種以政治思想為核心的宣傳教育活動(dòng)。不論思想政治教育的內(nèi)容有多么廣泛,政治內(nèi)容都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政治內(nèi)容當(dāng)然是由政治話語來表達(dá)的,因而在思想政治教育話語中,政治性話語是不可缺少的,也是不能回避的。
政治話語本身也有自身的存在價(jià)值和獨(dú)有魅力。政治話語表達(dá)政治話題和政治內(nèi)容是恰當(dāng)?shù)模o不妥之處。這種表達(dá)最直接,最明確,也是自然而然就形成的。對(duì)于關(guān)注政治特別是熱心政治的人們來說,使用政治話語是理所當(dāng)然的,他們并不排斥。我們黨有自己的一套政治話語,它是我們黨的性質(zhì)、宗旨、綱領(lǐng)、路線、方針、政策的直接表達(dá)。這套話語系統(tǒng)十分嚴(yán)謹(jǐn)講究,只要看一下我們黨的文件,看一下領(lǐng)導(dǎo)人的講話,就會(huì)發(fā)現(xiàn)這種政治話語有其自身的邏輯和藝術(shù),具有自身的魅力。文件中每一句話,每一個(gè)表達(dá),都經(jīng)過反復(fù)推敲和打磨,力求得到最準(zhǔn)確而又最恰當(dāng)?shù)乇磉_(dá)。可以說,黨的文獻(xiàn)在文字表達(dá)上所下的功夫,遠(yuǎn)遠(yuǎn)超過普通人的寫作和學(xué)者的著述。因此,黨的政治話語并不是粗糙而沒有魅力的東西。只要去翻看一下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其中還有一些十分精彩的表達(dá)。因此,輕視甚至輕薄黨的文件語言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那么,為什么又要對(duì)政治話語進(jìn)行轉(zhuǎn)換呢?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群眾對(duì)政治都密切關(guān)注,事實(shí)上多數(shù)群眾對(duì)政治不太關(guān)注,不太敏感。對(duì)于那些并不關(guān)注政治,與政治保持著相當(dāng)距離的人來說,只用政治話語開展教育就很不夠了,而且存在著一定的話語錯(cuò)位。他們認(rèn)為政治與己無關(guān),因而對(duì)于政治話語提不起興趣。政治是社會(huì)公共生活的領(lǐng)域,政治話語與日常話語有所不同,對(duì)許多人來說有相當(dāng)?shù)木嚯x感。很多人只是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用日常話語來表達(dá)思想愿望,而對(duì)于政治化的說法難以準(zhǔn)確地理解。
其次,政治話語相對(duì)于日常生活而言確實(shí)有其枯燥的一面。這是因?yàn)椋h的文件雖然都有其重點(diǎn)所在和實(shí)際工作目標(biāo),但在話語表述上則講究全面性,以避免在實(shí)際工作的片面性。因此,它不僅要講一些新話,而且也要講許多舊話,講一些經(jīng)常需要講而講過許多遍的話。有同志總結(jié)文件的起草工作說,文件的構(gòu)成是三分之一的老套話,三分之一的新套話,加上三分之一的新話和連接詞。這種說法未必十分準(zhǔn)確,但它出自經(jīng)驗(yàn)者之手也確實(shí)反映了一定的實(shí)際情況。這樣,新老套話一起說,四平八穩(wěn),當(dāng)然不會(huì)太生動(dòng)。而且,政治話語尤其講究準(zhǔn)確,沒有權(quán)威出處的話不能隨便說,以避免誤解和誤會(huì)。因此,在政治話語上,準(zhǔn)確性是第一位的,生動(dòng)形象始終是第二位的。在許多情況下,為了確保表達(dá)的準(zhǔn)確,只能犧牲表達(dá)上的生動(dòng)。
最后,政治宣傳重復(fù)得多了,人們會(huì)失去新鮮感和興趣,甚至導(dǎo)致有些厭煩和逆反。[3]任何宣傳,包括政治宣傳,都不可避免地會(huì)有一定的重復(fù)。這種重復(fù)有兩種目的和作用,一是重復(fù)能夠加深受眾的印象,使其有更多的了解和接受;二是重復(fù)有助于擴(kuò)大受眾覆蓋面。因?yàn)閷?duì)于一件事情的宣傳工作,不論進(jìn)行得多么廣泛,通常也總會(huì)有一些沒有宣傳到的人。而為了讓更多的人接收到政治信息,有時(shí)就需要多講幾遍。這樣,在許多情況下政治宣傳往往偏多。特別是在我們這樣人口眾多而又層次多樣的國家,更是如此。經(jīng)常有這樣的情況:某種程度的宣傳對(duì)有些人來說是合適的,但對(duì)另一些人來說已經(jīng)過多了。對(duì)于這后一部分人來說,沒有必要再次重復(fù)政治話語,而最好是實(shí)行話語轉(zhuǎn)換。
另外,也有些人對(duì)政治宣傳往往有某種戒備心理甚至偏見,認(rèn)為出于政治需要進(jìn)行的宣傳教育往往有一定的水分,并不完全可靠。對(duì)于一些政治觀點(diǎn)完全不同的人來說,更可能對(duì)政治話語有直接的抵觸。
那么,政治話語應(yīng)該向什么方向去轉(zhuǎn)換呢?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向日常生活轉(zhuǎn)換,即實(shí)現(xiàn)政治話語的生活化。也就是說,打通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兩個(gè)領(lǐng)域。這樣當(dāng)然是對(duì)的,對(duì)許多人來說是適宜的。公共領(lǐng)域并不是與私人生活無關(guān)的領(lǐng)域,政治問題并不是與每個(gè)人的個(gè)人利益無關(guān)的,而是有著十分密切的關(guān)系。我們說政治是經(jīng)濟(jì)的集中體現(xiàn),并不是虛言。它與個(gè)人的經(jīng)濟(jì)利益及其實(shí)現(xiàn)密切相關(guān)。孫中山說過,政治是眾人之事。只要把政治加以生活化的還原,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它就是人群中實(shí)實(shí)在在的生活問題。由于有這種內(nèi)在的聯(lián)系,在這個(gè)基礎(chǔ)之上,只要把政治話語加以生活化的表述,就易于讓受眾了解政治。
但我們這里重點(diǎn)強(qiáng)調(diào)的還不是這個(gè)方面,而是政治話語的學(xué)理化或?qū)W術(shù)化。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yàn)檎卧捳Z的生活化已經(jīng)是大家的共識(shí),不必多講了;另一方面,是考慮到現(xiàn)在的受眾已經(jīng)有較高的文化水平,特別是對(duì)大學(xué)生和知識(shí)者來說的,政治與生活的聯(lián)系不成問題,僅僅從生活上去講政治,他們會(huì)覺得不滿足。因此,政治問題要上升到學(xué)理的高度,從學(xué)術(shù)上去把握和講解,就更有說服力。大學(xué)生和知識(shí)分子重視學(xué)術(shù),服膺學(xué)理,這是他們的長(zhǎng)處。對(duì)他們來說,黨中央說的話,黨的領(lǐng)導(dǎo)人說的話當(dāng)然是有政治權(quán)威,大學(xué)生也會(huì)承認(rèn)這個(gè)權(quán)威。但他們會(huì)從學(xué)理上去思考更深一層的東西,想弄清為什么。因此,政治話題如果是讓專家來發(fā)表意見,從學(xué)理上解說,用學(xué)術(shù)語言來闡釋,就會(huì)收到好的效果。其實(shí),對(duì)社會(huì)公眾來說,讓專家出場(chǎng)來解釋,工作效果也都比較好。這一方面是由于專家是內(nèi)行,他們是講道理的,另一方面則是人們相信專家更為公正和客觀。他們站在利益的局外,秉持學(xué)者的立場(chǎng),具有客觀性的追求,因而是值得信賴的。因此,近年來,電視節(jié)目中經(jīng)常有專家出現(xiàn),講解人們所關(guān)心的問題。特別是當(dāng)有重大政策推出的時(shí)候,或者發(fā)生突發(fā)性的事件而人們感到困惑的時(shí)候,就會(huì)請(qǐng)相關(guān)方面的專家做講解。而不是像從前那樣只由政治人物或思想政治工作者來講解。這也可以說是新時(shí)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個(gè)新現(xiàn)象和新特點(diǎn)。
專家的解說中總會(huì)出現(xiàn)一定的學(xué)術(shù)名詞和學(xué)術(shù)表述,這是不可避免的,也正是專家話語的重要特征。人們通過這些術(shù)語明白了事情本身的道理,就自然而然地信服了。當(dāng)然可能似懂非懂,但這并不妨礙聽眾的信賴。而且有時(shí)正好相反,正是這樣的術(shù)語在某種程度上的費(fèi)解體現(xiàn)的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性使人們對(duì)專家充滿了信心。當(dāng)然,必須注意一個(gè)程度和限度的問題。就是說,專家的學(xué)術(shù)術(shù)語不能太多,而是只占一少部分,起某種點(diǎn)綴性作用。因?yàn)楫吘箤<也皇窃谙蛲姓f話,而是向公眾說話。如果專家的話語完全是聽眾所不懂的學(xué)術(shù)話語,那就妨礙了受眾的理解,也進(jìn)而影響人們對(duì)專家的信任。
2. 學(xué)理話語通俗化
學(xué)術(shù)話語或?qū)W理話語在說理上具有優(yōu)勢(shì),但是這種話語本身也具有兩面性的,有些情況下它本身也需要做一定的話語調(diào)適,甚至向其他話語轉(zhuǎn)化,特別是向通俗化話語轉(zhuǎn)化。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通常會(huì)包括著一定的學(xué)理性的內(nèi)容和話語。思想政治教育是講道理的,而道理不僅是普通人在生活中得到的那種經(jīng)驗(yàn)性質(zhì)的道理,也有由思想理論家提出并經(jīng)專家學(xué)者研究過的更深刻的道理。這樣的道理就具有學(xué)術(shù)的形式和理論的形式,呈現(xiàn)為學(xué)理性話語。我們黨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只是有一些政治思想和政治話語,而且也具有理論話語和哲學(xué)話語,體現(xiàn)出很強(qiáng)的學(xué)理性。這主要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話語。具有理論性和學(xué)術(shù)性話語的教育內(nèi)容,這是我們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優(yōu)勢(shì)。這是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理論水平的體現(xiàn),也是后世馬克思主義者長(zhǎng)期以來學(xué)術(shù)成就的結(jié)晶。并不是任何一個(gè)社會(huì)或社會(huì)群體的思想政治教育都能夠具有如此高層次的理論水平和學(xué)術(shù)化程度。思想政治教育內(nèi)容以這樣的學(xué)理性為基礎(chǔ),為我們?cè)鰪?qiáng)思想政治教育自信提供了重要的支撐。而對(duì)于受教育者來說,他們能夠?qū)W會(huì)一定的學(xué)術(shù)話語,并用以分析和解決問題,這也是他們學(xué)習(xí)樂趣和成就感的重要來源。
但是,學(xué)理性話語在面向大眾時(shí),也有其局限性。一是不夠通俗,不易為人們所理解。有些術(shù)語過于抽象,習(xí)慣于日常思維的群眾不易掌握。特別是現(xiàn)在微觀經(jīng)濟(jì)學(xué)大行其道,其中有些術(shù)語遠(yuǎn)離日常語言,令人不知所云。而一旦被生活點(diǎn)破,又令人啼笑皆非。比如所謂“流動(dòng)性”,其實(shí)就是“活錢”;所謂“量化寬松”,其實(shí)就是“印錢”。二是不夠生動(dòng),有一定的枯燥性。學(xué)術(shù)話語首先講究的是嚴(yán)謹(jǐn),它的術(shù)語要有一定的概括性,要超越于具體現(xiàn)象之上;它的表達(dá)要盡可能完整嚴(yán)密而沒有漏洞,等等。這樣,它的生動(dòng)性和形象性就必然受到影響。盡管它會(huì)有一種嚴(yán)謹(jǐn)?shù)拿阑蜻壿嫷镊攘Γ挥猩贁?shù)人搞專業(yè)人的才能享受得到,而多數(shù)非專業(yè)人士特別是普通群眾是感受不到的。三是不夠親和,它是冷靜的,但又是冷漠的,感性和情感不足,有時(shí)甚至還有一種高高在上的傲慢。特別是長(zhǎng)篇大論的學(xué)術(shù)話語,似乎有一種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味道。四是不夠透明,它有時(shí)候會(huì)被個(gè)別所謂專家用來蒙蔽群眾。有的人出于私人目的,故意把本來比較明了的問題弄得云山霧罩,以達(dá)到欺騙和愚弄群眾的目的。由于這些方面的原因,學(xué)術(shù)話語對(duì)思想政治教育又有不利的影響。
學(xué)理性話語最初也是來源于實(shí)際生活,但它經(jīng)過了學(xué)術(shù)共同體的加工和提煉,與生活語言拉開了一定的距離。而當(dāng)這種距離不斷拉大時(shí),就可能使這些術(shù)語成為學(xué)院小圈子中的語言,而與生活之間形成一道鴻溝。比如哲學(xué)語言,特別是西方哲學(xué)派別的哲學(xué)語言,已經(jīng)成為普通人根本無法看懂得的行話和黑話。馬克思當(dāng)年就尖銳批判過德國古典哲學(xué)的唯心主義思辨語言。馬克思說:“哲學(xué),尤其是德國的哲學(xué),喜歡幽靜孤寂、閉關(guān)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觀……從哲學(xué)的整個(gè)發(fā)展來看,它不是超然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門外漢看來正像脫離現(xiàn)實(shí)的活動(dòng)一樣稀奇古怪;它被當(dāng)做一個(gè)魔術(shù)師,若有其事地念著咒語,因?yàn)檎l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4]120這樣的學(xué)理話語就成為隔絕學(xué)術(shù)與生活的高墻。
學(xué)理性話語有必要向通俗化方向轉(zhuǎn)換。這種轉(zhuǎn)換有兩種情況:一是對(duì)這種話語做出通俗性的解釋和說明,以便于人們學(xué)習(xí)和掌握這種學(xué)理話語。比如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中有些術(shù)語,在教育教學(xué)過程中需要老師做出一定的解釋,以使人們有更好的理解。顯然,這種轉(zhuǎn)換是一種局部性的轉(zhuǎn)換。二是直接用通俗性話語表替代學(xué)術(shù)話語,將學(xué)術(shù)話語消解于無形。這是一種全面性的話語轉(zhuǎn)換。不論是哪種情況,都需要將學(xué)理話語通俗化。
通俗化就是將深?yuàn)W晦澀的學(xué)術(shù)語言轉(zhuǎn)化為受教育者所熟悉的簡(jiǎn)單明了的語言,使人們明白和掌握其中的道理。這種轉(zhuǎn)換主要是將學(xué)術(shù)語言轉(zhuǎn)換為非學(xué)術(shù)語言,特別是轉(zhuǎn)換為生活化的日常語言。用人們?nèi)粘I钪兴煜さ牡览砗驼Z言來解說理論和學(xué)術(shù)的話語。當(dāng)然,并不是所有的學(xué)術(shù)術(shù)語都同樣難懂,也并不是要避免所有的學(xué)術(shù)術(shù)語。有些必要的和無法避免的學(xué)術(shù)術(shù)語,也可以為人們所接受,并成為人們?nèi)粘T捳Z的一部分。在這樣的情況下,它就完成了自身的一種轉(zhuǎn)換。
通俗化不只是一個(gè)簡(jiǎn)單的語言替換問題,而是一個(gè)對(duì)學(xué)術(shù)成果進(jìn)行重新表述的問題。這首先就需要對(duì)學(xué)術(shù)成果有透徹的整體性的理解,只有在此基礎(chǔ)上才能真正實(shí)現(xiàn)通俗化,同時(shí)又避免庸俗化。在這種轉(zhuǎn)化中,思想的本質(zhì)沒有改變,思想的品格也沒有變異,但它的形態(tài)改變了。而思想依賴于表達(dá),當(dāng)表達(dá)改變了時(shí)候,思想本身也很容易一起跟著改變。因此,通俗化本身隨時(shí)伴著一種危險(xiǎn)性,即庸俗化的危險(xiǎn)性。通俗化與庸俗化雖只有一字之差,但具有性質(zhì)上的不同。其基本區(qū)別在于,在對(duì)學(xué)術(shù)成果進(jìn)行生活化和簡(jiǎn)單化的重新表述的時(shí)候,是否因此而降低了思想理論的品格,是否矮化和歪曲了原有的理論觀點(diǎn)。通俗化的結(jié)果雖然降低了表述的復(fù)雜性和難度,但沒有降低理論應(yīng)有的品格和品質(zhì);而庸俗化則是將高級(jí)思想變成低級(jí)思想,將高水平的東西變化為低水平的東西,將高價(jià)值的東西變成低價(jià)值的。經(jīng)過庸俗化的轉(zhuǎn)化,正面的價(jià)值可能變成了負(fù)面的,崇高理想的變成了低俗的東西。現(xiàn)在有人很善于這樣的“惡搞”,故意使通俗變成庸俗,以此嘲弄崇高、褻瀆神圣,是值得注意的。因此,真正把理論通俗化,把學(xué)術(shù)話語轉(zhuǎn)化為通俗話語,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dòng),是一種創(chuàng)新性的轉(zhuǎn)化。
3. 通俗話語趣味化
通俗性話語自然是有益的,它特別有助于人們的理解和接受。但正像任何一種話語類型都有其優(yōu)點(diǎn)和不足一樣,通俗性話語也是如此。它一方面可能缺少一定的權(quán)威性。平常的東西,簡(jiǎn)單的道理,往往不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過于容易而沒有難度,對(duì)人的思維沒有高一點(diǎn)的要求,沒有一定的問題刺激,也會(huì)減少人們的興趣。另一方面可能的不足之處,就是淡而無味。像白開水一樣,雖然也能解渴,但總是沒有大的味道。通俗的一般是比較平常和平淡的,平淡并不都是壞事,特別是高境界的平淡是很不易達(dá)到的。但是平淡也往往缺乏味道,而不易引起人們的興趣。有的人講話固然是很通俗,但是像一篇流水賬,沒有什么吸引力。這兩種情況都需要對(duì)通俗化話語實(shí)現(xiàn)再轉(zhuǎn)化,特別是實(shí)現(xiàn)通俗話語的趣味化。
我們看到,有些著名的演講家和具有高超思想教育藝術(shù)的人,他們的通俗話語都不是平淡無味的,而是具有很強(qiáng)的趣味性。比如毛澤東,他的講話和文章一般都是通俗易懂的,但同時(shí)也很有趣味,讓人愛聽愛看,具有很強(qiáng)的吸引力。
那么,這種通俗語言的趣味性來自哪里呢?其中包括著什么要素呢?大致說來,一是思想性,有一定的思想內(nèi)涵,這樣思想的魅力就會(huì)體現(xiàn)在話語上。語言是思想的表達(dá),離開了思想本身,話語就沒有了靈魂。而只要是有靈魂的話語,即使再平凡和平淡,也是淡而有味的,是不平凡的。我們傳統(tǒng)文化中很講究寫文章,特別是追求一種雋永的風(fēng)格,就是淡而有味。當(dāng)然這里的味不是思想,而是意境。二是幽默感,使人發(fā)出會(huì)心微笑。幽默感是什么不容易說得清,但它不是一種小的語言技巧,不是玩世不恭,而是熱愛生活的,是生活智慧的體現(xiàn)。林語堂說過,智慧不足的人沒有幽默,而只有滑稽;智慧剛好夠用而沒有富余的人也沒有幽默,而只有一本正經(jīng);只有智慧足夠而有盈余的人,才有幽默,因?yàn)橛哪侵腔鄣淖匀涣魈省_@種說法具有啟發(fā)性。三是形象化表達(dá),運(yùn)用形象思維來配合抽象思維,把抽象道理形象化。其中包括故事性敘述,有一定情節(jié),說明一定道理。比如運(yùn)用歷史上或文化藝術(shù)中的典故。比喻也是一種生動(dòng)形象的表達(dá)方式。古代的思想家們善用比喻來講述哲理,留下很多名篇名言。同樣,毛澤東也善用比喻,他的著述和講話中有著大量的精彩比喻,給人以深刻啟迪和教育。
不論是思想性、幽默感還是形象化,都是既可學(xué)又不可學(xué)的。一方面它們具有不可學(xué)的一面,帶有一定的天生素質(zhì)和智力特征的性質(zh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思想家的潛質(zhì),或都具有比較深刻的思想能力;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幽默感,即使是許多很有才華的人,其實(shí)也并不幽默;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做到語言形象化,因?yàn)橛械娜瞬⒉簧瞄L(zhǎng)形象思維。所有這些方面都具有不可學(xué)或不容易學(xué)的一面。但這并不是說,我們只能望洋興嘆,而沒有學(xué)習(xí)進(jìn)步的余地。多學(xué)理論多思考,自然有助于提高思維能力和思想水平。更加開闊胸懷,更深刻地體驗(yàn)生活,多接觸幽默好玩的作品,自然也能增強(qiáng)自己的幽默感。至于形象化思維和表達(dá)的能力,也可以經(jīng)過提高自己的文學(xué)藝術(shù)修養(yǎng)而有所提高。
三、思想政治教育話語轉(zhuǎn)換的其他路徑
以上所述是話語轉(zhuǎn)換的一些基本路徑。除了基本的路徑之外,還有一些非基本的路徑,也是需要注意的。比如書面話語的口語化、剛性話語的柔性化、熟悉話語的陌生化等等。
1. 書面話語口語化
書面話語與口頭話語有明顯的區(qū)別。書面話語是寫在書上或文章上的話語,盡管也有人用口語化語言來寫作,特別是文學(xué)作品,但作為正式的論著,通常其語言有規(guī)范性的要求,是與日常口語明顯不同的。它要求用規(guī)范的術(shù)語和語式來表達(dá),它講究表達(dá)的專業(yè)性、邏輯性和嚴(yán)謹(jǐn)性等。教材雖然不是論著,但它的編寫通常也是規(guī)范性的,使用的是書面化語言。可以說,它是一種特殊的書面化語言,主要是用大家公認(rèn)的語言來嚴(yán)謹(jǐn)?shù)乇磉_(dá)理論知識(shí),并顧及教學(xué)思路上的需要。有人稱這種語言為“教材語言”或“教材話語”。這種教材式語言可以用于教材的備課,也可以用于學(xué)生的研讀,但是不可以直接適用于課堂講授。如果照本宣科,把教材語言在課堂上重復(fù)一遍,是不會(huì)有好的教學(xué)效果的。為此還必須轉(zhuǎn)換為口語化的表達(dá),化為課堂話語。這里面就有一種轉(zhuǎn)換,是從書面語向口語的轉(zhuǎn)換。
這種轉(zhuǎn)換當(dāng)然不僅限于課堂上。在其他場(chǎng)合的宣傳教育中,特別是面對(duì)面的宣傳教育中,包括利用媒體的宣講中,都不能照搬書面化語言,而必須轉(zhuǎn)換為口語表達(dá)。口語化表達(dá)具有多方面的優(yōu)點(diǎn):一是簡(jiǎn)明通俗。書面語通常比較冗長(zhǎng),話語構(gòu)造比較復(fù)雜,而口語通常句式簡(jiǎn)短,能夠有效減輕人接受難度和理解負(fù)擔(dān);二是生動(dòng)活潑。書面語通常是比較嚴(yán)肅的,而口語則相對(duì)靈活,又帶著語氣,現(xiàn)場(chǎng)感強(qiáng),便于與對(duì)象互動(dòng),能夠活躍氣氛;三是具有個(gè)性化風(fēng)格。如果說書面語往往是統(tǒng)一的規(guī)范的,那么口頭語則往往是多樣化的。不同的人說話風(fēng)格不一樣,這些自然地都反映在口語表達(dá)中。而這些多樣化的風(fēng)格中,肯定會(huì)有一些特別受人歡迎的風(fēng)格。另外,在用于宣傳教育的書面材料的寫作上,也可以采用口語化的方式。比如理論讀物、輔導(dǎo)材料、報(bào)紙文章等,都可以口語化表達(dá)。當(dāng)然在這種表達(dá)中,當(dāng)然也要注意一定的規(guī)范性要求和藝術(shù)性。
2. 剛性話語柔性化
話語的屬性中還有剛與柔的區(qū)別。我們也許不容易從理論上去界定和劃分這兩類話語,但人們通常在實(shí)際生活中能夠感受到二者的區(qū)別。這兩種話語并無好壞之分,不能說某種絕對(duì)好,另一種絕對(duì)不好。可以說各有其優(yōu)點(diǎn)和不足,而且二者也可以相互補(bǔ)充、相輔相成。問題是把握好各自的度。剛性話語比較嚴(yán)謹(jǐn)嚴(yán)肅,比較正規(guī),比較理智,也比較有力量,但如果用得多了,人們就會(huì)覺得不夠溫暖,缺少親和力。同樣,柔性話語給人以心靈的慰藉,感情上的溫暖,能夠撫慰人的心理,但如果用得太多了,也會(huì)讓人覺得缺少陽剛之氣,缺少穿透力。在實(shí)際的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究竟用什么樣的話語更合適,取決于當(dāng)時(shí)當(dāng)?shù)氐那闆r,取決于所面對(duì)的對(duì)象的特征和需要,并不能先驗(yàn)地加以確定和固守。
從通常的情況看,我們的教育內(nèi)容表達(dá)還是剛性話語較多。因?yàn)槲覀冊(cè)谒枷肷鲜巧鐣?huì)本位,不是個(gè)人本位,那么關(guān)于社會(huì)的方方面面的理論觀點(diǎn)的論述,特別是那些追求理論嚴(yán)謹(jǐn)和嚴(yán)肅性的內(nèi)容,往往顯得剛性十足,給以人生硬的感覺。黨的文件是思想政治教育內(nèi)容的重要來源和文本體現(xiàn),由于其自身的屬性,往往也是嚴(yán)肅性有余,個(gè)性化不足的。特別是其中結(jié)論性和要求性話語較多,而論證性和說明性的話語較少。更不用說國家的法律條文了,那更是嚴(yán)肅嚴(yán)謹(jǐn)。因此,為了有效地開展這些相關(guān)內(nèi)容的宣傳教育,就需要對(duì)剛性話語做適當(dāng)調(diào)適和處理,實(shí)現(xiàn)從剛性話語向柔性話語的轉(zhuǎn)換。這并不是說所有的剛性話語都要不得,都要轉(zhuǎn)換成柔性的。這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而且事實(shí)上也是有害無益的。而是說,對(duì)某些表述進(jìn)行適當(dāng)程度的柔性化,使理性和感性,陽剛之氣和溫柔體貼之間有一個(gè)平衡。現(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可以看到,黨的一些文件中已經(jīng)開始出現(xiàn)某些柔性的話語,雖然不多,但很突出亮眼,給人一種溫暖感。比如在培育和踐行社會(huì)主義核心價(jià)值觀的文件中,就有一個(gè)很好的柔性詞匯“涵養(yǎng)”。當(dāng)我們說“打造核心價(jià)值觀”時(shí),就顯得過于生硬,而當(dāng)我們說“涵養(yǎng)核心價(jià)值觀”時(shí),就感覺舒適多了。
3. 熟悉話語陌生化
話語的熟悉和陌生也是一對(duì)矛盾。一般來說,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講人們所熟悉的話語。這一方面是教育者熟練表達(dá)自己思想觀點(diǎn)的需要,因?yàn)橹挥杏米约鹤钍煜さ恼Z言才能達(dá)到最好的表達(dá)效果。另一方面,這也是受教育者所需要的。只有用受教育者所熟悉的語言和話語,才能更容易地為他們所了解和理解。因而,要盡可能避免一些大家覺得陌生的話語。
但是,這并不是絕對(duì)的。過于熟悉的話語往往使人缺少新鮮感,缺少話語上的刺激,不容易引起人們的關(guān)注。而在熟悉話語中適當(dāng)?shù)卦黾右稽c(diǎn)陌生詞語,就會(huì)起到很好的提醒和醒目的作用。對(duì)一些為人們所熟悉的說法加以改變,用另一種說法來表達(dá),也能起到這樣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陌生化有一種效果,就是能夠拉開認(rèn)識(shí)主客體之間的一定距離,使主體能以新的眼光重新審視那些司空見慣的東西。在太熟悉的環(huán)境中,人們往往物我合一、物我兩忘,對(duì)許多事情習(xí)焉不察。而適度的陌生化則能使人們從中警醒過來,恢復(fù)判斷力。
因此,有些情況下,當(dāng)我們所進(jìn)行的教育已經(jīng)很多,甚至受教育者已經(jīng)聽得厭煩的時(shí)候,就應(yīng)該更換表達(dá)形式,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由熟悉話語向陌生話語轉(zhuǎn)換。用一些并不太常用的新語匯,新說法,來表達(dá)已有的思想觀點(diǎn),這樣至少從語言上能起到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有的同志認(rèn)為,只要我們的觀點(diǎn)沒有改變,就沒有必要用不同的話語來表達(dá)同樣的東西。這當(dāng)然并非完全沒有道理,因?yàn)楦匾氖撬枷敫拢皇侨藶榈刈儞Q新名詞,但道理還有另一方面,就是我們不能總是用相同的話語來表達(dá)相同的意思,而是要適當(dāng)?shù)刈⒁庠捳Z更新,用話語的陌生化來激起人們的新鮮感和好奇心,從而提高人們的興趣。
參考文獻(xiàn):
[1]劉建軍.論思想政治工作的十八個(gè)轉(zhuǎn)變[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8(4):1319.
[2]沈壯海.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2008.
[3]劉建軍,楊巧.創(chuàng)新思想政治工作的四個(gè)思路[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2(4):1419.
[4]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責(zé)任編輯:陸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