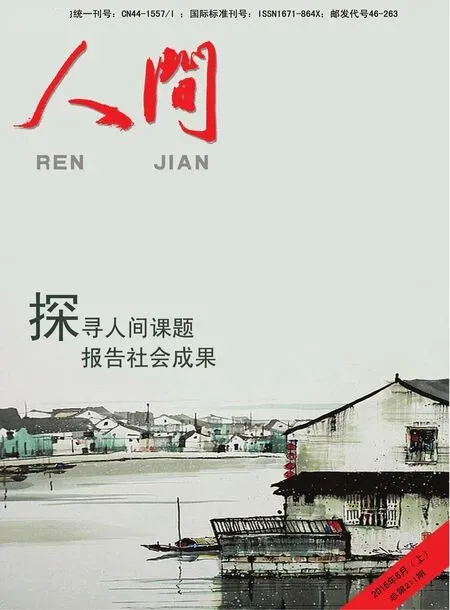論刑事訴訟中法官的庭外調查權
劉樹檳 張云霄(河北大學政法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0)
?
論刑事訴訟中法官的庭外調查權
劉樹檳張云霄
(河北大學政法學院,河北 保定071000)
摘要:法官的庭外調查權是很多大陸法系國家一項很有特色的法律規定。研究該規定有助于發展和完善我國刑事訴訟程序。本文運用多種方法探討了法官親自開展庭外調查的理論及實踐問題,目的在于反思我國現行的相關法律制度,提出我國法官庭外調查權的重構設想。
關鍵詞:庭外調查權;必要性;訴訟模式;完善
一、我國法律對法官庭外調查權的規定
廣義的法官庭外調查權,是指法官在整個審判階段,對客觀情況進行考察、驗證、取證的權力,具體包括文件資料查閱權、傳喚證人和要求出具證言權、臨時處置權、成立調查小組權等。其分為開庭前的調查、審理中的調查和評議中的調查三類。我國刑事訴訟法僅規定了審理中的庭外調查,因此本文將法官庭外調查界定為:在開庭審理過程中,法官依照辯護人的申請,按法定程序,收集、調取證據;或者對庭審中存有疑問的證據,在休庭后予以調查核實的訴訟活動的總稱。簡單說,就是在開庭過程中,由于存在法定的事由,法官對與案件有關的事實和證據問題,采取法定的方法,在法庭以外的其他地點所作的有關調查活動。
我國2012年新刑訴法對庭外調查規定略顯籠統。我國延續了大陸法系的職權主義訴訟模式,刑事審判主要圍繞“實體公正”展開,法官庭外調查權要求法院作為刑事審判的主體,除了承擔刑事審判的任務,還要承擔一定的調查取證任務。新刑訴法中涉及法官庭外調查的內容有:第三十九條規定了“辯護人認為在偵查、審查起訴期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收集的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材料未提交的,有權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調取”;第五十條規定了“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第一百九十一條規定了“法庭審理過程中,合議庭對證據有疑問的,可以宣布休庭,對證據進行調查核實,人民法院調查核實證據,可以進行勘驗、檢查、查封、扣押、鑒定、查詢、凍結”。同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2012年12月出臺的司法解釋也對庭外調查作了簡要的涉及。
由此可見,2012年新刑事訴訟法在繼續保留法官庭外調查權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了法官庭外調查權力的內容,在第一百九十一條增加了“查封”的調查方法。這也使得我國的法官庭外調查,不僅涉及案件事實、證據及適用法律等全部實體內容,而且涉及人身、財產等各項權利,從很大程度上關乎控訴和辯護的成敗。然而,縱觀整部刑訴法及兩高司法解釋,卻沒有對庭外調查如何“合理、正當”行使進行詳細的法律規制,對其基本程序沒有作出明確、完整的預置,這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二、法官庭外調查權存在的必要性
(一)法官有庭外調查權適合我國目前的訴訟模式。傳統上,我國采取的是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現行的刑事訴訟法適當地吸收了當事人主義的一些合理因素,建立了由職權主義和當事人主義相融合的一種“混合式”的訴訟模式,但這種訴訟模式仍帶有較為濃厚的職權主義色彩,因而純粹的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中的法官完全“消極中立”在我國還不能夠實現。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以控辯雙方的平等對抗為特征,它以擁有高素質的辯護律師為前提,而在我國目前的律師制度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取消法官的庭外調查權,則會使被告人處于更為不利的境地。此外,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下的法官完全消極中立也存在其固有的弊端。因此,在現實的條件下,保留法官的庭外調查權更適合我國的訴訟模式,更符合我國的國情。
(二)法官的地位決定了其庭外調查權的合理性。司法獨立與法官中立是一項公認的刑事訴訟原則。但法官保持消極中立必須要有相關的配套制度的保障。如英美等國家的法官處于完全消極中立的地位,但這是以其擁有完備的庭前準備程序、完善的被告人保護制度、強大的律師辯護與調查取證能力、庭審中直接言詞原則的貫徹為前提的,在這些配套制度的保障下,控辯雙方能夠平等對抗,被告人的利益獲得了相當的保護,法官才能保持其中立的地位而不再承擔庭外調查的任務。而我國相關的配套制度的缺失和不健全決定了在我國刑事訴訟中法官不可能完全消極中立,在必要時需要進行庭外調查來查明案件事實并保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三、關于我國法官庭外調查權的完善
(一)嚴格限制法官主動庭外調查。法官庭外調查極易侵犯當事人特別是被告人的訴權,有僭越法官中立原則之嫌,我們必須嚴格限制法官庭外調查的啟動:第一,當且僅當有利于被告人的情況,法官方可主動啟動庭外調查;第二,禁止法官庭外調查有關被告人有罪、罪重的事實和證據,取消刑訴法第五十條關于審判人員收集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證據的規定。刑事訴訟證明責任規定:“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民檢察院承擔”,法官主動調查被告人有罪、罪重的事實和證據,明顯與刑事訴訟證明責任相悖。
(二)明確法官行使庭外調查權的界域。結合我國當前司法實踐,立法應當明確庭外調查在下列情況下啟動:第一,辯護人當庭提出調取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的申請,法官審查后認為該證據可能影響正確定罪量刑的;第二,雖未經辯護人申請,但合議庭認為有利于被告人的新證據應當調取而沒有調取的;第三,對在庭審中經控辯雙方舉證、質證后仍然有疑問、確有調查核實必要的;第四,需要對庭審中提出的排除非法證據的必要性進行調查核實的;第五,需要對庭審中提出的回避申請進行調查核實的;第六,其他需要庭外調查核實的程序性問題,如辯護人是否享有辯護資格、訴訟代理人是否享有代理權限問題等等。
(三)庭外調查法官與庭審法官分離。庭外調查法官與庭審法官分離,防止先入為主。如果法官在調查中過多地接觸尚未開庭審理的事實和尚未舉證、質證的證據,難免會在調查中形成對裁判結果的內心預斷,導致之后的刑事庭審程序形式化,最終影響案件的公正處理。因此,可以借鑒國外預審法官制度,將執行庭外調查的法官與主持庭審的法官分開,不僅可以保證庭外調查的順利進行,還可以防止主審法官在庭外調查中形成先入為主、不客觀、不冷靜的判斷。
參考文獻:
[1]楊福慶.淺析刑事法官的庭外調查權[J].現代交際,2013(12).
[2]楊明.人民法院刑事庭外調查權重構[J].遼寧大學學報,2003(1).
[3]李奮飛.刑事訴訟中的法官庭外調查權研究[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4(1).
[4]費蓬煜,任學婧. 法官庭外調查權與其中立角色的維護[J].人民論壇,2013(11).
中圖分類號:D92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64X(2016)06-0056-01
作者簡介:
劉樹檳,1990年5月,男,漢族,祖籍河北滄州人,碩士在讀,現就讀于河北大學政法學院訴訟法專業
張云霄,1990年2月16,女,漢族,祖籍河北省邯鄲市邯鄲縣,碩士在讀,就讀于河北大學政法學院訴訟法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