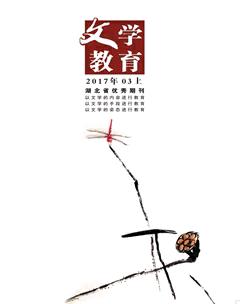論菲茨杰拉德筆下男主人公的形象延續(xù)
張曦萍
內(nèi)容摘要:菲茨杰拉德筆下創(chuàng)造的男主人公,總是對他自身的生活經(jīng)歷與美國的社會和歷史有所折射,因此在某些方面也有著明顯的共通之處。施塔爾與蓋茨比(分別出自《末代大亨的情緣》和《了不起的蓋茨比》)兩位主人公在這方面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且在形象上有著明顯的延續(xù)關(guān)系,與此同時(shí),施塔爾對蓋茨比形象的延續(xù)也反映出了作者人生和創(chuàng)作上的變化。論文擬從兩部作品主人公的性格、身份地位,以及象征意義與情感寄托等幾個(gè)方面來窺探菲茨杰拉德所塑造的角色形象,并試圖闡釋兩個(gè)角色之間的區(qū)別與形象延續(xù)的聯(lián)系。
關(guān)鍵詞:菲茨杰拉德 蓋茨比 施塔爾 形象
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1896-1940)是美國文學(xué)史上“第二次繁榮”的歷史階段中一顆耀眼的明星。這個(gè)優(yōu)點(diǎn)與缺點(diǎn)都異常明顯的年輕人,努力在他短暫的生命中創(chuàng)造史詩般的輝煌。他在僅二十年的創(chuàng)作生涯中,留下了五部長篇小說及160多篇才情恣肆的短篇小說,真實(shí)地再現(xiàn)了二十世紀(jì)二三十年代美國的社會生活以及人們的精神世界,他筆下的世界幾乎就是他本人的生活,他塑造了大量與自己以及身邊人相近的人物形象。
與所謂的“爵士時(shí)代”同時(shí),“美國夢想”就像一只被薩克斯風(fēng)吹起的氣球,飄在空中卻仿佛是伸出雙手就可以得到,讓人們覺得,只要你有才華,命運(yùn)就在你的掌握之中。菲茨杰拉德自己也成為了這一場爵士盛宴中盡情角逐歡樂的一個(gè),同時(shí)也是最清醒的一個(gè)。他在參與一場又一場的盛宴的同時(shí),又扮演了旁觀者的角色,將這一切以自己的深刻理解與體會記錄下來,并給予評判。分別出自《了不起的蓋茨比》及《末代大亨的情緣》的兩個(gè)男主人公——蓋茨比和施塔爾,便是菲氏為這個(gè)時(shí)代塑造的兩個(gè)杰出代言人。
一
菲茨杰拉德對人物的描寫總是印象式的,他不去描繪一個(gè)人物具體的、實(shí)在的外表,而是擅長抓住他們的精神實(shí)質(zhì)來塑造其性格——無論蓋茨比還是施塔爾,都是如此。
蓋茨比原名杰姆斯·蓋茨,“他是在十七歲時(shí)改名換姓的,也是在他一生事業(yè)開端的那個(gè)特定時(shí)刻……”i在他的心里,他不愿意承認(rèn)自己的父母,因?yàn)樗麄兟德禑o為,貧困潦倒。他對自己后來身份的塑造,來自自己柏拉圖式的理念:“他是上帝的兒子,——這個(gè)稱號,如果真有什么意義的話,就是字面的意思——因此他必須為他的天父效命,獻(xiàn)身于一種博大、庸俗、華而不實(shí)的美。因此他虛構(gòu)的恰恰是一個(gè)十七歲的小青年很可能會虛構(gòu)的那種杰伊·蓋茨比,而他始終不渝地忠于這個(gè)理想形象。ii”
在離家奮斗的那些日子里,他四處奔波,為了生計(jì),干著各種雜事。盡管生活辛苦,可他的內(nèi)心卻經(jīng)常處于激蕩不安之中,他日夜幻想著自己也可能會擁有的絢爛的生活,并且每一天都在為自己幻想中的那個(gè)世界增添新的內(nèi)容。他經(jīng)常莫名的自我陶醉,有時(shí)甚至達(dá)到驚人的程度,覺得擁有幻想事物理所當(dāng)然。但他又不是一個(gè)純粹的空想家,他從小為自己制定了各種計(jì)劃:鍛煉、學(xué)習(xí)、工作、練習(xí)演說和矯正儀態(tài),他一直充滿決心要出人頭地,去追求他的“美國夢”。
蓋茨比是一個(gè)實(shí)踐型的夢想家,同時(shí)也是一個(gè)不切實(shí)際的浪漫主義者。他固執(zhí)地相信過去可以追回,愛情可以重來。他富于幻想的性格使他將黛西塑造成了最高的夢想,不斷的癡迷追尋。在湯姆與蓋茨比爭吵的情節(jié)中,蓋茨比身上那種“虛弱無能的真摯性”爆發(fā)出來,一個(gè)男人承認(rèn)了自己內(nèi)心情感的時(shí)刻,就是他最最無能的時(shí)刻,仿佛不降低自己的男人姿態(tài),就無法表達(dá)自己的情感。于是蓋茨比的浪漫又被打上了一絲女性性格的特征。
與蓋茨比不同,施塔爾身上沒有任何明顯的、可供人挑剔的弱點(diǎn)。正如他在原文中“Starh”這個(gè)與“Star”(明星)讀音相同的名字一樣,施塔爾從一出場就是一顆耀眼的明星,是一個(gè)創(chuàng)業(yè)成功的代表。
菲茨杰拉德一生都在崇拜英雄,但在他四十歲前,從未創(chuàng)造出一個(gè)無可挑剔的英雄形象來,門羅·施塔爾是第一個(gè),也是有成功事業(yè)背景的一個(gè)。他以前的作品中,布萊恩(《人間天堂》的男主人公)和安東尼(《美麗與毀滅》的男主人公)都沒有職業(yè);蓋茨比的經(jīng)商活動有些見不得人;迪克·戴夫(《夜色溫柔》的男主人公)中途放棄了自己的事業(yè)。只有施塔爾,把精力投入電影行業(yè),承擔(dān)著各種責(zé)任,也獲得了巨大的聲譽(yù)。他既不像布萊恩一類的角色,每日揮霍無度;也不像蓋茨比一樣,經(jīng)營著一份破了產(chǎn)的感情。
尤其不同的是,施塔爾不像菲茨杰拉德其它長篇小說中的男主人公,性格偏女性化。相反,他是一個(gè)絕對強(qiáng)勢的男主人公形象,因此更加吸引那些已經(jīng)熟悉了菲茨杰拉德慣常風(fēng)格的讀者。“他站在那兒(雖然個(gè)子不高,但看上去總是那么高大),審視著他那個(gè)世界的紛繁復(fù)雜的事物,就像一個(gè)年輕而自豪的牧羊人,對他而言,日和夜都無關(guān)緊要。他生來就不睡覺,沒有休憩的才分,也沒有那種欲望。iii”在人們的眼中,他從年輕時(shí)代就有著出眾的能力,而且比一般人都更努力。
在腐敗之風(fēng)盛行、商業(yè)氣息濃重的好萊塢,他蔑視票房的價(jià)值,愿意用更有價(jià)值的作品去換取大眾的信任,甚至對觀眾也抱有一種責(zé)任感。他在工作中處處體現(xiàn)著自己的英雄氣概與出色的領(lǐng)導(dǎo)才能。同時(shí),他對自己手下的工作人員富有同情心,充滿人情味。他愿意耗費(fèi)寶貴的時(shí)間,解決演員對性無能的恐懼;耐心地指導(dǎo)編輯編寫劇本,向自己想要得到的效果靠近;他還非常關(guān)心攝影師的健康狀況。他處理事情并不優(yōu)柔寡斷,而是善謀善斷,他果斷地撤掉無法控制片場的導(dǎo)演里德·雷丁伍德,并找到合適的替代人。正因?yàn)樗^耀眼,遭人嫉妒,也不為電影界的上層人物容忍。
除此之外,蓋茨比與施塔爾兩者性格中還存在著對人際關(guān)系“商品化”不同的傾向。隨著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大行其道,金錢在社會中發(fā)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許多人開始將身邊的事物進(jìn)行物化考量,人際關(guān)系開始出現(xiàn)異化。這種異化就體現(xiàn)在,人們認(rèn)為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就是利用與被利用,可以用金錢來解決彼此間的一切事情,從而淡化了親情、愛情與友情。
蓋茨比在處理人際關(guān)系時(shí),多多少少的反應(yīng)出“人際商品化”對他的影響。他在最初找到尼克幫忙時(shí),首先不是考慮僅憑他們的友誼,尼克就可以邀請黛西到場;而是考慮尼克答應(yīng)幫忙后,給尼克什么“好處”。其次,蓋茨比在用奢華的物件顯示自己身價(jià)的同時(shí),還有意用他人來映襯自己的風(fēng)光,這一點(diǎn)在他向黛西指認(rèn)自己派對上邀請的名人時(shí),得到充分體現(xiàn)。甚至他對黛西的追求,也是愛情被物化了的舉動。得到這份愛情,是他融入上流社會、獲得身份地位的標(biāo)志。
在施塔爾身上則看不到這些“低檔次”的東西。他對凱瑟琳的追求完全出于對已逝妻子的懷戀,不沾染一絲金錢氣息,他單單是希望凱瑟琳可以同他一起完成美好的愛情夢想。他希望用自己的溫柔和魅力重新獲得一份愛情,“他們的結(jié)合是想象中最為恰當(dāng)和莊重的”。甚至對陌生人,施塔爾也不會將金錢利益放在考慮條件的首位。為了拍出一部高質(zhì)量的影片,對公眾承擔(dān)一份責(zé)任,他決定拍(完)一部注定要虧本影片,以此爭取信譽(yù)。不受“人際商品化”影響的施塔爾所作的一切,比蓋茨比更高尚、更有人情味,更富有擔(dān)當(dāng)精神。
蓋茨比與施塔爾兩個(gè)角色的性格與氣質(zhì)看似不相符,但卻仍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他們不遺余力的努力,他們的執(zhí)著,他們對舊愛的懷戀,他們對美好的不懈追求,他們的神秘魅力,他們同樣溫柔的笑容。這些都在印證:他們本應(yīng)是一個(gè)原型,只是施塔爾是“理式”,是理念中完美的那個(gè);而蓋茨比則是真實(shí)存在且有些缺點(diǎn)的、模仿“理式”的那一個(gè)。施塔爾本身就是蓋茨比形象的一個(gè)延續(xù),只是在這個(gè)延續(xù)的生命中,施塔爾已經(jīng)變得更為成熟,也更被認(rèn)同。
二
兩部小說在人物塑造的方式上極為相似,故事中心人物的身份、背景和來歷,都是通過對他們顯赫聲名的描述和旁人對他們的議論,才逐漸顯露出來,并為讀者所了解。然而菲茨杰拉德遣詞的細(xì)膩卻使人物的大致形象一樣可以從旁枝末節(jié)表現(xiàn)出來。
從書名的用詞來看,菲茨杰拉德都給了兩個(gè)主人公一種認(rèn)可。蓋茨比是“Great”,這個(gè)單詞在形容一個(gè)人的時(shí)候表示“了不起的”、“偉大的”、“卓越的”的意思。對于施塔爾,作者則用了“Tycoon”,它指的是在商業(yè)上非常成功從而成為一個(gè)富有或者是有地位的人。從這樣的用詞也可看出,蓋茨比只是“了不起”而已,相比之下,施塔爾則有更高的社會地位,變得“偉大”。從對書名的翻譯也可以看出一些苗頭。在1971年時(shí),翻譯家喬治高曾沿用林以亮的翻譯將《The Great Gastby》翻譯為《大亨小傳》,致使小說就此與“大亨”有了一些聯(lián)系。但是“大亨”這個(gè)詞在原書名中是找不到的,相反卻清楚地寫在《The Love of the Last Tycoon》中。而《The Love of the Last Tycoon》也曾被譯為《最后一位君子》。現(xiàn)在通行譯本的《The Great Gatsby》,對“Great”的翻譯多采用“了不起的”而非“偉大的”,也更不再用“大亨”這個(gè)詞。“偉大”的詞性是褒義的,有崇高和令人景仰的含義;“了不起”則是中性的,它只是表示了一種卓越,而現(xiàn)行的通行譯本則多采用“了不起”這一翻譯,這也是對蓋茨比形象的注解。反觀“Tycoon”,無論是被忠實(shí)地譯為“大亨”,還是意譯為“君子”,則都表現(xiàn)出了對主人公人格及事業(yè)的認(rèn)可。
蓋茨比從小立志追尋“美國夢”。在追夢的過程中,尤其是當(dāng)他遇到黛西,又失去黛西時(shí),他對“美國夢”開始有了錯(cuò)位的認(rèn)識,他開始信奉只有在物質(zhì)上取得足夠的富裕,才能得到自由與快樂,才能追回他的愛情。而不再是當(dāng)初懷抱的、靠自己的努力做出一番事業(yè),然后出人頭地的理想。于是為了富裕,他做起投機(jī)生意。在禁酒令已經(jīng)頒布后,做起非法販酒的買賣。在當(dāng)時(shí),正常情況下購買酒精要去藥店,因?yàn)橛行┚朴兴幱脙r(jià)值,所以蓋茨比后來含糊地說自己開的是藥店。發(fā)家之后,蓋茨比將自己偽裝成一個(gè)“富二代”,好像他從一開始就繼承了許多家產(chǎn)。但是這個(gè)來路不明,又喜愛在每個(gè)周末一擲千金舉辦晚宴的富豪,招引了眾人對他的猜忌。人們傳言說他是德國威廉皇帝的侄兒或是別的什么親戚,也有人說他當(dāng)過德國間諜,更有人說他殺過人。在一次聚會中,一個(gè)矮胖中年男人在蓋茨比別墅的圖書室,查看書架上擺放的書,然后下結(jié)論:蓋茨比就像大衛(wèi)·貝拉斯科。而后者是一個(gè)舞臺監(jiān)督,以布景逼真而聞名。人們討論蓋茨比可能擁有的各種身份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娛樂,并不關(guān)心他究竟是什么人。他們喜歡盛大的聚會,而蓋茨比每周都舉辦一場盛宴,則滿足了他們的“破壞欲”與“狂歡欲”。
蓋茨比不具有真正的社會地位。他只知道財(cái)富在很多情況下都可以起作用,但卻不明白金錢在社會關(guān)系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不明白這種“暴發(fā)戶”的形象和傳統(tǒng)豪門“富二代”的形象,有什么樣的差別。他的一切行為,都只證明了他是個(gè)膚淺的淘金主義者。他的粉色西裝,在湯姆·布坎農(nóng)這類人的眼里顯得無比滑稽,而他本人則更像一個(gè)小丑。這樣一個(gè)從來沒有社會身份的人,在遭到算計(jì)而被槍殺后,無人愿意為他莫名的死亡申訴,也沒有誰愿意參加他的葬禮。
施塔爾作為蓋茨比人格進(jìn)化的形象,有著自己成功的事業(yè)。他在二十二歲的時(shí)候成為一個(gè)制片人的合伙人,在年輕的時(shí)候就練就一副“強(qiáng)勁的翅膀”,“飛得高,看得遠(yuǎn)”,“頑強(qiáng)的——最終是瘋狂的——鼓著翅膀,不停地鼓著”。不像蓋比茨那樣做著有些不光彩的生意,他從一開始就邁入了電影產(chǎn)業(yè),然后憑著自己的智慧與努力一步步的在這個(gè)圈子里成長起來,逐漸成為電影行業(yè)的標(biāo)志性人物,像愛迪生、盧米埃爾、格里菲斯、卓別林一樣,只要提起這個(gè)名字,人們就會肅然起敬——不只是對他本人,還有他對整個(gè)行業(yè)所作出的貢獻(xiàn)。他成就了電影事業(yè)的黃金時(shí)代,使電影遠(yuǎn)遠(yuǎn)超過舞臺劇的影響力和受眾范圍。
在他走過的時(shí)候,人們都會笑著跟他打招呼,然后他向人們回話并揮手,“那樣子有點(diǎn)像拿破侖和近衛(wèi)軍的關(guān)系……他依然是他們的偶像,他們的末代君王。他們走過他的身邊,把招呼聲變成一種低聲的呼喚”iv。人們對他的決策幾乎不會有任何懷疑,所有人都信任他的能力和眼界,當(dāng)他傳達(dá)了一個(gè)想法時(shí),人們會認(rèn)為這就是“神諭”,根本沒有質(zhì)疑或者爭辯的必要,因?yàn)榇蠹叶颊J(rèn)為他幾乎總是正確的。他不僅擁有所有人都認(rèn)可的社會地位,而且還占據(jù)著人們心目中類似于對帝王的膜拜與俯首。他還努力承擔(dān)著對公眾的一種責(zé)任,愿意去拍一部入不敷出的“好”電影,來獲取公眾的信任;為了消除黑人對電影的偏見,他將那些好壞參半的電影重新評定,從他的計(jì)劃中淘汰了四部影片,其中一部甚至馬上就要開拍了。
施塔爾的死,不只是由于一場飛機(jī)事故,而是死于多方面的算計(jì)。在意外死于空難之前,他的同行布拉迪已先策劃了對他的勒索,又準(zhǔn)備指派他人實(shí)行暗殺。這種算計(jì)來源于工作上的矛盾與妒忌。由于菲茨杰拉德的突然離世,施塔爾死后的情況只在他生前的工作筆記中略有描述:“施塔爾去世那天,制片廠的所有人(包括馬克斯兄弟)都在哭”v。這是一個(gè)逝去了讓所有人都感到惋惜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