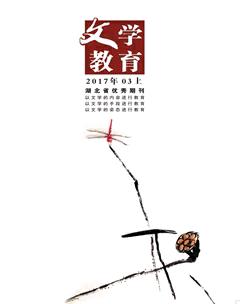論四川清代至民國年間族譜的教育功能
內容摘要:家族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細胞,是族人啟蒙教育的第一場所。族譜作為家族教育思想的載體,在社會管理、教化族人甚至維護國家統一上起著重要作用。本文通過對所得四川清代至民國年間部分家譜進行分析,結合清代教育實況,探討其在當時所起的教育教化功能及其對如今學校教育的啟示。
關鍵詞:四川 清代 族譜 教育功能
中國宗族社會有編修族譜的傳統。族譜是記載該家族發展史的文獻資料,也是該家族家法、族規的根據,更是一個家族的光榮榜,族人以榜上有名為榮耀。明末清初,四川諸多族譜均記載類似如,咸豐九年(1859),旺蒼縣龍鳳鄉白虎村《楊氏族譜》:“先世避元末亂,徙居湖廣麻城再避紅巾亂入蜀。”他們或因奉旨移民入蜀,或因避亂入蜀,或因經商入蜀。入蜀之后,插占為業,耕讀傳家。倉廩充裕后,建祠修譜,慎終追遠,教化后人。于是,各家族相互效仿,掀起了一股認祖修譜浪潮。
鐘琦《皇朝瑣屑錄》有云:“譜牒者所以濟宗法之窮,而宗法所系,恒必由之。……譜牒于祖宗源派,子孫流派,千百載并無淆混。”i編修族譜,除了梳理本家族源流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訂立族規家訓,團結族人,教化族眾。清代四川民眾推崇詩禮之教,宣揚儒家的忠孝仁義道德,這使族規家訓不僅起到了特定的家族教化作用,更使族規家法成為國法的補充,有效地管理了家族人員,維護了社會安定。
一.族譜是教化族人的重要根據
族譜又稱“家譜”“譜牒”“宗譜”等,編修族譜是凝聚族人的重要手段,同時又加強了社會管理。顧炎武認為,宗法的實行,是“扶人紀而張國勢”。ii民間的宗法實行,是國勢得以增強的手段,關乎政權的興衰。他從君主的政治經濟政策和民間的宗族活動,認識到歷代統治者念念不忘對民眾進行教化的“教化權”,其實是在民間,而不在國君。教化主要是通過家譜中的家訓或族規來規勸族人積極向善,遵從仁、義、孝、悌等。
教化族人遵守國法、家法。中國古代社會,國法與家法共存。國法在于獎懲國民,維護封建統治,規范社會秩序。家法在于教育訓導族人,維系家族繁衍。家法重在輔助國法,然而在封建家長的絕對支配權下,有時家法比國法更為嚴苛。光緒六年,渠縣《龔氏族譜》:“族眾當以忠孝為先,耕讀為本。如赤貧者,應當營謀生活,不可妄為。倘有玷辱家聲者,公同送官處究。”繼而“棄毀祖宗神主,棄毀父母死尸者,斬。”這種家法在今天看來是不可想象的,而在當時社會的警示作用可想而知。
提倡睦宗族、和鄉里、戒爭訟。各家族經過漫長的傳承、發展,班輩世系難免混淆,甚至族人間血緣關系日益疏遠。明末清初“填川”移民大多與原族失去聯系,入蜀后,部分族人又經歷了二次、三次、甚至多次遷徙。為加強族人間的聯系,達到“維人心”、“固族誼”的目的,編修族譜變得尤為重要。民國37年,達縣《陳氏支譜》中就明確提到:“譜系之設,可以明親親長長道也,并可以維族屬于不紊,俾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又,金堂縣竹篙鎮寶象村《陳氏族譜》:“今族眾人繁,其或創業中邑,徙陜西龍安、建昌等地者,代不乏人。由是,或因遠而忘其宗,或以疏而亂其祖,眾心惻然。夫世遠年湮,惟有族譜,可以聯屬宗親。”iii可見,在陳氏家族發展過程中,有的族人“創業中邑”,有的族人“遷徙陜西龍安、建昌等地”,這就使得部分族人間的聯系變少,進而造成“眾心惻然”“疏而亂其祖”的局面。而能聯屬宗親、穩固族誼的,當為族譜。
宗族本同根源,盡管分支分派,也應親睦團結。鄉鄰同井而居,且遠親不如近鄰,也應相互親近,不可結仇怨。此二者為家族發展必須維護的社會關系,若族中子弟與人為惡,定責之教之。南江縣石寨村《夏氏族譜》記載了其入川始祖之四子夏順音被當地孟姓人殺害,后其長子夏順立為弟報仇,進京告御狀,得到乾隆皇帝破格召見和御審,澄清了冤情,并賜以御品信物,還將名字改為夏順讓,教之多些忍讓。iv
敦孝悌以重人倫。立人之道,莫先孝悌。孝為百行之先,康熙18年(1679年),《圣諭十六條》首條即為“敦孝悌以重人倫”。而且一般家族族規均有“族中宜各親其親,各長其長”“敦孝悌以重人倫,遵鄉約以杜犯科”等。v
篤耕耘、尚勤儉。封建社會長期重農抑商,認為農桑為百姓衣食之本。明末清初,四川長期處于戰亂狀態。先是農民領袖張獻忠起事,接著有南明與清軍的斗爭,加上吳三桂反清,戰亂前后達三十四年。康熙元年(1662年)川省初定,土滿人稀。十年之后仍是有可耕之田而無耕作之民。vi繼而政策導向、自發移民入川之后,插占為業,辛苦耕耘,發家致富。為了牢記祖先創業之艱辛,人們將家族發展的過程及農桑傳家載于家譜,勉勵后人。
二.族譜是教育族人的重要教材
中國傳統社會里,“耕讀傳家”是人們追求的一種理想生活模式。這種思想在清代四川地區各家族族譜中反映得尤為明顯,特別是人死之后,其碑文幾乎都以“耕讀傳家”來褒揚。“耕”指傳統的耕田種地及養蠶織布等,是農民的本業,衣食足而知禮節;而“讀”則指誦讀儒家經典,進而知書達禮,修身養性。雖然舊時代“半耕半讀”的生活悠然、閑適,足以讓人安居樂業、盡享天倫,但是“學而優則仕”“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理想信條,又讓人對仕途心生向往,讀書則可以為貧寒子弟進入廟堂搭建橋梁。“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格言激勵著一代代讀書人伏案苦讀、樂此不疲。
族規家訓更是傳達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教育理念。《顏氏家訓》中顏之推認為,讀書是最容易而又最高貴的技藝,且讀書如庖廚之饌、御寒之衣,是世人增加智慧及閱歷的最佳途徑。vii對于讀書的重要性,四川地區各家族族譜中均有體現,光緒六年,渠縣《龔氏族譜·書錄序》:“今者,展閱家乘,咸曉然于雍睦之雅。披吟譜牒,群卓然于倫紀之休。非即能成教于家,以親九族。本支百世哉,惟合族昌大,子孫簪纓。后有馳驅皇路,黼黻大廷。后人之幸,亦前人之幸也。”光緒22年《馮氏族譜》:“教訓子孫為人生第一事,詩書尤為第一事。古人云:‘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viii民國11年《熊氏族譜》:“家道之盛衰,系于子弟之賢否,子弟之賢不肖,又系于教育之有無。”ix民國37年《謝氏蜀譜》:“子孫為承先啟后之人,未可任其游惰也。倘使資質愚弱,固應教導有序,漸開其錮蔽之胸。”又“古云子孫賢,族乃大,斯言洵不誣哉。”x
對于族中勤讀詩書并取得一定成績的子弟,將依據族譜規約給予獎勵。光緒六年,渠縣《龔氏族譜》:“一族內士子,務宜勤讀,倘經幸進院,費公給。賞賜花紅,合族共為迎接,以獎學術。發其鄉試,拔揚族長首事等,亦必隆以肆筵,助以斧貲,倘有違抗,公同議罰。”民國五年《范氏族譜》:“一議眼下生活程度太高,祠內嗣孫貧乏者眾,須增給學費以補之,庶可綿長祖澤。蓋子弟為闔族元氣,不可不加意培植也。”xi為了勉勵族人,關于教子、勸學、勉學的傳說故事,如雪梅教子、孟母三遷等故事常被記載在四川各家族祠堂、族譜、墓碑上,以及流傳在人們的口耳之中。
三.對當地文教的影響
族學是家族為教育子孫而開辦的家族學堂,一般設在宗祠內,由族中有學識的長者任教。明末清初,移民入川后還未站穩腳跟,他們無暇考慮讀書和教育,唯有努力耕作,所謂“衣食足而知禮節”,這種“先富后教”的思想在清代至民國年間的四川地區體現得尤為明顯。《資中縣志》轉引張氏家譜:“光緒時,其祖張開第延名師,置書籍,所設家塾‘優良為州郡之冠。”xii又民國30年,屏山縣《文氏宗譜》:“栽培成美,鼓勵氏族成才,況祖宗之最悅。后嗣讀書,曉得孝悌、忠信、節義等事。我族故祠做學館,令我族子弟來讀書。聰明者,知忠孝節義,光祖耀祖,愚昧者,使知尊老愛幼,方合祖宗之心。”該二譜反映了張氏、文氏家族對教育的重視,他們設立家塾、學館以施教化。和官學不同的是,族學重在德育,教化族人遵守仁義禮智信。官學是朝廷為加強中央集權而設立的偏應試教育的官辦學校。族學從客觀上迎合了官學科舉取士的思想,促進了當地教育的發展。到了民國,族學逐漸轉變為私塾或小學,《資中縣志·宗族》:“有的祠堂也是私塾,作為族中弟子讀書的地方。民國時,祠堂改作小學73個、私立中學1個;宗祠活動同時存在。”xiii
對于教育內容,族譜亦有規定,新都《吳氏族譜·家規·崇正學》:“人之擇術要正,趨向要端,而儒教為萬世不易之正宗,故讀書明理。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皆由此出,富貴功名由此進,極之希圣希賢亦由此而至此,誠千古之正學也。切不可誤入歧趨,妄信邪教如天主、白蓮、青蓮一切等教,其為害不小矣,凡我族人最宜戒之。”吳氏遵從儒教,以為正宗。族人需懂得孝悌、禮義,不可輕信邪教。另外該家族還主張因材施教、資助品行兼優而家貧者,新都《吳氏族譜·家規·嚴教訓》:“至于庭幃之中,教以孝悌,使子弟猶能知愛親敬長;接物之間,訓以謙恭,使子弟不至傲己凌人。倘族中有子弟英俊可教,彼父兄家貧無力,勸家富者助其資費以勵勤苦。俾得成名,異日自必深感。及光前裕后,闔族亦與有榮焉。……縱以免后之子弟,效尤如此,則教訓有方,子弟悉能守其正矣。”
但是傳統的儒教思想指導下的族學亦有其局限,如“重男輕女”等思想。光緒六年,渠縣《龔氏族譜·婦女叢德論》:“當深閨待字之年,從父為正;而值夭桃致詠之候,從夫為良。即或舉案難齊,偕老莫慶,須念承祧有后,從子維殷。‘從有三焉,固當時時凜覺;‘德有四矣,尤當一一毋忘。”
四.對現代教育的啟示
古代知識分子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人生追求的四重境界,這很好的將個人、家庭、國家三者有機統一起來。顏之推、王安石、蘇軾等做出了有力的實踐,被稱為大家、通才。他們的家訓、族規被各家族競相學習,甚至引以為典范。所謂家學淵源即使如此,孩子從小就生活在書香門第,耳濡目染,自然有利于其身心發展。對待這些傳統家族教育理念,我們應引以學習貫徹。當今應試教育背景下,現代學校教育過多關注學生的學習成績,而傳統家族教育可以通過家族中隆重的祭祀、傳承等活動,使他們感受并牢記孝悌忠信等祖訓思想,能夠使孩子從小樹立良好的道德觀、價值觀。因此,學校教育需要家族教育的輔助,二者相互配合才能培養出新時代優秀接班人。當然,傳統家族教育有其局限性,我們應取優去劣,弘揚傳統文化以純風俗,使這一古老的教育形式在當下發揮其更優的教化功能。
參考文獻
[1]馮爾康:《家譜的學術價值及其研究的現實意義》,《社會科學輯刊》,1989年第2期。
[2]朱明勛:《中國傳統家訓研究》,《四川大學》,2004年3月。
[3]黨明德、何成主編:《中國家族教育》,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12月。
[4]吳康零主編:《四川通史》卷六,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
[5]葉國愛:《族譜的教育價值研究》,《西南大學》,2010年4月。
[6]田佳立、張貴桃:《家譜——一部對家族成員進行縱向教育的教材》,《百花園地》,2010年第6期。
[7]張憲平:《試論家譜的教育功能》,《志鑒論壇》,2011年第3期。
[8]牛志平:《“家訓”與中國傳統家庭教育》,《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
注 釋
i 鐘琦輯錄,沈云龍主編:《皇朝瑣屑錄》,文海出版社,1897年,第1338頁。
ii 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文集》第5卷《裴村記》,中華書局,1959年,第101頁。
iii 陳善德等:《陳氏族譜》(打印本),2001年3月,第18頁。
iv 夏祥基等:《夏氏族譜》(打印本),2009年10月,第71頁。
v 吳康零主編:《四川通史》卷六,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第667頁。
vi 胡昭曦:《“張獻忠屠蜀”考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第53頁。
vii [南北朝]顏之推:《顏氏家訓》,金庸出版社,2009年2月,第91頁。
viii 陳世松、劉義章:《成都東山客家氏族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第49頁。
ix 陳世松、劉義章:《成都東山客家氏族志》,第183頁。
x 陳世松、劉義章:《成都東山客家氏族志》,第112頁。
xi 陳世松、劉義章:《成都東山客家氏族志》,第152頁~第153頁。
xii 四川省資中縣志編纂委員會:《資中縣志》,巴蜀書社,1997年,第684頁。
xiii 四川省資中縣志編纂委員會:《資中縣志》,第683頁。
(作者介紹:康雅迪,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語文課程與教學論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