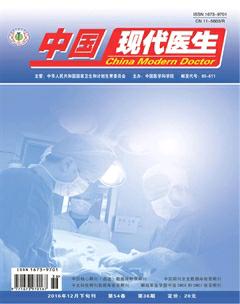急性卒中后感染的特點及危險因素研究
林萍 鄭麗芬 林一均
[摘要] 目的 對急性腦卒中患者住院時發生卒中后感染的特點進行分析,為臨床尋找可控危險因素及預防急性卒中后感染提供證據支持。 方法 參照急性卒中后感染的診斷標準連續收集2013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溫州市人民醫院神經內科住院治療的604例急性腦卒中患者,對其病歷進行數據研究,通過單因素及多因素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找出與卒中后感染相關的獨立危險因素。 結果 納入病例中卒中后感染的總感染率為21.2%,主要感染部位為下呼吸道感染(17.9%)、泌尿系感染(3.1%)。多因素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年齡≥65歲、住院期間有侵入性操作、使用鎮靜類藥物、未使用β受體阻滯劑、洼田飲水試驗≥3分、NIHSS評分≥15分、ADL評分<50分、超敏CRP≥5 mg/L是卒中后感染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或P<0.01)。 結論 卒中后感染發生與多種危險因素相關,臨床診療決策應當將卒中后感染納入管理規范,以改善患者近期預后。
[關鍵詞] 急性腦卒中;卒中后感染;感染;危險因素
[中圖分類號] R743.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6)36-0005-05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st-stroke infection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acute stroke, and to provide evidenc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acute post-stroke infection and looking for the controllable risk factors.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acute post-stroke infection, 604 patients with acute stroke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Wenzhou People's Hospital from Jan 1, 2013 to Dec 31, 2015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un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o identify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ost-stroke infection. Results The total infection rate of post-stroke infection was 21.2%. The major infection sites were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17.9%) an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3.1%). Multivariate un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found that patients age ≥65 years, with invasive procedures during hospitalization, sedative drugs, no β blockers, kubota drinking water test score≥3 points, NIHSS score≥15 points, ADL score<50 points and high sensitivity CRP≥5 mg/L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post-stroke infection(P<0.05 or P<0.01). Conclusion Post-stroke infection is associated with multiple risk factors.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should incorporate post-stroke infection into management practice to improve short-term prognosis of patients.
[Key words] Acute stroke; Post-stroke infection; Infection; Risk factors
腦卒中是一種以腦組織出現缺血性或出血性損傷為主要病理表現的急性腦血液循環障礙性疾病,發病迅速,預后不良,其高致殘率給患者及家庭帶來沉重的負擔[1]。隨著多項臨床研究的深入,多數腦卒中患者并非因為卒中而死亡,而是因為各種并發癥的出現而致死亡[2,3]。研究提示卒中并發感染嚴重影響患者的神經功能預后,并導致死亡風險增高,是腦卒中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4]。
卒中后感染首先由Vargas于2006年提出[5],隨后Emsley和Hopkins等對其定義進行了完善,提出了卒中后感染的定義:感染的發生和卒中相關,在卒中發生時無感染征象,也未處于感染潛伏期,而在卒中發生48 h后出現的各種感染[6]。國外研究顯示,20%左右的卒中患者均合并有不同程度的感染,且患者發生感染的時間多在卒中發生7 d內[7]。本研究分析卒中后感染發生的特點及獨立危險因素,并探討其與預后的關系,以為臨床建立卒中后感染患者的獨特管理模式、改善患者預后提供一定的理論基礎,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連續收集2013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于溫州市人民醫院神經內科住院治療的604例急性腦卒中患者。急性腦卒中診斷標準參照《中國急性缺血性腦卒中診治指南2014》標準[8],《美國心臟病協會、美國卒中協會自發性腦出血管理指南》[9]及第4屆全國腦血管病學術會議修訂的《各類腦血管疾病診斷要點》中腦出血的診斷標準[10]。目前尚無急性腦卒中后感染統一診斷標準,參照如下:(1)急性腦卒中發病48 h后至7 d內出現的各種部位的感染;(2)急性腦卒中后感染按臨床診斷報告,力求做出病原學診斷,各部位感染診斷標準可參照2001版《醫院感染診斷標準(試行)》[11]。
1.2 納入標準
(1)發病在24 h以內的急性腦卒中的患者;(2)符合急性缺血性腦卒中和急性出血性腦卒中診斷標準者;(3)卒中類型包括:①缺血性腦卒中患者:包括大動脈粥樣硬化型、心源性栓塞型、小動脈閉塞型、其他明確病因型和不明原因型等五型。②出血性腦卒中患者:包括腦出血、蛛網膜下腔出血。(4)包括反復卒中的患者。
1.3 排除標準
(1)發病至入院時間超過24 h的腦卒中患者;(2)卒中前或卒中48 h內合并感染者;(3)合并有嚴重免疫系統疾病者;(4)患有各種急慢性炎癥、腫瘤者。
1.4 研究方法
制定腦卒中患者感染情況調查表,對納入患者進行一般情況及感染情況統計,通過單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篩選出卒中后感染的獨立危險因素。最后比較感染患者和非感染患者入院時及治療21 d后的神經功能量表評分。
1.5 統計學分析
所有資料進行匯總后均輸入計算機,采用統計學軟件SPSS 19.0進行統計學處理。計量資料以(x±s)表示,采用Z檢驗或配對t檢驗,計數資料以構成比和率表示,采用χ2檢驗,先進行單因素分析,并擬合多因素非條件Logistic回歸模型,調整相關的混雜因子,尋找急性卒中后感染的獨立危險因素。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急性腦卒中患者的一般情況
本研究共納入急性腦卒中患者604例,其中男372例,占61.6%,女232例,占38.4%,年齡35~89歲,平均(67.9±13.5)歲。其中缺血性腦卒中患者544例,占90.1%,出血性腦卒中患者60例,占9.9%。發病時間1~24 h,平均(10.9±7.2)h。急性腦卒中患者男性比例多于女性,而缺血性卒中患者比例要高于出血性卒中,患者從發病至就診時間波動范圍較大,多數缺血性腦卒中患者均超過了最佳治療時間窗。
2.2 急性腦卒中患者卒中后感染情況
卒中后感染的感染率為21.2%,主要感染部位有下呼吸道感染(17.9%)、泌尿系感染(3.1%)。見表1。
2.3 急性腦卒中患者卒中后感染細菌菌種情況
卒中后感染的細菌菌種較多,其中肺炎克雷伯菌肺炎亞種所占比例較高,占總病例數的4.3%。見表2。
2.4 急性腦卒中患者卒中后感染真菌菌種情況
卒中后感染可合并有真菌感染,其中白色念珠菌感染最多,占總病例數的6.1%。見表3。
2.5 影響急性腦卒中后感染發生的單因素分析結果
通過臨床觀察及文獻報道納入可能的影響因素,采用χ2檢驗,其中有15項因素與卒中后感染相關,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或P<0.01)。見表4。
2.6 影響急性腦卒中后感染發生的多因素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本研究行單因素分析后,又對其進行二分類多因素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有8項因素是卒中后感染的獨立危險因素,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或P<0.01)。見表5。
2.7 影響急性腦卒中后感染發生的相關因素交互作用結果
在多因素分析所得的獨立危險因素的基礎上,分別對各因素進行兩兩交互作用分析,取α=0.05水平,發現侵入性操作與洼田飲水試驗、侵入性操作與ADL評分<50分、侵入性操作與應用鎮靜類藥物存在正交互作用。見表6。
2.8 急性腦卒中后感染者和非感染者入院時及治療21 d后NIHSS評分比較
分別比較入院時及治療21 d后感染組和未感染組的NIHSS評分,并比較治療前后NIHSS評分的變化。結果提示入院時及治療21 d后感染組的NIHSS評分均高于未感染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兩者各組內前后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7。
2.9 急性腦卒中后感染者和非感染者入院時及治療21 d后ADL評分比較
分別比較入院時及治療21 d后感染組和未感染組的ADL評分,并比較治療前后ADL評分的變化。結果提示入院時及治療21 d后感染組的ADL評分均低于未感染組,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兩者各自組內前后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8。
3 討論
3.1 卒中后感染的特點及分析
本研究得出卒中后感染的感染率為21.2%,感染部位主要為下呼吸道感染、泌尿系感染。急性腦卒中患者多伴有意識障礙、吞咽功能障礙和肢體功能障礙;另外,在急性腦卒中的治療中使用脫水劑或利尿劑,易引起痰液黏稠,導致呼吸道排痰不暢,增加感染幾率[12]。同時氣管切開、插管等侵入性操作,可破壞呼吸道屏障功能,增加感染幾率。泌尿系感染的發生可能與卒中患者出現尿失禁或尿潴留相關,而泌尿系的侵入性操作如留置導尿管也增加了外界細菌進入泌尿系的風險。
本研究發現卒中后感染的病原菌多數為條件致病菌,Prass K等[13]于2003年提出了卒中所引起的免疫抑制綜合征(Stroke-induced immunodepression system,SIDS),該研究發現卒中后的動物模型存在嚴重的免疫防御能力缺陷,特點是快速持久的細胞免疫功能抑制[14-16]。在腦卒中后感染的動物模型研究中,腦卒中后感染發生較為迅速,往往在誘導的腦缺血動物模型中,數小時即可出現免疫功能抑制狀態,且持續時間較長[17]。從而使機體防御能力下降,易引起條件致病菌感染。
3.2 卒中后感染的危險因素及分析
本研究通過單因素及多因素分析了影響卒中后感染發生的危險因素,多因素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年齡≥65歲的腦卒中患者更容易發生卒中后感染,隨著年齡增大,患者抗病防御能力降低,各臟器儲備能力差,且多伴有多種基礎疾病,因此,對于此類患者應特別注意防范感染的發生。侵入性操作使氣道或泌尿道與外界環境直接相通,黏膜的防御功能基本喪失,細菌入侵,導致卒中后感染。諸多研究證實,急性腦梗死后血腦屏障破壞,釋放大量促炎細胞因子,通過細胞間隙擴散或通過腦脊液、血液直接激活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交感神經系統和副交感神經系統[18]。急性缺血性腦卒中引起的交感神經系統激活,可降低感染的閾值和增加感染的風險[19],交感神經可促進神經末梢或腎上腺髓質釋放兒茶酚胺,通過對免疫細胞的影響,引起明顯的免疫抑制。有研究指出β受體阻滯劑能降低血清中兒茶酚胺水平,從而改善體內過度激活的交感神經狀態,降低卒中相關性感染的發生[20]。鎮靜類藥物一方面可以減輕躁動狀況,另一方面由于抑制咳嗽反射,氣道排出分泌物的能力減弱,增加了感染發生風險。吞咽功能障礙可引起飲水嗆咳、食物滯留,導致異物吸入,從而增加卒中后感染的發生風險。卒中后感染與神經功能缺損嚴重程度及日常生活活動能力下降的嚴重程度相關。中樞神經系統功能損害越重,日常生活能力越低下,卒中后感染的發生風險越高。超敏CRP與卒中后感染發生十分相關,CRP的升高通常指機體處于一種應激狀態,因此,臨床針對CRP增高的患者應予以高度重視。
對卒中后感染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進行交互作用研究時提示,在吞咽功能障礙、日常生活能力低下的患者中應盡量避免侵入性操作,如無絕對適應證的情況下應盡量避免鎮靜類藥物的使用。
3.3 卒中后感染對神經功能的影響
本研究并不能說明感染加重了神經功能缺損及日常生活能力的下降,而是反映卒中后出現感染的這類患者群體有著更嚴重的神經功能缺損癥狀、更低下的日常生活能力這一特點,且無論感染與否,兩者均會隨著治療時間而逐漸恢復,從兩者治療后的數據上看,感染組不如未感染組,說明感染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卒中后神經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的恢復情況,但卒中的嚴重程度與卒中后發生感染是否相關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以證實。
綜上所述,對于急性腦卒中患者應予以高度重視,在卒中患者的管理中應當將卒中后感染納入其中,全面系統的對卒中患者進行感染危險因素的分析與評估,從多方面入手降低卒中患者的感染風險,提高患者預后。
[參考文獻]
[1] 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神經康復學組,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腦血管病學組,衛生部腦卒中篩查與防治工程委員會辦公室,等. 中國腦卒中康復治療指南(2011完全版)[J]. 中國康復理論與實踐,2012,18(4):301-318.
[2] Olajumoke TO,Afolayan JO,Ojo KO. Stroke:Critical appraissal of intensive care management[J]. Niger J Med,2015,24(4): 307-309.
[3] 袁云華,劉丹,沈流燕. 卒中相關性肺炎的臨床分析及防治策略[J]. 醫學理論與實踐,2015,28(2):187-189.
[4] Brogan E,Langdon C,Brookes K,et al. Can't swallow,can't transfer,can't toilet:Factors predicting infections in the first week post stroke[J]. J Clin Neurosci,2015,22(1):92-97.
[5] Vargas M,Horcajada JP,Obach V,et al. Clinical consequences of infect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stroke:Is it prime time for further antibiotic trials[J]. Stroke,2006,37(2):461-465.
[6] Worthmann H,Tryc AB,Dirks M,et al. Lipopolysaccharide binding protein,interleukin-10,interleukin-6 and C-reactive protein blood levels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infection[J]. J Neuroinflammation,2015,12(4): 133-148.
[7] Ovbiagele B,Hills NK,Saver JL,et al. Frequency and determinants of pneumonia an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during stroke hospitalization[J]. J Stroke Cerebrovasc Dis,2006, 15(5): 209-213.
[8] 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腦血管病學組. 中國急性缺血性腦卒中診治指南2014[J].中華神經科雜志,2015,48(4):246-257.
[9] 魏玄輝,李姝雅,秦海強,等. 美國心臟病協會、美國卒中協會自發性腦出血管理指南[J]. 中國卒中雜志,2011, 6(2): 155-162.
[10] 中華神經科學會,中華神經外科學會. 各類腦血管疾病診斷要點[J]. 中華神經科雜志,1996,29(6):379-380.
[11] 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 醫院感染診斷標準(試行)[J]. 中華醫學雜志,2001,81(5):314-320.
[12] 徐玢,李建國,于東明,等. 急診重癥監護病房重癥腦卒中相關性肺炎的危險因素分析[J]. 中國醫藥導報,2015, (16): 119-123.
[13] Prass K,Meisel C,H?觟flich C,et al. Stroke-induced immunodeficiency promotes spontaneous bacterial infections and is mediated by sympathetic activation reversal by poststroke T helper cell type 1-like immunostimulation[J]. J Exp Med,2003,198(5):725-736.
[14] Folyovich A,Biro E,Orban C,et al. Relevance of novel inflammatory markers in stroke-induced immunosuppression[J]. BMC Neurol,2014,14:41.
[15] Friedant AJ,Gouse BM,Boehme AK,et al. A simple prediction score for developing a hospital-acquired infection after acute ischemic stroke[J]. J Stroke Cerebrovasc Dis,2015,24(3): 680-686.
[16] Gu LJ,Xiong XX,Ito T,et al. Moderate hypothermia inhibits brain inflammation and attenuates stroke-induced immunodepression in rats[J]. CNS Neurosci Ther,2014, 20(1): 67-75.
[17] Westendorp WF,Nederkoorn PJ,Vermeij JD,et al. Post-stroke infection: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BMC Neurol,2011,11:110.
[18] 段茜,郝俊杰,李剛. 急性腦卒中后的免疫抑制與肺炎[J].中華腦科疾病與康復雜志:電子版,2015,5(6):423-426.
[19] Yan FL,Zhang JH. Role of the 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and spleen in experimental stroke-induced immunodepression[J]. Med Sci Monit,2014,20:2489-2496.
[20] 陳麗娜,沈定國,賈頤,等. β受體阻滯劑對急性腦卒中后感染的影響[J]. 中國神經免疫學和神經病學雜志,2015,1(22):49-53.
(收稿日期:2016-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