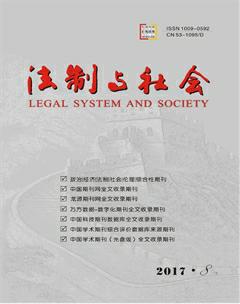關于妨害公務案件法律適用問題的研究
劉巨勝 王偉波
摘 要 《刑法》第277條對妨害公務罪的規定較為簡約,且兩高尚未制定相應的司法解釋,致使現階段基層司法機關對妨害公務罪的認定較為恣意,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為防止妨害公務罪成為司法機關打擊執法對象的“萬能法寶”,由此有必要對妨害公務的行為作出準確認定,尤其在當前司法實踐中,妨害公務行為在適用中仍存在很多爭議,更需要進一步理清以統一認識。有鑒于此,本文結合我院2014年以來辦理的妨害公務罪案件及其他地區的典型案例,探析存在的問題及司法對策,冀期對今后辦理妨害公務案件提供參考。
關鍵詞 妨害公務罪 法律適用 司法機關
作者簡介:劉巨勝、王偉波,天津市東麗區人民檢察院。
中圖分類號:D923.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8.336
一、當前妨害公務犯罪案件的基本情況
(一)當前妨害公務案件的特點
1.案件數量逐年增多,本文研究對象為天津市D區,該區2014年受理妨害公務刑事案件7件9人,2015年受理7件7人,2016年受理15件19人,2017年第一季度受理6件6人,妨害公務案件數量呈逐年上升趨勢,特別是2016年以來案件數量翻倍增長。2017年第一季度受理案件數已與往年全年平均數持平,經從公安機關了解,2017年妨害公務案件數可能呈現“井噴式”增長。
2. 涉案執法人員較為單一,《刑法》第277條對妨害公務罪列舉了4類人員執行職務的情形,分別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國家權力機關工作人員、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及執行國家安全工作的人員,司法解釋又對涉案領域及人員進一步做了補充細化。司法實踐中,除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外,其他機構人員未曾涉及,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中基本以人民警察居多,近三年占據妨害公務案件人員比例高達91%。
3.造成執法人員輕微傷比例較高。執法人員傷情狀況以輕微傷為主。2014年以來天津市D區檢察院受理所有的35件妨害公務案中,有43名執法人員不同程度受傷,其中有31件37人系輕微傷,2件2人構成輕傷,2件4人不宜評定傷情或不構成輕微傷,造成執法人員輕微傷傷情案件比例為88%。
4.緩刑適用率較高。由于妨害公務犯罪法定刑較輕,實務中對該類犯罪總體較輕,經過近三年法院判決研究發現被執法對象賠償執法者人身傷害損失或財產損失的,除非情節特別嚴重的情形例如另外造成周邊公共財產損壞,判處的刑罰較輕,拘役至有期徒刑六個月不等,且均適用緩刑。緩刑適用率76.5%,而對案件事實、情節類似的案件,如果被執法對象未賠償執法者損失,判處刑罰較重,有期徒刑八個月至一年半不等,且均判處實刑。
(二)出現上述特點的原因
1.公安機關執法查處力度較大,客觀上使得案件數量增多,執法過程中或由于被執法對象不理解及抗拒或執法者自身不規范行為,導致被執法對象與執法者產生身體沖突,此類情形多見于民警處理警情時。
2.法院濫用自由裁量權刑罰。刑法未規定妨害公務案件具體的處罰標準,也沒有相應司法解釋,法官在是否判處緩刑上全憑自由裁量,即賠償損失作為對被告人降格處理的依據,使得妨害公務案件處理越來越輕,賠錢判緩刑已成為一種司法慣例,致使刑罰標準越放越寬,有失法律嚴肅性。
3.公訴機關對妨害公務案件存在重追訴、輕監督的傾向。由于偵查機關與檢察機關同屬司法共同體“追訴”部門,檢察機關對妨害公務案件尤其是阻礙民警執法案件不好處理,不起訴就要背不支持公安干警工作的黑鍋,即便證據不太扎實也無法補證,也只好將案件推向法院。由于法律規定不明確檢法認識不一,法院運用自由裁量權判決,即使檢察機關認為判決錯誤,也不敢提起抗訴,因為缺乏足夠的依據和底氣,即便便提起抗訴改判的幾率也很渺茫,這在實際上支持了法院對妨害公務案件輕緩化處理。
二、妨害公務犯罪辦理中發現的問題
(一)對公務行為合法性分析是認定妨害公務罪的前提
根據刑法條文規定,“依法執行職務或者履行職責”是妨害公務罪客觀方面構成要件的要素之一,亦即職務行為的合法性是構成妨害公務罪的重要前提。何謂職務行為合法性呢,本文認為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認定:一是執法者得到明確授權,即擁有執行職務活動的資格,如輔助執法人員與正式執法人員一起執法時方能認定其主體適格;二是執法內容具有合法性,即必須在國家賦予的管理權限內及法律規定的權限內行使,超越職權、濫用職權的行為不應視為公務活動;三是執法程序應合法、合理、合情,做到既能按照法定程序辦事,又能保障人民群眾利益。只有具備以上三個要件,才能認定職務行為具有合法性。故作為司法人員中不應只關注妨害公務的行為,還應將目光逡巡至職務行為是否合法分析研判上,如果公務行為顯示出非法性、明顯不合理,那么被執法對象的行為就不應作為妨害公務案件來處理。
如李某某(女)妨害公務案中,一民警(男)著便衣現場查獲私賣汽油車主后,要求加油車主李某某配合調查,李某不愿配合欲離開,民警強行扣留李某私家車并與李某某發生身體沖突,后在爭執中被李某某抓傷。該案中民警未按照公務要求的法定程序開展執法活動,沒有法律規定民警可以強行扣留證人所有財產,且民警對李某某也存在拉拽等不當行為,并造成張某某身體擦傷,民警人未按照法定程序處理,侵犯了公民權益,其執行職務的行為不符合合法性要求,應當認定為李某某的行為不構成妨害公務罪。
又如天津市H區辦理的張某妨害公務案中,街道辦事處工作人員要求張某清理樓道工程土時遇張某反抗,杜某強行將張某帶離現場時被張某毆打致傷。該案中街道辦人員對張某某的強制帶離并無相關法律依據,且先行對張某身體有強拉硬拽不當行為,執法行為程序上存在重大瑕疵,張某阻擾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執行職務的行為不必然構成妨害公務罪,只有切實阻礙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行為才能認定為造成了妨害公務的后果。
(二)對妨害公務行為的認定應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
對犯罪的認定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既要有犯罪的客觀行為,又要有犯罪主觀故意,如果忽略后者,則易導致客觀歸罪。而對行為人主觀故意的認定,應通過其客觀行為來推定,只有行為人是認識到了警察在依法執行職務,明知道自己的行為會侵害正常的執法秩序,卻仍希望或放任這種危害結果的發生,才能認定為行為人具有犯妨害公務罪的主觀故意。在司法實踐中還要注意一點是行為人的犯意轉化情形,即實施妨害公務犯罪過程中犯意改變,如王某醉酒駕車遇交警路檢后駕車撞擊交警車輛后逃跑,交警在后追趕,王某為擺脫追趕故意連續撞上數十輛車致使交通癱瘓,交警無法繼續追趕,對該種情形王某改變犯意,應當以新犯意認定,故對其應當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而非妨害公務罪。
我國刑法關于妨害公務罪的法條本身規定不夠明確,存在模糊的空間,公檢法三家各家對此認識不一,導致執法標準也不甚一致,很容易出現認識的分歧,尤其對妨害公務行為達到何種程度標準才得以刑事處罰,司法實踐中一般以造成民警輕微傷的后果來認定,但這并不意味著未造成輕微傷的后果就不構成妨害公務罪。有人指出刑法修正案九規定暴力襲擊人民警察的從重處罰,立法本意是保護警察執法是身體不受侵犯的權利,對此本文不敢茍同,對該條文不應作咬文嚼字的分析而應作整體解釋,該條規定是以《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款為基礎的,確切說是刑罰加重條款,是一個注意規定而非法律擬制,不能據此得出只有襲擊警察身體的才能構成妨害公務罪,對于使用暴力、威脅方法阻礙了人民警察依法執行職務的,應當認定構成妨害公務罪,行為侵害的對象不僅僅限于執法人民身體,行為人對執法車輛、器材等物品造成損毀致使執法行為無法進行的,也應當以妨害公務罪論處。同樣對使用威脅手段阻礙依法執法的,視其危害后果及情節嚴重程度,對社會危險性的行為人也應當以妨害公務罪定罪處罰。
(三) 被傷害公務人員諒解不能作為從寬處理的依據
通過梳理法院判決發現,對行為人積極賠償被傷害公務人員的,公安機關多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審強制措施,法院基本對被告人判處緩刑,而對自始至終未能達成和解協議的,均對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強制措施,法院也對被告人多判處實刑,且刑期較重。司法實踐中是否賠償被傷害公務人員成為從寬處理甚至是不處理的根據,本文認為該種做法并不妥當,理由如下:
首先,被傷害執法人員無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或賠償要求,在辦理案件中我們發現有部分受傷民警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或者直接找到行為人索要賠償,我們認為,被傷害執法人員不宜也無權提出該項要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的規定,被害人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財物被犯罪分子損壞而遭受物質損失,有權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而執行公務人員本身是代表國家機關,其履行應盡職責的同時,國家機關亦賦予其一定的職責及人身保障,如公費醫療、工傷保險之類,被傷害公務人員在公務活動中的損失由國家予以彌補后,不能再因此向實施妨害公務的行為人索要財物,因此任何公務人員不能因為執行公務活動而從中獲利,其代表國家公權力維持社會秩序,而不是出于一己私利謀求利益,公務人員向執法對象提起賠償請求之舉極大損害了執法機關的形象,導致執法機關在人民群眾中的公信力下降,有甚者索取明顯不合理的天價賠償費用甚至還涉嫌違法犯罪,實踐中我們遇到過行為人先行賠償后再去控告執法人員涉嫌敲詐勒索罪的現象。
其次,被傷害執法人員的諒解不能作為從寬處理的根據,從妨害公務罪侵害法益來看,其保護法益是公務行為的權威性,是一種社會法益,是公共秩序得以維持的保障,對實施妨害公務的行為人進行處罰,是要看其所實施犯罪行為造成的后果及情節嚴重程度,與其是否賠償被傷害公務人員的損失及是否獲得被傷害公務人員的諒解并無關系。再者從妨害公務犯罪造成的后果來看,表面上是執法人員身體遭受侵害,系私權力受侵害,實際上則是執法權威遭到蔑視、國家利益遭受損失,系公權力被侵犯,不能以行為人對執法人員的經濟賠償來作為對公權力受侵害的補償,因為此二者并不對價,而且被傷害執法人員也無權代表國家機關出具諒解數,其只是在執法時才能代表國家機關,出具諒解書只能代表其個人意思表示,不能越俎代庖行使國家之意志。所以在前提尚且不能成立的情況下,法院如何能得出從寬處理進而適用緩刑的結論呢,顯然明顯不合理。
(四)從期待可能性角度完善對妨害公務人員的處理
期待可能性是指根據當時的具體情形有可能期待行為人不實施違法行為而實施其他行為,其強調對處在特殊情境下的行為人給與特別的關懷,不強人所難。期待可能性作為一種責任組卻事由在刑法理論中得到深入研討,在司法實踐中礙于法無明文規定故其適用的案例較為鮮見,但將期待可能性理論從書面運用至實踐中去,對保障公民權益及維護刑法尊嚴大有裨益,能進一步發揮司法懲惡揚善的功能,彰顯人文關懷,普及法律信仰。具體到司法實踐中,我們發現很多妨害公務案件可以運用該理論認定行為人不構成犯罪、免除刑罰或減輕處罰的問題。
我們調研中發現不少妨害公務案件出現了父子兵、母子倆都涉嫌妨害公務罪的現象,最后都被做有罪處理,這不得不引起我們深思,現代刑法發展的趨勢也是輕緩化,而我們司法者的心態怎么就如此冰冷呢?擇取張某妨害公務一案為例,行為人張某父親與民警撕扯后被控制在地,張某見狀上前幫張某解圍,期間與民警有拉扯、推搡動作,造成一民警輕微傷。我們認為作為兒子看見自己的父親被壓在地上吃土,本能的反應是上前幫助父親脫離危險,其與民警的拉扯行為是一種本能的舉動,是人之常情,此種情形不應期待張某作出其他適法行為,不應期待兒子看見父親受傷害而站在一旁無動于衷,雖然其行為對其父親的行為客觀上起了一定幫助作用,但刑法不應太苛責,而是保持謙益性,對張某的行為應理解、體諒,故本案不應將張某父親的行為作為犯罪處理。
又如李某涉嫌妨害公務一案,某日午夜時分國有公司職員李某醉酒后駕車從飯店駛回小區時發生事故,雙方協商未果后對方報警,警察來后發現李某醉酒欲將傳喚到派出所調查,李某不愿配合遂與警察周旋拒不上車,后四名警察強行將控制在地,過程中李某強烈反抗、掙扎,造成三名民警不輕微傷傷情。我們認為李某的行為不僅是他的自然反應,也是普通人遇到類似情況的正常反應,雖然李某行為客觀上有暴力性,但情有可原,法律不應期待李某在深知一旦涉嫌犯罪就丟掉工作的情況下作出乖乖束手就擒的適法行為,所以對李某應當減輕甚至免除刑事責任,可以考慮對其作撤案或相對不起訴處理,這也符合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的要求。
三、對策和建議
(一)完善立法及司法解釋,避免機械執法、隨意執法
從前文分析可以看出,當前司法實踐中妨害公務案件主要以是否造成執法人員輕微傷以上的傷情作為定罪標準,而我國刑法未將執法者人身損傷情況規定為妨害公務罪的構成要件,而是將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作為構成要件,這表明立法者的本意是將妨害公務罪的社會危害性表示為阻礙執法者依法執行職務。如果繼續堅持傷情論的定罪標準,而不顧案件其他實質性情節,就有如刻舟求劍,陳興良教授指出,犯罪概念中定量因素導致認定犯罪僵化和教條,不利于全方位同犯罪作斗爭。司法實踐中這種機械的定罪標準,使得現實中大量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執法而未造成執法人員傷情的案件難以用刑法來調整,一定程度上放縱了犯罪。
本文認為刑法將妨害公務罪放在分則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其宗旨是著眼于社會公共秩序的維護,具體來說是合法執法權益的維護。而現有司法實踐中以執法者人身是否遭受輕微傷以上的傷情作為入罪標準不甚恰當,難免讓人產生司法部門更加關注執法者本人的人身是夠是否收到侵害的懷疑,當然,本文亦不否認公共秩序的維護離不開執法者的行為,但在衡量社妨害公務罪的社會危害性的同時,也不能完全不考慮到執法者傷情等可以量化的情節,但是過多考慮到執法者的傷情,乃至將執法者是否受到輕微傷以上的傷情作為惟一或主要標準難免會失之簡單化,從而忽視了行為了對社會公共秩序的蔑視態度和侵害程度,有機械執法之嫌,無法真正起到打擊妨害公務犯罪的作用,
有鑒于此,本文認為針對妨害公務罪的現行條文,首先要進一步強化立法解釋,減少司法解釋中的自我授權現象。其次。要通過司法解釋進一步明確、細化入罪標準,量化入罪情節,運用肯定是列舉方式明確構成犯罪的具體條件,通過否定式列舉刑事確定不構成妨害公務罪的情形,進而約束司法部門適用法律的隨意性,通過并且在實踐操作一段時間后,結合發現的問題再加以修改完善;最后,兩高應當定期公布有代表性的判例,進一步對刑法條文加以適用解釋。以便指導基層司法機關審慎辦案。
(二)規范自由裁量權運用,加強審判監督力度
作為執法者,我們既不能突破現行法律的規定,又不能忽視了實踐中不合理現象,只有慎重運用自由裁量權,合理適用刑罰手段,才會填補立法與之執法之間的鴻溝。妨害公務案件行為人一定程度上算暴力型犯罪人,有一定的人身危險性,對其處以自由刑有利于懲治和預防犯罪。而對那些主觀惡性不深、行為情節較輕、認罪態度較好的行為人,可以考慮對其輕緩化處理,由檢察機關對其作出相對不起訴處理,或法院對其適用緩刑,從而減少自由刑處罰的適用比例,這亦符合刑罰懲罰的經濟學原理。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以下簡稱《量刑指導意見》)對妨害公務罪的量刑幅度區間做了基本規定,但我國刑法對減輕處罰沒有規定具體的限度,對緩刑適用沒有明確的標準,而實踐中掌握的以賠償執法人員損失作為適用緩刑的必要條件,顯然有違立法的本意,2015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中規定暴力襲擊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的,按照妨害公務罪從重處罰,《量刑指導意見》也規定對暴力襲警的可以增加基準刑的10%-30%。可見從重處罰是有限制的,而我們反向推之,從輕也應有一定限度,而不是一律適用緩刑。
通過調查我們發現存在同院不同判的現象,甚至出現前后不同罰的現象,固然片面強調同罪同罰有機械執法之嫌,但同一法院內出現如此明顯量刑不均衡現象,有損法律的公正性。有鑒于此,公檢法司之間應加強溝通協調,形成執法共識,具體來說四家單位可以通過聯席會議、會簽文件等形式就量刑達成一致意見,法司兩家之間應相互配合充分做好對被告人社會調查評估工作,對不符合緩刑適用條件的應對其處以自由刑的刑罰。而檢察機關應大膽履行法律監督職責,認為裁判定性有誤、量刑不合理的,即使不一定成功,也應當提起抗訴,充分行使法律賦予的審判監督權限。
(三)規范執法行為、提高執法水平
當今社會公民法律意識大為提高,執法行為也日益公開化、透明化,然而執法者與民眾之間的沖突現象扔層出不窮,妨害公務案件數量逐年增加,那么問題根源在哪里呢?雷洋案的發生讓我們驚醒,追根溯源,里面固然有當前改革大潮產生尖銳的社會矛盾這一根本原因,但誘發沖突的直接原因在還于執法行為本身,也就是執法行為的規范性問題。
以人民警察為例,作為執法群體主力的警察,在執法過程中應表現出執法者應有的克制和謙抑態度,充分爭取執法對象的理解與配合,而不是只要被執法對象稍微顯示出不配合,就對其上演一出“全武行”,遭到激烈反抗后再將其涉嫌妨害公務罪處理,如此行徑與惡霸何異。警察在執法過程中要充分保障執法對象的權利,嚴格遵循執法流程,及時亮明職務身份,全面履行告知義務,做到實體和程序方面均要合法,盡量避免執法瑕疵,或在發現瑕疵后及時加以補正。以確保執法權益和公民人身權利得到充分的保障。同時應當接受群眾監督,從心底不怕監督,更不應把監督者作為妨害公務犯罪分子處理,只要行為規范合法,態度誠懇謙卑,何愁不能形成警民一家的良好示范效應,從一案開始,帶動一所一片,進而促進全體警察執法行為規范水平的提升,則國家的權威和法律的尊嚴之維護大有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