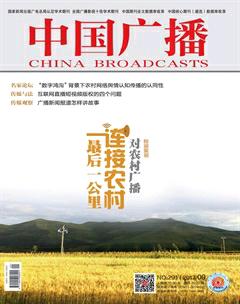農村聽眾離不了“村村響”
許偉++傅雪琴

【摘要】農村廣播村村響簡稱“村村響”,是我國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的一部分。目前,“村村響”成為構建和諧社會新農村建設的重要部分,是推動文化大發展的文化載體工程。本文具體分析“村村響”在新農村建設中發揮的獨特作用,以此探討新媒體時代“村村響”存在及推廣的必要性。
【關鍵詞】新媒體 村村響 應急廣播 最后一公里
【中圖分類號】G221 【文獻標識碼】A
美國自媒體大師杰可布·尼爾森(Jakob Nielsen )曾在《傳統媒體的終結》里預言:未來五到十年間,大多數現行媒體樣式將壽終正寢,它們將被以綜合為特征的網絡媒體所取代。這一觀點顯然是帶有激進色彩的媒體進化論。電視出來的時候,曾經有人預測廣播的“黃昏”來臨了;而網絡新媒體出來的時候,又有人恐慌廣播、電視、紙媒等傳統媒體都將被取代。
廣播真的衰落了嗎?答案是否定的。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個世界變化太快。2010年被稱為“微博元年”,我國進入網絡新媒體時代,在微博、微信的沖擊下,部分紙媒關門,電視開機率急劇下降,可百年廣播卻仍能巋然不動,“伴隨性”的特點使得廣播能與自媒體、網絡新媒體相互兼容。此外,汽車在城鄉居民家庭持續普及,車載廣播一直保持很高的開機率。這兩年,農村廣播“村村響”(簡稱“村村響”)工程的實施,農村收聽人群回歸,讓廣播覆蓋又多了一駕馬車。怎樣用好“村村響”,是我們必須要思考的問題。
“村村響”可以說是對傳統農村大喇叭的傳承和發展,是我國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的一部分。如今已有湖南、內蒙古、福建、山東、寧夏等省區整體推進“村村響”工程,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各級廣播電視部門采用調頻技術恢復農村廣播,力爭實現廣播“村村響”,使農村廣播的發展水平滿足于農村基層的需要,滿足廣播電視協調發展的需要。“村村響”成為構建新時期新農村建設的重要部分,是推動文化大發展的文化載體工程。當下各地“村村響”落地的形式有:大喇叭、可尋址調頻音箱、入戶可開關小喇叭等。廣播“村村響”設備使用相對簡單、成本低廉、易于推廣,“村村響”工程在基層發揮了重要作用。
時間證明,無論是廣播還是電視依然有著廣大的受眾群體,這些傳統媒體正通過自身變革來適應新時代受眾的需求。預測傳統媒體將被取代的人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世界范圍內的受眾存在著多樣性和差異性。例如:在我國,農村人口居住分散,受教育程度總體而言比較低,對新鮮事物接受能力不強。網絡新媒體盡管已經占據了大部分農村,“村村響”起到的獨特作用卻是網絡新媒體所無法替代的。
一、中央精神的“擴音器”
“村村響”承擔著傳達中央政策的功能并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在賈樟柯導演的電影《我11》里面,上世紀70年代,男主角坐著父親的自行車去上學,剛出門時院子里的大喇叭傳出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這是那個時代的文化印記之一。作為黨的方針政策宣傳的重要輿論陣地,即便是現在手機新聞可以隨走隨看,它也取代不了“村村響”在農村輿論宣傳的重要地位。
堅持黨性原則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核心思想,在網絡時代也同樣不能例外。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強調,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堅持黨性原則,最根本的是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農村的新聞傳播具有特殊性,受眾普遍文化程度不高,辨別能力較弱,而網絡新媒體在新聞傳播時充斥著以偏概全、政策解讀不清等情況,這樣會嚴重誤導農村受眾的認識。因此,仍然需要通過“村村響”準確地傳達中央精神,牢牢把握新聞的正確導向。2012年初,筆者到重慶市大足區調研,大足區文廣局的同志告訴我們,重慶多山,在山村征兵,有廣播的地方就容易完成任務,沒有廣播的地方,征兵任務都很難完成。無獨有偶,新疆南疆地區曾流傳這樣一句話:“有廣播的地方就有共產黨,沒有廣播的地方就沒有共產黨。”廣播像一面鏡子,村里的喇叭沒聲了,當地的基層政權也就渙散得差不多了。
如今,網絡已經四通八達,但是仍有很多偏遠地區無法連上網絡,看不上電視。筆者在四川南江縣調研時發現,在南江許多偏遠山村,不僅網絡難以覆蓋,就連電視、廣播信號也到處都是盲區。這時候,“村村響”就發揮了無可替代的獨特作用,解決了這些偏遠山區傳達中央精神“最后一公里”的問題,牢牢占據了輿論陣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鄉村之聲對受眾進行收聽內容調查分析發現,以傳達中央政策為主要內容的節目《三農信息》位于最受農民歡迎的廣播節目的第三名,這說明農民對了解中央政策有著強烈的需求。湖南韶山的“村村響”平臺通過轉播中國鄉村之聲的《三農中國》《三農信息》等節目,滿足了當地農民對政策、信息的需求,取得了不錯的宣傳效果。
二、農民的“信息港”和“歡樂園”
在農村,“村村響”是構建農村和諧文化體系的重要環節,通過“村村響”普及科學文化知識、傳遞經濟信息、提供文化娛樂服務等。2016年5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鄉村之聲組織多路記者,歷時兩個月,深入到河北、山西、吉林、黑龍江等12個省區進行了實地采訪,調研當前我國農村公共服務與城市的差距等問題,調查共收回有效問卷415份,其中一項調查是農村的文化娛樂生活有哪些,以下是調查情況的圖表分析:
根據調查,農村文化室沒有實現全覆蓋。有37%的受訪村民表示,村里沒有文體活動場所,也沒有文化娛樂活動;只有17%的受訪村民表示,村里每個月都有文化娛樂活動。大多數受訪村民表示,只在節假日、過年的時候才能看到文藝演出。農民對身邊文化活動內容的滿意度不高:只有一半的受訪者表示滿意,近30%的受訪者明確表示不滿意。從數據我們得知,當前農民的文化娛樂生活依然匱乏,收聽收看廣播電視仍然是農民最重要的文化娛樂生活。
當前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農村常住人口多為老弱婦孺,這些人員普遍文化程度不高,跟外界接觸少,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熟練使用智能手機,這個時候就需要一個他們能夠接受的傳播媒介。筆者在農村調研時發現,農民收聽廣播途徑多樣,有手機、收音機、可尋址音柱等多種方式,其中,“村村響”體系中的可尋址音柱覆蓋范圍最廣也最穩定。在山東汶上、遼寧東港等地區,可尋址音柱直接安裝在農田和大棚里,農民可以邊勞作邊收聽節目,不僅豐富了文化生活而且還不影響勞動,這是網絡新媒體、電視等傳播媒介無法實現的。在農村,農民很難做到按時收看電視新聞、定時閱讀報紙、及時上網瀏覽信息,而“村村響”則相對靈活,更有利于幫助農民接收信息。正如山東汶上縣農民李玉民所說:“咱家家戶戶都有電視了,還安個廣播有什么用呢?可一聽,確確實實是講了農業技術、防治病蟲害的一些知識,真能體會到小時候聽廣播的感覺了。”在湖北仙桃,一些農村在農戶家門口的電線桿上裝上了大喇叭,每天定時定點播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鄉村之聲的節目,這樣既不會打擾到農民休息,又能給農民提供精神需求。很多農民就搬著椅子,坐在家門口邊聽大喇叭里的節目邊收拾棉花,“村村響”切實豐富了農民的文化生活。endprint
三、應急指揮作用
農村尤其是偏遠地區,“村村響”在災害天氣來臨時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實際生活中,天氣災害或地質災害發生時,比如泥石流、洪水、地震,網絡信號中斷,網絡新媒體無法發揮作用,這個時候直接用掛在村頭的大喇叭反而更及時有效。
如今“村村響”已經在國家應急體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要特別說明的是,以“村村響”為表現形式的農村智能廣播網不是對傳統農村高音喇叭、紙喇叭廣播的簡單恢復,而是技術先進的新型智能廣播。它的控制終端在縣市廣播電視機構,并隨時可以播出重要通知。當重大自然災害發生時,其應急處理的優勢能立刻得以實現。以湖南為例,湖南省農村廣播“村村響”工程是湖南省投資近6億元建設的民心工程,計劃到2017年6月,工程建設全部完成,覆蓋湖南全省101個縣市區。2016年七八月間,湖南郴州市和古丈縣、華容縣、桃江縣、常寧市等縣市區在山洪暴發時,得益于農村廣播及時預警,有序轉移,沒有發生一例人員傷亡事故。
由此可見,“村村響”參與著防災救災體系的方方面面,絕對是不可忽視的一環。
四、媒體融合下的“村村響”
“媒體融合”這個概念最早由美國計算機科學家尼古拉斯·尼葛洛龐蒂(Nicholas Negroponte)提出,美國馬薩諸塞州理工大學教授浦爾(Pool)認為媒介融合是指各種媒介呈現多功能一體化的趨勢。現在各媒體機構都把“媒體融合”作為重要工作來抓,力求打造具有競爭力的新型主流全媒體矩陣。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在內容、渠道、平臺、經營、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從國家層面上引導媒體融合發展。筆者認為,農村不應該是新聞傳播的“盲區”,農民對政策信息、文化都有著迫切的需求,這都需要各方投入更大的精力,如果要打造全媒體矩陣還得有一塊留給“村村響”。
前面我們也提到,農村受眾具有其特殊性,我國農村相對分散,農民數量龐大,因此如果要打造全媒體矩陣,少了“村村響”是不完整的。我們姑且可以把“村村響”當作農民的新媒體,利用新技術對傳統的農村大喇叭進行重塑,使之符合時代需求。媒體融合環境下,如何更大限度地發揮“村村響”的作用,一些地方早就開始探索,他們利用數字、網絡技術實現了“村村響”的智能化。以湖北和山東兩省為例,早在2014年,湖北省就開始試點“村村響”工程,他們的“村村響”是技術先進的新型農村智能廣播網絡,省、市、縣、鄉、村五級播控中心上下對接聯通。利用新技術,實現信息在農村傳播效果的最優化。山東省臨沂市利用數字網絡搭建的“村村響”平臺融合了當地的優質廣播、電視資源,由當地廣電部門把關,起到了“信息篩選”的作用。不僅如此,臨沂市的“村村響”平臺增加了手機電話撥打和短信接入等遠程控制功能,確保使用者在千里之外也能輕松啟動本村或本鎮廣播系統進行應急廣播。融合媒體資源優勢,“村村響”成為解決農村信息傳播“最后一公里”的關鍵鑰匙。
有人認為,網絡新媒體作為工具,它有可能破壞鄉村文化的原始形態,完全失去文化本身的內涵,或起了消極作用。筆者認為這種說法過于偏激。融媒體環境下,我們不能再單論某一媒體的優劣,而應該積極主動地做出改變。通過現代的技術手段,“村村響”與網絡新媒體的融合很好地彌補了網絡新媒體在農村傳播力量的不足,而網絡新媒體則給“村村響”提供了更多、更豐富、更先進的內容,二者是相輔相成的。
注釋
指具有尋址功能、利用調頻方式傳輸音頻信號的音箱。
參考文獻
1.郭長江: 《論傳統媒體的正能量傳遞》,《中國廣播》,2016年第5期。
2.易重華:《網絡時代也要堅守新聞宣傳的黨性原則》,《學習月刊》 ,2013年第15期。
3.立風:《新媒體為鄉村帶來什么?》,《人民日報》(海外版),2016年4月7日,第8 版。
(本文編輯:聶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