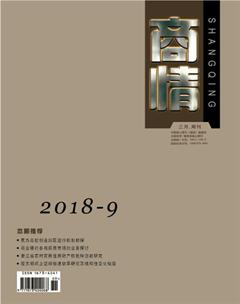身故保險金受益人指定不明解釋規則的修正
張姝妤
[摘要]保險法司法解釋三對受益人的解釋規則違反了身故保險金的制度價值,應予修正。身故保險金的制度價值決定了被保險人不能作為指定受益人,已經指定的應認定指定無效。單純的身份受益人指定應以被保險人身故時與其具有指定身份關系的人為受益人。姓名+身份的指定受益人則應重視姓名,而忽略身份。指定受益人僅載明“法定”時,應認定為未指定受益人;栽明“法定繼承人”時,則應解釋為法定繼承人及其繼承順序為指定受益人與受益順序。無指定受益人的,應以被保險人的法定繼承人及其繼承順序為法定受益人與受益順序。
[關鍵詞]身故保險金 受益人 指定不明解釋 保險法司法解釋三
人身保險合同實務中經常會因為身故保險金受益人指定不明而發生爭議,在適用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處理此類糾紛的過程中不免產生一些爭議與困惑。例如,2017年2月11日,王某、李某蜜月旅行途中因車禍共同遇難,妻子當場死亡,丈夫在送往醫院途中死亡。李某的父母在整理李某的遺物時發現了李某的初戀情人、當時的未婚夫、后來的第一任丈夫馬某在2016年1月5日作為生日禮物送給未婚妻李某的一份壽險保單。馬某以躉交的方式購買了這份保單,投保人為馬某,被保險人為李某,保險期限為10年,身故保險金額為50萬元人民幣,指定受益人一欄填寫了“李某和李某的丈夫”。馬某與李某因感情不合,于2016年10月協議離婚,離婚時未對保險單的現金價值進行分割,也未對保單作出任何變更。王某與李某于2017年2月8日結婚。據此,李某的父母請求保險公司給付50萬元保險金。王某的父母知道后,認為保險金應屬于其兒子王某的遺產,王某死后應由他們繼承。李某的前夫馬某則主張保單是自己花錢買的,指定的受益人也是李某和后來的丈夫即自己,因此只有自己才有權領取保險金。
本案中的爭議源于各方對指定受益人“李某和李某的丈夫”的不同理解。那么,依照我國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定,本案誰應如何確定李某身故保險金的指定受益人呢?投保人指定被保險人本人為其身故保險金受益人的法律后果如何;僅指定受益人的身份而未指明其姓名,或雖指定受益人的姓名和身份,但受益人在被保險人身故時不具有該身份時,如何確定受益人;僅寫明“法定”或“法定繼承人”,或未指定受益人時,如何確定受益人及身故保險金的歸屬等。要澄清上述問題,并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不能拘泥于有關法律或司法解釋的文字含義,機械地適用相關規范,而應從人身保險身故保險金的制度價值出發,反思我國現有規則的缺失,進而提出修正身故保險金受益人指定不明解釋規則的合理建議。
一、被保險人可否為身故保險金的受益人
我國《保險法》第18條第3款規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險合同中由被保險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險金請求權的人。投保人、被保險人可以為受益人。”如果簡單地從字面含義理解,被保險人可以被指定為受益人。但因我國《保險法》規定的受益人并未限定為身故保險金的受益人,理論上還可以理解為包含生存保險金、殘疾保險金、醫療費用保險金等保險金的受益人,因此,李某被指定為受益人表面上看并無不可。
但在我國人身保險實務上,則嚴格區分了身故保險金受益人與其他人身保險金受益人,保險公司的保單條款明確將指定受益人限定為身故保險金的受益人,除另有約定外,其他人身保險金的受益人為被保險人。例如,《國華意外傷害保險條款》(國華人壽[2013]意外傷害保險049號)規定,“您或被保險人可指定一人或數人為身故保險金受益人……”。“除另有約定外,意外傷殘保險金的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因此,嚴格而言,《保險法》第18條第3款的指定受益人實際上只能理解為“身故保險金的受益人即狹義上的受益人”,而不能理解為其他受益人,因為身故保險金之外的其他人身保險金的受益人并不需要特別指定,被保險人是當然的受益人。我國臺灣地區保險法第135條之三也規定,“受益人于被保險人生存期間為被保險人本人。”而從我國《保險法》第42條“受益人先于被保險人死亡”和“受益人與被保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的規定中,亦可明確地推出被保險人與身故保險金的受益人不是同一人,被保險人不能兼任身故保險金受益人這一前置條件。
被保險人不能被指定為狹義上的受益人,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身故保險金的受益人不可能由被保險人兼任。因為在任何含有死亡保險因素的人身保險合同中,身故保險金都不是為被保險人本人的直接利益,而是為被保險人間接利益,即為其遺屬或親朋提供經濟保障。將被保險人指定為其身故保險金的受益人,其生存時死亡保險事故不可能發生,不存在受領身故保險金問題;其死亡時保險事故雖然發生,但被保險人不可能死而復生受領其身故保險金。因此,被保險人為其身故保險金受益人的指定自始客觀不能履行,違反邏輯和常識,徒增混亂,應認定為無效。
二、身份或姓名+身份的指定應如何解釋
指定被保險人的配偶為身故保險金的受益人,系單純的身份指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以下簡稱保險法司法解釋三)第9條第2款第二項的規定,因投保人與被保險人不是同一主體,因此,應按保險合同成立時與被保險人具有配偶關系的人確定受益人。但因投保人馬某在保險合同成立時僅是被保險人李某的未婚夫而非丈夫,則馬某并非受益人。如果馬某當時已是被保險人李某的丈夫,則即使后來離婚也應認定其為受益人。而被保險人李某后來的丈夫王某雖然在被保險人死亡時具有丈夫的身份,也不應認定為受益人。因此,根據上述解釋規則,應認定為未指定受益人,保險金作為被保險人李某的遺產由其繼承人繼承。假如投保人不是被保險人的未婚夫而是被保險人李某,則結果完全不同,保險金將歸被保險人死亡時的丈夫即王某一人所有,王某死后則由其父母繼承。
但問題是為何僅僅因為投保人與被保險人是否為同一主體,就要采取截然不同的解釋規則?其法理依據和正當性何在?樊啟榮等學者認為,作此區分處理的初衷乃試圖兼顧投保人與被保險人的利益。當投保人與被保險人為同一主體,此時并無利益沖突,僅考慮尊重被保險人(投保人)真意以及保障被保險人遺屬即可。但倘若投保人與被保險人為不同主體時,依此解釋實則更加側重于保護投保人的利益。但對投保人的傾向性保護實與現行保險法以被保險人為中心的立法傾向相違背。
筆者贊成這一見解,因為無論投保人與被保險人是否為同一主體,身故保險金的根本價值都是為了保護被保險人的遺屬的經濟安全,而不是為了保護投保人因交納保險費的投資利益。首先,不是被保險人的投保人完全可以在征得被保險人同意后指定自己為受益人,除非法律禁止其作為指定受益人,如《保險法》第39條規定的“投保人為與其有勞動關系的勞動者投保人身保險,不得指定被保險人及其近親屬以外的人為受益人。”當然,這里允許將被保險人作為指定受益人是錯誤的,有悖于身故保險金的制度價值。其次,即使投保人不是指定受益人,也不影響其作為保單所有人或持有人享有的諸如保單質押、保單貼現或退保后獲得保單的現金價值的權利。再次,領取身故保險金的權利通常都由與被保險人死亡時關系密切的人享有,將與被保險人死亡時具有指定身份關系的人解釋為受益人,而保險合同成立時雖與被保險人有指定的身份關系但被保險人死亡時已不具有該種身份關系的人不應被解釋為受益人。只有如此,被保險人方能死而無憾。《保險法》第42條在無指定受益人時將保險金作為被保險人的遺產而非投保人的遺產,由保險人依照繼承法的規定履行給付保險金的義務,實際上也體現了身故保險金的分配應以被保險人為中心的觀念。最后,將與被保險人死亡時具有指定身份關系的人解釋為受益人,也是國內外保險法立法的慣例與理論的主流學說。梁宇賢認為,“指定之時,有該特定身份或關系,但保險事故發生時,已喪失該身份或關系者,則非受益人;倘指定之時,本無該身份或關系之人,但于保險事故發生時,具備該身份或關系者,為受益人,得請求保險金之給付。”
保險法司法解釋三第9條第2款第三項規定,“約定的受益人包括姓名和身份關系,保險事故發生時身份關系發生變化的,認定為未指定受益人。q塞一解釋規則顯然更看重的受益人在被保險人身故時是否仍具有指定的身份,而不看重受益人姓名的指定。身份+姓名的指定方式在人身保險實務中最為常見,但問題是這種受益人指定的含義究竟是否有疑義,如有疑義又應如何解釋為妥。筆者認為,實務中不僅在保單上載明了受益人的姓名和身份,而且載明受益人的身份號碼、住所、聯系方式等信息,但這些描述性的信息不過是為了方便保險人將來給付保險金,而不是作為被保險人必須具備的條件或要求。事實上姓名及其他描述性信息意味著受益人是明確無疑的,如果受益人在指定后、出險前身份變化,不再具有指定時的身份,典型的如夫妻離婚,受益人喪失被保險人配偶的身份,投保人不愿該受益人繼續作為受益人,則投保人完全可以另行指定受益人。投保人采取這種積極主動的變更指定受益人的方式,既是意思自治的體現,也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方式。不顧投保人可以變更而不變更指定受益人的主觀意愿和客觀事實,而采取司法解釋的方式將這種情形認定為投保人未指定受益人,則不僅有悖于意思自治原則,而且是低效率、高成本的。國內外保險法理論與實務界普遍的觀點則是重視姓名而忽略身份,僅以指定的姓名確定受益人。我們應當借鑒這一主流觀點,將指定無誤的姓名作為受益人,而忽略身份的變化。
三、法定或法定繼承人的指定應如何解釋
保險合同中還有在指定受益人欄目下,直接填寫或打印“法定”或“法定繼承人”字樣的情形,保險法司法解釋三將其解釋為“以繼承法規定的法定繼承人為受益人”。“法定”二字無論如何都不可能作如此解釋,這一解釋違反了意思表示解釋的基本原則,既非表示主義,亦非意思主義。“法定”沒有確切的含義,應認定為未指定受益人更為合理。“法定繼承人”的解釋基本上可以成立,但問題是如果將被保險人的所有法定繼承人都解釋為指定受益人,而不區分受益人的順序,由所有法定繼承人平均分配保險金,則明顯違反投保人的真實意思和身故保險金的制度價值。因此,合理的解釋應當是以繼承法規定的法定繼承人和繼承順序為受益人和受益順序。
四、沒有指定受益人時應如何推定受益人
當投保人沒有指定受益人時應如何推定受益人,《保險法》第42條的規定并非這一問題的答案。該條雖然已經明確將保險金作為被保險人的遺產,但筆者認為,無論投保人與被保險人是否為同一主體,身故保險金都不是被保險人的遺產,因為身故保險金不具有遺產的基本屬性即時間性,被保險人生前不曾享有,死后何來遺留。該條合理的修改應是,無指定受益人時,被保險人的法定繼承人為法定受益人,法定繼承順序為法定受益順序。由保險人向被保險人的法定受益人給付身故保險金。
五、結論
保險法司法解釋三對受益人的解釋規則違反了身故保險金的制度價值,應予修正。身故保險金的制度價值決定了被保險人不能作為指定受益人,已經指定的應認定指定無效。單純的身份受益人指定應以被保險人身故時與其具有指定身份關系的人為受益人。姓名+身份的指定受益人則應重視姓名,而忽略身份。指定受益人僅載明“法定”時,應認定為未指定受益人;載明“法定繼承人”時,則應解釋為法定繼承人及其繼承順序為指定受益人與受益順序。無指定受益人的,應以被保險人的法定繼承人及其繼承順序為法定受益人與受益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