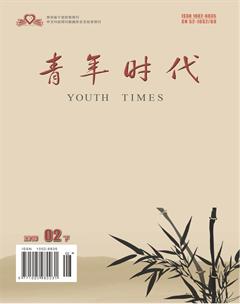鄉(xiāng)村“話語”結構下的國家干預
王剛
摘 要:農(nóng)村社會內(nèi)部自改革開放以來經(jīng)歷了巨大的變化,內(nèi)部權力狀態(tài)也形成了對應的形式結構。當前的精準扶貧戰(zhàn)略受到了大量社會研究工作者的關注,對于精準扶貧的必要性研究形成了豐富的成果。文章將從農(nóng)村社會內(nèi)部的話語權角度來分析精準扶貧在當下農(nóng)村社會扶貧中的必要性。
關鍵詞:農(nóng)村;話語權;精準扶貧
精準扶貧自2013年開始作為中國當前社會環(huán)境形勢下扶貧攻堅的一種新的戰(zhàn)略舉措,圍繞精準扶貧也開始了廣泛的社會動員。精準扶貧的提出被普遍地認為是對中國以往扶貧策略的新的轉(zhuǎn)向,是糾正過往扶貧不足的一種措施。事實上,精準扶貧并非對之前扶貧政策的完全摒棄,而是對精準的對象和單位做出了更進一步的明確和細化[1]。學界也嘗試對精準扶貧的必要性進行多維度解釋。莊天慧(2016)主張精準扶貧是扶貧的技術手段和管理方式上必須與時俱進,更加科學化和精細化的客觀要求[2]。汪三貴(2015)提出經(jīng)濟增長對減貧的影響力正在減弱,為抵消伴隨經(jīng)濟增長而帶來減貧效應降低,需要進行精準扶貧[3]。左停(2015)認為精準扶貧從扶貧機制上由主要依賴經(jīng)濟增長的“涓滴效應”到更加注重‘靶向性對目標人群直接加以扶貧干預的動態(tài)調(diào)整[4]。而鄭瑞強(2016)研究表明,精準扶貧是對經(jīng)濟新常態(tài)所要求的一種扶貧資源配置方式,資源的供需更加有針對性,防止資源配置不合理造成資源浪費,更加注重有質(zhì)量的扶貧效應,實現(xiàn)資源的有效功能性發(fā)揮[5]。學界不同視角解釋為何扶貧領域需要精準扶貧。文章從農(nóng)村社會內(nèi)部的權力結構方面論析精準扶貧的必要性。
一、農(nóng)村內(nèi)部的話語權
米歇爾·福柯認為話語即權力。話語的份量意味者權力的大小,話語中蘊含著強制力量或支配力量,真正的權力是通過話語來實現(xiàn)的[6]。對于農(nóng)村話語權的討論中,既有研究著重從傳播學角度探討農(nóng)民群體與社會其他群體在話語權上的地位差別,主要探析農(nóng)村弱勢群體的媒介話語權的現(xiàn)狀、成因及改變[7]。抑或話語權缺失與群體性事件的關聯(lián)[8]。在農(nóng)村社會內(nèi)部,成員之間的話語權大小存在大小差異,在分布上表現(xiàn)出明顯的非均衡特點。
誰掌握農(nóng)村社會內(nèi)部的話語權,誰就擁有了農(nóng)村內(nèi)部的權力。對于村莊內(nèi)部的權力歸屬與變化形式有諸多討論。朱戰(zhàn)輝認為隨著農(nóng)村經(jīng)濟的發(fā)展,農(nóng)村社會和農(nóng)民出現(xiàn)分化,農(nóng)村精英也經(jīng)歷了變化,不再集中與過去的體制內(nèi)精英。而農(nóng)村社會權力形成了仝志輝和賀雪峰等人認為的體制精英-非體制精英-普通村民的三層權力結構[9]。郭圣莉和王穎穎則認為農(nóng)村社會內(nèi)的精英是不斷流動的,將社會內(nèi)部的權力劃分為體制內(nèi)或者體制外這種對立的二元結構是不適當?shù)摹T谧岳枨蟮膶蛑拢r(nóng)村社會內(nèi)部的權力形態(tài)應該表現(xiàn)為相對一元的主從權力結構[10]。不論是體制內(nèi)外的二元對立結構亦或是一元的主從結構,都表明了一個現(xiàn)實,即當下的農(nóng)村社會內(nèi)部,“差序權力格局”成為一種普遍的現(xiàn)象。農(nóng)村社會內(nèi)部不再是一個均質(zhì)化的社會,其內(nèi)部成員因為經(jīng)濟、職業(yè)、學識、家族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影響,內(nèi)部的權力結構具有明顯階梯性,成員的話語權力具有明顯的強弱之分、大小之分。經(jīng)濟勢力越強,能力越強,占據(jù)體制內(nèi)身份,或者在當?shù)仉`屬于大家族的社會成員往往具有較強的話語權。反觀其他成員則處于話語權力弱方。
在這種“差序權力格局”之下,農(nóng)村扶貧也因此催生了“精英捕獲”這一現(xiàn)象,形成了扶貧“內(nèi)卷化”的結果,即扶貧資源在農(nóng)村社會的配置中被各類精英所占據(jù),扶貧資源并沒有惠及到貧困群體,“窮者越窮,富者越富。”雖然扶貧資源持續(xù)不斷地注入到農(nóng)村中進行扶貧,但是弱勢群體的話語狀態(tài)沒有受到明顯的改變。筆者在進行農(nóng)村精準扶貧調(diào)研時就曾得到基層扶貧干部這樣的論述:“作為貧困戶來說,他在整個組里面基本上是沒得話語權的。他沒得話語權才能夠成為貧困戶,是這樣一個原因。”農(nóng)村貧困戶在“精英捕獲”現(xiàn)象之下,形成了一個話語權與經(jīng)濟地位的惡性循環(huán):話語權地位低-精英捕獲-經(jīng)濟實力差-話語權地位低。在這種鏈條之下,農(nóng)村貧困戶的地位難以改善,農(nóng)村的貧困狀況也無法得以改變。
二、精準扶貧的內(nèi)涵屬性
精準扶貧作為扶貧的一種改進戰(zhàn)略,雖然在表現(xiàn)形式上同傳統(tǒng)的扶貧方式相比存在諸多的差異,但其本質(zhì)依然是國家資源介入到基層社會改善成員經(jīng)濟地位狀態(tài)的過程,是國家層面的一種發(fā)展干預。這種發(fā)展干預與以往不同的特點在于其干預方式的精細化,更加具有針對性。
在以往的貧困對象選擇中,往往都是瞄向的貧窮區(qū)域,如中國的幾大貧困集中區(qū)域;或者是貧困縣,例如國家級貧困縣。;或者項目瞄向貧困村;這些都說明在扶貧中國家資源仍然在較大區(qū)域上配置,沒有具體投放在農(nóng)村個體、家庭上。扶貧資源配置在大的層級上流動,國家干預的效果被分配到農(nóng)村社會成員的整體構成上。通過對中國貧困現(xiàn)狀的審視之下,會發(fā)現(xiàn)除少數(shù)表現(xiàn)為成片貧困之外,更多地呈現(xiàn)出農(nóng)村社會內(nèi)部個體家庭的貧困。成員個體的經(jīng)濟地位沒有發(fā)生明顯改變,農(nóng)村社會權力結構也未發(fā)生變化。社會福利的增加依靠最貧困群體的福利增加。而在這種資源配置模式下,農(nóng)村貧困群體卻難以獲得改變自身福利水平的機會。
不同的學者對精準扶貧的內(nèi)涵界定存在巨大的差異。例如莊天慧從三個角度總結了對精準扶貧的內(nèi)涵劃分。雖然界定的角度不同,但是在精準扶貧的內(nèi)涵中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和精準考核一直是理解分析的一個基本角度,也是精準扶貧運行的一般環(huán)節(jié)。圍繞扶貧對象涉及到精準識別和精準幫扶。扶貧對象精準就要做到精準識別,誰是貧困戶,貧困的程度有多深,致貧的原因包括哪些等等都要做到清晰的界定。這種精準識別的手段將扶貧對象的瞄定從地域性對象轉(zhuǎn)變?yōu)閱蝹€的自然人。通過精準識別的信息收集,分析貧困對象,用精準幫扶的手段來幫助貧困對象,實現(xiàn)貧困對象經(jīng)濟地位的提升。精準扶貧圍繞個體成員進行資源的配置,超越了以往以區(qū)域為扶貧資源投入對象的資源配置方式,精細化程度更高,針對性更強。
三、話語權地位的改善:精準扶貧的必要性
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把精準扶貧的六個要求歸納為:扶貧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通過精準扶貧的實踐操作,能夠獲得兩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將國家權力直接同貧困個體聯(lián)結了起來,破除了村莊這一層級內(nèi)權力結構對扶貧資源配置的影響。在村莊層級方面內(nèi),因為村莊話語權結構的影響,資源配置難以以一種理想的方式在成員之間進行分配。而精準扶貧則直接突破了這層阻擾,直接將資源分配將貧困個體連接;另一方面在于通過扶貧效果的提升,緩解“差序權力格局”下村莊發(fā)展的非均衡狀態(tài),以實現(xiàn)村莊內(nèi)部整體福利的提升,以及村莊社會內(nèi)部的和諧。
精準扶貧對農(nóng)村內(nèi)部權力結構的影響主要從提升貧困個體經(jīng)濟實力這一環(huán)節(jié)破除話語權地位低-精英捕獲-經(jīng)濟實力差-話語權地位低這一變化的惡性循環(huán)來實現(xiàn)。在貧困的認定主要以經(jīng)濟實力來衡量,以及經(jīng)濟實力是影響話語權的重要因素的現(xiàn)實狀態(tài)下,經(jīng)濟實力的提升能夠改善農(nóng)村貧困個體在農(nóng)村社會權力結構中的狀態(tài)。
四、結語
精準扶貧所做出的實際后果更多為改善成員的話語不平等狀態(tài)。農(nóng)村社會內(nèi)部的“差序權力格局”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而精準扶貧的實施并不會從整體上顛覆這一格局,“差序權力格局”也必然會繼續(xù)影響到農(nóng)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即時在精準扶貧的實施中,“差序權力格局”也會發(fā)揮作用,從而造成精準扶貧的不精準執(zhí)行。因此破除“差序權力格局”對精準扶貧實施的影響也將成為未來扶貧研究的一個重要話題。
參考文獻:
[1]李廣志.農(nóng)村空心化背景下精準扶貧的實施困境與對策研究[J].成都行政學院學報,2016(04):57-61.
[2]莊天慧,楊帆,曾維忠.精準扶貧內(nèi)涵及其與精準脫貧的辯證關系探析[J].內(nèi)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6,37(03):6-12.
[3]汪三貴,郭子豪.論中國的精準扶貧.貴州社會科學[J].2015(05):147-150.
[4]左停,楊雨鑫,鐘玲.精準扶貧:技術靶向、理論解析和現(xiàn)實挑戰(zhàn).貴州社會科學,2015(08):156-162
[5]鄭瑞強.精準扶貧的政策內(nèi)蘊、關鍵問題與政策走向[J].內(nèi)蒙古社會科學,2016,37(03):1-5.
[6]李月英,伊慶山.政府干預農(nóng)村發(fā)展過程中農(nóng)民平等話語權的建設——基于福柯話語理論的視角[J].濟寧學院學報,2014,35(04):105-110.
[7]周春霞.論農(nóng)村弱勢群體的媒介話語權[J].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29(03):150-153.
[8]李翔宇,周春曉.論我國農(nóng)民話語權的缺失與保障——基于農(nóng)村群體性實踐頻發(fā)的分析[J].領導科學,2013(5):63-64.
[9]朱戰(zhàn)輝.精英俘獲:村莊結構變遷鱉精下扶貧項目“內(nèi)卷化”分析——基于黔西南N村產(chǎn)業(yè)扶貧的調(diào)查研究[J].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7,19(05):55-62
[10]郭圣莉,王穎穎.支配與依附:村莊主從權力結構研究——基于村莊精英角色的分析[J].行政論壇,2017(06):8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