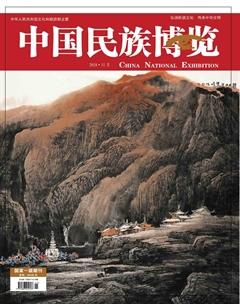民間傳說中的“儒”“釋”“道”
【摘要】在傳統文化中,儒家、道家、佛家的美學思想對中國社會生活的影響極其深遠,而民間傳說在口口相傳中與這些傳統文化緊密結合,讓傳說中的人物性格、故事情節、社會關系等無一例外地打上了“儒釋道”的烙印。本文以“西湖傳說”為對象,探究了儒家美學、道家美學、佛家美學的特點以及在“西湖傳說”中的體現,挖掘了“西湖傳說”獨特的美學價值,以期更多人關注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
【關鍵詞】儒釋道;西湖傳說;傳統文化;美學
【中圖分類號】G02 【文獻標識碼】A
一、儒家之美
儒家文化影響力巨大,它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流,曾經在治國安邦、禮樂教化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以人為本,生命至上;仁愛親人,推己及人;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等思想是儒家思想的要旨。儒家思想對中國傳統美學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論語》中的“美”字出現過十多次,孔子認為,美能夠使人快樂;美既可以是形式,也可以是內容。
(一)善之美
儒家認為“美與善同意”,強調了道德是一種向善的思想觀念。《顏淵》說:“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說的是君子成全別人的好事,不幫助別人做壞事。其中,“美”與“惡”是對立的;《八佾》中記載著:《韶》是歌頌舜的樂曲,《武》是歌頌武王伐紂的樂曲。兩首有不同的內涵,舜的天子之位是由堯“禪讓”而來,因此孔子認為盡善盡美;而周武王的天子之位是由討伐商紂而來,盡管是正義之戰,在孔子看來卻是盡美而未盡善的。由此可見,孔子將美與善進行對舉,將善作為美的標準與美的內容。
“西湖傳說”中有許多故事都教導人們積極行善。《斷橋的傳說》講述了段家夫婦收留了衣衫襤褸的老人,并用捕來的鯉魚和家釀的土酒招待他。后來老人贈送了酒藥給段家夫婦,使他們釀出了好酒,生意興隆。后來,段家夫婦又用做生意的錢造了“段橋”方便行人。這則故事中的主人公不計較流浪老人的貧窮,而是熱情招待,在得到回報之后建橋造福相鄰的舉動反映了中國傳統的“善舉”。如果說段家夫婦對流浪老人行善是知善的行為,那么“造橋”則上升到一種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自覺,達到“好善”的境界,與孔子理想中的美善相樂的境界。
(二)和之美
《論語·學而》中說道:“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意思是說,禮的作用在于使人的關系和諧為可貴。先王治國,就以這樣為美。“和”之美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有許多表現形式。如天地之和——和者天之正也……舉天地之道而美于和;天人之和——中國古人認為,天與人可以相互感應,要想獲得保佑,人類必須讓自身與“天”處于一種和諧狀態;人人之和——也是一種社會之和,《禮記》中的大同世界就是一種和諧社會。
《南屏晨鐘與晚鐘》中說道:南屏晚鐘營造了一種景物與聲音“共鳴”的和諧景象,正是這種天地之和的意境才使康熙皇帝放棄為將“晚鐘”改成“晨鐘”的想法。
《日照亭與印月潭》中描述了月亮與湖水相互映照,寄托蘇軾對已逝去朋友的思念,營造了一種陰陽相和、情景交融的美感。《平湖秋月的傳說》中也引用了紹興才子徐文長的詩句:一色湖光萬頃秋,天堂人間共圓月,也描繪了天人相和的美妙景致。
《西湖景致六吊橋》則將西湖兩岸男女青年相會的和諧場面刻畫了出來,展現了一種人與人相處其樂融融的和諧美。
(三)情之美
男女相愛的情節在中國文學中非常普遍,張生與鶯鶯、賈寶玉與林黛玉都傳頌至今。儒家思想中對“情”的態度是承認的,認為它是一種客觀存在。《孟子·告子上》:告子曰:食、色、性也,說的是食、色為人類生存所必須。表明儒家認為情欲是人性的客觀存在,不可去除。儒家代表朱熹也說“情既發,有善有不善,在人如何耳”。儒家對“情”的觀念奠定了中國傳統美學以“情”為美的基礎。
《蘇小小墓》講述了名妓蘇小小與鮑仁愛情的真美;《雷峰塔》展現了白娘子與許仙愛情的凄美;《柳浪聞鶯》記敘了織錦小伙兒柳浪與黃鶯仙子愛情的純美。在《西湖女神救漁女》中主人公是漁夫藕兒與漁女紅蓮,他們的愛情得到了西湖女神的護佑;《小漁夫救龍女得妻》則再現了漁夫苦兒與龍女的愛情悲劇,催人淚下。“西湖傳說”中像這樣的愛情故事還有很多,描繪的全部都是男女之間純潔、真誠的情感,展現了儒家文化中的“情”之美。故事中男主人公大多具有質樸、勤勞、誠實、善良的品質,積極向善;女主人公美麗、溫柔、自尊、自愛,忠貞不渝。男女主人公都熱愛生活、不畏權貴,他們的愛情是中國古代崇尚的純潔之愛。
二、道家之美
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在《道德經》中提到“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這是一種無限美,超越了有形的局限性,以“無”為美,是指以“無”為特點的“道”。在道家思想中,“道”既是哲學范疇,又是美學范疇。道以自然、無意識為美。另一代表人物莊子繼承了老子以道為美的思想,如“至樂無樂”,說的是世俗所謂的快樂及其對象并不是真正的美;另外,美給人帶來的快樂是不可感受、不可經驗的。正是由于這樣的思想形成了道家以“淡”、以“柔”、以“自然”為美的傾向。
(一)淡之美
《老子》中提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老子認為,無味超越了有限的味,具有無限的全味,無味不是不味,是一種境界,比世俗的美味高級得多。這種淡是一個美學范疇,看似平淡無味,實際上卻蘊含著無窮無盡的美的意味,超越了人的生理欲求,提倡一種平淡的趣味,追求的是一種淡泊、寧靜、淳樸的狀態。中國古典美學深受這種美的影響,使中國人的美感走到了一個新的方面。
《梅妻鶴子》的主人公是北宋詩人林和靖。他深惡當朝昏庸腐敗,不愿為官,到處游山玩水,最后在故鄉杭州的孤山下過著隱居生活的故事。他以梅為妻,以鶴為子,與鹿為伴,吟詩作畫,生活雖清貧、孤獨,但恬淡、知足。《吳山城隍廟》中,唐代詩人吳仁壁隱居的西湖雞籠山草房,說自己“久避塵世,乃庸碌無能之輩”而拒絕為吳王錢镠的母親寫墓志銘,最后被沉江而死。《蘇小小墓》中的蘇小小也是一不愛金銀,二不要金屋,生性只愛西湖山水,只喜遨游兩峰三竺,把榮華富貴看作糞土。這些人物寧靜淡泊的生活狀態與精神追求與道家所展現的“淡”的美非常一致,倡導了一種超脫功利、淡泊世物的人生觀。
(二)柔之美
“柔”在中國古代是與“美”并列的審美用語,甚至是比“剛”更勝一籌的審美范疇。《老子》說,“強大處下,柔弱處上。”“柔弱勝剛強”“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由此可見,柔是比剛更美的境界。同理,“小”“弱”也是老子所崇尚的。
《雷峰塔》中的白娘子的形象為“柔”“弱”“雌”;而法海的形象為“剛”“強”“雄”,最后白娘子與小青一同戰勝了法海,將法海趕入螃蟹當中。這以柔克剛,以弱勝強的結局與道家的審美觀念完全一致。《小黃龍》中,主人公善良的小黃龍一直受作惡多端的老黃龍壓迫,這里,小與大形成了形象對比;而他們行為上的反差更加明顯:小黃龍為了造福人類,甚至忍痛將自己的 鱗片揭下來化作金錠接濟窮人,而老黃龍卻經常噴火燒毀窮人的房子。“西湖傳說”中濟公的故事也非常多,濟公是神仙,完全不同于傳統仙人的衣冠楚楚、道貌岸然;濟公是和尚,卻酒肉穿腸過,也不似一般僧人嚴守清規。這種形象與老子描繪的“下”“賤”極其相似。
(三)自然之美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出了人的理想應該是自然。道家所討論的自然,是作為人的本質的自由問題。社會的發展,使人擺脫了初級的、混沌的“天人合一”狀態,開始有了對自然“主體與客體”的認識,導致人與自然甚至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復雜,自由越來越受到局限。這是道家所拒斥的。自由是什么呢?是人在實踐過程中對“主體與客體”、人與自然規律的重新認識與超越,是擺脫生理本能而與宇宙萬物融為一體的心靈上的超脫與自由。
“西湖”的故事中,“自由”是所有人物都向往與追求的。《石香爐》中,魯班兄妹有著高超的制造技藝,他們不僅能招收180個徒弟,還能憑著手藝制作出巨大的擁有“魔力”的石香爐,鎮壓了為非作歹的“黑魚精”。顯然,他們是掌握了自然物的規律,而使自己獲得自由。而《七仙女爭鏡美天堂》則描繪了另外一種更高層次的自由。故事將天宮描述成冷漠虛偽的世界;而人間則充滿溫情友善。七仙女為了追求自由寧愿化作山峰也要留在人間。這種自由,沒有約束,沒有控制,擺脫了社會與身份的束縛,使心靈得到解脫。
三、佛家之美
佛教于西漢末年、東漢初年傳入中國。唐代,中國的佛教進入鼎盛時期,并逐步發展,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宋代以后,佛教已經深入影響了政治、思想、文學、音樂等許多方面,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佛教認為,“色即是空”“寂滅為樂”,認為人對物質世界美好事物的貪愛執取是引起人生無限痛苦的根源,因此形成了獨特的審美情趣。西湖景區的寺廟非常多,靈隱寺、凈慈寺、法喜寺、法凈寺等都是著名的佛教圣地,因此西湖的許多傳說與佛教有關。不僅如此,傳說中的故事情節滲透著濃郁的佛教思想,體現著佛教的審美。
(一)因緣美
佛教理論的核心是緣起,所有結果都有其緣由。“見緣則見法”“圣教自淺至深,不出因緣二字”,《楞嚴經疏》與《稻稈經》都闡明了這個道理,顯示了任何事情、任何結果都有其因緣。所以,應該培植積極的、好的因緣,要學會培植好緣、廣結善緣、隨順因緣、改善逆緣。
“西湖傳說”中善有善報的故事非常多,這樣的“報應”說就來自于“因緣論”。《觀音塘上觀音堂》中講述了少女阿花在雪夜救助了一個老人與一個小孩。后來才知道這兩人是觀音菩薩與龍王變的。而阿花因此受到了“神佛起身相迎”的禮遇;相反,故事中,觀音堂前的水井預示著“樊江司”來生會變成一頭長滿癩皮癬的牛。這是因為樊江司年輕時用奸詐手段侵占他人錢財而得到的報應。故事的結尾還配詩一首:頭頂三尺有神靈,行善作惡記分明;若想遠離地獄門,須知因果會報應。與此類似,《吳山第一泉》《十二生肖石》《王婆與大井》等許多故事中都善有善報的因果聯系。
(二)涅槃美
佛教中的“圓寂”就是涅槃。釋迦牟尼的觀點是:死是痛苦的結束,又是新生命的開始。因此,涅槃是美的。
“西湖傳說”中的許多人物死后化作另一種形象,獲得新生。《尋太陽》中,劉春犧牲后化作啟明星;《七仙女爭鏡美天堂》中,七仙女化作七座山峰,與凡人為伴;《一株楊柳一株桃》中,小桃、小柳兩姐妹化作蘇堤邊的桃樹和柳樹;《虎跑泉》中,為民找水的兩兄弟化作兩只猛虎。這些輪回、新生,與“西湖傳說”中著名的“梁祝化蝶”類似,符合涅槃之美。
(三)光明美
“光明山”“光明心殿”“光明土”這些佛教圣地的名字足以證明佛教向往、追求、贊美光明,達到了“光明崇拜”的程度。凈土宗中教主名號有13個,其中12個是與“光明”有關的。《無量壽經·光明遍照》指出,佛光比日月之光亮千億萬倍。另外,佛教還提出了“外光明”——日、月、火、燈、珠、鏡等能象征佛光,驅除黑暗。
“西湖傳說”中《韜光仙水》《尋太陽》、《古寺庵》、《石龍山》講述了主人公對光明的向往。同時,另一些傳說則表達了對“外光明”的追求。《三潭印月》中的月亮;《寶鏡》中的鏡子;《烏龍》中的寶珠;《夜里吊水不點燈》中的火與燈。這些外光明之物反映了人們以物為載體,表達內心對光明的追求與向往,與黑暗及邪惡的抗爭。
“儒”“釋”“道”是美學,它們深深影響了中國人民的審美思想與情趣;同時又是哲學,其思想對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都有極強的指引作用。中國的“民間傳說”吸收了這些精華,形成了獨特的文化遺產。充分利用民間傳說的價值,弘揚其中的真、善、美,對當代人的人生觀、價值觀有著積極的引導作用。藝術工作者要結合媒體發展新態勢,利用先進的傳播手段,使民間傳說這一人民智慧的結晶散發出新的光彩。
參考文獻:
[1]杭州圖書館編.“西湖傳說”故事集成名勝古跡卷[M].杭州:杭州出版社,2012.
[2]宗白華.美學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祁志祥.中國美學原理[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
[4]陳鼓應.老子注釋及評價[M].北京:中華書局,1999.
[5]祁志祥.中國美學原理[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
[6]索甲仁波切.西藏生死書[M].呼和浩特:內蒙文化出版社,1998.
[7]祁志祥.中國美學原理[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
[8]黃德寬.關注名俗文化之美[J].出版廣角,2014.
作者簡介:劉超(1976-),男,漢族,湖北省武漢市人,中國傳媒大學播音主持藝術學專業2016級博士研究生,浙江傳媒學院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教師,研究方向:語言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