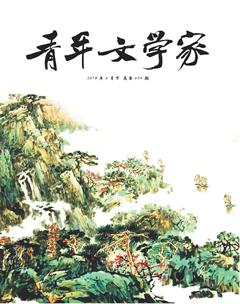平安時代白居易詩歌廣泛流傳的原因研究
許凌薇
摘 要:日本歷史上曾多次派使節(jié)到我國學習先進的政策文化,甚至各種節(jié)日祭典、民間習俗等等,唐朝時期更是頻繁派遣遣唐使到我國學習,白居易的詩歌在此時傳入日本,對日本平安時代漢詩的發(fā)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筆者通過查閱大量文獻,追尋白居易詩歌傳入日本的歷史蹤跡,結(jié)合平安時代日本的社會背景以及白居易詩歌的特點,探索白氏詩文在平安時期備受推崇的原因。
關(guān)鍵詞:唐朝;白居易;平安時代;漢詩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18-0-01
白居易詩歌的研究一直是國內(nèi)學術(shù)界學者們研究的熱門。比較有名的是杜曉勒教授的著作《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隋唐五代文學研究》。在這篇著作中杜教授認為:“雖然在我國對于白居易詩歌的研究比不上對于同時代詩人李白和杜甫的研究,但依然有很多可圈可點的地方。”[1]杜教授的研究,為此后白氏詩文研究的學者提供了寶貴資料。其他對白居易作品頗有研究的學者,如李爾康、李國標等,我國學界對白居易的研究已經(jīng)較為全面。在日本學界,研究中唐文學的學者花房英樹所著《白氏文集的成書》、《白居易文學》等,對白居易文學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除此之外還有平野顯照、小守郁子等,對白居易研究做了更全面的分析。可以說日本學者對于白居易研究比起國內(nèi)的相關(guān)研究狀況絲毫不遜色。本文從白居易詩歌的特點出發(fā)并結(jié)合當時的平安時代,探索白氏詩文受歡迎的原因。
一、中日文化交流的淵源
日本兩千多年前就與中國大陸頻繁交流,汲取中國的優(yōu)秀文化營養(yǎng),融合成日本特色文化傳承至今。日本歷史上第一部記錄日本古代神話、傳說、童謠等的文學作品《古事記》(712年)中,就有提到中國《論語》的記錄:天皇又命令百濟國說:“如有賢人,則貢上。”可見早在公元七世紀日本就已引進中國文學典籍向古代中國文明學習了。文字方面,日本最初學習中國的漢字并在此基礎(chǔ)上演變成了現(xiàn)在的假名。古代日本法典是用漢字寫成的。比如圣德太子于在公元604年頒布的十七條憲法,就完全是用中國的漢字撰寫的。縱觀這部法典的大致內(nèi)容,主要是對官僚和貴族的道德規(guī)范以及佛教思想的敘寫,其中許多思想及詞匯都是模仿當時的中國,由此可見中國對日本產(chǎn)生了由表及里的文化滲透。
白居易詩歌傳入日本的事件最早見于《日本文德天皇實錄》的記載:太宰少貳藤原岳守從唐朝商人帶來的物品中挑出《元白詩筆》呈獻仁明天皇。天皇愛不釋手,因此給太宰少貳藤原岳守提升官位。這是有文字記載的白居易詩歌最初傳入日本的情況。此后遣唐使陸陸續(xù)續(xù)的帶回了更多有關(guān)白居易的作品。據(jù)《日本國見在書目》記載,當時傳入日本的白居易詩集有《白氏文集》70卷,《白氏長慶集》29卷。許多文人也開始收錄白居易的詩歌。如大江維時編輯的《千載佳句》中共收錄了1110首詩,白居易的詩歌就占據(jù)了一多半;藤原公任編纂的《和漢朗詠集》中也收錄了眾多白居易的詩集。[2]《源氏物語》、《枕草子》中,也直接引用大量的中國古典文學典籍,其中引用白居易的詩歌最多。
二、平安時期人們對白氏詩集喜愛的原因
白居易詩歌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他的作品傳入日本后就成為皇室、貴族等的必讀詩歌。“這種自上而下的,由皇室到宮廷,由宮廷到普通老百姓階層的白氏詩文崇拜之風迅速風靡全國。”[3]白居易的詩集為什么在平安時代如此受到推崇?筆者翻閱大量相關(guān)文獻,并結(jié)合當時的時代背景、白居易的生平傳記及其詩歌的特點進行了如下分析研究(1)日本天皇對白氏詩文的推崇。“早在平安時代中期,嵯峨天皇就尤為鐘愛白氏詩集;到了醍醐天皇時期,還聘請專門學者為皇宮貴族講解白氏詩集以提高對其詩文的認知水平;到村上天皇時期還舉辦了以白居易詩歌韻律為模板的作詩大會。”[4]宮殿中以天皇為首,與王宮大臣門一起作詩吟賦,仿佛也陶醉于大海彼岸盛唐的繁華之中。天皇的行為被百姓效仿。他們信奉天皇,也信奉天皇所熱愛的文化。(2)白居易的閑適詩風。一提到平安時代,腦海中想到的大概會是《源氏物語》中嬌羞美艷的深宅閨秀,又或是雍容華貴的王宮生活等風花雪月的浪漫之情,奢侈浮華之風。其實這種現(xiàn)象只存在于當時的都城京都之中。除了京都,其他地方還是一派蕭條。當時的皇室權(quán)力已經(jīng)逐漸衰落,王公大臣們也沒有把心思放在開疆擴土上,也不覺得自己應(yīng)當擔負起帶領(lǐng)國家和民族走向繁榮富強的國家重任。沉醉于風花雪月之中,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白居易閑適詩中閑散生活的意境、悠然自得的風格,正好迎合王公貴族的趣向。(3)日本人喜歡白氏詩文與日本人本身的審美觀念有關(guān)。日本國土狹小但風景優(yōu)美,處處透露著細膩婉約的幽雅。同時日本又多自然災(zāi)害,使得大和民族對于大自然有更深的認知觀念,也造就了他們的“物哀”意識。“常常對自然界的一花一木,抱有傷感之情。欣賞自然的同時卻又對此感到傷感,總會產(chǎn)生諸多的哀愁善感之詞。而白居易詩詞中那份追求自然之美,超越現(xiàn)實達到寧靜祥和的永恒之美,更是日本人所心馳神往的。”[5]正是白居易詩歌中類似于“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的詩句,打動了日本人心中對大自然傷感的脆弱心弦。
三、結(jié)語
日本多次派遣使節(jié)學習我國文化,白居易的詩文正是在這種文化的交流之中被帶到日本風靡一時,同時也給予了日本漢文學發(fā)展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日本人對白氏詩的認同,更多的還是自身與詩風中某種精神的契合而引發(fā)的共鳴。白居易的詩歌在日本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直到今天仍然是日本學界熱議的話題之一。
參考文獻:
[1]杜曉勒.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1995.
[2](日)川口九雄等 和漢朗詠集[M].日本巖波書店,1995.
[3]黃仁生.論漢籍東傳日本及其回傳[J].常德師范學院學報,2002.
[4]王永波.白居易研究著作述評[J].周口師范學院學報,2005.
[5]曹順慶.東方文論選[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