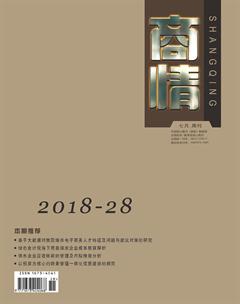精準扶貧政策下的農村精神殘疾患者家庭脫貧研究與探討
聞運
[摘要]隨著精準扶貧政策的推行,各貧困地區相繼出臺并實施了產業化扶貧、醫療衛生扶貧等一系列措施,但與其他貧困人群相比,精神殘疾患者由于存在認知、情感和行為障礙S-~ii的原因而無法從事正常的生活和社交活動,由此導致精神殘疾患者家庭脫貧面臨特殊困難。針對精神殘疾患者家庭脫貧所面臨的特殊性,應通過社會保障來兜底、加大農村精神殘疾患者家庭教育救助力度等舉措來幫助他們如期順利實現脫貧。
[關鍵詞]精準扶貧 農村精神殘疾患者 脫貧
2015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貴州同部分省區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的座談會上強調“扶貧開發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在精準”。2015年11月召開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也提出要確保到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并提出按照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具體情況,實施“五個一批”工程,以解決好“怎么扶”的問題。圍繞“精準扶貧、不落一人”總要求,湖北省委、省政府也先后制定和頒發了《關于全力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決定》等一系列大力推進精準扶貧的文件和措施。
一、研究背景及某村精神殘疾患者情況
精神殘疾是指各類精神障礙持續一年以上未痊愈,存在認知、情感和行為障礙,影響日常生活和活動、無法進行社會參與的殘疾,其中精神分裂癥所占比例最大。1993年全國7個地區精神病流行病學抽樣調查顯示,精神疾病總患病率為13.47‰,估計全國有各類精神病患者1600萬人左右,其中2/3在農村。因此,在中央“精準扶貧、不落一人”總要求下,了解他們的家庭現狀和脫貧需求,并由此采取有針對性的脫貧幫扶舉措,已經成為擺在當地政府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
該建檔立卡貧困村地處大別山腹地的革命老區,自然資源貧乏。截止到2015年12月,精準識別后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共有56戶129人。在貧困戶中,精神殘疾患者共有19人,占貧困人口的14.7%。根據我國的精神殘疾分類標準,8人為二級精神殘疾患者,他們生活不能自理,生活長期、全部需要他人監護;11人為四級精神殘疾患者,基本可以生活自理、與人交往、從事一般的工作、學習,僅偶爾需要環境提供支持,但在交流溝通方面面臨的障礙較多,在理解交流、與人相處方面面臨中度障礙。
二、該村精神殘疾患者生存狀況
(一)該村精神殘疾患者生活質量較低
由于長期以來人們對精神殘疾存在誤解,同時,精神殘疾患者所患的疾病導致他們的行為舉止不適應社會,常易觸犯人與人之間交往的成規。因此,就形成了一種偏見與歧視。這種歧視使精神病患者即使康復后也難以平等地融入社會,在就業、婚姻等問題上有很多障礙。相關研究表明,超過80%的精神殘疾人家庭表示其經濟狀況“有些困難”或“十分困難”,而絕大部分受訪家庭對未來是否能夠脫貧致富表示“不抱希望”。據調查,該村19位患者中只有16人生活偶爾可以自理,3人生活完全無法自理;19位患者的個人年均純收入不到1000元,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二)該村精神殘疾患者家庭負擔沉重
家庭負擔是指精神病患者因患病給家庭造成不良影響,是疾病負擔的重要組成部分。精神病為慢性疾病,病程反復發作遷延不愈,目前尚無法根治,需要長期,甚至是終生服藥治療或維持治療,且社會功能嚴重受損。相關研究表明,有95.3%的精神病患者處于中青年段,中青年成為精神疾病的高發年群體,中青年是家庭的經濟支柱,他們的患病也必然構成家庭的間接經濟損失。因此,精神病所導致的直接和間接經濟消耗均較高,必然給患者家庭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使家庭長期處于經濟緊張狀態。在調查中我們發現,受家庭經濟條件限制,該村19名精神殘疾患者很少主動治療或根本不進行不治療。
三、現有的脫貧幫扶政策對精神殘疾患者貧困家庭脫貧特殊性識別度不足
(一)現有的產業化扶貧難以讓精神殘疾患者貧困家庭實現增收
現有的產業化扶貧主要是建立健全政府、市場主體、農戶等互為一體的產業精準扶貧機制,通過建立貧困對象與市場主體利益聯動機制,以提高貧困家庭自身造血功能。但在現實中,我們發現由于精神殘疾患者本身及患者家庭自身的局限性,產業扶貧政策和措施難以真正有效地幫扶精神殘疾患者貧困家庭實現脫貧。首先,產業化扶貧政策本身的配套措施不完善。根據我們的調查,現有的農村貧困家庭對產業化扶貧的意愿主要集中于農業產業中的畜牧業、種植業、水產業和林特業,但啟動資金從何而來、產業化過程中的風險防控、產品銷售渠道等配套舉措的缺失極大地限制了廣大農村貧困家庭包括精神殘疾患者貧困家庭發展農業產業的意愿。其次,受制于精神殘疾患者的缺陷,不具備充分就業條件,精準扶貧下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帶動貧困戶合作經營、技能培訓扶貧、安排就業等就業培訓和就業對接服務難以真正有效地開展。
(二)醫療衛生扶貧
隨著農村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普及,精神分裂癥伴精神衰退也列入了大病補償中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金報銷支付特殊病種,但在現實中由于家庭貧困和社會存在的歧視與偏見,精神殘疾患者往往要承受經濟、精神雙重壓力,同時,精神殘疾又是一種病因不明的慢性疾病,大部分病人需要長期服藥鞏固治療,大多數家庭難以承受,這就造成精神殘疾患者因此90%以上的患者不能按有效療程治療。在調查中,我們發現該村這19名精神殘疾患者幾乎沒有接受過精神疾病方面的專業治療。
隨著精準扶貧的實行,該地區衛計部門在當地推行了精準扶貧醫療救助,主要采取了對醫療救助對象開展健康體檢、建立健康檔案和將貧困戶因病住院就醫費用實際報銷比例提高到90%以上等醫療衛生扶貧措施,但此健康體檢僅針對常規性項目,無法使精神殘疾患者真正了解自己的病情,同時3名精神殘疾患者極少參加精神疾病方面的專業治療,住院就醫費用實際報銷比例的提高對他們來說也就沒有實質意義。
四、精準扶貧下的農村精神殘疾患者家庭脫貧對策思考
(一)兜底保障農村貧困精神殘疾患者的基本生活和醫療
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中提出對貧困人口中完全或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由社會保障來兜底。但現有的農村社會保障政策將精神殘疾患者排出在保障范圍之外,大部分精神殘疾患者無法獲得低保、五保等基本的社會保障服務,因此建議在精準扶貧政策下探索設計專門的精神障礙保障制度,堅持普惠基礎上的特惠制度,構筑專門的精神殘疾人社會保障體系,以此來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醫療、康復以及就業等方面的權利,使他們逐步擺脫貧困。如設立精神障礙福利基金以幫扶貧困精神障礙患者及家庭,在其所在的街道社區或鄉鎮衛生院開展精神障礙患者的康復訓練項目以及創辦精神障礙患者福利企業,以便幫助處于緩解期的患者就業,自食其力,重返社會。但對于病情遷延不愈且無法負擔治療費用的嚴重精神障礙患者,政府應考慮給予直接的財政支持,以保證這類患者能夠得到持續有效的康復治療,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
(二)加大農村精神殘疾患者家庭教育救助力度,消除貧困代際傳遞
制定貧困戶子女教育優惠政策,對農村精神殘疾患者家庭實施免費高中教育,完善貧困戶大學生學費減免制度。以雨露計劃為依托,加大對適齡接受中、高等職業教育的農村精神殘疾患者家庭子女傾斜支持力度,并在讀書期間每年給予補助,引導他們順利完成職業教育,提素質、學技能,并扶持他們實現穩定就業,為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培養技術、技能人才,阻斷貧困世代傳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