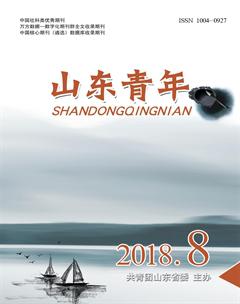農(nóng)民工問題研究綜述:概念、現(xiàn)狀及發(fā)展趨向
亓彩云
摘 要:農(nóng)民工問題是社會(huì)熱點(diǎn)問題,隨著農(nóng)民工隊(duì)伍的日益壯大,作用越來越凸顯,問題也越來越多,對(duì)農(nóng)民工的研究也不斷增加,不斷深入。本文從農(nóng)民工的概念界定、農(nóng)民工的現(xiàn)狀研究、農(nóng)民工群體發(fā)展趨向三點(diǎn)出發(fā)對(duì)農(nóng)民工問題做一綜述,整理最近6年的理論研究成果。并在19大背景下,提出進(jìn)一步解決農(nóng)民工問題的意見建議。
關(guān)鍵詞:農(nóng)民工;農(nóng)民工問題;研究綜述
“農(nóng)民工”是指在本地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或進(jìn)入城鎮(zhèn)務(wù)工的農(nóng)業(yè)戶口人員,它是我國(guó)特有的城鄉(xiāng)二元體制的產(chǎn)物,是我國(guó)在特殊的歷史時(shí)期出現(xiàn)的一個(gè)特殊的社會(huì)群體。在我國(guó),農(nóng)民工因其“亦農(nóng)亦工、非農(nóng)非工”特征,導(dǎo)致其往往游離于城市體系邊緣,無法充分享受城鎮(zhèn)各項(xiàng)權(quán)利。本文試就2011-2017年來國(guó)內(nèi)學(xué)術(shù)界關(guān)于農(nóng)民工問題的研究現(xiàn)狀作一簡(jiǎn)要回顧和梳理。
一、 農(nóng)民工的概念界定
《中國(guó)農(nóng)民工調(diào)研報(bào)告》序言中指曾出: “農(nóng)民工是我國(guó)經(jīng)濟(jì)社會(huì)轉(zhuǎn)型的特殊概念,是指戶籍身份還是農(nóng)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從事非農(nóng)產(chǎn)業(yè)、以工資收入為主要來源的人員”。楊思遠(yuǎn)教授認(rèn)為: “農(nóng)民工是指擁有農(nóng)業(yè)戶口但離開土地從事非農(nóng)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的雇傭勞動(dòng)者”[1]。可見,對(duì)農(nóng)民工的定義并不完全一致,但都具備以下兩個(gè)特征:一是“農(nóng)民身份”,二是“從事非農(nóng)產(chǎn)業(yè)”。
近幾年的對(duì)于農(nóng)民工概念界定的研究多集中于新生代農(nóng)民工。王春光于 2001 年首次提出“新生代農(nóng)村流動(dòng)人口”的概念[2],韓長(zhǎng)賦通過進(jìn)一步研究,將農(nóng)民工劃分為三代: 第一代是上世紀(jì)80年代出來打工的,這批人亦工亦農(nóng),離土不離鄉(xiāng);第二代大多是上世紀(jì)80年代成長(zhǎng)起來的,是目前農(nóng)民工的主力軍;第三代則是上世紀(jì) 80 年代和 90 年代出生的。他認(rèn)為,第二代和第三代農(nóng)民工是農(nóng)民工的主體,也就是新生代農(nóng)民工[3]。對(duì)于新生代農(nóng)民工沒有一致的概念確定,一般劃分標(biāo)準(zhǔn)是以 1980 年作為分界線,新生代農(nóng)民工與第一代農(nóng)民工有著明顯的代際差異。一般來說,新生代農(nóng)民工的受教育程度高,職業(yè)期望值高,物質(zhì)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二、 農(nóng)民工的現(xiàn)狀研究
關(guān)于農(nóng)民工現(xiàn)狀的分析,是相關(guān)研究的重中之重,而且從社會(huì)學(xué)、經(jīng)濟(jì)學(xué)、政治學(xué)、人口學(xué)、法學(xué)等不同學(xué)科、不同視角、不同維度進(jìn)行了剖析,從目前農(nóng)民工的發(fā)展現(xiàn)狀來看,存在多重“貧困”問題。在此從經(jīng)濟(jì)、政治、文化、心理四個(gè)維度出發(fā),分析農(nóng)民工作為“弱勢(shì)群體”的生存和發(fā)展現(xiàn)狀。
(一)關(guān)于農(nóng)民工經(jīng)濟(jì)情況的研究
農(nóng)民工的經(jīng)濟(jì)地位低,勞動(dòng)就業(yè)權(quán)利難以得到有效保障。農(nóng)民工就業(yè)中,行業(yè)多為建筑業(yè)、服務(wù)業(yè),場(chǎng)所多為私營(yíng)企業(yè),目前的數(shù)據(jù)顯示,勞動(dòng)合同簽署不足一半,就業(yè)流動(dòng)性較大[4];農(nóng)民工月平均工資2631元,市民3304元[5],工資水平低,存在明顯的“同工不同酬”現(xiàn)象;主要支出為食品、寄回或帶回錢物、房租[6],他們的消費(fèi)是“金字塔底層”的消費(fèi),消費(fèi)結(jié)構(gòu)比較單一,恩格爾系數(shù)高,消費(fèi)能力差。在社會(huì)保障領(lǐng)域,農(nóng)民工的社會(huì)保障保障水平低,覆蓋范圍窄,特大城市的樣本分析中,養(yǎng)老、醫(yī)療、失業(yè)等社會(huì)保險(xiǎn)參保率非常低,農(nóng)民工主要參與工傷保險(xiǎn),而這一比例也只達(dá)到46%[7],雖然不同樣本分析下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jì)不盡相同,但結(jié)果都是參保比例非常低;社會(huì)救助和社會(huì)福利主要依賴于政府援助,但農(nóng)民工受身份桎梏,很難享受到工作所在地的福利和服務(wù)[8];住房保障水平低,單位住房和租房是主要方式,住房公積金繳納只占23.8%,享受廉租房、經(jīng)濟(jì)適用房、公共租賃房、限價(jià)商品房等住房?jī)?yōu)惠政策的只占5.2%[9]。農(nóng)民工的經(jīng)濟(jì)狀況是農(nóng)民工生存狀況的最直接體現(xiàn),但各項(xiàng)研究均表明,農(nóng)民工存在就業(yè)環(huán)境差、工資水平低、消費(fèi)能力弱、社會(huì)保障少、住房環(huán)境差等等的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保障問題,經(jīng)濟(jì)狀況并不好。
(二) 關(guān)于農(nóng)民工政治情況的研究
農(nóng)民工的政治情況主要表現(xiàn)為政治參與少,話語權(quán)弱,公民權(quán)利難以維護(hù)。政治參與是公民表達(dá)政治意愿、實(shí)現(xiàn)政治權(quán)利的重要手段,但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存在農(nóng)民工政治參與意識(shí)增強(qiáng)與參與途徑缺失之間的矛盾和農(nóng)民工政治參與能力提高與參與制度不足之間的矛盾及困境。農(nóng)民工政治情況的主要特征為:無政治群體,體制內(nèi)不容納、體制外非組織化,政治權(quán)利的喪失與公民權(quán)的不平等[10],即在城市政治生活中,農(nóng)民工階層與政治沒有任何制度性聯(lián)系,在城市公共事務(wù)方面幾乎沒有任何政治權(quán)利和政治影響力。主要原因是二元分割戶籍制度下,農(nóng)民工的政治權(quán)利在農(nóng)村而非城市,其次《憲法》、《選舉法》對(duì)農(nóng)民工政治參與身份缺失[11]。從諸多研究文獻(xiàn)中可以發(fā)現(xiàn),農(nóng)民工的政治參與嚴(yán)重不足,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很多政治權(quán)利難以享有。
(三) 關(guān)于農(nóng)民工文化情況的研究
農(nóng)民工群體理應(yīng)享受城市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shè)的成果,但在經(jīng)濟(jì)利益都難以維護(hù)的現(xiàn)實(shí)情況下,文化精神領(lǐng)域受到各方力量忽視,文化需求難以滿足。農(nóng)民工群體在城市環(huán)境中自我形成一個(gè)“次文化圈”, 文化生活呈現(xiàn) “孤島化”、“邊緣化”特征。在生存權(quán)利難以保障的前提下,農(nóng)民工對(duì)文化生活的關(guān)注度較低,參加文化生活的比例也較低。導(dǎo)致農(nóng)民工的文化生活單調(diào),心理壓力較大,文化消費(fèi)較少,文化需求難以滿足,文化權(quán)益亟待得到保障等問題;其次在參與方式上比較單調(diào),個(gè)體性較強(qiáng),社交性不足,農(nóng)民工業(yè)余時(shí)間更多地花在了上網(wǎng)、看電視、睡覺等個(gè)人活動(dòng)上,以個(gè)體性的休閑方式為主,與他人互動(dòng)交流的休閑娛樂活動(dòng)較少。同時(shí),大多數(shù)農(nóng)民工沒有參與任何形式的組織,對(duì)社區(qū)活動(dòng)的參與度也不高[12]。對(duì)于新生代農(nóng)民工而言,文化程度和自身素質(zhì)的提高,對(duì)精神文化的需求越來越強(qiáng)烈,滿意度卻在低位徘徊
[13]。總之,農(nóng)民工工作時(shí)間差、收入差、社會(huì)排斥、政府文化公共服務(wù)設(shè)施的缺失導(dǎo)致這一局面。
(四)關(guān)于農(nóng)民工心理情況的研究
心理健康是農(nóng)民工自身素質(zhì)和適應(yīng)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心理健康直接關(guān)系到社會(huì)和諧與穩(wěn)定。農(nóng)民工心理健康水平變遷的橫斷歷史研究從1995-2011年進(jìn)行分析,SCL-90量表分析結(jié)果得出17年來中國(guó)農(nóng)民工心理健康水平總體上在逐步提升,其中人際關(guān)系、抑郁、焦慮、敵對(duì)、恐怖和偏執(zhí)六個(gè)方面改善最為突出[14]。但相對(duì)于城市居民,還存在著一定的心理問題,主要表現(xiàn)為心理失范、心理壓力等,主要影響因素有社會(huì)歧視、社會(huì)差距、“養(yǎng)家糊口”的壓力、工作時(shí)間、工資水平、企業(yè)管理水平、年齡、身體健康狀況、教育水平、婚姻問題、子女教育問題等[15]。這些因素中,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近今年的研究逐漸推翻女性心理問題比男性嚴(yán)重的結(jié)論,認(rèn)為農(nóng)民工群體中,男性心理失范問題比女性突出[16]。受經(jīng)濟(jì)壓力、政治狀況、社會(huì)排斥等眾多因素的影響,相較社會(huì)平均水平而言,農(nóng)民工往往面臨著更嚴(yán)峻的心理健康問題。
三、 農(nóng)民工的發(fā)展趨向研究
通過農(nóng)民工的現(xiàn)狀研究可以發(fā)現(xiàn),農(nóng)民工作為社會(huì)弱勢(shì)群體,在經(jīng)濟(jì)、政治、文化、心理四個(gè)方面都處于弱勢(shì)地位,目前農(nóng)民工的發(fā)展模式基本還是“回流”和“再遷移”兩種形式,無論哪種形式,都不利于農(nóng)民工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
總體來說,農(nóng)民工的戶籍身份是農(nóng)民,從事的卻是非農(nóng)職業(yè),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的迅速發(fā)展和戶籍制度的桎梏導(dǎo)致農(nóng)民工問題的產(chǎn)生。在十九大會(huì)議精神的指導(dǎo)下,新時(shí)期農(nóng)民工工作的重心包括兩點(diǎn):第一,繼續(xù)強(qiáng)化農(nóng)民工市民化工作。這對(duì)于解決農(nóng)民工困境、推進(jìn)新型城鎮(zhèn)化、擴(kuò)內(nèi)需促消費(fèi)和統(tǒng)籌城鄉(xiāng)發(fā)展等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xiàn)實(shí)意義;第二,進(jìn)一步完善返鄉(xiāng)農(nóng)民工就業(yè)創(chuàng)業(yè)政策及服務(wù),實(shí)施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重點(diǎn)支持和鼓勵(lì)農(nóng)民就業(yè)創(chuàng)業(yè),促進(jìn)農(nóng)民工多渠道就業(yè)創(chuàng)業(yè)。農(nóng)民工面臨“市民化”和“返鄉(xiāng)”時(shí)難以抉擇,盡管不同研究得出的數(shù)據(jù)并不完全一致,但諸多數(shù)據(jù)支持了農(nóng)民工的市民化傾向,例如2011年測(cè)得的農(nóng)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比重為68.30%[17], 2012 年測(cè)得的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比重為64.30%
[18],2016年用不同的數(shù)據(jù)庫(kù)測(cè)到的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比重為分別是75.39%[19]和63.20%[20]等。陳金明、趙陽也從城鄉(xiāng)統(tǒng)籌角度肯定農(nóng)民工的兩大發(fā)展趨向?yàn)椋阂皇寝r(nóng)民工返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或者就地就近轉(zhuǎn)移,成為中小城鎮(zhèn)新市民或新的產(chǎn)業(yè)工人,二是農(nóng)民工返鄉(xiāng)專事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成為新型農(nóng)民。而影響農(nóng)民工市民化和返鄉(xiāng)的主要因素包括城市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農(nóng)民工素質(zhì)和政策導(dǎo)向等,其中政策導(dǎo)向最為關(guān)鍵,具體包括戶籍政策、就業(yè)政策、社會(huì)保障政策、公共服務(wù)政策等。
因此在下一步的工作中,首先要建立城鄉(xiāng)統(tǒng)一、平等的就業(yè)制度,以實(shí)現(xiàn)農(nóng)民工在城市中穩(wěn)定就業(yè)、平等獲得勞動(dòng)報(bào)酬,平等享受職業(yè)培訓(xùn)的目標(biāo);其次,構(gòu)建較為完善的農(nóng)民工社會(huì)保障制度,農(nóng)民工社會(huì)保障問題是影響農(nóng)民工實(shí)現(xiàn)市民化的一個(gè)重要因素,與城鎮(zhèn)企業(yè)職工享有同等的參保權(quán)利是農(nóng)民工的基本訴求之一;實(shí)現(xiàn)城鄉(xiāng)一體化進(jìn)程中農(nóng)民工公共服務(wù)的均等化,服務(wù)供給以需求為導(dǎo)向,提供多元化、針對(duì)性的服務(wù)。
[參考文獻(xiàn)]
[1]楊思遠(yuǎn),中國(guó)農(nóng)民工的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考察, 2005, 中央民族大學(xué).
[2]王春光,新生代農(nóng)村流動(dòng)人口的社會(huì)認(rèn)同與城鄉(xiāng)融合的關(guān)系. 社會(huì)學(xué)研究, 2001(03): 第63-76頁(yè).
[3]唐園結(jié),劉明國(guó)與韓長(zhǎng)賦, 城鄉(xiāng)統(tǒng)籌解決“三農(nóng)”問題的重大舉措——國(guó)務(wù)院研究室副主任韓長(zhǎng)賦解讀《國(guó)務(wù)院關(guān)于解決農(nóng)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 農(nóng)村工作通訊, 2006(04): 第14-19頁(yè).
[4]張?zhí)睿袊?guó)農(nóng)民工社會(huì)保障制度研究, 2014, 遼寧大學(xué).
[5]盧海陽,梁海兵與錢文榮, 農(nóng)民工的城市融入:現(xiàn)狀與政策啟示. 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問題, 2015(07):第26-36+110頁(yè).
[6]褚榮偉與張曉冬,中國(guó)農(nóng)民工消費(fèi)市場(chǎng)解讀——金字塔底層的財(cái)富. 經(jīng)濟(jì)理論與經(jīng)濟(jì)管理, 2011(07):第34-46頁(yè).
[7]馮虹與張玉璽,特大城市農(nóng)民工社會(huì)保障研究——基于戶籍制度改革的視角. 山西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6(04): 第124-128頁(yè).
[8]陸春萍與毛志宏,甘肅省農(nóng)民工社會(huì)保障問題研究. 西北人口, 2015(02): 第42-46頁(yè).
[9]韓克慶與林欣蔚,城市化進(jìn)程中的農(nóng)民工住房保障問題研究. 湘潭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 2015(03):第23-27頁(yè).
[10]周慶智, 農(nóng)民工階層的政治權(quán)利與中國(guó)政治發(fā)展. 華中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 2016(01): 第1-10頁(yè).
[11]劉建發(fā), 農(nóng)民工政治參與立法保障的探討. 社會(huì)科學(xué)家, 2011(12): 第76-79頁(yè).
[12]廉思與陶元浩,服務(wù)業(yè)新生代農(nóng)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實(shí)證研究——基于北京的調(diào)查分析. 中國(guó)青年研究,2013(05): 第55-59頁(yè).
[13]王明學(xué),胡祥與劉閔,新生代農(nóng)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研究.中國(guó)青年研究,2013(01): 第93-99頁(yè).
[14]黃四林等, 中國(guó)農(nóng)民工心理健康水平變遷的橫斷歷史研究:1995~2011.心理學(xué)報(bào), 2015(04):第466-477頁(yè).
[15]胡宏偉,王金鵬與曹楊,新生代農(nóng)民工心理問題與求助行為研究.西北人口,2011(05): 第27-33頁(yè).
[16]李衛(wèi)東,李樹茁與M.W.費(fèi)爾德曼,性別失衡背景下農(nóng)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別差異研究. 社會(huì), 2013(03): 第65-88頁(yè).
[17]黃錕.城鄉(xiāng)二元制度對(duì)農(nóng)民工市民化影響的實(shí)證分析[J].中國(guó)人口·資源與環(huán)境,2011,21(03):76-81.
[18]楊萍萍.農(nóng)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響因素實(shí)證研究[J].經(jīng)營(yíng)與管理,2012(07):71-74.
[19]羅豎元.農(nóng)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模式選擇:基于返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的分析視角[J].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7,17(02):70-81+152.
[20]梅建明,袁玉潔.農(nóng)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響因素的實(shí)證分析──基于全國(guó)31個(gè)省、直轄市和自治區(qū)的3375份農(nóng)民工調(diào)研數(shù)據(jù)[J].江西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6(01):68-77.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xué)哲學(xué)與社會(huì)發(fā)展學(xué)院,山東 濟(jì)南 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