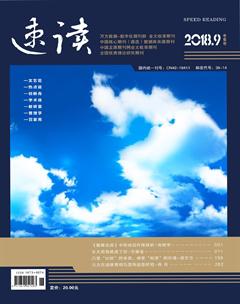中華傳統音樂“樂和”之美
黃永健 王樂樂 岳頂聰
摘 要:西方音樂強調“數”的和諧,中國傳統音樂雖然也強調和諧,但是受中國傳統哲學影響,主要從心理而非數理方面獲得“樂和”之美感。中國傳統音樂具有其發乎文化本源的“聲”與“音”以及一套完整的與“禮”相匹配的音樂教育模式,且與政治教化密切相關。與西方音樂尤為重視數理美感相比,中國傳統音樂(國樂)更加強調政治教化功能。
關鍵詞:正能量;中華傳統藝術;傳統音樂;音樂教育
在人類藝術史上,音樂自始至終都占據著舉足輕重的位置,同理,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在中國傳統藝術文化系統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位置。中華民族文化塑形的夏商周時代,即開始了禮樂文化的建構。當代學者聶振斌在其《中國藝術精神的現代轉化》一書中認為,禮與樂不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化,而是中華民族走向文明時代所創造的文化。禮樂文化致使中國文化得到定向發展,是中華民族古代文明的標志。禮樂文化在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上具有本源地位,也可以說,它是中華民族的元文化。
當代學者李心峰先生認為,三代文化的精神實質是禮樂,三代藝術的精神實質也是禮樂。三代禮樂文化在西周時期發展到極致,三代禮樂文明和禮樂文化代代相因沿革,損益增刪,有其內在的貫通性和一致性,所謂“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為政》),“三代之禮,民共由之”(《禮記·禮器》)。當時的樂,不僅指音樂,學術界采納郭沫若的看法,“樂”包括音樂、詩歌、舞蹈、繪畫、雕鏤、建筑、儀仗、田獵、肴饌等,凡是使人快樂,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東西,都可以廣泛地稱之為“樂”。但它是以音樂為代表的。樂為禮服務,以禮為內容,以禮的實行為根本目的,而當時的“禮”,也總是要訴諸使人愉悅的藝術——樂,以使人們心悅誠服地將外在制約轉化為內在的精神需求。所謂“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禮樂之事也”(《禮記·樂記》)。
音樂訴諸聽覺,發生學意義上的音樂早于語言,兒童在說話之前用聲——聲帶發出的人籟之聲表示他(她)作為一個生命體的存在,由聲而帶出音——帶有一定曲調和音律并蘊含感情與觀念的音聲,也就是說,兒童在學會用語言及其它手段表情達意之前,使用本真的聲音(含有樂的本真性)來表情達意。西方有所謂的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也叫語音中心主義,有人將邏各斯翻譯成“道”,不過老子的“道”是不能用語言表達出來的,而西方的邏各斯卻可以用語音表達出來,因為在語音中聲音和意義清澈地統一在一起,也就是說原初給事物命名時的原始聲音與事物的本性是一致的,聲音里涵泳著原初的真理。中國自古重視詩的聲律,并發展出一整套聲律搭配的韻律系統,說明中華先哲與西方先哲一樣,也是認為聲音具有非同小可的含攝功能。
當代音樂學學者在反思中國古典音樂的精神特征時指出,中國以樂(天籟、太一)為本體的音樂觀念往往過于強調音樂的中庸和諧之音,并以此為正統與標準,這便阻礙了音樂的多元發展,導致了中國古代音樂的單一性。同時,中國古代以“樂”為本體(樂、音、聲三者,樂為本體,聲與音是樂的表現)的音樂觀念,容易形成重“道”而輕“器”的四相傾向,即重視對音樂義理的體驗,而輕視對作為樂的表現的音與聲的追求,對音樂演奏技藝的價值加以貶低,所謂“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樂記·樂情》),唱歌與彈琴這些音聲上的技藝皆是樂之末節,難登大雅之堂,只有義理智慧才是樂的根本,因此樂“道”在上,而樂“器”在下。這種觀點具有一定的說服力,但是,這還是以西方音樂的標準,來對中國傳統音樂所做出的學術判斷,如果我們將中西音樂的對比研究放在文化人類學的視野之內,比如我們將中西兩種音樂審美理念放在兩種文化的哲學背景中加以考查,則西方重分析、崇思辨、判二分的思維特性與中國重整體、崇綜合、和圓成的思維特性,各自表現于音樂的“聲”與“音”,并且很難說西方音樂一定優于中國音樂。
研究者指出,就“和”而言,與西方認為音樂來自于“數”的和諧(也即外在的聽覺和諧)不同,中國傳統音樂雖然也強調和諧,但是受中國傳統哲學影響,重感性的中國思維方式強調心靈的感悟而非科學的分析,主要從心理而非數理方面獲得美感。中國人認為音樂之美來自于“心理”的和諧,即儒家強調的音樂與道德、人情之和諧(美與善的統一),來自于道家提倡的心靈與自然的和諧,而非單純的節奏、旋律上“數”的和諧。簡言之,中國音樂的和諧不在“聲”與“聲”之間,而在“情”與“聲”之間,核心內容是“自然”和“情感”——即儒道之“心理”和諧。典型如古琴音樂,不追求華麗的聲音效果,而追求“止于邪”、“正人心”的道德訴求,聽之最容易讓人體會“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中正平和,溫柔敦厚、無過無不及的儒家思想。
近年來,中國音樂家譚盾以其融合中西,轉換生成的系列音樂作品——《風雅頌》《死與火》《馬可·波羅》《地圖》《文書》獲得了國際認同,譚盾用其包含民族文化底蘊和音樂美學內涵的創新之作,獲得了中外音樂學界的廣泛認可。譚盾音樂在結構、主題、和聲、節奏、文化方面生動地傳達了中西音樂融合后的獨特韻味和魅力,美國當代音樂家約翰·凱奇評價譚盾:“人類生存的宇宙,本身就是一個無限豐富、無比生動、極度藝術化的音響空間……從譚盾的作品來看,他是在力圖擴展音樂音響范疇,包括找尋那些被音樂家們久已棄置、淘汰但卻與人類生活密不可分的自然音響”。約翰·凱奇所說的“自然音響”實際上是中國傳統音樂中的“天樂”——天籟之聲,莊子極力推崇的“大音”,這種“大音”(“天樂”、“天籟之聲”)的美學極致是“和”(“中和”),受中國傳統哲學影響,中國人認為音樂之美來自于“心理”的和諧,即儒家強調的音樂與道德、人情之和諧(美與善的統一),來自于道家提倡的心靈與自然的和諧,而非單純的節奏、旋律上“數”的和諧。譚盾以其特具中國哲理內涵的音樂作品,打動后殖民語境中的中西方聽眾,說明中國傳統音樂美學并未過時。
孔子在教育上主張“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在個人的綜合素質養成方面,主張“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游于藝”之“藝”——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其中的“樂”主要還是音樂,而游于藝的美好境界是:暮春三月,春天的衣服穿定了,陪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個小孩子,在沂水旁邊洗洗澡,在舞雩臺上春吹吹風,一路唱歌,一路走回來。由個人的道德修煉和音樂涵養推而至于整個社會的和諧美善。
如果我們說音樂在人類藝術文化價值系統中占據重要的地位,則中國傳統音樂憑借其獨特的中國人文精神,彰顯中國文化中的“和諧”理念,而“和諧”理念正是對治全球化時代人類面臨的文化危機的重要思想,“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國語·鄭語》)。《禮記·中庸》上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藝術主要表現人類的情感(喜怒哀樂)并通向對于真理的認知,音樂表現情感(喜怒哀樂),推而廣之,音樂及其他中國傳統藝術門類,無不蘊含著對于“中和”的追求和攀升,只不過中國音樂在這方面表現的更為顯豁而已。
樂和是一個從個體生命到宇宙大全的圓融境界,《呂氏春秋·古樂篇》指出:先王作樂是為了調和陰陽之氣,使五谷豐登,以定群生。“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淤塞,不行其原,民氣郁瘀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所以樂和首先關注的是個體生命,其次是為了政和、人和,由于樂和的調理,“于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次序,風雨時至,嘉禾繁祉,人民龢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樂和——正人正己,政治太平,倫理有序,季節調適,萬物生長,天文物理人情和諧振動,天下齊治。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傳統音樂具有其發乎文化本源的“聲”與“音”以及一套完整的與“禮”相匹配的音樂教育模式,且與政治教化密切相關。與西方音樂尤為重視數理美感相比,中國傳統音樂(國樂)更加強調政治功能,更加突出其正能量的傳遞。正如研究者在評價當代中國音樂時所指出的那樣,當代中國音樂藝術日益在娛樂化、商品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時,僅僅追求娛樂至死的音樂也就失去了其文化根基和存在的根基。在走向現代化的今天,音樂應該不僅僅是一種娛樂和消遣的方式,它還應該是一種積極的文化行為,應該勇于承擔其更為重要的歷史使命和精神傳承的責任,實現“樂而志清”的人文理想。
參考文獻
[1]聶振斌.中國藝術精神的現代轉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68,72.
[2]郭沫若.公孫尼子與其音樂理論[M].重慶:重慶文治出版社,1945:163.
[3]韓凌,余亞斐.論中國古代音樂的本體——以樂、音與聲的關系為向度[J].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2.
[4]張隆溪.道與邏各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67.
[5]張春燕.中國傳統音樂之美及其內涵的跨文化傳播[J].北京社會科學,2016,2.
[6]張娜.譚盾音樂的中西異合[J].音樂創作,2014,5.
[7]凌繼堯.中國藝術批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9.
作者簡介
黃永健(1963—),男,安徽人肥東人,深圳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研究員,深圳大學藝術設計學院教授,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學博士,主要從事藝術理論、藝術文化學、文化產業研究。
王樂樂,濟南大學泉城學院商學院助教。
岳頂聰,深圳大學藝術學理論一級學科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