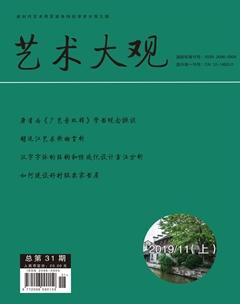現代展示藝術中情景化演繹手段的前景思考
摘要:展覽之所以能取得有效的信息傳達結果,是因為它能使觀眾完全集中在主題上。現代展示藝術是充滿挑戰的,創造性的,復雜的和終極協作的。現代展示藝術的核心內容是要通過情景化演繹將展覽的主題與其他所有看似沒有直觀聯系的元素融合在一起,使之能夠圍繞要傳達的展示信息與觀眾形成溝通,并簡化溝通的過程,以產生重要的協同作用,并增加展覽的有效性。
關鍵詞:情景化;展示環境;演繹;信息交換;溝通;氛圍
一、現代展示藝術的現狀與發展
現代展示藝術的發展重點更多的是對新文化、新科技、新知識的推廣與交流,也是“情景化演繹”的現代展示與傳統展示本質上的區別。展示活動針對地受眾群體越來越多的是非專業性參觀者,所以展示活動的設計者們希望透過更多元的展示手法和展示形式,使參觀者能夠獲得除信息以外更多東西,比如參觀過程中身心的愉悅,新鮮的感官體驗。展示設計的策劃重點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期,仍將是圍繞如何高效地傳播信息,使受眾群體更易于接受和理解的同時調動參觀者的情緒,積極參與互動、交流與反饋,參觀者也自然會對如此“生動”的展示而印象深刻。所以筆者認為,“情景化演繹”的展示形式對未來展示藝術的發展提供了無限可能。
二、情景化演繹的特有屬性
情景化演繹的展示手段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現代展示藝術最好的敘事是如何構建、訪問和體驗的。
情景化演繹有時會借用文學作品的敘事手法來闡明虛構藝術領域。對情景化演繹手段的使用,不僅限于電視劇、電影和游戲的制作,筆者堅信,情景化演繹是現代展示藝術中最有效的“敘事”方式:它可以講述關于展品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也可以引發參觀者對自我身份的新的思考。情景化演繹的展示手段,讓展品“描述自身”,引發參觀者更多的聯想與反思。
不要再把藝術品作為物品來看待,要將它們看作體驗的觸發器[1]。
把創作過程神秘化——這是業余選手用來增加情趣的游戲[2]。部分展示活動的主辦方和設計者為了能夠給展覽宣傳制造更多的噱頭,將能夠產生沉浸式體驗的多媒體數字技術視為展覽領域的貨幣來源,大量應用于展示活動中。在現今媒體環境中理解展示藝術就意味著我們要滿足很多需求。在3D技術,可穿戴技術,沉浸式體驗,非線性敘事崛起的時候,我們如何在其中親身體驗一個文本或者文物被重新改造了,并且這些媒體威脅到我們依賴和消費“所有”的能力——所有展覽,所有藏品,所有敘事[3]。
就算在這個信息化暴虐的時代,多媒體技術也不應該被視作具有最高優先級的技術,它只是輔助情景化演繹的展示手段之一,我們也應該感興趣媒體的其他維度,如社會的、環境的和文化的。設計者應當正確地看待數字媒體手段的介入,不能為了標榜科技、現代就“濫用”多媒體技術,也不能過分依賴多媒體技術去制造展示效果。我們必須依賴平時的訓練有素,我們相信工作過程,我們相信創造力來自對錯誤的利用和調整,我們相信方法論的必然力量[2]。在廣泛討論技術的力量與潛力之前,應優先考慮展覽“接受者”“消費者”的需求,始終秉持著對受眾、對作品負責任的態度才有可能做出好的設計作品。
情景化演繹的展示手段為展覽內容的深刻、分層、切片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式和參考依據。鼓勵對現代藝術和創作的現成概念進行不斷的質疑,挑戰,顛覆,解構和重建非常重要,甚至是根本的[4] 。作為故事的講述者兼制造者,展覽始終在“解讀”觀眾,觀眾也始終在解讀展覽。通過情景化演繹手段,展示的“可讀性”將繼續被重新構思,展示的參與性也將繼續被重新定義。
觀眾是否“獲取了信息”,不管是顯示在屏幕上,寫在墻上,還是用數字方式傳達進耳朵里?他們理解了哪些信息?通過什么方式?情景化演繹給展示藝術的創造能力帶來了什么全新內涵,又拿走了什么?還有什么是有用和有趣的?設計者還能怎么做,應當怎么做?作為展示藝術工作者的我們,應該慎重地思考情景化演繹的表現手法在未來展示藝術中的應用,以及情景化演繹在我們的精神世界里“建筑”的一絲“詩意”。我們將始終帶著這些思考,不斷地摸索前行,尋求展示與人之間的“終極平衡”。
參考文獻:
[1]朱莉·德克爾.賓至如歸:博物館如何吸引觀眾[M].王欣,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6.
[2]邱志杰.總體藝術論[M].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12.
[3]簡·基德.新媒體環境中的博物館——跨媒體、參與及倫理[M].胡芳,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6.
[4]侯瀚如,奧布里斯特.策展的挑戰:侯瀚如與奧布里斯特的通信[M].顧靈,譯.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
作者簡介:王粟(1988-),男,山東省乳山市人,碩士研究生,魯迅美術學院藝術工程總公司,研究方向為現代展示藝術研究。